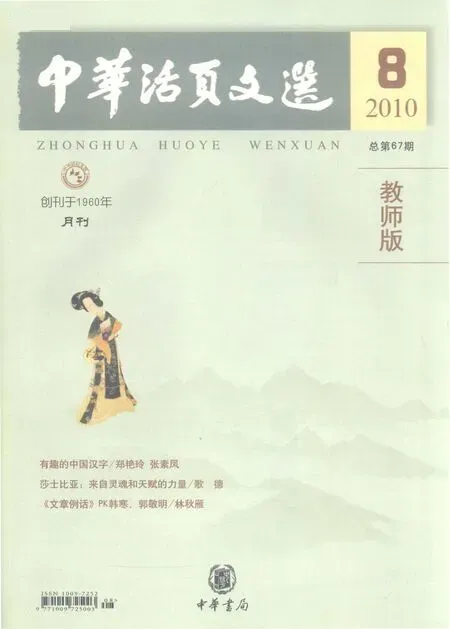莎士比亚:来自灵魂和天赋的力量
■歌 德
莎士比亚:来自灵魂和天赋的力量
■歌 德
莎士比亚的一切全都来自内部,我的意思是说来自他的灵魂和他的天赋;外在环境对他的影响很少。他和他的时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他通过经验,熟悉了乡村、宫廷和城镇的风土人情,研究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各色人物。至于他的生活的其他方面是很平凡的;他所经历的那些艰难、困苦、激情、成就,总的说来,正像我们随时随地都能遇到的那样。他的父亲。一个手套和羊毛批发商,家境优裕,娶了乡里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做过市参议会委员和乡镇镇长;可是,在莎士比亚十四岁的时候,他已临近破产的边缘,只能抵押妻子财产,辞去市政厅职务,让儿子中途辍学来协助自己的商务。这个年轻人,虽然全力以赴,但也并不是没有遇到困窘和走入歧路的;如果传说可信,他是当地的一个酒徒,力图为自己的家乡博得好酒量的盛誉。据说有一次他在别德福特的一家小酒店里与人赌饮比赛,喝得酩酊大醉,蹒跚而归,或者根本无法回家,而是和几个伙伴在路旁的一株苹果树下过了一夜。无疑地,这时他已经开始写十四行诗了。他像一个真正的诗人那样到处漫游。跻身嘈杂的乡村聚会,参与快活的田园剧,过着充满诗意的丰富而大胆的异教徒的骚动生活,这是在当时英国乡村里所常见的。总之,他不是一个奉行礼法的典范。他的情欲是早熟的,也是轻率的。他还不满十九岁已经娶了一个年长八岁的富裕的自耕农的女儿,她很快就做母亲了。他的其他荒唐行径也同样带来了不幸后果。他追随当时的风尚,热衷于偷猎,据理查·台维斯牧师说,“他常到路西爵士的林苑去偷猎鹿和兔子,路西爵士常鞭打他,有时还禁闭他,最后把他驱逐出乡村……”;而他的报复心却是如此强烈,后来竟使路西爵士成为他笔下的一个蠢法官。更不幸的,几乎就在这时,莎士比亚的父亲被关进狱里,经济濒于绝境,而他自己已有了三个孩子,一个接着一个;他必须生活,可是在家乡却无法糊口。于是他到伦敦,投入舞台生涯,从事最下等的职务,做一个“剧院仆役”,也就是说,一个学徒,或者一个临时演员。有人甚至说他开头的职务更为低贱,在剧院门口为听戏的绅士看管马匹谋生。总之,他历尽艰难困苦,不是从想象而是从事实体验到了尖锐的蔑视。他是一个喜剧演员,“国王陛下的一个可怜的戏子”。这是一种悲惨的职业,这种职业历来都因为较之其他职业相形见绌及其逢场作戏的性质而偏于卑位。当时由于群众蛮横,他们经常用石子去扔演员,又由于长官严酷,他们有时竟用割耳之刑去惩罚演员,这种职业就被贬于更低贱的地位了。他体会到了这一切,满怀辛酸地说:
唉!这竟是真的,我曾经走遍各地,
让自己在世人面前穿上彩衫,
割裂自己的思想,廉价出卖最贵重的东西。
他又说:
在失去命运的眷顾遭到世人冷眼的时度,
我独自哭泣自己孤苦无依,
用徒劳的呼吁去冒渎聋聩的苍天,
回顾身世飘零,诅咒命数不济,
但愿我像那个更有希望的人,
有他的光景,也有他所享有的友情……
我最不餍足的就是我最欣慕的;
这一类思想几乎使我看轻自己。
我们还可以在他笔下的那些忧悒性格中看到这种长期忍辱含垢的痕迹,他这样说:
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
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
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
官吏的横暴,和微贱者费尽辛勤所接来的鄙视,
要是他用一柄小小的刀子
就可以结算他自己的一生?
但是这种卑贱的地位的最坏的影响就是它腐蚀人的灵魂。在一群丑角中间自己也会变成丑角。生活在污秽的地方,就无法保持清洁,这是办不到的;一个人纵吏竭力振作也无济于事,环境会迫使他同流合污。布景的机械刻板,服装的庸俗杂乱,蜡烛和油脂的臭味,再加上所谓优雅高尚的夸耀,矫揉造作的低级表演,嘘声和彩声的喧哗叫嚣,不分贵贱的结交,玩弄人类感情的习性,这一切都非常容易损害一个人的灵魂,驱使他走向放纵的下坡,引诱他失态无礼,在后台胡作非为,和跑码头的女演员谈情说爱。莎士比亚像莫里哀一样无法逃避这种处境,也像莫里哀一样为此悲伤——
啊,请为我去谴责命运女神吧,
那迫使我从事有害职业的罪恶女神。
没有为我的生活提供更好的东西,
只有公众风习培育出来的共同方式。
伦敦流行着一种说法:他的一个伙伴,扮演理查三世的勃贝琪曾约定一位市民的妻子幽会,而莎士比亚却捷足先登,受到很好的接待,等勃贝琪到来,莎土比亚已欢度了良辰。他通知勃贝琪说,“征服者威廉”比“理查三世”早来一步了。你不妨把这件事看作诡计的一例,或者看作是接二连三出现在戏剧圈子里面的布置好的某种粗俗的阴谋。他在剧场外面和一些时髦的年轻贵族潘勃洛克、蒙高茂莱、塞桑普顿等人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热烈奔放的青春以意大利的欢乐和优雅的风范,哺育了他的想象和感情。除此之外,如果再加上诗情的狂喜和陶醉,再加上当世界头一次在这些人面前展开时,他们头脑里所产生的一切力量和意念的融会交流和汹涌沸腾,那么你就能够理解 “他所创造头一个成果”《维纳斯与阿唐尼斯》了。事实上,这是他头一次发出的声音,在这声音里面他显示了自己的整个面貌。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一颗心在接触到美——任何一种美的时候,会发出这样激动的颤抖,对新鲜灿烂的事物会感到这样忘我销魂,它是这样热烈兴奋地陶醉在自己的爱好和向往之中,是这样一心一意地专注在极度的逸乐里面。他笔下的维纳斯是举世无双的;没有一幅铁相的画像比他更为辉煌绚烂,也没有一幅丁托列托或者乔尔乔涅的圣洁妓女画像比她更为温柔美丽:
她乘着盲目的激情开始攫取,
脸上冒着热气,血在沸腾……
像饕餮者一般贪心无餍,
她的嘴唇征服,他的嘴唇俯顺,
任凭蹂躏,甘心交付赎金;
她的欲壑难填,
要把他唇上的珍宝榨尽。
像一头空腹的苍鹰,因饥饿而凌厉,
用尖啄撕裂羽毛和骨肉。
扑动翼翅,狠命吞噬,
直到心满意足,牺牲告罄;
她就这样去吻他的前额、双颊和下颏,
吻完了一遍再吻一遍。
这一切都是使人心神摇荡的,首先在感官方面,我们被这肉感的美弄得眼花缭乱,可是我们的心也同时涌起了洋溢的诗情;饱满的青春淹没了一切、甚至没有生命的东西也都栩栩如生;自然的景物在旭日的照耀下显得可爱迷人,瑰丽的天空现出了一片节日景象:
看啊!可爱的云雀已经不安于栖息了,
从浸润着露水的幽居飞向高处,
去把清晨唤醒,在银色的曙光里,
太阳庄严地升起,
它这么辉煌地俯望下界,
山峰和树尖都闪着一片金黄。
奔放的想象和纵情的欢乐一直骚动不停,这种情绪是会把人带进出神入化之境的。伦敦没有一个美貌纤弱的女子不在自己桌上放着一本《维纳斯与阿唐尼斯》。他也许发觉自己超越了界限,因为他的第二首诗《琉克里斯的被辱》的格调完全不同了;不过由于他具有广阔的灵魂可以同时去拥抱事物的两极,正如他后来在自己的剧本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仍旧随心所欲地去挥写。“爱情的销魂”是他一生中的大事;他心地温柔,又是一个诗人,这就足以使他受到迷惑和欺骗,一次又一次地去体验去经历那种周而复始永无穷尽的幻想和痛苦。
他经历了许多次这一类的爱情。有一种可称为玛丽奥·台洛姆的爱情,这是一种痛苦而盲目的专横情欲,虽然使他感到压抑和耻辱,可是他却不能也不愿从中摆脱出来。他的表白流露了最深刻的悲哀,充分地揭示了爱情的疯狂和对人类弱点的敏感:
当我爱人发誓说她忠实不渝的时候,
我相信她,尽管我知道她在撒谎。
赛列曼的爱文赛斯脱这样说过;但是莎士比亚满怀着乞求和欲念为之拜倒的却是怎样一个污秽的赛列曼啊!
……你的嘴唇,
亵渎了自己的鲜红的美饰,
像对我一样,屡次在虚伪的婚约上留下痕迹,
僭夺了别人眠床的租金。
承认我爱你合法吧,我用眼睛求你,
正像你爱那些人,用眼睛向他们求爱一样。
这是只有在妓院里才能找到的直言无隐和厚颜无耻;最精细的艺术家一旦放手去写这些柔软的、淫逸的、纠缠人心的情绪,他们就会沉湎在那种精神迷惘、骚乱和神魂颠倒之境。他们比王子还高贵,可是他们却堕入情欲的底层。善恶混淆;一切东西都颠倒了。
耻辱像蛀虫钻在芬芳的玫瑰花心,
玷污了你那蓓蕾般的美名,
可是你把耻辱变得多么甜蜜可爱!
你用怎样的甜蜜去包藏你的罪孽!
那谈论你平素行为的口舌,
虽然把你的嬉戏说成放荡淫逸,
但是连非难也变成了一种赞美;
称呼你的名字就会使毁誉受到祝福。
如果情欲是这么专注,那么理由、论据、意志、荣誉又算得了什么?请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这样回答你:“你要说的我都知道,你所说的一切有什么了不起?”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巨大的爱情犹如一股洪水淹没了心灵的一切嫌恶和一切审慎,一切事前的想法和一切公认的原则。这颗心对于一切平凡的欢乐不再感到兴趣而仅仅偏执于一端。莎士比亚羡忌他的情妇手指所抚弄过的琴键。他一看到花朵,他就从这些花朵后面看出了情人的倩影;他一想到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他的光芒四射的灿烂的诗句就立刻涌上心头:
春天以来,我一直不在你身旁,
那骄傲绚丽的四月穿上了盛装,
把青春的灵魂赋予万物,
连庄严的土星也一起跳跃欢笑。
他看不到春天的美丽:
我不惊叹百合的纯白,
也不赞美玫瑰的嫣红。
这一切春天的甜蜜全都化为她的芳沁和倩影。
我这样谴责那早开的紫罗兰,
甜蜜的贼,你那沁香是从哪儿来的
若不是从我爱人的呼息里偷来的?
你卤莽地从我爱人的脉管中取出紫红,
慌忙地涂在你的嫩颊上作为骄傲的艳装。
我为了你的雪白的手去谴责百合花。
那薄荷的花蕾也偷了你的金黄美发,
玫瑰羞怯地躲在荆棘上。
红的学你羞涩,白的学你绝望,
而不红不白的却把羞涩和绝望一并效仿……
在这些赃物里还加上你的呼吸芬芳,
我见过鲜艳的众葩,却从未见过
不偷盗你的甜蜜和颜色的花。
这种热情洋溢的矫饰描绘,趣味横生的刻意雕琢,真可与海涅以及但丁同时代人媲美,它们表示绵绵不断的欢乐梦想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在这样专横这样持久的情欲统治之下,还有什么感情可以存在?家庭的感情吗?他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并且“一年”才回去探望“一次”;说不定上面引用的诗句正是他在某次回家途中写下来的。良心吗?“爱情太年轻了,它不知道什么叫做良心。”嫉妒和愤怒吗?
你出卖了我,我把自己最高贵的部分
出卖给自已的叛逆:我那卑贱的肉体。
退缩吗?
他心满意足地充当你的可怜的贱役,
献身给你,倒在你的身旁。
他不再年轻了,她爱上了别人,一个年轻、漂亮、浅发的男子,他的最亲密的友人,这个人是他介绍给她的,也是她想去诱惑的:
我有两个爱人:安慰和绝望,
他们像两个精灵,一直对我劝诱;
善精灵是个十分漂亮的男子。
恶精灵是个颜色恶劣的女人,
邪恶的女鬼要骗我进地狱,
从我身旁诱走了善良的天神。
当他完成了这件事的时候,他不敢向自己承认,只有默然忍受一切,像莫里哀一样。这在日常的生活琐事中是怎样的不幸啊!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那个伟大的不幸的法国诗人莫里哀,他也是一个天生的声学家,但更是一个职业的嘲笑者,一个多情人的挖苦者,一个受欺丈夫的奚落者,他演完了他的一出最受欢迎的戏剧之后曾经大声向一个同伴说:“亲爱的朋友,我完了。我的妻子不爱我了。”无论光荣、事业和创造都不能满足这些炽热的灵魂,只有爱情才能使他们餍足,因为爱情才能满足他们的头脑、感觉和心灵;人类的一切力量,想象也同样,只有在爱情中才能凝聚起来,发挥作用。他像缪塞和海涅一样说:“爱情是我的罪恶”;在他的十四行诗中,我们还发现了其他恋爱事件的痕迹,它们同样是放荡不羁的;特别其中有一次是专为某一位贵妇而发的。固然他的前期创作 《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维洛那二绅士》更加完整地留下了这种热情的烙印;可是我们只要体味一下他后期所写的几个女性形象,看他是怀着怎样细致的柔情和怎样深厚的热忱无微不至地去爱她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
他的全部天才就在这儿;他属于那种感情细致的心灵,像一具精巧的乐器,只要略一触碰,就会颤动起来。我们在他身上最早发现的就是这种优美的敏感性。“我最亲爱的莎土比亚”,“亚冯河畔的甜蜜的天鹅”,班·琼生的这些话足以说明他的同时代人所一再提出的看法。他是多情和仁慈的,“彬彬有礼的风度,优美卓越的品格”。如果他的内心洋溢着欢乐,他也能够像真正的艺术家那样吐露衷肠。他为人所喜爱,大家都乐于和他结交;再没有比这种魅力,这种男子具有半女性的烂漫风韵更为甜蜜动人了。他的谈话是机敏的,聪颖的,精巧的;他的欢乐是明快的;他的想象是迅捷的,丰富的,正如他的同伴所说,他从不涂改自己所写的东西,即使他把一场戏重写一遍,那也只是由于他要改动内容而不是要改动字句,要表现后来突然涌上心头的绚烂思想,而不是专注于诗文的字斟句酌。这一切特点都应归结为:他具有一种易于感受的天才;我的意思是说,他自然而然地懂得了如何忘记自己,使自己渗透到描写的对象中去。看一看你们周围那些同时代的伟大作家,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看看他们的思想活动,你们就可以明白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些话的全部意义了。他们凭藉一种非凡的直觉力,可以使自己一下子化为各种描写的对象,人物、动物、花卉、草木、风景,不论这些对象是什么,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他们都通过自己的直观而感受了那种构成明显的外形的力量和倾向;他们的无限复杂的灵魂由于时刻不停地转化而变成一种囊括万有的容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似乎比别人生活得更为丰富;他们无需教导,他们的才能得自天赐。我曾经见到过这样的人,他只要随便谈到一身盔甲、一套服装、一组家具,就可以比三位学者加起来更深刻地理解中世纪。他们写作的时候自然而确切地通过自己的灵感——一种幻想形成的推理链锁去进行再创造的。莎士比亚只受过不完整的教育,懂得“一点拉丁文和极少的希腊文”,几乎完全不懂法文和意大利文,他不曾旅行过,只读过当代文学,他在家乡小镇的法院里学得一点法律条文;你不妨由此估量一下他对人类和历史所具有的全部知识。可是像他这样的人一次就可以摄取许多对象,他们掌握这些对象比别人更精密、更迅速、更全面,他们的头脑容纳了无比丰富的东西,直欲泛滥外溢。他们绝不停留在简单的推理上,他们把自己的整个身心,自己的回忆、意念、情绪浸沉在每一个观念里面。他们有声有色地表现自己的思想,运用丰富的比喻;他们纵使在谈话的时候也充满了想象和独创的风格,措辞亲切大胆,有时滔滔不绝,但又往往不遵规矩法度,因为他们只是按照突发的感兴侃侃而谈。他们的语言有着惊人的魅力和光泽,他们的创作激情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他们采取跳跃式的办法把各种互不相关的观念联结在一起,消除它们之间的距离,使悲怆转化为幽默,使激烈过渡到温柔。他们一直保持着这种惊人的欢乐情绪。如果他们偶尔找不到适当的观念,或者他们的悲伤过于沉重,他们就代之以诙谐的笔调,采取丑角的口吻,纵然对自己有所损害也在所不惜。我知道有这样的人,当他认为自己快要死去或者萌生自杀念头的时候,也会咕噜一些不吉利的双关语。他的内心好像有着一个漫无目的始终旋转的轮子,即使会把自己碾成齑粉,他也必须让这个轮子转动不停;丑角的插科打诨便是他的发泄的出口;你在莪菲莉霞的下葬、克利奥配屈拉的临终、朱丽叶的殡礼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个不能克制自己的人,这个讽刺的傀儡。不论这些人是高贵的或是低贱的,他们总是充满了激情。他们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善良与邪恶;他们由于有着一种不由自主的好奇心而把自己的灵魂扩张到广袤的领域。他们以可厌的丑行尽量地贬低自己以后,就高高地昂扬起来,形成一种姿态惊人的升华,由于感到了骄傲和喜悦而浑身颤栗。莎士比亚在经历了那些沉闷的情绪以后说:
我偶然想到了你,于是我的心
像云雀在破晓时唱着赞美诗,
从阴沉的大地飞上了天庭的大门。
接着一切都消失了,好像一个炉灶的火焰在异常猛烈的燃烧以后,没有留下灰烬。
你在我身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时令:
黄叶已经飘零,或者剩下几片,
挂在迎着寒风而摇曳的树枝之上,
那荒废的歌坛,过去曾有可爱的小鸟歌喝。
你在我身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傍晚:
夕阳的余辉已在西方消褪,
转瞬之间就要被黑夜吞没,
那死神的化身,将使一切沉睡……
当你听到阴惨的丧钟,
报告我已离开这污浊的世间,
要去和更污浊的蛆虫同住的时候,
请不要再为我的死去而悲恸,
当你读这首诗的时候,也不要再记起
写这首诗的手;因为我太爱你,
要是你想到我会引起悲痛
我宁愿在你那甜蜜的思想中被遗忘。
这种快乐和忧愁神圣的陶醉和深刻的悒郁,细致的柔情和脆弱的沮丧之间的突然交替,说明了这个充满激情的诗人总是纠缠在悲哀和喜悦里面,他可以感受到最轻微的刺激,他的欢乐和痛苦比别人更深厚更精细,他的梦想也比别人更热情更甜蜜,活在想象世界中的优美生灵和可怖生灵在他们的内心中骚动着,这些生灵也正如它们的创造者一样充满了激情。
虽然他是这样一个人,像我所描述的那样,但是他毕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很早就安于一种有秩序的、通情达理的、一般市民的生活,从事商务,明于远见,至少在外表是这样的。他在舞台上有十七年之久,虽然只担任次要角色,他还以充沛的精力把自己的才智用于自己的创作,格林称他为“用我们的羽毛来装饰自己的骄傲的乌鸦……自诩为唯一轰动全国剧坛的替人打杂的差役”。他在三十三岁的时候,有了足够的积蓄,在斯特拉福买了一幢有两座谷仓和两个花园的房子,从此他的生活越来越稳固了。一个人靠自己的劳力只能挣取到小康的生活,倘要致富,就要让别人来为自己劳动。这就是莎士比亚为什么在充当演员和作家之外,还要去担任剧院的经理和董事的原因。他在“黑衣僧剧场”和“环球剧场”获得一部分股权,承收十分之一股息,购买了一大片土地和不少房屋,给女儿苏珊娜一份嫁奁,最后回到家乡依靠产业在自己的家宅过着退休生活,像一个善于处理自己的产业并参加一定市政工作的循规蹈矩的地主,安分守己的公民一样。他每年的收入有二三百镑,大约等于现在的八百或一千二百镑。据传说,他的生活甚为美满,和四邻相处也极为融洽,总之,他似乎并不怎样考虑到自己的文学成就,因为他甚至没有想收集和出版自己的著作。他有一个女儿嫁给医生,另一个嫁给酒商;后者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签写。他借钱给别人,在他那片小天地里头角峥嵘,声名昭著。就他的一生来看,这是一个奇怪的归宿;乍一看他更像一个店主,而并不像一个诗人。我们是不是把这一点归之于英国人的天性,他们以持有收租账簿的乡绅和地主的生活作为人生的一大乐事:环境舒适,四邻和睦,平静地享受着已经得到的尊荣,家庭中的威信,地方上的名誉?或者,我们是不是要把莎士比亚看作像伏尔泰一样是一个有常识的人,虽然他赋有丰富的想象,但他在才情横溢下保持着健全的判断力,从怀疑中产生了谨慎,由于向往而养成了节俭,在洞悉了人类的各种内心活动之后,决意像康迪德一样,认为人最好去“耕耘自己的园地”?我宁可这样认为:正如他那丰满而充实的头脑所提出的,他仅仅依靠自己的洋溢的想象的力量,就像歌德一样照亮了洋溢的想象所带来的危险;他在描写情欲的时候,也像歌德一样,成功地克制了自己的情欲;熔岩并没有在他的行动中爆发出来,因为在他的诗文里面找到了迸流的出口;剧场挽救了他的生活;他怀着怜悯的心情,经历了各种随人生俱来的愚蠢和卑贱,带着宁静而忧伤的微笑,安身在这种愚蠢和卑贱之中。为了排遣郁闷,他倾听着幻想世界的空中音乐而沉湎其中。最后,我也愿意这样想:他的机体组织正如其他方面一样,是属于那个伟大世代和伟大时期的,他像拉伯雷、铁相、米盖朗琪罗和卢本斯一样,他的肌肉坚固,他的神经敏感,这两方面是势均力敌的;在那个时代经过了最严厉考验而构造得最坚固的人类肌体,可以经受情欲的风暴和灵感的烈焰,可以始终保持着灵魂和肉体的平衡;天才是盛开的花朵,而并不像现在似地是一种疾病。这一切我们只能去推测;如果我们要深入地认识这个人,我们就必须通过他的作品去看他。
(选自《读莎士比亚》,〔德〕歌德等著,张可、王元化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邮购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