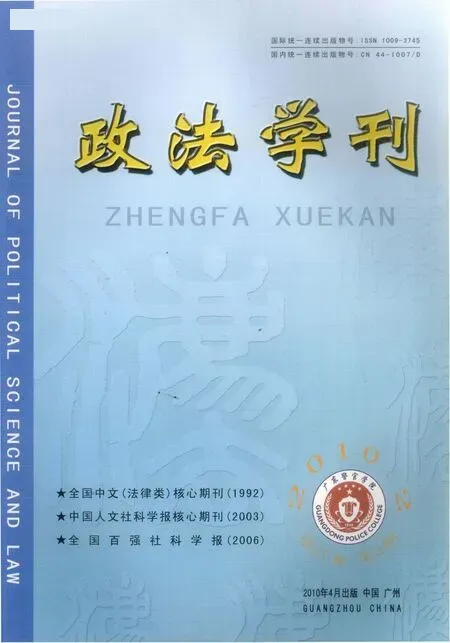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博弈
——粤东北乡村治理
丘国中,谢乃煌
(嘉应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博弈
——粤东北乡村治理
丘国中,谢乃煌
(嘉应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习惯法在国家正式司法或行政活动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其在实践领域仍然事实上发挥了规则的作用。以粤东北为例,习惯法与国家法在基层法院司法实践中的博弈,以及在各种调解活动和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博弈,证明了习惯法难以估量的作用。
习惯法;国家法;博弈;粤东北;乡村治理
导言:“习惯法”概念探讨
笔者倾向于以法律多元主义的立场探讨习惯法。法是多元化的、多层次的,它产生和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特征,包含不同的种类,既有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各种成文法,又有经过各种民间组织、群体制定或约定俗成的习惯法。那么,究竟什么是习惯法?梁治平先生的定义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 “习惯法乃是这样一套地方性规范,它是在乡民长期的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它被用来分配乡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和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主要在一套关系网络中被予以实施。就其性质而言,习惯法乃是不同于国家法的另一种知识传统”。[1]15-16在这里,法律被宽泛地理解为一种“使人类行为受规则统制的事业”,它也包括那种直接出自社会的活生生的秩序。这样一来,法律就不再被认为是国家的独占物,而是社会生活的共生物,其中也包括被认为是在乡民长期的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地方性规范。
一、当代粤东北习惯法的基本状况
(一)从乡规民约的角度考察粤东北当代习惯法的状况
乡规民约简称乡约,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乡民以地缘或血缘关系为基础,在其共同生活中设立的规则。乡规民约是传统村落习惯法或地缘习惯法的主要成文载体。乡约最早产生于中国,后来传播到东亚各国,成为一项法律文化传统。据学者考察,最早的乡约大致兴起于北宋。这一时期的蓝田《吕氏乡约》是后世的范本。《吕氏乡约》出现后,朱熹予以修订,成为《朱子损益吕氏乡约》或《损益蓝田吕氏乡约》,影响不断扩大。后世乡约基本以其为宗。明代中期社会出现深刻危机,乡约成为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王守仁于正德十三年在赣南强力推行乡约,《赣南乡约》成为《吕氏乡约》之后的又一个范本。清代官方更加重视乡约。康熙和雍正都曾模仿明太祖朱元璋提出上谕。乡约并不是由皇权国家所制定的法,而是民间法,其中包括大量的习惯法。在中国传统的“礼法”之治中,并不存在乡约的地位。但是,一般官方都以各种方式体现其对乡约的支持和认可,因此,乡约在事实上获得了一种事实上的合法性授权。[1]157-160
传统乡规民约在当代粤东北农村地区具有广泛的应用,目前它主要是以 “村规民约”和 “村民自治章程”等方式存在。通过考察乡规民约,在一定程度上即能反映传统习惯法的当代遭遇。
粤东北传统的乡规民约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近现代社会变革中经历了许多波折。在粤东北传统民间社会的乡规民约中,习惯法是其主要形式。目前,村规民约主要由村民会议负责制定。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目前粤东北村规民约很多属于国家规划的产物,其内容多体现官方意志。例如,丰顺县北斗镇拾荷村 2000年制定的《村民自治章程》和《拾荷村规民约》便是如此。
《拾荷村村民自治章程》(摘要)
第一,经济管理。对于土地的管理和调整;关于村办企业;关于村级财务。第二,社会秋序管理。倡导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每个村民要团结友爱,平等相处,树立正气,遵纪守法;喜事新办,严禁铺张浪费,丧事从简,提倡火葬。对这方面违法行为的控制和处罚。第三,村民组织设置。第四,村政的民主监督。第五,其他。
《拾荷村村规民约》摘要
第一,村民的权利。……第二,村民的义务。第三,对村民行为的奖励 (包括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第四,有关处罚的规定。……
本村规民约由村委会下属各职能委员会予以执行。[2]54-55
但在五华县棉洋镇琴江村和葵岭村,笔者看到一种至今仍然发生效力的传统乡规民约。比较起来,这两种村规民约在内容上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更像行政法律文件,而后者则有较多的传统乡土气息。另外,两者存在如下差异:前者范围广泛,从村内组织设置、运行规则、职责到村民的权利义务,再到对村民的奖励和惩罚都有详细的规定。而后者则集中于本村的日常生产生活秩序。前者村民义务具有优先性,或者说制订它的目的是促使村民完成国家与政府的各项任务;而后者虽然也较多地规定义务,但是这种义务是成员对村落共同体所负有的、直接关涉共同利益的义务。前者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看,都可以发现该村规民约的法律政策缩影,用语也非常现代化、形式化,而后者用语比较古朴和实质化。
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制定时间的差别。1987年11月通过并于 1988年 6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试行),其中第二十条规定:“村规民约由村民会议讨论制定,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由村民委员会监督执行。村规民约不得与宪法、法律和法规相抵触。”据考察,目前粤东北乡规民约,丰顺县拾荷村的模式占多数,它们往往是由民政部门提供示范样本,村委会 “填写”后便张榜公布的 (一般村委会足以决定,最多在村民代表会议上讨论,而没有提交村民会议表决通过的)。
这种变化反映出村规民约之所以失去乡土性,其原因是国家加强了对民间自治的指导和控制。在国家放权与收权的不断调整过程中,尽管有所恢复,但习惯法并没有能够达到其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的那种状态。这从乡规民约逐渐失去其乡土气息和经验色彩的事实中可以看出。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习惯法已经从历史舞台上逐步退场呢?应该说,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习惯法在正式司法或国家行政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其在实践领域仍然默默地发挥着事实上的调整规则的作用。
(二)从不成文习惯法考察粤东北当代习惯法状况
从一般生活经验来看,可以说,在粤东北农村地区,尽管国家法的作用要大得多,但日常生活和交往的规则仍然主要由习惯法来调整,如传统婚姻习惯法中订婚习惯仍然以不同形式存在着。1978年以后,地方性制度开始得到恢复,血亲、姻亲以及朋友圈子内的社会关系逐步得到加强。传统社会中的家族组织也开始重新获得活力,宗族复兴。当然,这种复兴并没有达到 1949年以前的程度,其主要表现为修族谱、建祠堂、举行庆典等内容。这些情况反映出传统习惯法恢复一定影响力的可能性。在具有这种社会基础的条件下,即使传统习惯法已经很少留存于当下社会中,其规范内容也仍然对于当代立法产生重要影响。这种民间社会关系及地方性制度的恢复,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某种民间共同体组织的恢复。民间共同体则具有创制、实施和维护规范的能力。
五华县葵岭村甲的菜地与下面乙的祖坟相邻,甲在自己的菜地中间挖个坑,平时装雨水,供浇灌之用;乙得知后气势汹汹地前来阻拦,大有拼个你死我活之势,乙的理由是:甲挖了自己祖坟的 “坟脑”,势必使祖坟 “风水失效”。村委会主任前来调停,劝说甲退让,将坑填平。从法律上来讲,甲在自家自留地里面作业,其行为受保护(除非有证据证明坑里的雨水将实际渗灌乙的祖坟),乙纯属无理取闹。但从习俗上来讲,甲在乙祖坟的“坟脑”位置挖坑,包括村委会主任在内的很多人也认为不妥。①五华县人民法院:案例选编,2001,第 321页。
据笔者对粤东北习惯法所作的调查,本地旧有的习惯法有三种命运:第一种,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条件消失或者与国家制定法严重冲突,因而已经完全在制度形态上消失;第二种,虽然并不严重违反国家法,但因为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迁而消失或正在消失,或者已经转化为成文法类型的民间法;第三种,不严重违反国家法,或者与国家法具有一定的契合,而仍然发挥着强有力的规范作用。
以上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习惯。但是习惯法也包括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发生的惯例或习惯法。按照朱苏力先生的观点,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乡镇企业制度,以及市场经济改革,均曾以经验与习惯为先导。也就是说,习惯法并非仅存在于历史的回忆中,在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发的各种非正式制度中也存在习惯法。
二、当代粤东北习惯法与国家法在实践中的博弈
下面将场景设定为粤东北农村地区,主要针对基层司法领域中的习惯法实践进行分析,以便发现习惯法在粤东北民间治理中的问题,并探讨解决相关问题的思路、措施或方案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习惯法仅仅是乡土社会中的习惯法,而只是为了更集中以及更准确地说明问题而作的设定)。
(一)在基层法院司法实践中的博弈
法院的基本职能是什么?是实现普遍性规范的具体适用以及形成普遍性规则,还是解决具体纠纷?应该说,标准答案应是前者,这是法治作为“规范之治”的本来含义。但是,如果按照基层法院的法律实践来看,答案却会比较偏向于后者。在当代粤东北农村基层法院审判以及调解的活动中,解决纠纷仍然是其工作的中心。对此,这里用一个案例加以说明。
原告,男,汉族,现年 45岁,河源市某县人,农民。
被告,男,汉族,现年 38岁,河源市某县人,农民。
原告诉被告人身损害赔偿一案,河源市某县人民法庭于 2006年 6月 5日依法受理,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经审理查明,2004年 4月 5日,原告耕地被被告的耕牛践踏毁坏,于是原告当即牵回耕牛并拴在自家院里。被告到原告家索要耕牛,未与原告示达成赔偿协议,并由此发生争吵打架,被告手持木柴将原告头部打伤,后经邻居劝阻回家,原告即被送到该市第二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为 “颅内损伤”,住院治疗 8天,又在家休养三个多月,造成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损失共 3500元。原告两年内多次到村委会、镇派出所、司法所反映要求解决无果。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委托代理人律师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一年的规定,法庭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查,原告确已过一年的时效期限,本有时效中断的事由 (到村委会、镇派出所、司法所反映要求解决,提出权利主张)但原告无法提出证据。但鉴于此案被告在村里影响不好,原告合法权益确须维护,为起到教育被告,惩戒打架行为人的目的,合议庭主动到镇派出所调取原告时效中断事由的证据,并由法庭主持调解,但被告坚决不同意。后通过向被告施压,与律师共同努力,被告和原告最终同意在调解书上签字由被告一次性付给原告 2800元人民币作为赔偿。②
在此案以及类似的其他案例中,可以发现,纠纷解决往往是基层法院最为重视的事情,而坚持制定法规范的权威性和 “规则法治”则处于第二位。对于纠纷解决的目标而言,法官是成功的。本案中的原告获得了 “说法”和赔偿,被告受到了惩罚,实现了法律的正义。法官灵活地运用法律的原则性规定,维护了当事人的权利,“巧妙”地运用了调解手段解决问题,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但是,从规则之治的角度来看,法官的做法是有瑕疵的。例如,按照诉讼时效的规定,超过时效的应当驳回起诉;法官应当恪守中立,一般不宜主动调取关于一方时效未过的证据。
在粤东北的农村地区,并不仅仅存在一种法律和秩序。在国家正式法律之外,还存在不同的群体、传统、风俗以及相应的规范性知识。作为这种规范性知识的主要代表,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一同主导着各种纠纷的解决。有时,习惯法会被国家制定法所否定;另外一些情况下,国家制定法则向习惯法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
(二)在各种调解活动实践中的博弈
调解通常分为诉讼内调解与诉讼外调解两类,诉讼内调解是在诉讼过程中以法官为调解主体的调解;诉讼外调解包括以行政机构为主体的行政调解,以及以民间自治组织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体的民间调解。在各种调解主体主持的调解活动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习惯法在粤东北民间社会中的实践情况。
在诉讼内调解方面,由于基层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所面临的矛盾与压力,为了有效地化解矛盾以及解决纠纷,法官经常选择使用调解这种介于正式诉讼与私力救济两极之间的纠纷解决机制。由于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它已经得到官方正式承认。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进行的调解,是诉讼内调解。对于婚姻案件,诉讼内调解是必经的程序。至于其他民事案件是否进行调解,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调解不是必经程序。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有同等效力。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的诉讼外调解更多地体现了对民间习惯法的重视。例如:
2000年 8月 23日下午,五华县潭下镇举水村村委会组织人员到该村一山头挖山泥,因事前没有了解情况,不慎挖到该村李姓家族的祖坟。此事在举水村引起了轩然大波。8月 24日下午 2点,李姓家族成员多人气势汹汹地聚集在村委会门口,堵住进出道路,进行巨额索赔。矛盾随时可能激化。镇派出所接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同镇有关部门一起组织村民和村委会干部进行调处。李姓村民提出了每墓穴 3万元的赔偿要求,被村委会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派出所提出了如下调处意见:(1)村委会在这次山坟纠纷中确实存在过错,应向李姓村民公开道歉,缓和村民情绪; (2)调查清楚被挖到的山坟有多少穴; (3)村委会应进行适当赔偿,但金额不宜过高; (4)如确实不能达成协议,可引导村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根据派出所的调处意见,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村委会向李姓村民作了公开道歉,态度诚恳,渐渐平息了村民们的激动情绪。在补偿金额上,经多次反复协商,双方终于在春节前达成一致,村委会就被挖的穴坟墓共补偿 3万元。①五华县人民法院:案例选编,2001,第 321页。
在这起纠纷之中,纠纷的焦点是坟地破坏及其赔偿问题。按照民间传统习惯,祖坟被挖对受害方来说,是极其严重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挑衅行为,该行为应当也必然会受到严厉的报复与惩罚。由此关于坟地的民间习惯引起的宗族纠纷,敏感、复杂,很容易演变成为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与此同时,山坟被挖应如何定性以及如何补偿,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因此,事发后一些人乘机索要巨额赔偿,而另一方却不接受,发展下去肯定会成为恶性事件。潭下镇派出所调解这起纠纷非常出色,他们不仅以最快的时间赶到现场稳定村民情绪,组织双方协商解决问题,当双方僵持时,能马上提出公正公平且比较合理的调解意见,最终为双方所接受。从官方对这起调解活动的叙述本身来看,纠纷的解决完全是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进行,派出所创造性地通过调解化解了矛盾,解决了纠纷。那么,纠纷是否完全没有依据规范解决呢?并非如此。派出所实际上是以一种隐晦的方式选择了关于坟地的民间习惯法作为其调解的规范性依据。从国家制定法的角度,调解是没有法律依据又不违法的条件下实现的。但从超越国家主义的法律观来看,调解实际上是依据民间习惯法实现的。可以设想,假如派出所完全抛开当地习惯处理纠纷,会出现两种情形:仅仅按照法律是否有所规定来处理这起纠纷,则受害方可能无法获得应有的赔偿,矛盾与纠纷将难以真正化解;而完全以无规范的谈判解决纠纷,即双方通过力量与利益的角逐来获得结果,势必会破坏人们对规范的信任或信仰,最终对社会秩序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以民间习惯法为依据处理这起纠纷,是最符合各方利益与需要的选择。然而,对于该派出所来说,民间习惯法的合法地位并没有合法界定,因而在对这起案例的叙述中策略性地忽略了其所依据的规范类型。
以农村为中心的乡镇还往往设有法律服务机构,提供法律服务,称为 “法律服务站”、“法律服务室”等。这些机构,它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村民自治组织,而从事包括调解活动在内的有偿性质的法律服务工作。在主持调解的主体中,更为重要的是村民自治组织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些主体的人员经常并不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而是按照本地习惯进行调解。
人们不禁会问,当法律执行者经常采取一些变通或模糊的方式运用法律解决问题时,是有助于社会的依法治理,还是会破坏法治国家的秩序?法律在基层法院的运作过程中,是否会被习惯法所暗中渗透和解构?虽然法院审判仍然以合法程序进行,判决也以法定的规范陈述得到表达,是否其背后隐藏着其他秘密?严格按照制定法行事,难以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而能够有效解决纠纷的习惯法,又没有合法地位,那么,法官和当事人是否会利用这种局面,将司法活动变成一种谋取私利的交易场所?等等。[3]211这些问题都在迫使我们反思那种依赖单一的国家制定法的法治进程。同时,也迫使我们反思国家制定法及其价值或意义。
(三)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博弈
按照官方解释,所谓村民自治,简而言之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 “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自治章程是村民和村干部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综合性章程,也是村内最权威、最全面的规章,村民形象地称之为“小宪法”。村规民约一般是就某个突出问题,如治安、护林、防火等作出规定,作为村民的基本行为规范。习惯法在村民自治领域之中的实践,主要体现为村规民约及其实践。村规民约突出的特点就是通过对村民权利和义务的确定,告诉村民们有权做什么,应该做什么,通过奖励与处罚规定来引导村民行为。从理论上讲,村规民约的订立应该归入私法自治范畴,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发生冲突,就应该得到法律保障。可以设想,既然习惯法是内生于村民生产生活并为村民们所熟悉和信赖的规范资源,习惯法及其价值观念将会较多地进入到乡规民约,从口耳相传的不成文法转变为较为规范的成文法。[4]34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习惯法,应当可以有条件地纳入村规民约这种自治规范的范畴。但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往往不如想象的那么显著。
从粤东北目前村规民约的实践来看,村民自治的现状与制度设计者预期距离还较大,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许多相互纠结在一起的矛盾与问题。从村民自治来看,例如制度弱化,按照上级命令指派党支部书记兼村干部,或者利用非法手段以及权势控制村治,从而使自治失去意义、功能退化,村干部或者成为准政府成员或其代言人,或者退化为特殊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社区公共利益的代表;权力失衡,村庄自治权力无法独立于基层政府权力的控制等等。从政府推行的 “村规民约”的角度来看,也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其一,范围广泛,极大地压缩了私人权利的空间与范围,其中某些内容甚至超越了制定法所赋予的权限;其二,义务优先,从各种村规民约文本来看,其中很多内容是国家政策的具体化和场景化,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点,因而有人称之为 “失衡的契约”;第三,乡土性不足,村规民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法律与政策文本的延伸部分,用语也高度现代化和形式化;最后,奖惩成为村规民约推行的主要手段,这与传统社会中村民们对传统乡规民约的自觉遵从形成鲜明对比,也反映出村民们对村规民约缺乏认同感。
以上情况表明,在村民自治及政府推行的“村规民约”中,习惯法确实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村民自治的实践与其理论预期之间的偏差所造成的。村规民约的各种规范文本的出现,使得村规民约越来越形式化、官方化或规范化,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制定法与政府政策的摘抄本或翻版。而且,村规民约与村民们所熟悉和信赖的习惯法及其价值观念无法有效地融合,因而其作为自治规范的性质与意义有所弱化。[5]67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村民自治的规范资源,并削弱了村民自治在构建法治秩序方面的效果。从有效地促进村民民主与自治的需要出发,习惯法应当引起足够地重视,并作为一种重要的规范资源引入村民自治进程中。[6]
习惯法在村民自治中的实践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促进村民们对于村民自治的参与感,对村规民约的认同感,并且加强他们对于依据规范进行治理的法治意识。其二,补充与完善村民自治与村规民约的规范结构,使国家制定法、规章制度、习惯法以及道德等多种规范能够更加协调地发挥作用,共同促进与保障村庄社区的秩序。以上两个方面,无论是促进村民们的规范意识或规范信仰,还是实现村庄的秩序,都将有助于在广大农村构建法治与和谐社会。[7]32
[1]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 [A].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中的秩序、公正与权成 [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丰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丰顺县志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3]苏力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 [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5]田成友.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6]于建嵘.失衡的契约——对一示范村村民自治章程的分析 [J].中国农村观察,2001,(1).
[7]五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五华县志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马 睿
A bstract: In formal judicialor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customary laws are not given due attention.However,in practice they still play the role of regulation.Taking northeast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the game between customary law and constitutional law in grass-root court and in coordinating various activities and village autonomy proves its important role in practice.
Key w ords:customary law;constitutional law;game;northeast Guangdong province;rural governance
The Game between Customary Law and ConstitutionalLaw-The Rural Governance in Northeast Guangdong Province
Qiu Zhong-guo,Xie huang
(Jiaying University,Meizhou 514015,China)
D921.8
A
1009-3745(2010)02-0035-06
2010-02-22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 东北乡村治理法制问题研究》成果 (项目批准号:07G08)
丘国中 (1974-),男,广东兴宁人,嘉应学院法学讲师,从事民商法学研究;谢乃煌 (1969-),男,广东五华人,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法学副教授,从事民商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