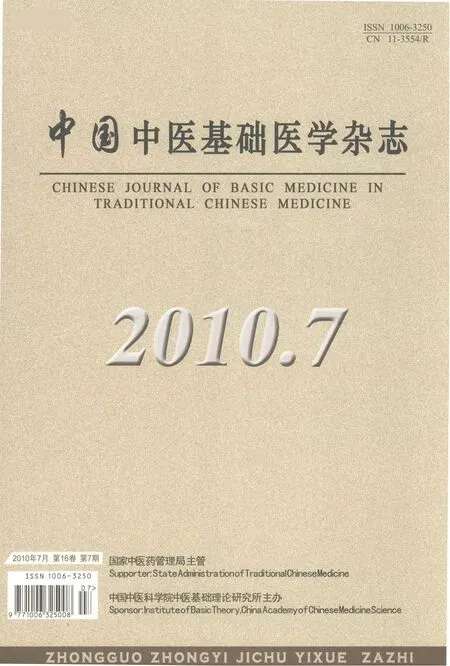刍议“胃为贮痰之器”
张志敏,张大鹏,武志娟
(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中医科,广东 广州 510120)
刍议“胃为贮痰之器”
张志敏,张大鹏,武志娟
(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中医科,广东 广州 510120)
胃为贮痰之器;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
痰证理论肇始《内经》、《难经》,历经后世诸多医家发挥,至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通观《内经》并无“痰”字,只有在《素问·经脉别论》中论述人身水液代谢的途径。自晋·王叔和《脉经》及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始有“淡饮”之名,与张仲景《金匮要略》之《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遥相呼应,为后世痰证学说以及理论奠定了基础。明·李中梓基于“脾肺二家,往往病则俱病”,故提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之论,对后世影响颇深。然细考《内经》“肺为贮痰之器”之论不足为凭,故斗胆质疑,不妥之处敬请各位高明斧正。
1 从脏腑的生理功能来看
中医藏象学说认为,脏腑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生理功能特点的差异。正如《素问·五脏别论》所云:“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实。六府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肺为五脏之华盖,四脏之首,其生理功能特点同样是“藏精气而不泻”、“满而不实”,又“通与天气”,为至高至清之脏,主一身之气,总司人体呼吸之事,若真能为“贮藏之器”,又如何实现其在生命过程中的生理功能呢?从这一点看,“肺为贮痰之器”显然是错误的。另外,《素问·灵兰秘典论》对肺的生理功能进一步概括为“相傅之官,治节出焉”,位高非君,故官为相傅,主行营卫之气,故治节由之,岂可贮痰?虽然肺、脾、肾在水液代谢中密切相关,中医学根据肺在气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解剖位置等特点,又将其称之为“水之上源”。然将肺称为“贮痰之器”从根本上违背了《内经》区别脏腑的基本原则,有明显的错误,用于指导临床则可能会导致很多弊端。相反,胃为六腑之一,如《素问·五脏别论》所云:“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脏之浊气,名曰传化之腑。”痰为气血津液代谢的异常病理产物,为五脏所化生之浊气,其所贮藏之处必为受盛之所、化物之处。脾胃互为表里,且为“仓廪之官”,水谷入胃,更虚更实,经过“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这一过程之后,再由肺将脾转输的水谷之精布散全身。而肺与胃的生理功能在水谷代谢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其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谷气通于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结合胃的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特点来看,“胃为贮痰之器”较“肺为贮痰之器”则更具合理性的一面。
2 从病因病机分析
追溯疾病的原因,在外感致病因素方面“风为百病之长”。《内经·风论》以“风中五脏六腑之俞”为“脏腑之风”,以别于偏风、脑风、漏风、内风、首风等。而肺风之状,表现为“多汗恶风,色皏然白,时咳短气,昼日则差,暮则甚”。经云:“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饮食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腑。”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正如“邪风之至,疾如风雨,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经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外感疾病的传变,由表及里,由肌表到经脉,再由经脉传至六腑,最后再到五脏。而从疾病的预后来看,病至五脏,预后凶险。痰为气血津液代谢的异常病理产物,病在痰可以通过“燥湿”、“健脾”、“温化”、“渗利”等法治疗,预后多良好,尚未至“半死半生”的阶段,故“肺为贮痰之器”,从疾病的预后来看与临床不符,难以立论。另外,“肺主气司呼吸”,主管一身之气机;从内伤病因来看,七情致病有九气之不同,《素问·举痛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病机病证之异,似与痰证有别,在此更难见“肺为贮痰之器”之凭证。
3 从肺病的临床表现来看
《内经》虽然并无“痰”字,但却在不同章节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既阐明了人体气血津液代谢的过程,并在生理、病理、疾病诊断、临床表现、刺灸治疗等方面提出关于痰饮为病以及治疗等具体的观点。只是后世医家不明经义、断章取义、自以为是才导致诸多“新论”。《内经》中对肺病的临床表现始终坚持在以其生理功能为基础的整体观念指导下阐释其临床表现,如肺咳、肺痹、肺痿,真正体现了天人相应、人体自身的整体性以及人与社会相统一的观念。从《生气通天论》始论“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的肺病表现,到《咳论》、《痿论》主论肺病之咳、痿,再到《至真要大论》从运气学说角度论太阴肺病的临床表现,可谓篇篇箴言,字字珠玑。具体肺病临床表现之症状如寒热、多汗、多涕、咳嗽、胸痛、咯血、身重、浮肿、胁下痛引缺盆、背寒冷如掌大、心悸、短气等。而痰证临床表现不仅仅是有形之痰或者狭义地认为咳嗽之痰,由于无形之痰饮可随气血流行于全身,或停留于局部,故临床表现之复杂,岂能“肺为贮痰之器”一言以毕之?若仅仅从在“肺为贮痰之器”来论肺病之临床,则枉先贤立论之苦心,临证用药治病,可谓一叶障目,害人匪浅。惟后汉张仲景得先贤不传之秘,在《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首倡痰饮、咳嗽分论。一方面揭示两者的相关性,更重要的是将痰饮、咳嗽分论,为后人辨治提供了更多的方法和思路。无论痰饮、咳嗽,治疗从肺、从脾,或从肝、从肾之论,张仲景之后能明经旨者再无他人。
4 从痰证的治疗上分析
肺为娇脏,主气司呼吸而为水之上源,人体呼吸动息不停,若一刻呼吸受阻则生命立危,故机体为保障肺的呼吸功能不受阻碍,凡有微小之邪侵袭则立即表现“咳逆倚息”、“上气不得卧”等。正如陈修园在《医贯》所云:“盖肺为清虚之府,一物不容,毫毛必咳。”肺为五脏之华盖,呼之则气虚,吸之则气满,只受得本脏之正气,受不得外来之邪气,邪气干之则呛而咳作。张仲景论痰饮之证治,“当以温药和之”。而肺为清虚之脏,既不受外感之邪气,又不受水谷之浊气,如何受得药气之温热?若“肺为贮痰之器”而又不耐药气之温化,如此痰证真可谓“不治之证”,这显然与临床不符。自古以来,许多医家认为咳喘必因于痰,咳喘之症状为肺之主症,为“肺为贮痰之器”摇旗造势,全然误解《内经》之旨。正如黄帝与雷公在讨论病例的过程中讲到咳喘以及误将该案咳喘从肺论治的危害。《素问·示从容论》黄帝云:“咳喘者,是水气并阳明也。”并指出“若夫以为伤肺者,由失以狂也。夫伤肺者,脾气不守,胃气不清,经气不为使,真藏坏决,经脉傍绝,五藏漏泄,不衄则呕,此二者不相类也。”医理昭昭,以明示后之学者。奈何当今之医,不详读经书,或偏见一叶,或偶读一句,则奉为圭杲,用之临床则误人不少,如此则为先贤所不啻,显然“肺为贮痰之器”是没有理论依据的。通过《内经》中黄帝评雷公在治疗案例中的错误可以知道,“咳喘者,是水气并阳明也”,此论即是“胃为贮痰之器”最好的证据。
综上所述,“肺为贮痰之器”无论从脏腑的生理功能、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和治疗等方面来看,均证据不足,虽李氏以“脾肺二家,往往病则俱病”,但与经旨有悖,而且与临床不符,故难以苟同。若“脾为生痰之源”,则“胃为贮痰之器”之论证据更加确凿,毕竟“咳喘者,是水气并阳明也”而非肺也。
[1]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77-78.
[2]李古松.“肺为贮痰之器”辩[J].浙江中医杂志,2008,43(7):377.
[3]蒋兆定.肺为贮痰之器诌议[J].辽宁中医杂志,2003,30(10):806.
R222.15
A
1006-3250(2010)07-0541-01
2009-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