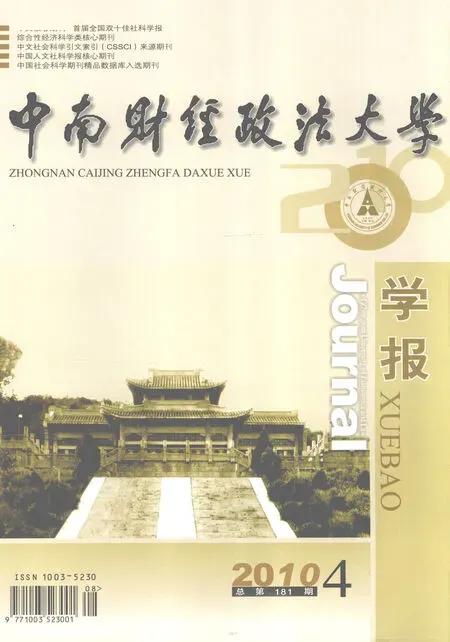美国地方政府的收支限制及反思
甘行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滞胀”,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美国也不例外。低增长、高失业和高膨胀并存,经济绩效恶化与财政绩效恶化同时。公共部门膨胀,财政支出过高,政府运行成本高昂,税收负担增长很快,政府效率低下,对于公众日益强烈的服务需求,政府的回应令人失望。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的州和地方公共部门经历了重大的财政重塑。州和地方政府试图改变其收入体制、支出组合和服务传递装置,通过地方政治过程、立法机关提议和公民投票的方式发动了一场限制地方政府收支的浪潮,其目的在于限制州和地方政府汲取收入和安排支出的能力。这场地方政府收支限制运动的重点是州政府。在地方一级,大量限制措施的对象主要是针对财产税。从时间上看,这些地方性限制措施可追朔到19世纪甚至更早时期,其中大多数是作为现代“税收抗议”的结果而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比如,堪萨斯州1970年实施了法定财产税收入限制,亚拉巴马州1972年实施了限制总体财产税率的宪法修正案,加利福尼亚州1978年通过了13号法案,马塞诸萨州1980年实施了“21/2法案”。少数限制措施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如卡罗来多州通过的“纳税人权利法案”等。
一、美国地方政府收支限制的类型
美国地方政府的收支限制措施有6种形式。第一,综合财产税率限制,即确定一个税率限额,不经过选民的投票,就不得超过这一限额。这一限额适用于所有地方政府的综合税率。综合财产税率限制是地方政府收支限制最普遍的形式。其不足在于,在评估财产价值的实践中易于采取变通措施进行规避。但若辅之以评估值的限制,则该措施就具有潜在的约束力。第二,特定财产税率限制,与综合财产税率限制相同,只是该措施适用于特定类型的地方辖区比如学区或县等,或适用于狭义的服务领域。其不足之处在于,在评估财产价值的实践中易于采取变通措施进行规避,或者,就特定的服务而言,可通过基金之间的转移进行规避。但若辅之以对评估值的增长限制,则该措施也具有潜在的约束力。第三,财产税征收额的限制,即通过规定财产税征收额的年增长率(百分比形式),来约束财产税征收的收入总量,与财产税率无关。在其它情况不变时,收入限额的固定性可以强化该措施的约束力,但另一方面,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又会淡化该措施的约束。第四,总收入或总支出的增长限制,即对可征收到的收入额实行封顶限制,约束该财政年度的支出额。这些限制措施通常要按照通胀率进行指数化调整。在其它情况不变时,收入限额或支出限额的固定性强化了该措施的约束力。第五,财产评估值的增长限制,既然征收的财产税是财产的评估值和税率的函数,那么该措施就控制了地方政府通过重估财产的方式或通过财产价值的自然升值或行政管理升值的方式来筹集收入的能力。其不足之处在于,该措施易于通过提高财产税率的方式进行规避,但若辅之以综合财产税率限制或特定财产税率限制,该措施就具有潜在的约束力。第六,完全公开课征财产税的实际情况,即要求在规定税率或征收额的增长率之前,要进行某种形式的公众讨论和特别的立法投票。其不足之处在于,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税率或增加征收额,只需要通过立法机构的正式投票获得是简单多数就可以达到目的[1]。
二、美国地方政府收支限制的后果
各州实施的收支限制措施不完全相同,同一个限制措施在各地方的约束严厉程度也不一致,因而这些限制措施在各辖区的社会经济效应也不完全相同。这种社会经济效应因地方政府类型、服务类型、居民结构、辖区的空间位置及其相对繁荣程度的不同而不同。总的说来,这些限制措施给不同的辖区带来了不同的福利损失。
第一,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收入结构。减少了地方政府对税收特别是财产税的依赖①,增加了对非税收入比如收费、债务、州级政府转移支付以及其它杂项收入来源的依赖。在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中,与财产税相比,收费与其他杂项收入急剧增加。在实施地方收支限制之前的1972年,只有3个州取自收费和杂项收入的地方收入多于取自财产税的收入,而在实施地方收支限制之后的1999年,有23个州取自收费和杂项收入的地方收入高于取自财产税的收入。对州级政府转移支付的依赖大大增加。财产税的相对作用下降了1/3。1972年,财产税对地方政府收入的贡献比州级政府转移支付平均多出48%,1999年,州级政府转移支付与财产税对地方政府收入的贡献几乎达到了完全同等的地位。
第二,改变了地方政府服务责任的配置,带来了权力与责任向州级政府的纵向转移,强化了州级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形成了一种集权效应,削弱了地方自治,限制了地方政府的选择。地方财政限制大大改变了州和地方公共部门。州和地方政府收入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持续增长,其中,州级政府的份额大大增加,几乎是地方政府份额的3倍。平均说来,从1972年到1999年这种集权程度增加了12%。在1972年,有18个州的地方收入份额大致等于或大于其州政府的收入份额。到1999年,这个数字减半。只有4个州的地方自有收入来源的收入份额大于州政府,而之前有13个州的地方自有收入来源的收入份额大于州政府。1999年,新墨西哥、阿拉斯加、佛蒙特、夏威夷、特拉华、纽约和新罕什布尔等州呈现出一种以州为主导地位的财政结构。地方政府的作用在加州、新泽西州、密西根州、马萨诸塞和佛蒙特州分别下降了38%、40%、36%、55%、和47%[2]。同时也带来了地方政府的分化和“碎片化”,导致地方政府职能和责任的横向转移,强化了特别服务区的作用,增加了有限目的政府(即专区政府)的相对收支权力,淡化了一般目的政府的相对收入责任和作用。因此在地方一级实现有效率的预算权衡和服务协调变得十分困难。从绝对规模看,1972~1997年之间,美国特区(专区)政府的数量增加了45%,美国基层的地方政府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第三,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在面临收入约束的背景下,地方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并未减弱,为了对地方居民的偏好和需求保持“灵敏反应”,地方政府被迫从事“财政创新”,采取变通措施。而这些变通措施仅仅提供了次优的解决方案,本身存在很大的扭曲,使地方政府行为在透明度和反应的灵敏度方面大为下降,地方政府的责任也大为减弱和淡化。比如,在加州,为了克服“13号法案”所带来的融资约束,地方政府在融资方面已经严重扭曲,采取各种途径筹集收入[3]。
第四,改变了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限制了地方居民了解地方社区及其公共服务目标的能力,大大影响了地方政府灵活满足地方公共需求的能力,带来了教育投入的下降和教育绩效的恶化,导致了城市服务质量的整体下滑,降低了地方公共部门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西方有学者对马塞诸萨州1980年通过的“21/2方案”所决定的财产税对财产价值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②,得出结论认为,“21/2方案”降低了当地的财产税,同时也降低了当地的房产价值[4],从而背离了地方居民所追求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另一方面,财产税的限制又淡化了它在联系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方面的作用。
第五,随着收支约束特别是财产税收入约束的强化,地方公共部门的扭曲也迅速增加,新的融资机制和服务传递机制产生了严重的效率问题和公平问题。以收费为基础的服务提供,虽然有可能改善效率,但也有可能挑战公平(如果不用于资助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和劳务)。地方政府在面临收入约束的情况下,对服务效率的追求也可能带来私有化和采用服务合约的压力。而这又可能淡化政府的控制和责任。同时,这些措施对各社区的影响程度与其相对繁荣程度有关。这些限制措施对于公平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虽然可通过增加政府间的转移支付、采取更为累进的州级收入体制来补偿,但强化州级政府作用的同时又会削弱地方自治。
总之,美国地方政府的收支限制浪潮推动了州和地方政府的公共部门改革,对于美国基层的地方政府结构及其提供的服务组合和长期的融资机制都存在重要的潜在的实质性影响[2]。这些影响并非良性,而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强化,特别是在经济紧缩的背景下会显得尤其突出。这些限制措施将继续扭曲地方财政结构和服务传递结构,并形成一个更加分化、复杂、不太透明、不太公平、缺乏效率、反应迟钝、责任退化的州和地方公共部门。
三、对美国地方政府收支限制的反思
在美国,无论是出于一般目的,还是出于教育目的,地方民众进行的“税收抗议”的重点都是财产税[5]。美国的公众舆论一直把财产税视为“最糟糕”或“最不公平”的税种之一。财产税一直处于选民前后矛盾的愿望之中[5]。一方面,选民希望减税,另一方面,选民又希望地方政府提高服务水平,保证税收的确定性。面临这种非理性的矛盾,地方政府被迫通过税收操纵来构建一种名义税收低于其实际税负水平的“财政幻觉”。而这种“财政幻觉”又违背了税收的确定性原则(包括公平、简便和可控性原则),结果引起了民众的愤怒和税收限制措施的引入。面临收入约束和选民的非理性,地方政府实施进一步的税收操纵,结果又加剧了财产税信誉的下降和政治生命的衰弱。在实施了收支限制措施之后,财产税在地方政府总收入中的相对作用下降了37%[2]。而且现有的财产税在公平与效率原则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受到某些压力的影响,现行财产税制减轻了自住房屋财产的相对负担,限制了财产税在教育融资方面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加州,财产税的使用限制十分严厉,此时的财产税呈现出州政府税收的特征,只是将财产税的收入分配给地方辖区而已。这样,地方财政自治的程度已经很弱。现行财产税负担的分配在各类型财产之间以及同一类型财产内部可能既不公平又无效率。因此,财产税将继续成为改革和调整的重点。然而,财产税毕竟是人类有记录的历史以来最古老的税种,在缺乏可行的替代手段的情况下,财产税仍将是地方财政的主要基础,在地方公共财政中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地方财政实践的发展历程表明,财产税的相对作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财产税收入仍然稳定在地方总收入的大约30%[2]。
财产税在美国的发展经历令人深思,迫使人们重新理性地看待财产税,正确认识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融资的工具,既存在优点,又存在缺点。美国地方政府的收支限制运动与财产税本身的缺点和美国居民对财产税的不满有着密切的联系。正确认识财产税的局限性,并寻找妥善的办法加以改进,克服其不足,是任何一个使用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国家应有的态度。在我国正酝酿财产税改革的今天,认识到这一点,并做相应的准备工作,尤其重要。关于财产税的不足,美国学者奥滋(Oates)有过精辟的分析。如果地方财产税是资助地方公共支出的可用的最好工具,那么为什么财产税会如此不受选民的欢迎?他总结了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财产税是看得见的、有形的,纳税人通常收到的是一份明确的必须马上支付的账单。第二,财产税的价值评估存在行政管理问题。第三,房主的收入与其纳税义务之间缺乏完美的有机联系,使得财产税在纳税人收入固定的情况下尤其不受欢迎。第四、以财产税融资会导致各辖区之间的财政不公[6](P78—90)。事实上,优点与缺点同出一源。
第一,看得见的财产税,作为地方公共劳务价格的准确信号,成为联系地方公共劳务成本与地方公共劳务受益的纽带,能够激发地方居民的权利意识,促使地方居民关心地方公共支出的配置效率,有助于提高地方自治水平,改善基层民主政治状况,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引导地方公共决策产生有效率的结果。特别是在中国地方自治程度很低的情况下,采用财产税为基层政府融资,可以成为中国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看得见的财产税负担很难令纳税人欣然接受,易于引起纳税人的抱怨和不满。在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情况下,要扩大财产税的征收范围,特别是将广大的农民也纳入征税范围之内,难免会产生公民接受方面的政治阻力,势必会增加纳税人的遵从成本。所以,改革和完善财产税制之际,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点。
第二,以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与其他融资工具相比,在征税实践中多了一个环节,即财产价值的评估。显然,单从形式上看,这一环节就增加了财产税的行政管理成本。理论上讲,可以通过改进评估实践来降低财产税的行政管理成本。但实践中如何改进评估工作,值得研究。其实,利用财产税资助地方政府劳务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与周期性的不动产市场密切相关。商业性不动产的价格呈现不规则的剧烈波动使得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也相应地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在经济减速或停滞时期,财产税带给地方政府的收入会下降,在经济扩张时期带给地方政府的收入可能会增加。如果现任政府官员缺乏责任感,决策短视,那么,地方政府收入就会缺乏长期的保证。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实行健全的财政管理和妥善合理的财政政策,创造真实的储备来应对经济周期的变化。建立一种顾问制度,减少评估工作量,以便更好地确定应税财产价值(确定一个保险价值),淡化经济周期的影响,保持地方政府收入的稳定性。
第三,一般而言,个人的房屋消费与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财产税能够较好地体现可支付能力原则。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当个人的房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周边环境的改善而增值的时候,个人的财产税纳税义务有可能与其纳税能力相背离。而房产价值的增值只有通过上市交易才能实现。在交易之前,让个人为这个尚未实现的价值承担纳税义务,是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的,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相违背。如何处理这一矛盾,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
第四,财产税在促进地方自治的同时,易于引起地方财政不公。富裕的地区因为财产多可以以较低的财产税率资助较多的公共劳务,结果可能导致地区之间公共支出不平等。在美国,表现在公立教育方面尤为明显。各地区通过财产税资助的公立教育不平等已经引起了许多官司和改革的呼吁。事实上,财政不公不是财产税才有的缺点,而是所有地方税共同存在的普遍缺陷。因此,当地方政府拥有财产税作为独立的自有收入来源之后,虽然减少了对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依赖,但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调整地区之间的财政不公。在中国改革和完善了财产税,赋予地方政府独立的自有收入来源之后,同样还需要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充当调节地方财政不公的收入平衡机制。
第五,地方政府官员控制有关财产税率的投票议程的能力也是令财产税不受欢迎的方面。在美国彻底的分税制下,各地方财产税率的高低由各地选民投票决定。这样,一方面,地方官员有无能力控制投票议程增加了地方公共劳务供应的风险,另一方面,地方官员操纵投票议程的能力又易于引起选民的强烈不满。当然这是美国特有的现象,可以说是美国地方民主政治的一个负面效应。在西方政治学界,美国的地方政府体制俗称为“碎片化的政府体制”(意思是指美国地方政府数量庞大、功能重叠、边界不清)。这种体制按照多元民主理论来讲有利于保障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来讲有利于表达公共经济领域中的消费者偏好,但其整体效率低下、无力及时应对社会问题,对整个区域经济和社会公正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当然中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税权下放不够。然而,在重构中国地方财政体制、呼吁中央向地方下放税权、促进中国基层政治体制转型的今天,美国特有的这一现象令人反思:过度的民主、过度的地方自治也同样存在遗憾和不足。因此,在中央向地方下放财权的问题上,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度”。健全相关的配套措施,特别是通过相关立法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确保地方适度的财政自治,方是长远之策。
注释:
①在地方一般收入中,地方销售税的使用略有增加。到1999年,地方一般销售税仍然只占地方一般收入的3.9%,选择性销售税占1.5%,所得税在地方一级微不足道,在各州一般收入中占1.3%。
②这种实证研究以“21/2方案”决定的财产税作为外生变量,测试了财产价值的最大化假说——任何约束政府提供公共劳务水平的法律都会降低社区的财产价值。结果发现,财产税增长相对较快的社区,其房产价值的增长也相对较快。这一结论意味着“21/2方案”将财产税约束在最优的水平之下(至少从个别社区来说是如此)。
[1]Philip G.Joyce,Daniel R.Mullins.The Changing Fiscal Structure of the State and Local Public Sec tor:The Impact of Tax and Expenditure Limitation[J].Public Adm inistration Review,1991,51(3):240—253.
[2]Daniel R.Mullins.Popular Proces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and LocalGovernment Finance[C]//David L.Sjoquist.State and Local Finance under Pressure.Northampt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Inc,2003:95—162.
[3]Joan M.Youngman.Property,Taxes,and the Future of Property Taxes[C]//David Brunori.The Future of State Taxation.Washington,DC: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1998:111—128.
[4]Kebin Lang,Tianlun Jian.Property Taxes and Property Values:Evidence from Proposition 21/2[J].Journalof Urban Econom ics,2004(55):439—457.
[5]Low ery,David.Public Opinion,Fical Illusion,and Tax Revolution:The Political Demise of the Property Tax[J].Public Budgeting&Finance,1985,5(3):76—78.
[6]Wallace E.Oates.Property Taxation and LocalGovernment Finance[M].Cambridge,Massachusetts: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