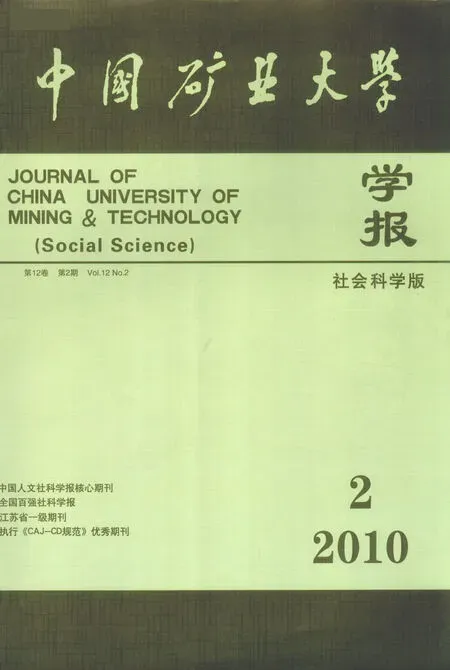刍议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进路
田海燕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江苏徐州 221008)
刍议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进路
田海燕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江苏徐州 221008)
共同体是人们彼此平等、相互关爱、和谐温馨的生活形态。我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形态包括传统的宗族共同体与村落共同体、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共同体,但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图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些共同体形态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公民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当前乡村自治的学理诉求与实践圭臬。公民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进路是通过重塑乡规民约与发展公民教育、培育乡村公民社会、发动村民积极参与自治实践来培育乡村公共精神。
乡村;公民共同体;公共精神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的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由于乡村是中国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最具稳定性的时空坐落,乡村共同体的现代性构建无疑凸显了其自身的重要性。当前乡村基于现代性基础上的共同体化是否可能,成为转型时期寻求乡村理想生活形态的当下追思。
一、共同体的历史蕴义与存在形态
乡村作为居住区域,是相对于城市社区而言的,在中文的语义学上指涉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们在一起生活的聚居区。英文的“community”在中文中有社区、社群、社团、共同体等不同译名,但共同体与其他译名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概念有着强烈的伦理意涵[2]。
1.西方语境中的共同体
19世纪末,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以社会联结纽带的不同为标准区分了“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两个概念。共同体由“本质的意志”所导致,是在自然情感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凸显其“自然而然”的特征。在与个体成员的关系上,共同体自居本位,个体通过信仰其默认的共同价值而融入其中。社会则由“选择的意志”所导致,是以外在利益为基础的,以契约、交换和计算为形式的社会联系方式。超越集体而居本位的个体出于工具性的理性选择而进入社会。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3]2。“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3]3
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历史语境由梯次递进的古典古代共同体、虚假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种发展形式所构成,分别指涉氏族制度特别是母系氏族、以父系氏族为入口的国家以及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氏族制度作为初民社会组织体,其伟大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4]158-159。国家是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作为社会的组织集合体而采取了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实施了统治”[5]。自由人联合体指涉“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6]294的联合体,它“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意义上的复活”[4]179。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是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6]119,它代表的是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即共产主义社会。
由此可见,西方语境中的“共同体”一词不仅仅指涉的是人们基于共同的主、客观特征而组成的生活集体、地域组织或利益集团,更强调的是一种好生活的理念,共同体是人们彼此平等、相互关爱、和谐温馨的生活形态,它所期待的是一种亲密无间、相互信任、守望相助、默认一致的人际关系,传达的是一种休戚与共、祸福相连的感觉与和谐、安全的意象。
2.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历史形态
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耕作区大多地处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造成了传统乡村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正是在这个条件下形成的。在传统乡村社会,血缘和地缘是典型的人际联结方式。血缘关系决定着人际的亲疏,维持着社会的稳定;“生于斯,死于斯”的地缘关系则固定着人和土地的亲和。家族共同体和村落共同体构成理解传统乡村社会生活模式的关键词,前者表现为家族内彼此帮扶,后者表现为村庄内荣辱与共,以血缘和地缘为依托的乡土底色构成传统农民精神发育的“心理场”。传统乡村社会的共同体,是以乡土为生活基础,以生命的协同、整体的亲和作为生活原理,宗族血缘关系以及村落地缘关系在农村生活中的农耕、治安防卫、祭祀信仰、娱乐、婚葬以及农民的意识道德中的共同规范等方面具有共同体意义上的相互依存关系[7],秦汉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控制的模式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8],县级以下的传统乡村在宗法领袖、地方士绅等非制度性精英的安排下,自主地决定本地的事务,运用宗法关系下的伦理道德和宗教压力等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传统乡村处于一种自治或半自治的状态。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族共同体、村落共同体与乡绅自治形成了华夏文化强烈的重德求善的伦理价值取向。
恩格斯认为“共同体”(Gemeinwesen)“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9]。公社(commune)一词最早是指中古欧洲自治城镇的组织。至近代,这一名词含义演变为由人民集合而成的组织,如法国巴黎公社、中国人民公社等。巴黎公社是1871年法国工人建立的第一个工人政权,它实现的是人民管理制自治,将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初步付诸实践。马克思主张把分布城乡的自治社区组织成为全国性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用以取代凌驾于社会之上、与社会相对立的国家政权赘瘤。后来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背离了巴黎公社初步实现的工人民主自治的优良传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严密控制下的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由国家统一管理。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了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依照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迅速在农村建立起了高度统一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是政社合一、一大二公,政治上表现出强烈的国家全能主义倾向,是以党政国家为轴心的趋中性的控制结构。国家的政权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靠着广泛的政治动员来统一社会意识和增强社会共识。“中国共产党把它的权威渗入了每一支稻穗。”[10]我国人民公社的现实违背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高度划一的行政共同体形态极度压缩了社会空间,乡村自治无从谈起。
二、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的背景与载体
当前中国广大乡村正在经历着传统细胞的裂变与新生。传统乡村民众小富即安,不假外求,乡土文化浸润出纯朴安分的小农性格。然而近年来农民的流动性空前高涨,城镇化速度和水平也大幅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推算,截至2009年底,农村实质性常住居民约5.63亿①目前全国总人口已达到13.37亿(资料来源:中国人口信息网2010-4-27),至2009年底,按统计口径算,我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了6.22亿人(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已经达到了1.52亿人(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如此推算,2009年底农村常住居民数量约为5.63亿。,占全国人口的42%,农民正在走向其身份的历史性终结,农民的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依赖非农收入。农村居民向大城市和周边城镇的大规模流动说明乡土中国的“离土时代”[11]已经到来。经济发展模式型塑着乡村的社会结构,与外出打工潮相伴生的是农民人际关系结构的改变,业缘在血缘和地缘的母体中呈滚雪球样迅速孕育并逐步脱胎出去,培养了村民与陌生人之间的理性、宽容、合作的精神,也疏散了乡村传统结构,导致传统熟人社会开始陌生化和疏离化。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图式的嬗变,农民在社会生活行为选择中越来越凸显个体工具理性,而传统的村落共同体和家族共同体的作用又持续弱化,农民的精神皈依陷入迷茫和矛盾状态。
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千年变局”之中,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后的必然趋势,土地规模化集约经营和大机械化的普及大大减少了农业所需的劳动力,这其中必然包含大量农民向现代市民的转化过程。农民在向市民的转化过程中面临精神层面的重塑,既考验着传统乡村“文化网络”的张力,也呼唤着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特质。对于村民自身而言,他们接受着市场经济对于乡土观念的改变,主动向市民转化。但是即使已经进入城市的“昨天的农民”也并非完全脱胎而成市民,只不过刚刚成为小市民。小市民意识是升华了的农业意识,又是不成熟的工业意识。现代性背景下的村民必须自觉开始其人格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在面向未来的国家治道变革中,村民自治是中国城市化尚未完成时的一种暂时性和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其目的在于提高乡村公民的自治能力,化育乡村公民的民主意识和自治精神。具有了公民性的乡村居民,不仅能更好地实施乡村自治,在城市化完成后,也能够具备未来城市社区自治的能力和品德,村民自治构成了现阶段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的平台,这正是村民自治对于国家发展的长远意义。
乡村自治意味着农民共同治理本村的事务,提供力所能及的村庄共享物品,提升村民的福祉。但是诚如马克思所言,农民如袋中的马铃薯般具有分散性,而农民个体无法完成村庄公共产品的提供,必须借助于共同体的力量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治。乡村人们对共同体的希求,基于传统的“路径依赖”,首先便体现在对家庭和亲族的依赖上,目前亲族以低廉的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乡村社会组织化的积极作用。但是长远来看,其封建残余、人情关系也蚕食着民主观念与行为方式。而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共同体是高度集权的产物,并非乡村社会的原生组织形态,且随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对于乡村社会的型塑和农民的民主自治意识的觉醒,这种高度行政化的共同体早已寿终正寝。因此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去家族化与去行政化,以农民组织为表现形式的乡村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成为必然。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也就是以血缘、地缘为联结的传统共同体向公民共同体的转化过程。较之乡村历史上共同体形态,乡村公民共同体由于其具备更为广泛的公共性、开放性、参与性和包容性的品性而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能够为村民自治制度的成长提供优质的民主土壤与丰富的社会资源。但市场经济和乡村业缘关系的发展和农民非农化程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共同体本身的消逝,“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12]的农民不能丢弃共同体守望相助的伦理特质。只有不断增进乡村伦理与自治文化在乡村社会成员内心植根的深度,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乡村实质性的自治,并藉此为乡村公民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一种可能图景。
三、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进路:公共精神培育
现阶段乡村社会夹生的民主文化所衍生出的行为规范与正式规则无法形成良好的互动方式,乡村所缺少的这种共同体构建的文化凝固剂正是与现代民主自治相伴生的公共精神。乡土社会人们彼此互助、相互认同和归属的意识正是那扇通往共同体安宁、温馨家园的大门,而理性、宽容、合作的公共精神则为共同体在现代性基础上的复活提供了条件。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既要批判借鉴西方在民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公民意识与普世价值,又要始终以本土关怀为圭臬,彰显中国乡村共同体意识的母体文化内涵,以通达权变的方式得出公共精神的内涵与创设化育路径。
1.重塑乡规民约与发展公民教育
公民的美德和善行并非天生或自发产生的,而是通过教育和社会化获得的。重塑乡规民约和乡村公民教育弥补了乡村社会普遍秩序的不足,有助于形成村民共同治理的价值观念和道德风貌,培育共同理想与信仰,发挥公共精神的凝聚作用作为村民自治的精神动力和支柱。而外在的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也只有与村民内心的道德准则结合起来,二者互为促进才是公共精神培育的现实进路。
乡村应多管齐下重塑乡村公民人格,带动和培育公共精神。首先,回归深嵌于华夏文明的文化之根,化育集体生存伦理。充分发掘传统乡村伦理积淀的历史粘合力和文化归属内聚力,倡导“死丧相恤,祸福相比,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13]的共同体生活方式,村民无论强弱贫富,都有义务维持共同体的生存,都有权利享受共同体的庇护,从而形成村民自发遵守的集体伦理和村社话语。其次,大力提倡文明科学的乡规民约和淳朴善良的传统民风民俗。制定规范邻里关系、公共卫生、婚丧嫁娶、建房标准、综治联防等民生细则,作为树立良好村风、调解群众纠纷的公共准绳,形成一种具有集体性与持久性的行为约束机制。再次,发展现代性公民教育。借助村民自治宣传栏、村广播站、地方电视台等贴近农民的媒介,并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知识优势,对村民进行民主自治理念宣传教育,培养村民的公民品质,促进农民思想与个性的完善。最后,建立公众道德引导培育机制。注重吸收改革开放30余年来精神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提倡村民参与、公益服务、集体主义等,宣传村民自治政策法规,宣传选举、参与、监督程序与方式,将民主自治的行为方式内化为公共知识而为农民所共享,引导村民通过村民组织参与到村民自治的过程当中来。
2.培育乡村公民社会
当前农村出现了具有公民性的组织,如专业合作协会、“村民集资协会”等经济合作组织,“老年人协会”、“妇女禁赌协会”、“红白喜事理事会”等社会服务组织,“民主理财小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等民主监督组织。这些组织在经济互助、公共服务、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公共事务参与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初步具备了公民社会的特征。这些组织创造了村里新的公共空间,以及较为完备的村民参与渠道、参与程序,村民能够在各自利益的基础上有组织地进行沟通与协调,培养公共利益意识,并通过有约束力的章程来解决公共事务,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
在乡村公民社会的引导和培育上,基层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第一,制定政策引导和保护乡村公民社会。基层乡(镇)政府作为公正化身的道德意涵不可褪色,应充分意识到公民社会对村民自治发挥的正向作用,制定相应政策引导村民自发组织和参与乡村公民社会。只有正确界定和扶持乡村公民社会,政府才能通过强大的约束和保护力量确立农民的现代性公民地位;而政府对自身权力的扩张亦有赖于同公民共同体建立新型治理关系。第二,充分辨识村民团体的性质。从全国范围来看,现有村民团体鱼龙混杂,有些借助家族势力发展起来,有些则带有帮会的性质。基层政府在制度设计时既要考虑到乡村社会对稳定安全与民主自治的现实需要,又要考虑到乡村反向制约力量的存在,防止其中出现对抗政府和国家的因素,警惕家族封建残余和帮会势力篡改公共精神教育与实践的导向。第三,引导乡村公民社会自觉关注能力建设,鼓励其有意识地学习行动策略,通过多种方式建立合作、分享经验、扩大影响。
3.发动村民积极参与自治实践
“真正的知识,主要来自经验。”[14]村民自治实践不仅具有民主教育和美德培养的功能,更是知识的运用和内化的过程。共同体的平等意涵要求赋予乡村公民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实践将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还原为现实生活,不断促进公共精神要素的使用,使其自我增殖,道德资源在使用的同时不断自动增加供给。在公共事务的参与、公共空间的交流与公共产品的享用过程中,村民们逐渐学习到自相为谋、自相监督,人们的精神和性格中也培养起了将共同善当作首要善的品质。
促进村民参与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畅通村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利用公民社会建立社情民意收集的分片包户制度,畅通村民了解政策、反映诉求的渠道。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基层政府与村民共同体可协调分工积极解决,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和共同利益;不能解决的也应给予解释说明,理顺群众情绪。二是拓宽民主监督途径。一方面,在继续发挥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民主理财小组作用的同时,其他乡村公民组织也须对于村务公开的内容、质量、时间予以监督,充分发挥村民在民主监督方面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公民社会须强化对基层干部勤廉双述、村民询问质询和民主评议等制度落实工作的民主监督,保障村民的正当权益。三是充分发挥村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无论是村党组织和村委会,还是乡村公民共同体,都要充分尊重村民的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通过提供良好的服务,调动村民共同参与村民大会、技术培训、乡间娱乐等有益的乡村集体活动,使村民彼此间成为共享经验、感情和价值的共同体,建立普遍性的公共交往伦理,在参与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既是公共服务的享有者,也是维持公共服务秩序和乡村治理的主体,进而在村民中间形成普遍的公共责任意识。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6429094.html(2007 -10-24).
[2] 池忠军,刘立柱.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视域中的社会建设[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2).
[3]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池忠军.社会生活共同体建构的德性之维[J].道德与文明,2008(6).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项继权.中国农村社区及共同体的转型与重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
[8] 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M]//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3.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5.
[10]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622-628.
[11] 孙庆忠.离土中国与乡土文化的处境[J].江海学刊,2009(4).
[12] (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
[13] 管仲.管子·小匡[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144.
[14]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89.
Rural Citize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IAN Hai-yan
(School of Literature,Law and Politics,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Technology,Xuzhou 221008,China)
Community is a way of lifestyle in which residents care for each other and live in a harmonious way.The historical forms of China’s rural society included traditional clan community,village community,and administrative community in the period of people’s communes.But with the rural value system and social relations schema evolving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times,these patterns no longer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imes.Now citizen community building has become academic aspiration and practical criterion for village self-government.The practical method for citizen community is to cultivate public spirit by remodeling local rules and developing civic education,fostering rural civil society and arousing villager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village self-government.
village;citizen community;public spirit
D669
:A
:1009-105X(2010)02-0040-05
2010-04-28
田海燕(1985-),女,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