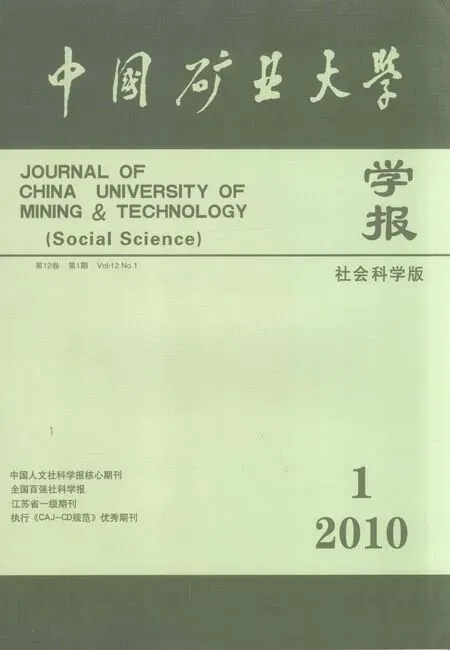语言与生存——梅洛-庞蒂的语言和他人问题
张 中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语言与生存
——梅洛-庞蒂的语言和他人问题
张 中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以知觉为起点,梅洛-庞蒂将现象学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同时也使现象学具有了新的视野。而在梅洛-庞蒂后期哲学中,他十分关注语言和他人问题。他认为,借助于语言,我们才能真正切近他人、理解他人。而更为关键的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自我与他人才能真正走向融通、共存与共生。可以说,在梅洛-庞蒂看来,自我与他人是在语言与身体中介下的一种“含混”、“互逆性”的“共谋”的实存。
语言;他人;交织;互逆性;共生;现象学
法国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M 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是从“知觉”开始他的现象学研究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知觉”是他现象学的起点。而且,在他的早期研究中,梅洛-庞蒂由知觉出发,开始注重于长期被压制的“身体”的现象学研究。他的意图和思路是:通过知觉、身体的研究,反思或打破意识哲学的羁绊和困扰。虽然早期的梅洛-庞蒂及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瓦解意识哲学的作用,但事实上,他自己也很快就发现,这些并不能真正解决胡塞尔以来现象学的“唯我论”问题;也不能真正推翻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身/心(主/客)二分。
于是,梅洛-庞蒂在他其后的研究中,开始转向为关注语言问题和他人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也逐渐成为当代法国哲学、乃至欧陆哲学研究的“重点所在”。因此可以说,梅洛-庞蒂的哲学不仅给予现象学以新的眼光和新的视野;同时也给予法国哲学以新鲜的原动力;甚至给20世纪后期的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活力——包括后现代哲学。
当然,梅洛-庞蒂的后期哲学主要是从关注语言问题开始的。
一、语言的“交织”
1.语言与意义
后期的梅洛-庞蒂认识到自己从知觉与身体出发所做的驱除意识哲学的种种努力,以及对于“身体间性”、“世界之肉”的弘扬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目的。所以,他逐渐开始关注语言和文化问题。这主要是因为,“知觉的首要对象是世界,是被知觉的世界,因此依然涉及到人与世界的关系。而正是在这里,出现了意义的表达问题。”[1]241这就是说,梅洛-庞蒂希望通过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的研究,从而拓展对于身体问题研究的局限,最终能够进一步理解自我、他人的行为与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早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就十分关注语言问题。他还专门写下“作为表达和言语的身体”一章,用意在于谈身体、表达问题。不过在那时,梅洛-庞蒂的主要兴趣和学术视野还停留在对于“身体”的迷恋和考察中。“语言”作为真正的思考主题,在他的中后期的哲学中。
当然,对于语言的解释历来层出不穷。但一般而言,人们仅仅是将它看作为透明的、表象式的工具。“语言是表象观念的工具,进而言之,就像在早期现代哲学中,语言本身仍然表现为观念化形态。”[2]49胡塞尔(Husserl)就是持这样的观点。当然,后期的胡塞尔已经认识到这种局限,并开始将语言与生活世界联系起来,从而“使语言与生存联系起来,导致语言问题的研究从逻辑学转向生存论。”[2]49也就是说,在《逻辑研究》时期的胡塞尔那里,他还是强调一种理想化的语言,强调一种静态语言,而不是语用学 。而这种看法显然是与现实不符的,也是不可能真正解释语言与存在问题的。
而在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哲学中,语言并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意识、思想被看作本质性的,而语言却仅仅被看作是工具性的、透明的东西 。但是,“语言”在梅洛-庞蒂看来,并非仅仅只是工具,它涉及到人的意义和生存问题。而且,梅洛-庞蒂从儿童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以及索绪尔那里寻求到了资源支持。他最终认识到:语言是一种约定性的文化产物;语言是一种超越性的东西;语言意义的产生和实现关系到自我与他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不过,对于他自己的这种颠覆性思想,梅洛-庞蒂依然是持一种一以贯之的谦虚与含混的态度:“语言既不是事物也不是精神,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其地位有待于去发现。”[1]259事实上,他已然发现。
所以,对于梅洛-庞蒂而言,语言是一种不透明的,其意义要在不断地、多次的“配置(disposition)”中来显现。他认为:“有语言的不透明性:语言不断地让位于纯粹的意义,语言仅受到语言本身的限制,意义只有嵌入词语中,才显现在语言中。”[3]50而且,他还在《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索邦1949-1952课程》的某处说过:“思想寓于语言之中,它是思想的身体。”[1]259
从强调身体的作用,到强调语言的作用,看似梅洛-庞蒂要超越以前思想。但事实上,梅洛-庞蒂的语言和身体最终却是紧密相连的——它们都与所谓的“肉”、“世界之肉”相连。也就是说,在梅洛-庞蒂看来,语言之“肉”和身体之“肉”是同质的。而借助于语言之“肉”,他也就可以克服和瓦解理智主义语言观。他因此而认为:“事物的侵越性与潜在性并没有进入到它们的定义中,表达的不过是我与它们当中的一个,即我的身体的不可思议的相互关联。”[4]57可以说,梅洛-庞蒂的语言观也是一种含混而互逆的语言观。在他看来,“在某种意义上,就像瓦雷里说的那样,语言就是一切,因为它不是任何个人的声音,因为它是事物的声音本身,是水波的声音,是树林的声音。”[5]192这样,他实际上就将语言的视野扩大到了更广阔的空间之中了。梅洛-庞蒂坚持认为:“只有当只想思想的聚合性的言语具有足够数量、且足够雄辩以便没有歧义地指向我,作者或其他人指示思想,以便我们拥有思想物化地呈现在言语中的整个经验时,我们才说一种思想得到了表达。”[6]所以,语言既是一种表达,又是一种互逆性的不透明空间。它牵涉到言语及其运用;牵涉到自我、他人和世界的存在。
2.语言与存在
梅洛-庞蒂是这样来看待语言和人的关系的:“并非人在说话,或者并非人拥有语言,而是语言在人身上说话。”而“人在说话之前应该重新让自己被存在所要求。”[1]319这就可以说,语言、人、存在都是独立的、本己的、主体性的。而在这样的状况下,“存在、语言、人三者形成这样的关系:存在的本质特征为了我们的生活而被语言所守护。”[1]319
此外,梅洛-庞蒂曾经指出:“对于语言学家来说,语言是一个观念的系统,是理智世界的一个片段。”[5]190这就是说,对于语言学家来说,语言仅仅是工具性的、透明的——它和存在无关。但事实是如此吗?显然不是。至少,“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解释世界的语言使事物在世界中相遇。”[7]也就是说,语言是我们解释和理解世界的窗口或裂隙。通过语言,我们才能看到本己的力量和自我的智识;能真正穿越自我与他人的界限,到达真正的理解与共识 。梅洛-庞蒂还说:“每一个词语本身并没有什么涵义,它们只是彼此被装在一起时才获取涵义。在这些集合体中,一种犹豫会产生出来,这时,需要由主体把词语带回,互相寻找。主体就将是这一犹豫或这一发明。”[8]178因此,也可以说,在语言或言语事件中,自我或主体就会生成——“他我(alter ego/other self)”也会在此生成。但问题是,人及其存在却是一个文化事件——他需要运用语言,却又需要穿越语言。这实在是一个吊诡的问题!不过,梅洛-庞蒂依然坚信:语言问题就是表达问题——它与身体、肉身化主体密切相关。并且,语言就源自于知觉及其处境的变迁。
至于语言的本质,梅洛-庞蒂说:“语言的本质就在于,其构造的逻辑从来都不属于那些被置于概念之中的逻辑,而真理的本质在于,它从来都不会被占有,它唯有透过某一表达系统(这一表达系统带着另一过去的印迹和另一未来的胚芽)被搞混的逻辑才是透明的。”[9]39这就意味着,语言在他看来就是灵性化的和肉身化的、可见与不可见的;而并非是理智的、固定的、静止不变的。由此可见,梅洛-庞蒂依然还是坚持他的原有看法,即:语言是一种含混的、互逆性的言语运用,它的处境就是生存本身的境域。所以他说:“我在言语的运用中学习理解。”[3]119
梅洛-庞蒂还告诉我们:“语言涉及我们,迂回地通达我们,吸引我们,牵引我们,将我们转变成他者、将他者转变成我们”[9]164。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语言不仅能够连接意义与无意义、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还能连接自我与非我;也能够将我们牵引至共同的理解和存在。而伽达默尔(Gadamer)也曾经说过:“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10]
后期海德格尔(M artin Heidegger)曾经为语言所蛊惑,他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同时他还着迷于斯蒂芬·格奥尔格的一句话:“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11]151很显然,梅洛-庞蒂也受到了海德格尔这一思想的影响。所以,他说:“完整表达的概念是无意义的,任何语言都是间接的或暗示的,也可以说是沉默。”[3]51但这种沉默却是一种饱含期待和趋向的“沉默”。即是说,语言作为中介和迂回策略,始终将自我与他人、世界牵涉和关联,它与这些共处一种“共谋”的关系之中。
二、与他人共在
1.他人与自我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je pense,je suis)。”——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他人”。然而,“在20世纪欧洲大陆哲学中,胡塞尔最先遇到他人问题这一难题,并因此引发了现象学传统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关注。”[1]335但胡塞尔基于先验主体的意识现象学不可能解决这一难题,所以胡塞尔后期就提出了“主体间性”的思想以期解决这一问题。但这也显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多是转移了话题而已。因为胡塞尔的“意向性(itentionality)”观念是不可能避免“唯我论”的——即使他使用了“移情(empathy)”这一途径。可以这样说,在胡塞尔的现象学里,“他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地位的。有鉴于此,梅洛-庞蒂基于“知觉”提出了“身体间性”的观念——既是要对抗意识的主体地位,也是要重塑他人及其位置。
当然,海德格尔和萨特都关注过他人问题。但对海德格尔来说,他人与自我是共处于同一世界的。“此在”的在世需要通过用具的“上手”来体会,“他人不是现成的对象,相反,对象于他人、于我都是上手的或者在手的。”[1]338这就是说,在海德格尔那里,他人在“我”的视域里、视野下,也正是在此,我能真正知觉到他人及其存在。但这样的解释很显然也会陷入到“唯我论”。而海德格尔后来又认为,此在的存在是与他人的“共在”,但这也还是要回到此在的主体境域中去。而至于萨特,联想起他的一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就可以知道他对于他人的看法。当然,这句话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理性解释。如果公允地对待萨特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萨特没有、也不能真正走出“自我中心论”。因为萨特是基于人的生存和历史的考察才提出他人问题的,所以萨特的“他人”就会陷入到“为我”或“为他”的“自为”与“自在”的二元对立之中。同时,他也并不能够解释他人的“意识”与我的“意识”的关切问题。当然,这些都是意识哲学范围内不可克服的矛盾。
而梅洛-庞蒂的“身体间性”当然也并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问题。所以,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就提出了所谓的“世界之肉”的观念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不过,似乎最终也不能令人信服。而这之后,梅洛-庞蒂主要将语言引入自己的哲学中,甚至提出了所谓“文化间性”的概念。他说过:“真理不仅‘寓于内在的人’,更确切地说,没有内在的人,人在世界上存在,人只有在世界中才能认识自己。”[12]6这就是要将每个人放置到世界之中,通过不断地重新“配置”,从而才可以达到与他人的“共谋”和理解融通。
显然,梅洛-庞蒂十分看重“身体”的中介作用,他说:“每个人都在身体中包含他人,得到其他人的证实。”[3]225而且,他还强调:“人是这样一种存在,对他来说,在他的存在中,关系到他的存在本身,他就必须要抓住他的存在。……因此,他的存在与需领会的存在,几乎是同一种存在。”[8]23这就意味着人的存在作为一种本己的责任和权力,他需要通过知觉和身体来实现。而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却说:“他者就是将来。与他者的关系就是与将来的关系。”[13]不过,列维纳斯的所谓“他者”却是一种“绝对的他者”、“伦理的他者”。而在其中是没有“我”的,或者说,“我”是需要“隐匿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我何在?可是,梅洛-庞蒂却转移了视线,他说:“理解为什么我(Je)能思考他人(Autrui)是没有困难的,因为我,因而也是他人,不介入现象的结构中,与其说我和他人存在,还不如说我和他人有价值。”[12]7他说的是,我可以理解他人,他人与我是同质的——我即他人,他人即我。而且,梅洛-庞蒂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与他人是平等的、共存的、共生的、有价值的。
当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曾经把“他者(the Other)”分为两类,即“个体的他者(the personal other)”和“非个体的他者(the impersonal other)”。并且,他认为像“死亡”和“上帝”就属于后者。有论者认为后者也可叫做“他性(O therness)”[14]。而列维纳斯这样的“绝对他者”固然是重要的,但问题并没有被消解——“我”在哪里?“我”真的能够“退隐”吗?或者依然还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况且列维纳斯的“他者”更是一个伦理的概念,而和其他人的“他人”概念尚有些不同。不过,梅洛-庞蒂却对理解他人的信心很充足。他坚定地说道:“在使他人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不可接近的而且是不可见的时,我就确保了他的异己性,我就脱离了唯我论。”[5]101但是,“他者是我所陌生的,他者对我无动于衷,却又凝视着我,他者的他性关涉到我。我与他人的关系不是认识的关系,我不能将他者归结为纯粹的认识对象。”[15]这就是说,自我与他人依然还是个两难问题——只是在梅洛-庞蒂那里得到了缓解;而在列维纳斯那里却是彻底决裂了。
2.共在与共生
海德格尔曾经认为,此在与他人是共在的——但他没有驱除“唯我论”的倾向。而梅洛-庞蒂却认为:“之所以我能‘通过’身体本身理解他人的身体和存在,之所以我的‘意识’和我的‘身体’的共在延伸至他人和我的共在,是因为‘我能’和‘另一个人存在’从此以后属于同一个世界,是因为身体本身是他人的先兆,移情作用,我的具体化的回声,是因为感官的启动在起源的绝对呈现中使之成为可替代的。”[3]218这就是说,在他看来,通过知觉与身体,我可以感知他人,他人也可以感知我——没有所谓的“主体”;我与他人的关系是“交织”的、“互逆性”的。而“他人和我是通过主体向世界和世界向主体的生存投射而从存在的开放中诞生出来的。从第一次知觉开始,我已经在自身中带有了世界和他人。”[16]
当然,在这里就必然会涉及到一个问题——自由问题。萨特是强调绝对自由的。但梅洛-庞蒂却反对这种绝对的自由观,他说:“自由无所不在,也可以说,无所在。”[12]546这就是说,梅洛-庞蒂认为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观念。“自由总是有条件的有限的自由。与我们的知觉场和时间场一样,自由也有一个‘自由场’。”[17]而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很显然自我与他人的共在需要相互“配置”和调适。也就是说,自我与他人都不能因己而损害他人。但问题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一个文化世界里,“我”的活动必然会带有目的性和利益性,必然会损害到另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力。因此,梅洛-庞蒂认为需要身体作为中介,从而配置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达到理想的状态。他因此说:“自然的‘事物’,机体,他人的行为,我的行为只是由于它们的意义才存在,但显示在他们那里的意义并非还是一种康德式对象,构造它们的那种意向性生活并非还是一种表象,通达它们的那种‘理解’并非还是一种理智活动。”[18]325那它们到底是什么?不言而喻,在梅洛-庞蒂看来是一种“知觉”的结构行为——即现象学的重构。那这就是说,自我与他人也就会在这种知觉及其重构中走向共在和共生。自我与他人的现实在场与否都不重要,因为至少海德格尔说过:“然则在场同时也遮蔽自身,所以在场本身即不在场。”[19]
所以,往往现实的、苦难的切近就会时刻提醒着那些活着的人们:“我们注定是有意义的”,“我们注定总要表达某种东西。”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死亡时,“死亡把一种无法抵抗的率直赋予邻人的面容。”[20]——这就是自我与他人的最直接遭遇和最强烈融合。这也就是说依照梅洛-庞蒂的看法,在日常世界里,我们借助于自己的语言、身体、知觉,我们将会很容易将自己与他人拉近,或者说“逼近”他人,但并不能够真正成为“他人”。如现象学所说的“移情”,并以此创造出一个“他我”,似乎并不是那么可信和可理解。所以,唯有借助于知觉身体的中介和迂回,将自我与他人重新构造、配置在一个合理的位置,让他们达到共存、共生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而这也是梅洛-庞蒂一直渴望看到的和努力寻求的理想状态。伽达默尔曾说过:“只有通过他者,我们才能获得有关我们自己的真正知识。”[21]这就意味着自我需要他人的印证和支持。反之,他人也需要“我”的凝视和确证。惟其如此,方有共存与共生。
梅洛-庞蒂同时还说:“我的身体可以包含某些取自于他人身体的部分,就像我的物质(substance)进入到他们身体中一样,人是人的镜子。”[4]48这是一种理想的视野和心态。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我”能够理解“他人”;能够想象他人。但这种镜像式的理解是否能够真正达到,或者说有多少把握达到,却是一个未知数。不过对此梅洛-庞蒂依然很有信心:“至于镜子,它是具有普遍魔力的工具,它把事物变成景象(spectacle),把景象变成事物,把自我变成他人,把他人变成自我。”[4]48这里的“镜子”当然是具有“自反性”的隐喻,但自我与他人并非镜子关系那么简单,所以梅洛-庞蒂的这种愿望仅仅是一种理想而已。不过,借助于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梅洛-庞蒂依然醉心于知觉与身体的中介、反思、迂回。甚至可以说,在梅洛-庞蒂看来,知觉永远是首要的。唯有借助于此,方可形成此后的连续互动和互逆反馈;也才能达致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共存、融合与共生。
也就是说,在梅洛-庞蒂的哲学中,“语言”、“身体”将作为中介,从而联系自我与他人、世界的关系,并最终做到共在、共融与共生,而这一切均源自于知觉。所以我想,梅洛-庞蒂最终就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通过知觉来理解使我们认识到各种实存的活动,我们刚才触及到的所有问题都将归结为知觉问题。”[18]324
[1] 杨大春.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 杨大春.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3]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眼与心[M].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M].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6]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哲学赞词[M].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3.
[7]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88.
[8] (法)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M].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9]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世界的散文[M].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0] 洪汉鼎.理解的真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276.
[11]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51.
[12]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3] (法)Emmanuel Levinas.Time and the Other(and additional essays)[M].trans.Richard A.Cohen, Pittsburgh, Pennsylvania: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87:64-77.
[14] 吕炳强.现象学在社会学里的百年沧桑[J].社会学研究.2008(1):31.
[15] 莫伟民.莱维纳斯的主体伦理学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6(6):10.
[16] 佘碧平.体验、表达和他人:论梅洛-庞蒂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读解[J].云南大学学报,2007(6):24.
[17] 张尧均.在内在性与超越性之间——梅洛-庞蒂的肉身时间观[J].厦门大学学报,2004(1):114.
[18]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M].杨大春,张尧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9] (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83.
[20] (法)E·列维纳斯.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J]朱刚,译.世界哲学,2008(1):98.
[21] (德)Hans-Georg Gadamer:The Problem of Histo rical Consciousness[M]//In Paul Rainbow and W.Sullivan(eds.).Interp retive Social Science:A Reader.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 rnia Press, 1979:107.
Language and Existence:Merleau-Ponty’s Language and Others
ZHANG Zho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Starting f rom percep tion,Merleau-ponty led phenomenology to a new field,and endowed it w ith a new vision.M erleau-Ponty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p roblem s of language and others in his philosophy in the late period.He thought that we could app roach and understand others by language. W hat is impo rtant is that in this w ay one and others can coexist and integrate w ith each o ther.In Merleau-Ponty’s opinion,oneself and others are the“mixed”,“interconvertible”and“conspiratorial”entities by the medium of language and body.
language;others;interlacement;interconvertibility;coexistence;phenomenology
B565.59
A
1009-105X(2010)01-0028-05
2010-01-09
张中(1973-),男,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