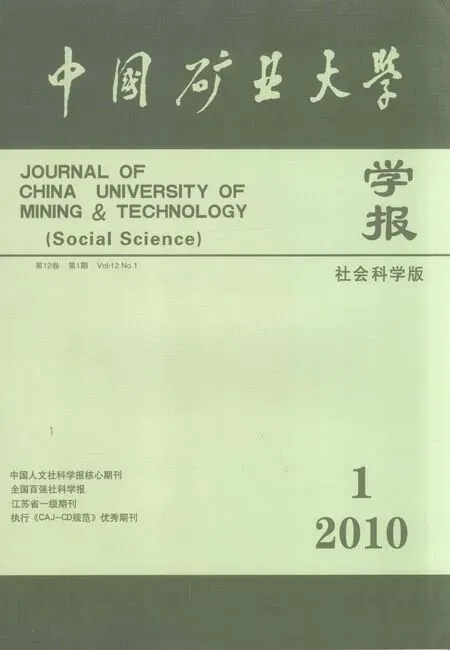彰显生命的本真
——对庄子“吾丧我”生命哲学的解读
张 淼
(曲阜师范大学哲学系,山东日照 276826)
彰显生命的本真
——对庄子“吾丧我”生命哲学的解读
张 淼
(曲阜师范大学哲学系,山东日照 276826)
“吾”与“我”是先秦文献中重要的第一人称代词,但是二者在不同语境中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庄子“吾丧我”中的“吾”、“我”便具有各自的含义,“吾”为本真之我,“我”为遮蔽本真的现象之我。由于“我”存在有诸多的困境而导致“吾”不能获得自由和显现,因此,庄子通过“坐忘”、“心斋”的修行方法来彰显“吾”的存在,实现人的生命境界的提升。
“吾丧我”;困境;生命;境界
庄子生命哲学思想是我国先秦诸子思想中最为独特的一种,他继承了老子对人生命的终极关怀的思考方式,不断地追问个体人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如何实现个体生命的超越。他在深刻洞察人生、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诸种弊端之后,通过冷峻的哲学思考为人的生命价值作了回答,“庄子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即生命的问题。和一般的哲人把政治秩序作为其思考的中心不同,庄子思考的主要是生命在乱世中的安顿。”[1]29正是由于庄子注重个体生命,注重解放个体生命,注重实现人的生命价值的超越,所以,他的生命哲学始终受到世人的关注,而在“吾丧我”的表述中集中体现了庄子的这一生命哲学主题。
一、“吾”与“我”
在先秦诸子中,诸如《老子》、《论语》、《孟子》以及《庄子》等著作中,“吾”和“我”在一般情况下在指代对象及其意义上基本没有很明显的区别,二者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互换和交替使用。例如《老子》第四章中有:“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2]90该句中的“吾”就是指第一人称代词“我”。又如《论语·季氏》有:“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3]172其中的“吾”即可换作“我”,表示第一人称代词。又如《庄子·养生主》中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4]113该句中“吾”就是指自己,意义上等同于“我”。当然,这并不是说二者完全等同,在某些情况下,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这需要我们在阅读文本时认真辨别和注意。例如,在《论语》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吾”既可以表示第一人称单数的“我”,也可以表示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但是,某些时候,“我”有特殊意义,在“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3]87句子中,“我”在这里就不再是解释为第一人称代词的“我”,而是指“自以为是”的意思。又如在《庄子·齐物论》的开篇中有一句“吾丧我”,同时出现了“吾”与“我”两个词,但是二者之间有着明显不同之处。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不同及其所表示的真实含义,我们将这段话引录如下: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关于这段文中的“吾丧我”三字,历来有着不同的注释和解读,对这三个字的不同解释也就形成了对“吾”与“我”所指代的不同意义的诠释。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下几种。晋人郭象对此注释道:“吾丧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识哉!故都忘外内,然后超然俱得。”[5]45而唐人成玄英在其注疏中也指出:“丧,犹忘也。……而子綦境智两忘,物我双绝,子游不悟。”[5]45元赵德《四书笺义》中认为:“‘吾’‘我’二字,学者多以为一义,殊不知就己而言则曰‘吾’,因人而言则曰‘我’。吾有知乎哉,就己而言也,有鄙夫问于我,因人之问而言也。”[4]35今人陈鼓应则认为:“吾丧我:摒弃成见。‘丧我’的‘我’指偏执的我。‘吾’指真我。”[4]35
从这些不同时代人的注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吾丧我”三个字的意义,在郭象的注释中,尽管没有明确地指出“吾”、“我”究竟指代什么,或者是包含了何种具体的含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吾丧我”实际上是指个体生命对于自身或肉身的暂时遗忘。在成玄英的注疏中,他对于“吾丧我”的解释在沿袭郭象解释意义的同时,又有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丧我”即为忘我,是对“物我”、“形我”或者是外在之“我”的遗忘,不仅包括肉身,还包括精神乃至有精神所产生的某种境界,是一种“境智两忘”的状态。这已经触及到了庄子人生哲学的修养功夫。但是,成玄英也没有明确地解释“吾”、“我”的意义所指。赵德已经意识到“吾”、“我”有不同之处,但他也只是从指代对象的主客体角度作了区分,并没有指出二字各代表的真实意义。今人陈鼓应则明确地指出了“吾”是指真我,“我”是指偏执的我,但是,这种解释也令人感到很模糊,究竟“真我”和“偏执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
其实,在有关庄子的文献中,尤其是“吾丧我”这一句话中,“吾”、“我”在义理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二者分别具有某种特定的含义。因此,我们辨别“吾”、“我”的不同意义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理解“吾丧我”乃至庄子生命哲学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何准确把握这两个字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联系与之相关的“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意义来理解较为恰当,只有将这两句话联系起来理解才能够从根本上准确把握“吾”、“我”的真实意义。关于“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相关文献在《庄子》一书中共出现了四处,兹分别摘抄如下:
“南伯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颜成子入见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尝居山穴之中矣。当是时也,田禾一睹我,而齐国之众三贺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卖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恶得而知之?若我而不卖之,彼恶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4]745
“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4]622-623
“吾固告汝曰:‘能儿子乎?’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4]693
“啮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言未卒,啮缺睡寐。被衣大说,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4]653
在这四段相关的引文中,唯有第一段《徐无鬼》中的文句与《齐物论》的文句在很大程度上有相似之处,都是南郭子綦与颜成子游之间的对话,文中所蕴含的意义也基本相似。从总体上来看,在这四段中,无论是“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形体掘若槁木”、“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还是“形若槁骸,心若死灰”都表现了同一个思想内容,即修行者在修行中出现的一种生理和心理状态。从直观外形上看,在面貌神情和形体特征都呈现出一副枯木状;而从内心体验上看,则呈现出心如死灰状。这种状态庄子借用老子的口吻说是“游心于物之初”,也就是修行的最初阶段,而这也正如婴儿自然淳朴的状态一样,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都在无意识、本真的情况下自然流露,是“吾丧我”的真实境界。
对理解“吾丧我”有重要帮助的还有另外一句,即“丧其耦”。在《齐物论》中,庄子提到了子綦的“丧其耦”状态,所谓的“丧其耦”,是指“失其匹配。”[5]43从具体所指上来看,是指夫妻二人之间失去一方,即失去其“配偶”,由其引伸出的含义则是指失去了与主体所匹配的对象,在南郭子綦的这段话中,其意义与他回答的“吾丧我”的意义有相似之处,是在“丧失”之后出现的一种状态,也就是“无己”。
从上面这些引文及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吾”、“我”是人的两个不同层面上的内容表述,是人的生命存在中的两种不同状态,“吾”是内在的、无形的、本真意义上的人的存在,是人的生命的本真显现,属于主体地位。老子所讲的“婴儿”、“赤子”状态也正是庄子所谓“吾”的本真体现。“我”则是外在的、有形的束缚人性的存在,它是人的本真生命无法得以真实体现的遮蔽物,是处于客体、从属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将“我”视为人的生命的真实存在形式而不去追寻“吾”的意义,庄子则在无奈的生活世界中去探寻“吾”,去发现“吾”,其目的在于追求一种自由、逍遥的生命境界。
二、“我”的困境
为什么庄子在其哲学思想中提出了“吾”与“我”这样两个不同概念,而且还特别强调了“吾”的重要地位,使“吾”成为庄子生命哲学要表现的主题?这正是庄子探寻人的生命本真之所在。其中主要是因为庄子在通过对当时的社会、对人生观察之后,他发现了“我”的存在有着诸多困境,“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所归,可不哀邪?”[4]58有形的“我”始终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为了适应社会,成为“社会人”,由此也产生了无尽的烦恼。如果不能斩断这些烦恼,摆脱这样的困境,那么人始终只能是被役使的物,而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不能获得彻底的自由。正是“我”的这些困境导致了“吾”隐没而不彰显,是人们始终不能见“吾”的重要原因。
首先,庄子对人生短暂、虚无发出了慨叹,而许多人却无视短暂生命的存在,为了诸种利益不惜穷兵黩武,草菅人命。“我”正是在这种困境中生存而不觉知,从“我”的困境入手显示出庄子对人的生命的关注与重视。
庄子生活在“礼乐征罚自诸侯出”的周王朝衰落时代,这也是战争极为频繁、人民的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时代,与庄子同时代的孟子也曾对当时社会作出如下记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6]175统治者为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人口资源等利益,彼此之间经常大动干戈,以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这导致人民生活动荡、甚至尸横遍野。庄子曾对卫国国君及其统治状况作了如此描述,他说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4]129庄子本人是宋国人,宋国国君偃在当时被称为“桀宋”[7]1632,庄子也把极端凶残的宋国君偃比作又黑又丑的“骊龙”[4]974,把宋国形容为暗无天日的重重深渊,俨然如人间地狱。人民都是以生为喜,以死为悲,而在悲喜交加的心境中往往过着不得安宁的生活,对于此种戕害人民的战争现实,庄子感慨统治者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4]129然而,“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4]657个体的生命非常短暂,就是在这样短暂的人生旅程中,人们不能够把持自己的生命,不能够体悟到生命的真实意义,自己处于厄运、困境中浑然不知。正是在这种严酷的现实面前,庄子看透了人生,不断反思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冷峻的观察中发现了“我”的无奈,去追寻“吾”的真谛。
其次,庄子认为,人生在世总是处于一种不自由的生活状态,这种不自由是由外物所造成的束缚而产生的心理感觉,这种外在束缚包括有道德约束,诸如儒家的仁义礼智等,也包括有人在社会中忙于追求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而造成的困惑与痛苦。因此,庄子从道德与功利两个方面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了人之所以不能够获得自由,发现真我,达到一种逍遥的人生境界的重要原因。
道家创始人老子曾经对道、德与仁义礼的次第关系做了阐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215,他认为仁义礼等外在形态的伦理律则是对人性的束缚,不能够充分展示人的生命的自然状态。庄子继承了老子对于仁义礼在人性中存在弊端进行批判的思想,也对儒家的仁义礼进行了批判。庄子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生命之外的仁义礼,而是生命自身,对于那些把仁义礼看作“至重”的律条,漠视生命本身的存在,甚至像孟子所言的“舍生而取义”无疑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是对生命的极大误解。庄子将这些伦理观念比作是“黥”刑和“劓”刑,“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汝将何以游于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4]237通过仁义这种外在的束缚来限制和压抑人的本真之心不符合人道。因此,庄子对这种情况深感慨叹,他说:“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槢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4]323就是上古黄帝也是以仁义来限制别人,才导致尧舜为了仁义而不惜四处奔波,仁义已经成为束缚人性的一种“桎梏”。同样,“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4]280一方面,仁义成为虞氏获取天下的重要方法;另一方面天下人为了仁义而不惜舍弃性命,这岂不是很可悲的事吗?在庄子时代,仁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谋取利益的手段,“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4]298对此种假仁义的行为,庄子指出:“诸侯之门,仁义存焉。”[4]302有权有势者称为推行仁义的积极分子,成为仁义的代表,他们将仁义作为自己为政的护身符,仁义由此而变成了极为虚伪的东西,是欺骗和统治人民的工具。一个人倘若行仁义,便会成为“灾人”,除了会对世人产生危害,反过来也会危害自己,真可谓是“害人又害己”。如果让一个迷失真心、本我的人去治理国家,社会必定会大乱。这样仁义不仅成了拖累人的强制力量和精神负担,不仅害人害己,甚至由害人害己而导致祸害社会。
庄子生活的社会,不仅战乱纷争,而且物欲横流,疯狂的追名逐利成为一种时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满足有甚于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4]280可以说,在“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亡其身,岂不惑哉!”[4]858生命的本真和自由在利益争夺面前被扭曲了,人为物、为名、为利所牵累,生命反而被视为外物。可见,对人性的束缚不仅仅来自仁义礼等道德律条,还有来自于这些无形事物的限制。
正是因为这些身外之物的迷惑,人们为了保持和获取功名利禄常常是“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4]52外在的“我”总是常常处于一种“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的生活状态中,由此而不能获得人生的自由。因此,在此之前的老子就已经意识到“吾之有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2]121正是由于这个有形的、外在的我束缚着人的自由,身体也与被外物所迷惑的“心”一样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无论是睡梦之间还是在梦醒之后都无法摆脱与其他事物不断地接触和冲突,结果是昼夜忙碌却不知道究竟何为,身心疲惫不堪却又没有收获。在庄子看来,这样的人生真是一种悲哀!
三、“丧我”方能见“吾”
通过对“吾”与“我”的不同分析,以及对“我”所受到束缚的揭露,庄子认为,要想获得真正的自我,获得精神上自由,达到人生的逍遥,就必须“丧我”。只有通过不断的“丧我”,才能够达到“吾”的显现目的。那么,如何才能“丧我”,怎样才能凸现“吾”的存在?庄子提出了他的具体修行方法,即“坐忘”、“心斋”等修养方法,通过这些具体方法的实施,层层剥落了束缚在“吾”之上的外物,最终达到人生自由的一种超越境界。
为了摆脱对人生本真生命束缚的桎梏和枷锁,庄子提出以“坐忘”的方式来达到丧“我”见“吾”,即通过不断地自身修养功夫,逐步丧失掉遮蔽在本真生命上的功名利禄、喜怒哀乐诸种烦恼等外在的束缚,实现返朴归真,显现真实自我的目的。庄子假借孔子与颜回之间的对话来表达何为“坐忘”以及如何“坐忘”:“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4]240
在这段对话中,颜回向老师孔子讲述了自己“坐忘”的过程,这一遗忘过程是有层次、有步骤的完成。首先忘掉了儒家提倡的保证实现仁义的外在形式——礼乐,然后又忘掉了比礼乐更高一层次的儒家最为重要的精神核心思想——仁义,在此基础上,最后忘掉宇宙间的一切事物、自己身体乃至自我意识的存在,进入了物我两忘、是非皆泯的境界。“坐忘”这一修行活动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修行者能够“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这也就是指从外在形态上讲,要忘掉自己身体的存在,即“离形”;从内在形态上讲,要忘掉自己所学的知识,即“去知”。老子曾经讲过:“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2]250就是要求修道者在修道的过程中逐渐放弃、减损外界的束缚以及自身知识的束缚,庄子的“坐忘”与之有着相同道理。通过“坐忘”这种修行方式,最终是要实现与大道相契合的境界,而这个过程重点强调的是“忘”这一动作。这个“坐忘”的修行状况就是《齐物论》开头有将南郭子綦凭几而坐,凝神静虑,如丧耦状,进入了离形去知,身心俱遣,物我两忘的境界。因而,从外表上看去,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答焉堕体,像是失去了匹偶。从内里看,精神上却摆脱了一切现实的诸种束缚,妙通大道而获得自由,合于大通而与天地同游了。
如果说“坐忘”是丧“吾”见“我”的初级方法,是“吾游心于物之初”的话,那么,“心斋”则可以称之为高级的修行方法,它同“坐忘”一样也是实现“丧我”的重要修行方法,但对修行者要求更高,是用“气”来体道。所谓的“心斋”是指:“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4]139对待宇宙万物要以一种虚静的心来把持,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自己的内心世界空净,显现出“吾”的存在。庄子通过“坐忘”、“心斋”的修行方法实现了“丧我”的目的,使人丧失了“我”,消解了束缚人之本性的外在物,呈现出了本真之我,也使得人的生命境界得到提升。
人的生命境界如何?庄子通过“坐忘”和“心斋”的修行之后想要追求达到一个何种逍遥的理想境界呢?我们通过《庄子》一书内容可知,这个理想生命境界是通过所谓的“神人”、“圣人”、“至人”乃至“真人”等不同于凡人的行为活动表现出来,即“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4]20他们都是庄子理想生命境界中理想人格的化身。在这些理想人格中,虽然他们具体存在特征上有着某些细小差别,但是,在其本质意义上没有实质性的不同。诸如庄子对“圣人”的理解,他所谓的“圣人”具有着样的品格:“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4]944-945“真”是“圣人”所具有的一个最可贵的品质,“真”也正是社会化的“我”在剥落了种种外在的束缚之后达到的“吾”的本然状态。“圣人”超越了世俗的功名利禄,他对外物无动于衷,超越了世俗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超越了功名利禄等诱惑,故不为外物所累,“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绕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4]101他与外物的关系是“圣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4]264与“圣人”一样,“至人”也是人性本我之“真”的体现者,“不离于真,谓之至人”[4]983。“至人无己”是指“至人”已经超越了外在形态束缚下的我,而达到了物我一体、泯灭是非的境界,他能够“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4]635对于生死、利害业已经泰然处之而不为所动,所谓“至人……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4]98已经达到超凡脱俗,自由无碍的境界。
除了“圣人”、“至人”之外,尚有“神人”也是如此,“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4]28“神人”可谓是得道之人,可以往来世间而不为世间诸种功名利禄束缚。这样看来,追求至真至美至乐的神人的生活境界是庄子生命哲学的最后归宿,成为一个了达世事的“神人”,也是庄子在“丧我”之后出现的能够优游于道中的理想人格之代表。另外,“真人”也同上述三种非凡之人一样,具有超世绝俗的特征,“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4]199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4]199真人已经达到了不累于外物而能够自由驾驭外物,由此也就达到了庄子所追求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488的逍遥境界。
四、结语
荀子曾批判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8]393,指出庄子在天人关系的探讨中,过多地关注了天道而忽视人道。从表面上看荀子的批判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当我们在考察了庄子“吾丧我”的生命哲学意蕴之后就会发现,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庄子其实更关注人道,关注人的生命价值。正因为如此,庄子才在人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其重心以及落脚点最终还是人道。在庄子“吾丧我”的表述中,除去遮蔽在本真的“我”之上的种种束缚,还原“吾”的本来面目,是庄子生命哲学的核心,也是庄子实现生命价值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庄子的实际旨趣,在于维护和肯定真正意义上的个体之‘我’,消解与之相对的‘我’:所谓‘吾丧我’,也就是以本然、真实之‘我’(‘吾’)解构非本然、非真实的‘我’。”[9]正是通过“坐忘”、“心斋”等具体的修行方法,不断地忘却、剥落外在的物我乃至自身的知识,使心灵达到一种虚无的境界,从而实现“丧我”的目的。“丧我”后使人获得了心灵上的暂时安顿,生命境界得以提升,本真之我得以显现,这也是庄子生命哲学中所要表达的重要思想。
[1] 王博.庄子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9] 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6.
Display of True Life
ZHANG Miao
(Department of Phylosophy,Qufu Normal University,Rizhao 276826,China)
“I”and“Myself”are important first-person pronouns in the Pre-qin literature,but the two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different contexts.In Zhuangzi“I lose various types of myself”“I”,“Myself”each have their separate meanings,“I”means the actual or the true myself.“Myself”is the superficial or phenomenal myself.As the“Myself”is in the many plights of the existence,thus leading to the“I”being not free and showing myself.Therefore,Zhuang Zi displays the existence of“I”and realizes the superb state of man’s life by some Buddhist ways such sitting in meditation and forgetting about all secular and worldly things.
I lose various types of myself;plight;life;state
B223.5
:A
:1009-105X(2010)01-0022-06
2010-02-01
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张淼(1975-)男,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