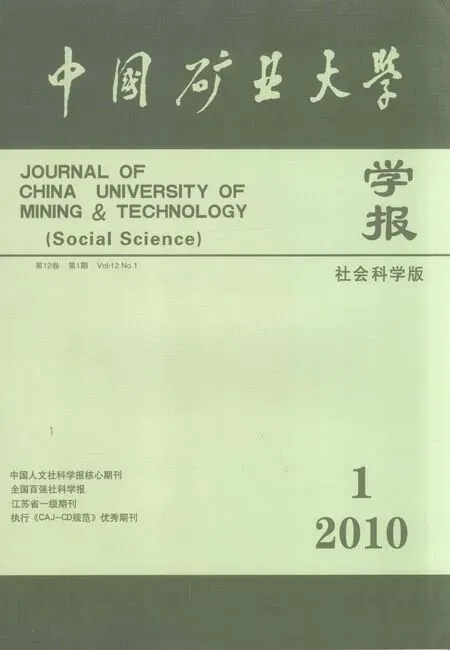追寻认知与自由的道路
——卢卡奇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沉思
吴建良
(南开大学哲学系,天津 300071)
追寻认知与自由的道路
——卢卡奇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沉思
吴建良
(南开大学哲学系,天津 300071)
考察卢卡奇在其名著《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进路进行深度剖析的运思轨迹,我们会发现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条追寻认知与自由的道路。这条道路曲折迂回,先后经历了形式理性主义哲学、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三个阶段。德国古典哲学不断地往前推进,但最终未能摆脱自由与必然、唯意志论和宿命论的“二律背反”困境。卢卡奇试图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历史辩证法的原则来克服古典哲学的困难,但他最终还是偏离了马克思并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窠臼。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而简单地否定卢卡奇对德国古典哲学所作的深刻思考,因为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能够“走进德国古典哲学”并“回到马克思”的重要路标。
二律背反;总体性;形式理性主义;批判哲学;历史辩证法
卢卡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主要集中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论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这一章节中。但是要想更深入地领会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必须把它视为整篇论文,甚至整部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加以解读。卢卡奇在考察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脉络的时候自觉地运用了理论与实践在作为总体的历史中相互作用、不断生成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在他的论证过程中理论发展的逻辑与实践发展的逻辑交替而行,彼此照应,始终都力求将考察的对象纳入历史的总体中加以理解,而总体在卢卡奇看来又具有相互联系的两层含义:一是结构性的总体,强调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二是历史性的总体,强调对社会现实的真正认识只有在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的整体中才能得到。考察卢卡奇的运思轨迹,我们会发现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历程,这条道路曲折迂回,先后经历了形式理性主义哲学、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同时也就是三种路向。
一、形式理性主义哲学之路
在卢卡奇看来,形式理性主义不仅与非理性主义相对立,而且不同于一般的理性主义。简要地讲,它主要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作为理性主义,它总是力图“把各种现象统一起来,与在各种现象内在关系之外去探求它们的原因和联系的观点相反,它力图探求各种现象内在的因果关系,并要求使用数学的、理性的范畴来解释各种现象”[1]183;其二,它通过建立形式体系来把握对象,并认为这是人的理智能够认知世界的唯一方式;其三,它与那种只是作为部分性体系,最终只能是作为达到——非理性——目标的手段的理性主义不同,它要求成为认识整个存在的普遍方法。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形式理性主义这一认识路线的形成及确立,依靠着一种宏大而坚实的观念,即“因为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因此,它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以及只要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么它就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1]182。而这一观念又通过数学和几何学方法所取得的成功而得到强化,因为数学和几何学就是这样的形式体系,它们从一般和对象性前提中设计、构造出对象,整个体系的任何一个个别的环节都是可以由它的基本原则创造出来,都是可以由它来精确地预测和估计的。数学和几何学的方法被视为力图认识整个世界的哲学方法的样板,以致像斯宾诺莎这样的哲学家完全按照几何学的模式来创造现实的客观关系。
这种通过形式体系来认知世界的哲学方法如果不被加以反思,它可能会永远沉陷在把形式的和数学的、理性的认识,和认识一般,和“我们的”认识简单地等同起来的独断主义之中而浑然不知。但是,这种形式理性主义的认识路线遭到了以康德为代表人物的批判哲学的质疑: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以“自在之物”为核心概念,系统地论证了抽象的、形式的理性化的“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
康德把世界严格地区分为现象界和本体,人的理性只能认识现象而对本体一无所知。他指出:“感性的直观能力(它为知性形式提供了内容)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一种接受表象以某种形式给以的刺激的能力而已……这些表象的非感性原因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而我们也不能将它们作为客体而加以直观……然而我们可将现象的原因一般称作超验的客体”[1]186。这个所谓的客体是先于一切经验自在地既定的。反向而思之,既然作为现象原因的“自在之物”这一所谓的“客体”是自在地既定的,那么通过直观而获得的感性内容也必然是既定的、非创造的、偶然的。感性内容可能是经验事实的直接构成部分,也可能只是构成经验事实的最终的物质基础,无论怎样,由此之故,经验事实从其本质上来讲也具有既定的性质。康德曾明确指出,纯粹理性并不能提出任何一个综合的、构造对象的命题,即其原理决不能“直接从概念中获得,而始终只能间接地通过这些概念对某些完全偶然的东西,即可能的经验的关系中才能获得”[1]188。这就意味着,只从已有的理性的部分体系的概念结构出发不能实现对世界的总体认识,对世界的总体认识不可能从已有的部分体系的概念结构中推导出来。为了达到对世界的根本性认识,这些形式体系不得不与既定的、并非人的理性所创造的、处于偶然状态的经验事实相遇,从而产生出新的构造对象的命题,然而这种关于认识对象的新命题中除了对经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所表述外,对于这些经验事实及其关系本身的最终的非感性的、先验的原因却一无所说。也就是说,作为概念内容的既定的经验事实并不能借助知性概念进入理性的形式体系之中,经验事实的既定性不能被溶化为理性的形式,它仍然处于偶然性、非理性之中,即不能被设想为是由“我们”的知性所创造的。这样一来,对于试图通过形式体系的构建而实现对世界总体的认识的形式理性主义的方法原则来说,无异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一方面由于从理性的部分性体系的概念结构出发不能认识作为总体的世界,必须要建立统一的理性体系;另一方面又由于作为概念内容的经验事实的既定性不能被溶解为理性的形式,始终处于非理性状态,处于理性的形式体系之外,这就意味着这种力图建立把握世界总体的统一体系的努力是必然不能成功的。正如卢卡奇所总结的:“这一体系化的原则和对任何一种‘内容’的‘事实性’的承认(这一内容——原则上——是不能从形式的原则中推导出来,因此只能被当作事实而加以接受)必定是不能统一的”[1]189,哲学思维陷入了“二律背反”之中。至此,形式理性主义认识原则的幼稚独断性质及其无法摆脱的困境也就暴露无遗了。
如果德国古典哲学认知世界的道路在这种抽象的进退两难前就止步不前,那么它也就不见得有多深刻了,它也不可能成为未来思想的沃土。与此相反,德国古典哲学通过对形式理性主义的反思揭示了原有的认知路线的困境之后,它开始以批判哲学的形态继续寻求穿越困境的道路。
二、批判理性主义哲学之路
从卢卡奇的理论逻辑来看,批判理性主义哲学主要是指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及《判断力批判》等著作思想为主线的德国哲学。费希特、席勒等思想家的某些学说从其思维范式来看也被归属到了批判理性主义哲学这一阵营。
形式理性主义认识道路的障碍已通过批判哲学的反思而得以显现:“思维只能把握它自己创造的东西,这种宏大的观念在力求把世界的总体把握为自己创造的东西时撞上了既定性,即自在之物这一不可逾越的界限”[1]195。这也就意味着沿着原来的方向前进是找不到出路的。为此,卢卡奇敏锐地洞察到了德国古典哲学认知路线发生了重大转向:“思维如果不想放弃对整体的把握,那么就必须走向内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力图找到那个思维的主体。存在可以被设想为是这一主体的产物,这时,就没有非理性的裂缝,没有彼岸的自在之物”[1]195。与形式理性主义把经验作为既定的事实来接受,并把它们视为与作为认识主体的“我们”相异在的客体的思维相反,费希特认为,我们之所以“把全部事实看作是先验的,甚至把经验也看作是先验的,这是由于我们已经把经验推论为不可推论的。”[1]196这也就意味着客体之所以被视为客体,被视为对象性的存在,也是主体“自我”意识的产物。这样主体也就能被设想为全部内容的创造者。依循这一思路,哲学家们意识到主体与客体发生分化之前有着同一的本源。在这个本源中主体与客体处于同一的状态,从这个本源出发,每一种既定性可以被把握为它的产物,把经验中的主体与客体的两重性把握为从这种原初统一中派生出来的特殊情况。
康德发现这种主体与客体同一的状态存在于实践之中,不过它所指的实践仅仅是指道德实践。他发现在道德行为中,在道德行为的(个体)主体对自身的关系中存在这种意识结构,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关系。然而具体的道德行为并不只是与主体自身的内在意识相关,每一种道德行为一旦具体化,德国古典哲学的老问题又会在较高的哲学水平上重现出来。因为“在自己创造的,但纯粹是转向内心的形式(康德的道德律令)和与知性、感性异在的现实、既定性以及经验之间的不可逾越的两重性,对行为个体的道德意识来说,要比对认识的直观主体来说,表现得更为清楚。”[1]198由于康德的伦理学只是停留在对个体意识中的道德事实进行哲学解释的阶段,这样一来,一方面,这些事实同样也就变成了纯粹的、被发现了的而不能被设想为是“被创造的”东西;现象与本质的分裂并没有得到解决,世界并不能被统一地加以理解,反而连主体也被分裂为现象和本体,即理论的和实践的主体。另一方面,本应该由道德领域的发现而建立起来的自由,即自主,变成了纯粹内在的心灵自由。如卢卡奇所说“自由变成对内在事实加以评价的观点,这些事实,它们所有的原因和结果,甚至包括所有与构成这些事实的心理因素有关的东西,都完全地服从客观必然的宿命论机械主义。”[1]199由此可见,康德在道德实践领域内所作的哲学努力一方面没能解决认识世界总体的问题,同时也不能赋予人的存在以真正的自由。康德没能找到真正的克服纯粹直观的实践原则。他所说的道德实践,其主体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仍然是直观的,并不能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发生作用和影响。在康德看来自由只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只存在意志的自由,而现象界的一切关系则是必然的。由此,对他来说,认识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就是要越来越使认识变为对那些纯粹形式上的联系、那些在客观现实中、没有主体介入而发生的“规律”的完全有意识的直观。而在现实世界中活动着的所谓的“行为”的主体能够做的也不过仅仅是在这种对客观规律加以直观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一种立场,以使这些规律根据他的意思,按照他的利益(自动地、不受他的干预地)产生作用。这样一来,人的一切关系都被放到了自然规律的水平上,社会存在被等同为自然存在。“一方面,人的所有关系(作为社会行为的客体)越来越多地获得了自然科学概念结构的抽象因素的客观形式,即自然规律抽象基础的客观形式,另一方面,这个‘行为’的主体同样越来越对这些——人为地抽象了的——过程采取纯观察员,纯试验员的态度”[1]208。本想通过转向实践来穿越形式理性主义认识路线障碍的批判哲学至此不仅未能实现它的最初目的,反而跌入了宿命论的深渊。
虽然康德在其《实践理性批判》的结尾处表明:自然过程的“永恒的、铁的”规律性和个体道德实践的纯内在的自由的分离是永远无法消除的,但是批判哲学并未就此放弃对世界总体的认知和人的真正的自由的追寻。
在寻找“行为”的主体,即“创造了”作为总体的现实的主体的努力失败之后,哲学家们发现,在一个现实的具体的领域——艺术中存在这样一种形式原则:对于这种形式原则而言,内容是无关紧要的,有关“自在之物”以及“理念的偶然性”等等的所有问题对这种原则而言都不再起作用。也就是说在作为整体的人的世界变得分裂破碎的时候,艺术乃以一种具体的总体的形式存在着。在艺术世界所有的内容都不再是既定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因为它们是“直觉的知性”的产物,关于“直觉的知性”用康德的话来说“它不仅在认识中,而且在直观中也是主动的,而不是纯粹感受的”[1]217。这样一种形式原则的发现对于批判哲学家而言它具有重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性质的意义。康德由这一原则的发现而看到了完成自身的理论体系的希望,而他的后继者们则把它视为哲学体系的基石。席勒把美学原则规定为游戏冲动,并鲜明地指出:“人,只有当他具有人这个词的完全意义的时候,他才游戏,而只有在他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全的人”[1]218。这也就是说,只有在游戏中,在艺术化、美学化的世界中人才是真正自由的、完全意义上的人。这样一来,被视为普遍方法的艺术原则就面临着将整个世界美学化的任务,要把生活的全部内容生成为美学,把握在美学的形式之中。但果真如此,客观现实中人的“行为”也就被一笔勾销了,主体又重新变为纯直观的“主体”,人的自由同样也再次沦为纯内在的自由。
至此可见,批判理性主义哲学为了摆脱形式理性主义哲学的思维困境,在始终牢牢抓住形式与内容的逻辑对立不放的前提下,不断地转变视域:从纯粹理性的范围转到实践领域,从实践领域再转到艺术领域,艰难地一步步地往前推进。但最终还是没能达到对世界的总体认识,找到人的真正的自由。关于批判哲学所探寻的道路及其根本性的困境,卢卡奇作了深刻的总结:“当批判立场随着在对我们来讲是既定的现实中和我们对这现实的关系中发现二律背反,被迫在思想上相应地也把主体撕成碎片。”[1]220无论是道德实践原则,还是艺术原则的发现,都只不过是为主体的分裂增加一个新的领域,在这些部分领域中内容都可以被视为“创造的”,而不是既定的,但是要达到对世界的总体性的把握,就必须“把这种分裂的各个部分的创造形式的统一推论为创造的主体的产物,因此,说到底就是要创造‘创造者’的主体。”[1]221
三、黑格尔哲学之路
批判理性主义哲学虽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认知与自由的问题,但是它预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向:“未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力求克服主体的物化的分裂及其客体的——同样是物化的——僵硬的不可理解”,“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分裂的,但是必须统一的人”[1]221。若能将批判哲学所展示的“分裂的不同形式看作是通向重建的人的必要阶段,并让它们进入被把握的总体的正确关系之中,当它们成为辩证的时候,它们的分裂也就消融了”[1]221。黑格尔哲学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他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扬弃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自由与必然,理性与感性以及绝对主观性和绝对客观性等等。“这些固定化了的对立是理性的唯一志趣……必然的发展是生活的因素,而生活永远是在对立中形成的:而最有生气的总体只有通过重建,只有从绝对的分离中才能产生出来。”[1]222因此,形式理性主义和批判哲学所不能克服的所有问题都被具体地集中在了辩证法的问题上。
黑格尔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是精神与物质,自由与必然,理性与非理性等等对立形式从根本上来讲都可以归结为形式与内容的对立。要想解决以往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必须建立一种崭新的逻辑学,这种逻辑学是将概念建立在内容的物质特性之上的,在这一逻辑学中所有概念都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处于不断生成之中的。这也就是他所谓的具体概念的逻辑学、总体的逻辑学。在这种逻辑中,“辩证的过程发生了,主体和客体之间一成不变形式的僵硬对立溶化了”[1]223,它们成了同一的总体。这也就意味着:“真理不仅被把握为实体,而且被把握为主体”[1]223;主体(意识、思维)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主体因此在一个由它自己创造的、它本身就是其意识形式的世界中运动,而且这个世界同时以完全客观的形式把自己强加于它。这样一来,辩证法的问题及随之而来的主体和客体、思维与存在、自由和必然等等对立的扬弃的问题才可以被看作是解决了。
黑格尔通过辩证逻辑的建立为把对象把握为同一的总体找到了方法,但是具体的、消解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对立的辩证过程到底以什么形态存在着呢?历史。只有在历史中,在历史的生成中,在性质上新的东西的不断生成中,才能发现这种主体与客体的辩证作用过程,才能真正消除事物和事物概念的独立性及因此而造成的僵硬性。并且也“恰恰是由于历史的生成迫使想与这些因素相符合的认识把概念结构建立在内容之上,建立在现象的独一无二的和新的性质上,因此它同时就迫使这种认识不让这种因素坚持其纯粹具体的独特性,而是把它们放到历史世界的具体的总体,放到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本身之中去,只有这样认识才成为可能。”[1]226-227也正是鉴于这样的考虑,黑格尔突破性地把历史问题纳入了自己的概念体系。
如果黑格尔不离开把历史视为辩证法唯一可能的生存因素这一立场,那么,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以及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都不再表现为僵硬的对立,而是积极地转向统一。现实也就具有了是由我们创造的真实性质,是我们自己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如果我们把全部现实看作为历史,那么现实就可以被把握为我们的“行为”。卢卡奇在黑格尔的这一思维趋势中似乎看到了恢复人的真正的自由的前景。因而他进一步指出:“唯物主义的困境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这种困境被发现原来是理性主义的局限性,是形式知性的独断主义,它只把我们有意识的行为认作为我们的活动,而把我们自己创造的历史环境,即历史过程的产物看作是依靠与我们异在的规律而影响着我们的现实”[1]227。似乎只要明白了这一点,一切客观的,制约“我们”的,异在的力量都具有了主体的性质。只要能“具体地指出这个是历史主体的‘我们’,即那个行为实际上就是历史的‘我们’”[1]228,那么恢复主体自由的道路也就找到了。
然而,就在这一关口,黑格尔哲学却误入了概念神话的迷宫。在其体系中,历史之外的世界精神成了历史的主体,这样,历史也就不再成为主体与客体相同一的总体。黑格尔在历史的彼岸建立了自我发现的理性的王国,然后从理性王国出发,把历史把握为阶段,把出路把握为“理性的狡黠”。历史过程中“行为对行为者本人来说就变成了先验的,表面上获得的自由突然变为对控制他们的规律进行反思的那种虚构的自由”[1]229。人在世界精神的自由行进中沦为手段。卢卡奇指出,由于历史是辩证方法的自然的、唯一可能的生存因素,所以黑格尔的这种尝试必定不能成功。一方面,这个被设想为超历史的过程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表现出历史的结构;另一方面,历史过程对于黑格尔的理性来讲又重新变成了偶然的,原本想通过辩证的方法来克服的内容对于形式的事实性和非理性的问题又重现出来,这样一来,思维又重新跌入了主体与客体的直观二元论的窠臼之中。至此可见,德国古典哲学沿着黑格尔辩证法的道路前进也同样未能完成对世界的总体的把握和在思想上重建被物化消灭了的人,找到人的真正的自由的任务。也正是由此,卢卡奇试图在德国古典哲学止步的地方重新寻找出路。
四、卢卡奇的探索与困境
卢卡奇依循德国古典哲学理论演进的逻辑一直往前追寻,直到“集古典哲学之大成”的黑格尔哲学。他发现德国古典哲学只是达到了对处于物化状态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它始终没能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哲学思维中的二律背反问题,因为“二律背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由这个社会连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1]232。只要现实社会依然处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形态之中,那么整个世界就处于物化结构之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人创造的世界表现为与人相异在的,疏远的,制约人的客观实在。哲学中出现二律背反问题,实际上只是物化结构在人的意识领域中表现出来了,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物化意识。只要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德国古典哲学就永远也摆脱不了自身的理论困境。也就是说,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和解决问题的答案在纯思想、理论的领域都不能找到。于是卢卡奇意识到必须把视线转向真正的实践(相对于康德的本质上仍具有直观性质的道德实践而言)领域。在这一领域中,行为的主体将通过自己的活动现实地改变社会的物质基础,并最终通过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人类历史阶段,来实现问题的全部解决。
德国古典哲学始终被禁锢在纯思想的范围内,也正因为如此,它“把它的生存基础的所有二律背反都推到了它在思想中能够达到的最后的极点”。[1]231虽然它最终未能走出困境,但是它的“这种推演的方式,即辩证的方法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1]231卢卡奇认为,要想最终摆脱德国古典哲学的思维困境,重建人的被消灭了的自由,就必须将黑格尔的概念的辩证法改造为马克思的具有革命性质的历史辩证法。无产阶级的这种意识一旦形成,它将以实践的方式破除现实存在的物化结构。只有这样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的对立问题,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人的意识及其存在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团结起来一致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而是纷纷拿起武器为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战。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相继失败,第二国际已名存实亡。卢卡奇深入考察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揭示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而是具有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目的:一方面,他试图从理论上论证并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理性地位,并以此驳斥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的第二国际(前者鼓吹经济决定论,贬低马克思哲学,试图从唯物主义中清除历史与辩证法;后者盗用其中概念,攻讦俄国革命);另一方面他试图解决革命道路中出现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就会成为一种物质性的力量。”[2]而卢卡奇所处的时代环境却让他觉察到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并未能导致普遍性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正是受这一问题的困扰,卢卡奇决定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彻底化,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沉思来寻求它的哲学根据,并且试图以理论的方式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再次强调这一样一种观点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正确认识:“只有当,一方面人类存在借以形成的全部范畴表现为这种存在本身的规定,另一方面这全部范畴的顺序、关系和联系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表现为现在的结构特征时,起源和历史才可能一致,或更确切地说,才可能纯粹是统一过程的因素。范畴的顺序和内在关系因而既不构成一种纯逻辑的次序,也不是按照纯历史的事实来安排的。”[1]282这样一种把历史视为是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总体的观念深深地印入了卢卡奇的脑海之中,成了他考察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自觉意识,他在考察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逻辑时便自觉地运用了这样的方法原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卢卡奇思想的深刻之处,是他离马克思最近的地方,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卢卡奇也正是在这里离开了马克思,重新奔向了黑格尔。卢卡奇所理解的辩证原则在本质上来讲是黑格尔式的,留有很深的唯心主义痕迹。在卢卡奇的这种黑格尔式的辩证逻辑之中,马克思所强调的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是找不到地方安置的。卢卡奇针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把社会历史看作是纯粹自然规律运动的过程,因而否定了一切能动性和创造性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们片面地把经济发展的必然性看作是决定一切的东西,忽视思想和政治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所起的能动作用,提出所谓的必须适应新形势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重点放在眼前的经济利益上,放在议会里,运用“渐进”手段向社会主义进化。卢卡奇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强调无产阶级意识的作用。矫枉过正,卢卡奇在否定庸俗经济决定论的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经济因素起最终决定作用的理论,将总体性的社会存在性质与经济优先性错误地对立起来,最终陷入“唯意志论”。卢卡奇的这一思想倾向曾被列宁批评为犯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3]。张一兵教授在《卢卡奇与马克思》序言中指出:总体上看来,卢卡奇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反对康德式的韦伯。”[4]也是很有见地的。马克思早期思想中较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得到了卢卡奇淋漓尽致的发挥,这对于无视主体能动性,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但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虽然在马克思早晚期著作有着不同的侧重。将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必将重新陷入形而上学的思维困境,这也正是卢卡奇最终没能真正“回到马克思”的原因之一。
总的说来,卢卡奇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考是深刻的,虽然他最终还是偏离了马克思,但是其理论价值不能被简单的全盘否定。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让我们洞察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真实困境,为我们厘清了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理路,对于我们摆脱庸俗唯物主义的影响,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及其革命学说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讲,卢卡奇对德国古典哲学所作的深刻思考,已成为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理解马克思的重要路标。并且,在现代社会中卢卡奇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并非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人类追寻认知与自由的道路将无限地往前延伸。
[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
[3]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12.
[4] 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8.
Pursuing Knowledge and Freedom——Lukacs’s Meditation on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WU Jian-liang
(Philosophy Department,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is profound and its development is very complex.Lukacs deeply analyzes its development with unique perspective and methods in his famous book“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Following him,we will discover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that is,pursuiing the way of knowledge and freedom.This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or three directions:the form rationalism,critical philosophy,Hegelian dialectics.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moved forward gradually,but ultimately it failed to get rid of antinomy dilemma of freedom and necessity or voluntarism and fatalism.Lukacs tried to start from orthodox Marxist standpoint and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of classical philosophy with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dialectics,but he eventually deviated from Marx and got involved in idealism.But we can not simply deny his meditation on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because he sets a sign to thoroughly understand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and Marx.
antinomy;totality;form rationalism;critical philosophy;historical dialectics
B507
:A
:1009-105X(2010)01-0006-06
2010-01-07
吴建良(1975-),男,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