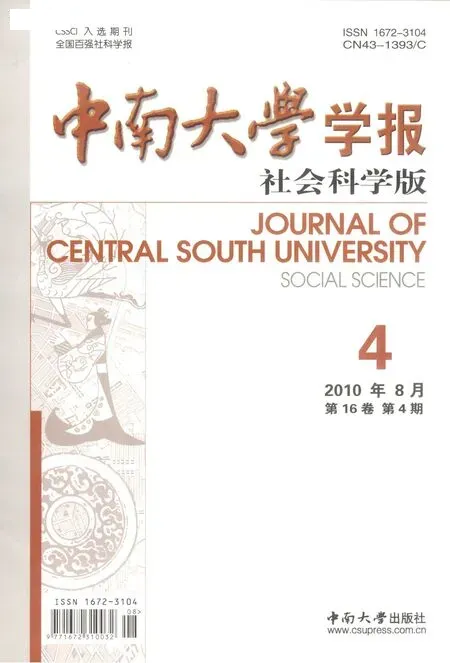索福克勒斯关于“命运”的思考
——两部“俄狄浦斯”的悲剧观比较
王静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
索福克勒斯关于“命运”的思考
——两部“俄狄浦斯”的悲剧观比较
王静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
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两部悲剧中对命运的体认有一个内在的发展过程:在《俄狄浦斯王》中,命运更多显现为一种外在的必然性力量,个体和命运之间是一种紧张关系;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的俄狄浦斯开始转向对自身和城邦命运的内在沉思,最后与悲剧命运达成和解。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悲剧;命运;自然本性;理性
《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Oedipus at Colonus)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公元前496~406)创作的两部关于俄狄浦斯的悲剧,两部悲剧最突出的主题之一就是古希腊的命运观。在《俄狄浦斯王》中,命运是一种外在的必然性力量,俄狄浦斯身陷于个体与城邦的关系之中,他努力逃脱命运的谕言,但他所有的努力反而愈加促成命运的迅速完成,个体抗争必然的命数所激发出的崇高感是这部悲剧的特色;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俄狄浦斯置身于城邦之外来思考个体与城邦的关系,个体与城邦不再处于紧张的对抗状态,而是在个体的沉默中达到了对必然性力量(命运)的超越,冲突减弱了,对宇宙(cosmos)秩序的理解加深了,俄狄浦斯回归内心深处去沉思自然本性更深的本质,最终达到与命运内在的和解。
一、《俄狄浦斯王》:自然本性对于“命运”的盲目反抗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以酒神精神来描述人的自然本性,以阿波罗精神来象征城邦的礼法,即城邦的尺度。《俄狄浦斯王》这部悲剧中的命运冲突主要由城邦的礼法(nomos)与人的自然本性(physis)的矛盾产生,“弑父娶母”是这一矛盾的深刻隐喻。任何文明的社会均有儿子−母亲的乱伦禁忌,《俄狄浦斯王》就是以这个禁忌作为整个命运冲突的核心,直接将文明的根基展现在最明亮的地方,以揭示出人性根本的困境,人的根本悲剧性命运。当俄狄浦斯听说“弑父娶母”这一谕言之后,为维护城邦的礼法,他在非理性力量的支配下盲目地逃避,但他的逃避反而更加速了谕言的实现,“弑父娶母”的行为最终触犯了城邦的礼法,动摇了城邦的秩序,忒拜城也因此被瘟疫笼罩。为了消弭忒拜城的灾祸,俄狄浦斯自刺双眼、流亡放逐,他最终认识到命运是一个比他更强大、更顽固的存在,罪愆本身须成为必然,这并非仅仅由于个体的失误,而主要在于命运的不可违抗。俄狄浦斯以自身的流亡放逐来解决城邦礼法与人的自然本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为维护城邦礼法所作出的个体的牺牲,可视为是阿波罗精神。
在《俄狄浦斯王》中,被“弑父娶母”这条可怕的神谕击中的有三个人:先王拉伊俄斯、母亲伊俄卡斯忒和俄狄浦斯。他们都深信这一谕言的可靠存在,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驱避厄运的降临。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意欲杀死自己的婴孩,俄狄浦斯意欲逃离科林斯王国远走他乡,但婴孩被善良的牧人挽救,而科林斯国王波吕玻斯并不是俄狄浦斯的生父,他们试图摆脱命运的种种努力反而促使他们与命运愈走愈近。那么,这条显示命运的神谕到底是指什么? 它有何隐喻? 其实,答案就在主人公“俄狄浦斯”Oedipus(Oidipous)这一名字中。“pous”的希腊文原意为“脚”。“Oidi”在希腊文中有两层意思:一是“肿疼的”,这是俄狄浦斯的身体特征,是他与生俱来的局限;二是“认识”之意,这是俄狄浦斯一生的追求目标,是试图认识自己局限的种种努力。所以,“Oidi-pous”既可理解为“肿疼的脚”,也可理解为“认识自己”;“Oidi-pous”的两层涵蕴体现了其内在的“认识你自己”和“自知其无知”的辩证关系。“认识”的结果是知道引起忒拜城瘟疫的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是“人”,“无知”的结果是接受城邦赐予他的礼物——母亲,引起忒拜城新的瘟疫。无论俄狄浦斯作何选择,忒拜城的瘟疫都无法避免,除非俄狄浦斯深省他作为“人”的局限性。
但是,一个脚肿痛(有缺陷)的人是否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局限? 索福克勒斯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是从神和人的关系开始的。古希腊是一个敬神的民族,神是人类最高理性的体现,从神的影像中,人类看到自身的局限,如果有人胆敢冲破人神的界限,妄图与神较量,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神的旨意,那么他必将要遭到神的报复,承受最可怕的命运。索福克勒斯借歌队唱出自己的隐忧:“关于拉伊俄斯的古老的预言已经寂静了,阿波罗到处不受人尊敬,对神的崇拜从此衰微,……如果有人不畏正义之神,不敬神像,言行上十分傲慢,如果他贪图不正当的利益,作出不敬神的事,愚蠢地玷污圣物,愿厄运为了这不吉利的傲慢行为把他捉住。”[1](160)因此,俄狄浦斯的悲剧中也有其个人自身的因素,即他并不能很好地把握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尺度,在理解“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时,他缺少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审慎”的美德,也就是对“认识你自己”和“自知其无知”缺少内在的理解。
当俄狄浦斯得知“弑父娶母”的神谕之后,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离开科林斯国,但他并不理解神谕的真正涵义,以为离开了就可以逃脱命运的诅咒,并为此暗自欢喜,在探索命运的过程中,他流露出对“自己”茫然无知(他甚至连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但另一方面他仍心有余悸,担心暗示命运的征兆会不经意地出现,所以生活中的任何细节都会引发他对谕言的忧虑。例如,他在追查杀害先王拉伊俄斯的凶手时,他的心中充满了隐忧,伊俄卡斯忒不解其情,试图安慰他,说拉伊俄斯是被一伙强盗打死的,而非死在自己儿子的手中,他们已将孩子丢弃在没有人迹的荒山之中,“那不幸的婴儿没有杀死他的父亲,倒是自己先死了。从那时以后,我就不再因为神示而左顾右盼了。”[1](159)伊俄卡斯忒以为“杀死了孩子”就可以摆脱命运的纠缠,不必再为神示担忧——“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因为神示而左顾右盼了” ——从这句无知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猜想她说此话时的轻狂神情,这种在命运面前的无知和轻狂,只有从最浅薄无信的人的口中才会说出!俄狄浦斯亦同样如此,报信人前来讣告波吕玻斯的死讯,他以为波吕玻斯就是自己的父亲,“父亲”的死使他摆脱了谕言的折磨,所以他也不再相信神谕:“我们为什么要重视皮托的颁布预言的庙宇,或空中啼叫的鸟儿呢?它们曾指出我命中注定要杀我父亲。但是他已经死了,埋进了泥土;我却还在这里,没有动过刀枪。除非说他是因为思念我而死的,那么倒是我害死了他。这似灵不灵的神示已被波吕玻斯随身带着,和他一起躺在冥府里,不值半文钱了。”[1](162−163)俄狄浦斯对待神谕的态度,与伊俄卡斯忒如出一辙。他们父母子三人所有行为的动机都是源于对“弑父娶母”这条神谕的表面笃信,这种“信”是自我保护的需要,而非发自内心的对于神谕本身的真正敬畏,所以,他们采取种种抵抗命运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正是由于这种自负和盲目,才是导致他们最终悲剧命运的主要根由。
尼采将俄狄浦斯这种由酒神精神引导的违犯禁忌,看作是突破城邦礼法局限性的尝试,因而这是一种积极的罪行。命运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就是一条神律;当这种神律压迫在俄狄浦斯身上时,承受者虽然流露出若干苦痛,但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对于命运主动承担的英雄主义的倾向。对俄狄浦斯个人来说,他本可以置身于城邦之外,然而他却主动选择留在城邦追查杀害先王的凶手;俄狄浦斯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城邦承担悲剧的命运,“你们每人只为自己悲哀,不为旁人,我的悲痛却同时是为城邦,为自己,也为你们”[1](136);从某种程度上说,俄狄浦斯是可以逃避命运的惩罚的,但他真诚地想为城邦消弥灾祸,结果却导致自己的毁灭,这是自甘的、主动的受罚。“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这种命运的神秘的三重性告诉我们什么呢?那破解自然——双重变态的斯芬克斯——之谜的人,必定要破坏神圣的自然秩序,弑父娶母。这个神话似乎轻轻地告诉我们,智慧,尤其是俄狄浦斯的智慧是违反自然的暴行,谁用知识把自然推入毁灭的深渊,谁就得在自己身上体验到自然的瓦解。‘智慧之矛调转矛头刺向智者,智慧是对自然的犯罪’,这是神话向我们高喊的可怕语句。”[2](59−60)《悲剧的诞生》中这样分析俄狄浦斯背负的可怕命运。
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理性对于“命运”的理解与超越
索福克勒斯继《俄狄浦斯王》之后,在晚年以同样的人物为素材创作了《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虽然这部戏剧也是取材于“俄狄浦斯”的家族传说,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情节却是剧作家个人的独特创作,其间不仅贯穿着索福克勒斯对于“命运”这一问题的持久思考,更包含他对于“原罪”这一观念的认识。希腊人是不相信“原罪”这一观念的,那么,俄狄浦斯遭受命运的放逐意味着什么,是什么促使他犯罪?
在这部戏剧中,俄狄浦斯对命运充满了怀疑,对自己的不幸充满了抱怨,他无辜遭受命运的严厉裁判,但这些罪行并不是他故意犯下的,那么,凭什么应当他遭受责罚?为了城邦的安危他自刺双眼、流亡他乡,本以为他这样做就可以消弥城邦的灾祸,但结果却反而引起亲族间更加残酷的仇杀,那么,他遭受如此悲惨的命运又有何意义? 年轻时为拯救城邦所做的种种努力,如今看来不过是一场虚空。
受尽了折磨的俄狄浦斯流浪在雅典城街头,身心疲惫,靠他人施舍度日;当雅典城民知道他是俄狄浦斯时,都非常害怕,想把他驱逐出去。俄狄浦斯为自己作出了申辩:“荣誉或美好的名声有什么用,它们还不是一场空!大家都说,雅典城对神最是虔敬,比别的城邦更能爱护受难的客人;可是在我看来,哪里是这么回事?你们叫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将我赶走,只因为你们害怕我的名字;其实你们并不害怕我这人和我的行为,因为我是受害者而不是害人者;……我的天性怎么算坏呢?我是先受害,然后进行报复的;即使我是明知而为之,也不能算坏人。但事实上,我是不知不觉走上这条路的,而那些害我的人却是明明知道而要毁灭我的啊!”[1](194)这完全可以视作俄狄浦斯为自己的“罪行”所作的辩诬。鲁迅说过:“无论谁只要站在‘辩诬’的立场,不论辩白与否,其实都是一种屈辱”,[3](88)生性高贵的人是不屑辩诬的,然而,苦难的磨砺却使俄狄浦斯变成一个易怒的、不平的、充满怨恨的老人,他对自己所经受的屈辱特别敏感,也特别幽怨;但另一方面,长期的放逐生活和内在的高贵精神已教会他除了最低的生活需求之外不再奢求任何别的东西,他对人世消退了热情,他的逐渐变得冷淡的悲凉之心使他能够获得超然于物外的平静。
他的小女儿伊斯墨涅急匆匆来找他,报告他她的两个哥哥正在争夺王位,她还带来一个神示,说俄狄浦斯能保证忒拜城的安全。很快,忒拜城派来俄狄浦斯的内弟克瑞翁强行逼他回国,以消除城邦的灾难,他拒绝了,他们起了冲突,面对克瑞翁对他的指责——说他是一个杀父的人,一个有污染的人,一个和不洁净的婚姻有关系的人,俄狄浦斯提出了抗议。他说,如果神示说,有什么注定的命运要落在我父亲身上,他必将死在他儿子手里,那责任怎么在我呢? 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如果像我这样生而不幸的人同我的父亲打了起来,把他杀死了,却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事,也不知道我杀的是什么人,你有什么理由谴责这无心的过失呢?“我没有犯罪。”我的婚姻,“是我接受了一件礼物;但愿我这不幸的人不曾因为有功于城邦而赢得这件礼物!”[1](203)——俄狄浦斯认为,无端受罚的命运是他被迫接受的,他没有任何过错。当他的大儿子,那个曾经把他驱逐出境的波吕涅克斯也来到他的面前寻求帮助时,他同样拒绝了儿子的恳求。此时的俄狄浦斯心如止水,他仿佛看穿了世间的一切,只希望能够藏身于冥府。悲剧从悲剧歌中产生……生活不过是一种欺骗。慈悲女神为他打开了死亡的大门,俄狄浦斯无痛而终。
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歌队起到揭示俄狄浦斯悲剧命运的关键作用。歌队是古希腊悲剧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它除了渲染舞台气氛、活跃戏剧场面等作用外,更是作为剧作家的代言人而出现的。悲剧诗人借歌队把自己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让自己不加掩饰地在虚幻的世界里保持理想的天地和诗意的自由。所以,歌队的作用不容忽视,它是作为戏剧生命而存在的,通过歌队,我们可以窥测剧作家一幅潜藏着的、更加真实的面孔。《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有一段歌队的唱词,我以为它对我们理解这部戏剧的意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歌队(首节) 在我看来,谁想活着更长久而不满足于普通的年龄,谁就是个愚蠢的人;因为那长久的岁月会贮存许多更近似于痛苦的东西;一个人度过了他应活的期限以后,你就会发觉他不再享有快乐了;那拯救之神对大家是一视同仁的,等冥王注定的命运一露面,那时候,再没有婚歌、弦乐和舞蹈,死神终于到了。
(次节) 一个人最好是不要出生;一旦出生了,求其次,是从何处来,尽快回到何处去,等他度过了荒唐的青年时期,什么苦难他能避免?嫉妒、决裂、争吵、战斗、残杀一类的祸害接踵而来。最后,那可恨的老年时期到了,衰老病弱,无亲无友,那时候,一切灾难中的灾难都落在他头上。
(末节) 这不幸的人就是这样,不仅是我,像那个从各方面受到冬季波涛的冲袭的朝北的海角,他就是这样受到那可怕的灾难的猛烈冲袭,那灾难永不停息,有的来自日落的西方,有的来自日出的东方,有的来自中午的太阳的方向,有的来自幽暗的里派山。”[1](224)
这段表现俄狄浦斯对于生命的绝望之辞,似乎正是索福克勒斯的心声。从这段歌词中,我们不难猜测诗人的悲观主义倾向和对于死亡的向往之情。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部悲剧的崇高之美呢? 歌队认为俄狄浦斯奇特的、无痛苦的死亡是神对于他一生所遭受的天遣的苦难的一种公正的补偿,因为他所受的苦难无缘无故,但是,现在“也许一位正义的神在扶助他。”俄狄浦斯,这位高贵而独断的国王,在经历了人生种种骇人的痛苦之后,拒绝了人世间所有背弃过他和爱恋过他的人们的各种诱惑的诺言,选择命运女神为他安排的死亡,他洗去长期流亡堆积于身的重重泥土,穿上女儿为他缝制的生命的华服,在电闪雷鸣中消逝于圣山之中,内心充满安宁和平静,他最终与命运和解。
三、两部悲剧命运观的内在统一
索福克勒斯的这两部俄狄浦斯悲剧可以看作一个和谐的整体,两部悲剧的主人公在与命运的抗争中,经历了一个由必然地犯罪——自愿地受罚——情感上与命运和解的过程,这是一个在对“自我”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完成的对“命运”的理解和超越。如何处理好人与神的关系,是理解“命运”的关键,索福克勒斯将俄狄浦斯放在与神的冲突中展现其对命运的认识。两部悲剧中都有神谕出现,但悲剧主人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违抗,一种是顺从,违抗导致毁灭,顺从产生超越;在两者差异的背后潜藏着共通的情感基础,那就是宣扬对“命运”的虔敬之情。俄狄浦斯一生为逃避命运而与命运作不懈的抗争,却依然陷入命运深不可测的罟网,成为命中注定的罪人,见证了命运的残酷,也见证了人生的虚妄;当明白命运是一条无法克服的神律时,俄狄浦斯在情感上超越了个人的痛苦和不幸,从而达到内心的从容和平静,他的愿望与神的安排一致。
其次,两部悲剧都在思考个体与城邦的关系。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身陷于城邦中去思考个体与城邦的关系,他看不清自己的本性,亦不明白城邦的礼法,进退失据,成为一个盲目的反抗者;而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俄狄浦斯置身于城邦之外思考个体与城邦的限度,他知道自己的局限,亦知道自己无力改变什么,所以他能够理解个体与城邦的关系,在“认识你自己”和“自知其无知”的辩证关系中作出正确的选择,但他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宿命论者,而是因为看清人世真相之后,他明白没有任何城邦值得他去为此献身。
维柯在《新科学》中划分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荷马时代来分析人的神性和人性的关系的发展规律。[4]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是一位勇于承担城邦不幸命运的英雄,他的痛苦是一种具有“神性”特质的英雄的痛苦;而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俄狄浦斯”是一位沉湎于自身不幸的伤感中的个人,他的痛苦是一种充满“人性”的个体的痛苦。神和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很少关心来世,但“来世”这一问题随着人们在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发现了无可救药的邪恶和不公正之后,越来越成为诗人关注的主题。继索福克勒斯之后的欧里庇得斯,则将普通市民引入古希腊戏剧,希腊悲剧逐渐放弃了对神的赞美,放弃了对伟大事物的憧憬,放弃了对重大事物的责任心,放弃了对人的尊重,放弃了让人们摆脱世俗欲望的可能性,最终导致悲剧的消亡。晚年的索福克勒斯的思考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显示出希腊悲剧由“英雄”向“个人”转化的端倪。
施莱格尔在《旧文学与新文学史(1815)》中认为,索福克勒斯的作品的美反映了他的心灵美和内在和谐。他的英雄人物中自然的、温和的、感人的,象人一样美,这是由于人间对众神的回忆尚在。[5](136)席勒的观点与施莱格尔不谋而合,在《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中,他着重分析了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的区别:“索福克勒斯是古典素朴精神的代表,欧里庇得斯是希腊悲剧精神感伤化的开始,欧里庇得斯注重对现实中人物的心理刻画,与索福克勒斯注重对非凡人物的精神刻画区别开来,索福克勒斯是刻画人的神性和人性最为完美结合的古希腊悲剧作家。”[6](95)
《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这部悲剧中的“俄狄浦斯”显然不同于《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的庄严和崇高,他的苦难感中更多一种世俗的幽怨和个体意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两部悲剧中的“俄狄浦斯”的形象的统一性呢? 有许多思想家则倾向于以“新教”的方式来理解《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的“俄狄浦斯”这一形象的崇高之美,例如,黑格尔认为,古希腊人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内在精神的自由,而新教的耶稣基督则超越了俄狄浦斯的悲剧命运;他说,只有把基督受难看作是这位无辜者的命运遭遇,而不是由于其它罪孽所导致的牺牲时,这个故事才是美的。[7](381)歌德也认为基督教精神达到了对俄狄浦斯苦难命运的超越:“人总是服从不可避免的命运,所有的宗教都坚持这点……基督教借助信仰、爱、希望来十分适意地完成;从而产生忍耐,它是一种甜蜜的情感,把我们的生存当作是珍贵的恩赐,哪怕我们得不到盼望中的享受,而是被十分讨厌的痛苦所折磨。”[8](945)所以,我们若想理解俄狄浦斯受难的崇高之美,就不能把他的牺牲理解为由于他触犯了“弑父娶母”的罪行而遭受的惩罚,而是应把他当作一位无辜者独立承受命运的重负,如同耶稣虽然无罪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其实,两部悲剧中的“俄狄浦斯”都是在追求人性的尊严和意义,他们以各自亲历无法忍受的痛苦的方式来探究人所能忍受的苦难的极限——人的尊严和意义是根据人忍受苦难的程度来确定,每个人忍受痛苦的能力不一样,因此,每个人的尊严和意义也不尽相同。“没有任何尊严能比得上正在忍受痛苦的灵魂的尊严。”[9](205)两位“俄狄浦斯”都在对痛苦的忍耐中培养自己的坚韧和对尊严的意识——这种对于人的尊严、地位、理性、节制、献身等英雄主义品质的追求,通常被称作是“希腊精神”;古希腊悲剧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精神。“悲剧中的主人公,无所顾忌地安然忍受命运所带来的一切困苦和磨难;正因为如此,他也就成为这一自在存在的体现者,这一无条件者和绝对者:他沉静地俯视世界事态之流,对自己的构想满怀信心——它们任何时候也不会实现,任何时候也不会摧毁。使悲剧人物感性地被推翻和被消弥的厄运,成为精神崇高者不可或缺的因素。”[10](132)谢林在《艺术哲学》中这样阐述对于“悲剧性崇高”的理解。
平静地接受命运,无论曾经身遭怎样剧烈的痛苦;与命运和解,才是对于命运最完美的理解方式——人只有在此信念中才能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也只有在此信念中,人的“救赎”才成其为可能,天性的高贵才得以保存。俄狄浦斯,这位独自承受命运重罚的无辜者,他的悲剧命运显示出了古希腊人崇高的尊严。
[1] 古希腊悲剧经典[M]. 罗念生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2] 尼采. 悲剧的诞生[M]. 周国平译. 北京: 三联出版社, 1986.
[3]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 维柯. 新科学[M]. 朱光潜泽.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5] 施莱格尔. 旧文学和新文学史(选)宁瑛, 译.张黎, 校. [A] //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6] 席勒. 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 张佳珏译. [A] //席勒文集(第六卷)[M]//张玉书选编.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
[7] 黑格尔. 精神哲学[M]. 杨祖陶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8] 歌德. 威廉•麦斯特[M]. 董问樵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9] 汉密尔顿. 希腊思想[M]. 徐齐平译.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
[10] 谢林. 艺术哲学[M]. 魏庆征译.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
Sophoc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Fate”——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Oedipus’ Tragedies
WANG J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ate was an intrinsic development in the two tragedies of Sophocles: Oedipus, The King and Oedipus at Colonus. In Oedipus The King, the fate was more showed an inevitable force of the external, whi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destiny was a kind of tension. While in Oedipus at Colonus, Oedipus began to re-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city, and finally he reached the reconciliation with the fate.
sophocles; oedipus; tragedy; fate; nature; ration
book=16,ebook=253
I106.3
A
1672-3104(2010)04−0127−05
[编辑: 胡兴华]
2010−04−02
王静(1974−),女,江苏南京人,讲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