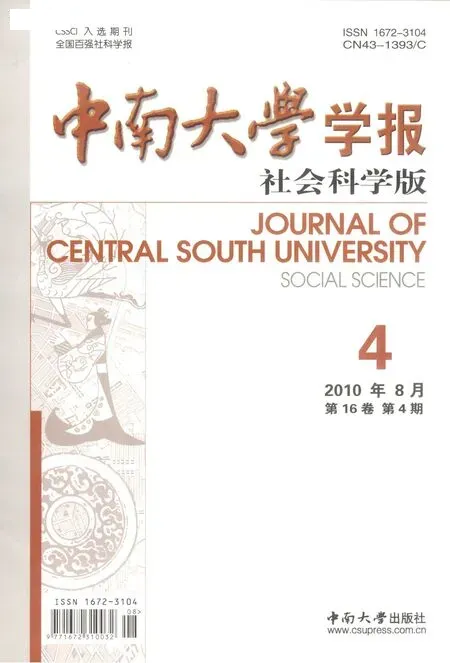肯尼迪在美苏古巴导弹系统危机中的“战争边缘策略”
张红,刘会宝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上海,200062)
肯尼迪在美苏古巴导弹系统危机中的“战争边缘策略”
张红,刘会宝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上海,200062)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事件是冷战期间美苏之间最严重的一次直接对抗,肯尼迪采取了以武力威吓、制造风险、自我克制、准备谈判为特征的“边缘策略”。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追求谈判可能性边界的过程。核时代使得国际危机的处理方式发生变革,在核时代这个常量限定的条件下,博弈双方会控制边际收益,达成利益均衡点并缓和危机。
肯尼迪;赫鲁晓夫;战争边缘策略;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国际危机;边际成本原理
在处理国际危机事件时,各方的决策者都是理性的行为者,①[1]在理性行为体模式中,“国家作为单一的行为体,以人类的理性计算进行选择。根据这一模式,决策者设立的明确政治目标及其优先次序,选定实现目标的手段,并设想各种选择的结果”。②[2](37−39)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在论述霸权战争时指出“这些问题被概括成理性的成本/收益估算。在某一点上理性的确是适用的。政治家无论是明示还是暗示都在进行理性的估量,然后试图让国家的航船沿着这条航线行进”。[3](204)这就使得在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追求谈判的可能性边界,在这个可能性的边界上,决策者往往通过不同的方式寻求己方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均衡点,这个均衡点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不断移动,各自都努力使得这个均衡点倾向于自己的一方,但是都不会离开可能性边界。在国际危机事件中,这个模型有一个常量前提,即双方都拥有足以伤害对方的强大能力和禀赋特征,这个特征是静态的,是双方进行博弈时理性决策的限定前提。
肯尼迪在美苏古巴导弹危机中采取的“战争边缘策略”就是综合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在保证不突破常量前提的情况下,实现利益均衡的最大化。“战争边缘策略”在行为上表现为边缘军事行动,就是制造风险、增加不确定性和通过强大军事恫吓把对手带到灾难的边缘。肯尼迪的这一策略表现出了三个变量特征:第一,军事和舆论的威胁与恫吓;第二,自我克制;第三,寻找途径准备谈判。在核时代具有毁灭性的常量限定条件下,武力威吓度与理性度的此消彼长关系构成了一个斜率为负的等成本曲线,这条曲线与谈判可能性边界有一个切点,这个切点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最终形成,边界内的A点虽然是双方可以承受的,但是谁都不愿意付出,因为没有收益,或收益很小;边界外的B点超出了任何一方的承受力,因此双方都支付不起,即核灾难的结局。博弈的最后是均衡点E点,见图1(笔者根据经济学中边际成本的原理制作)。

图1 “战争边缘策略”的边际成本示意图
一、军事威胁与舆论恫吓
“战争边缘策略”的本质就在于制造风险,这个风险应该大到让对手难以承受的地步,从而迫使对手按照己方的意愿行事,使得博弈双方的均衡点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变动,这是基于成本/收益估算的理性驱动的结果,属于交易前的行为特征。
1962年7月,赫鲁晓夫已经开始向古巴运送导弹和军事技术人员,而且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从7月中到危机爆发之前,苏联动用了超过85艘船只,从不同港口开行了183次以上,向古巴共运送了42枚中程导弹及其全部发射装置,162枚核弹头,42架伊尔-28型轰炸机,还有大批防空导弹及43000名苏联军人”。[4]1962年8月份西德情报局向美国递交了第一份有关古巴导弹的情报,尽管美国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但是由于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还是做出了相应的反应。一方面,通过广播严正声明不能容忍苏联把进攻性武器引进古巴,另一方面采取了危机的预防性措施,即“美国在古巴周围实施了紧密的空中和海上巡逻,特别对苏联过往轮船进行侦察”。[5]此外,1962年9月21日,美国军方制定了三个紧急行动计划,分别为Operations Plans 314-61、316-61以及312-62,并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就危机的形势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了分析,指出此次行动的使命是对古巴进行海上和空中封锁,以使古巴的共产主义经济崩溃。[6](435)这是肯尼迪政府“边缘军事行动”的最初步骤。
1962年9月24日,总统特别助理施莱辛格就导弹危机问题向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凯森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三点建议:“(1)建立一个靠近古巴的空中与海上侦察系统;(2)控制来自古巴的旅游,资金和舆论宣传;(3)签发一个由加勒比地区各国政府签订的联合声明,以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古巴侵略和发展危害加勒比地区安全的军事能力。这些措施首先是针对卡斯特罗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侵略行径。由于这种威胁仍然还不切实,除非古巴人失去了理智,因此我们的措施只是象征性的。”[6](437)从这个备忘录可以看出,肯尼迪政府把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看作涉及国家安全的高度。美国在处理这一事件的特点是:军事上的准备、舆论上的宣传和威吓相结合。这充分表明军事的直接冲突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作为理性的决策主体,美国政府充分地意识到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特别是核冲突的后果有可能付出高昂的成本,而获得甚至是零的收益。
1962年10月9日14日,肯尼迪派出U-2侦察机对古巴西南部进行了侦察,“U-2飞机在古巴上空的侦察任务总计6分钟,拍摄照片928张……,照片显示,在圣克里斯托尔地区发现了1个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基地,在瓜纳哈伊地区发现了2个中远程弹道导弹发射基地。另外,3个中程弹道导弹基地正在建设中,还发现21架伊尔-28中程轰炸机”。[6](11−12)1962年10月15日,四十多艘军舰和四千多名海军陆战队在美国南部和加勒比海地区开始了代号为“PHIBRIGLEX-62”的两栖登陆演习。[6](2−3)这次演习就是针对苏联造成的危机的一种武力示威和恫吓。1962年10月16日11时45分,肯尼迪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特别会议,并成立“特别小组”,命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执委们不断的开会研究对策,详细考虑了一系列的可能的行动:什么也不做;向联合国投诉(这一行动实际上等于什么也不做);实施封锁或隔离(这是实际选择的方案);向古巴导弹基地发动外科手术式空袭;先发制人,向苏联发动一场全面的核打击。肯尼迪最终没有选择单纯外交途径,“肯尼迪对单纯的外交途径不感兴趣,考虑到国内政治方面的要求和国际方面的影响,他认为进行一场军事行动对他个人的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都有利”。[7]在探讨军事行动的选择问题时,肯尼迪也没有采用麦克纳马拉所提出的“外科手术式”空袭和大规模轰炸的计划,而是接纳了鸽派所提出的更为灵活的海上封锁计划。“1962年10月21日肯尼迪做出最后决定:在海上对古巴进行封锁,同时准备空中打击和两栖登陆行动”。[6](26)
1962年 10月 12日联合参谋本部业务司司长Unger给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秘书 Nitze的备忘录上,涉及主题为有关古巴的政治和军事行动。[6](13)紧接着1962年10月15日,在美国东南部以及加勒比地区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两栖军事演习,“包括四十多艘军舰和四千名海军陆战队的美军在美国东南部和加勒比地区按照原计划开始了代号为“PHIBRIGLEX-62”的两栖登陆演习,一直到20日停止。演习的目标是推翻假象的独裁者“Ortsac”,即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名字的反写”。[6](2−3)
上述档案材料显示的都是肯尼迪在发现古巴存在进攻性武器和弹道导弹基地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反应,这种反应有舆论层面的,也有军事行动。一方面结合舆论的宣传,达到道义的高地;另一方面是做好应急准备,通过军事演习对古巴和苏联的示威和武力恫吓,目的是向苏联传达一个信息,即:美国会不惜一战来保卫加勒比地区的安全。这是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采用边缘政策的重要步骤,也是“战争边缘政策”的第一个变量特征,即武力和舆论的威胁和恫吓。这是对赫鲁晓夫施加强大的心理攻势,以使博弈的力量均衡点尽大可能向美方移动,通过威吓苏联增加成本,增加谈判的砝码,获得边际收益。
二、理性支配下的自我克制
危机在双方的博弈中不断被推向高潮,双方都在小心翼翼的接近彼此的心理底线。在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形下,肯尼迪充分利用媒体的力量,试图在某一时刻突破苏联方面的心理防线。他利用电视讲话的公开手段动员战争威吓苏联。1962年10月22日下午7时,肯尼迪发表声明,“过去一周来美国发现古巴有进攻性导弹基地和运载核武器的伊尔-28型轰炸机的基地,这构成了对所有美洲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最明显的威胁,这种突然且秘密做出的决定是出于预谋的挑衅性的不正当地改变现状的行动”,“我已经下令对运往古巴的一切军事装备加以严格隔离。一切船只如果发现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必须开回去。呼吁美洲国家组织采取行动,要求在联合国监督下拆除和撤走进攻性武器”。肯尼迪还表示,“封锁只是初步措施,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紧急行动计划:将出动1080架次的战斗机进行空中攻击,并且,一个总数为18万人的登陆部队也被集结在美国东北部港口。20日,已命令美国在全世界的武装力量都处于戒备状态,海军部署了 180艘舰只进入加勒比海。B-52轰炸机队奉命载足原子武器进入空中,一架着陆,立即有另一架飞上去顶替”。[8]22日,肯尼迪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公开了处于秘密状态的危机,并宣布其隔离措施:加强对古巴本土的监视;宣布在古巴的发射的任何弹头都将被视为是苏联对美国的攻击,并对其进行报复性的还击。[9](552)
23日上午10时,美国国家安全会议执行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的第一阶段强调了苏联在古巴安装进攻性导弹及其基地的强有力的证据;随后会议讨论了业已发展的危机并对所做出的决策进行理性的分析;第三个阶段是对封锁效果的评估,总统询问了中央情报局局长有关对古巴实施封锁(不包括食品和药品)的分析,并且把这次危机与柏林危机进行了比较;第四阶段是关于国防部呈送的报告:总统批准对运往古巴的装有进攻性武器的所有船舶进行封锁,这一文件在下午6时正式生效,并于10月24日成功实施了阻截。[6](47)在这次会议上甚至预言,如果因为某一单一事件引起军事对抗,那么美国将有必要采取措施消除古巴的地空导弹和空空导弹的攻击力。
同日,华盛顿接着召开了美洲国家外长会议,会议以绝对多数票数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支持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所采取的各种措施。23日下午6时51分,美国国务院发给苏联大使一份电报,美方在电报中称“我们所关心的是我们双方在这一事件上都应当保持谨慎,以至于不使这一事件无法控制。美洲国家组织已于今天下午投票表决了关于隔离期的决议,该决议将于格林威治时间24日14点生效,我希望您能及时向您的船只说明这一情况”。[6](52)当晚肯尼迪宣布:“美国海军于24日格林尼治时间下午2时,开始封锁古巴。美国海军在距古巴海岸500海里的海域设立了拦截线,并对苏联通往古巴的空运进行了封锁。”[6](49)而此时,“25艘苏联潜艇与商船仍然朝着隔离线方向驶来,其中两艘装有“进攻性武器”的船只大概两小时后接近隔离线”。[10](271)美国军队的备战级别此时也已经达到比开展战争的等级只差一级,据鲍勃回忆,当时肯尼迪认为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是1/3。当时形势的紧张程度使得赫鲁晓夫精神紧绷,坐卧不安。赫鲁晓夫曾对身边的同志说:“同志们,咱们到大剧院去一趟。现在局势一片紧张,而我们要在剧院露面,我们的老百姓和外国人将看到这个情况,这将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但我们自己当时却惴惴不安的……,因此,我虽然在克里姆林宫,却度过了一个极其不安的夜晚。” [11](2170)
1962年10月24日以后,美国已经正式对加勒比海域实施了封锁。这是对双方的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随时可能发生战争。27日晚,苏联的一艘装载有导弹的“格罗尼兹”号逐渐靠近了拦截线,但是肯尼迪批准放行了。肯尼迪在整个危机期间,还是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慎用武力,包括后来出现的美国侦察机遭到萨姆导弹的袭击,机毁人亡,在这一危机关头,美国联席会议强烈要求对古巴进行大规模的空中打击,并要求在7天后入侵古巴,但是肯尼迪仍然竭力克制,避免任何军事行动。
上述事实表明,肯尼迪政府在做出每一项决策之前都会做出全方位的理性分析,分析任何一项行动可能会产生的一切后果,及其补救措施。而其每一项决策都是试图以强大的武力阵势和边缘军事行动来威吓和阻止不利于自己的敌方行为,以理性的决策达到敌方对施动一方非理性行为的判断。双方最高决策者都保持了高度克制,没有采取直接的军事行为。因理性度降到最低,威吓度上升到最高点的紧急状态下,边际收益将达到最高点。
三、寻找途径,准备谈判
在美国1962年10月24日对古巴附近海域进行海上封锁后,形势有所变化,苏联的部分船只已经改变路线,但是,仍有一些船只在逐渐接近古巴,对于这种形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罗斯托(Rostow)在给肯尼迪的备忘录中提到:“我们要求船只停止通行,并根据决议对其进行搜查;这一搜查命令由我们的军事人员具体操作;如果有船只拒绝接受停止命令或拒绝接受检查,我们将继续执行我们的检查命令,特别注意的是慎用武力,因为如果是运送货物的船只就会造成无辜的伤亡”。[6](57)10月27日下午,美国国务院再次向苏联大使发去电文,主要是向苏方提出美方可以接受的条件,实际上就是在努力争取以谈判的方式解决这场危机事件,电文显示:“(1)你方同意在联合国适当的观察和监督之下从古巴撤走这类武器系统,并答应在适当的安全措施下保证不再将此类武器运进古巴。(2)我方同意在通过联合国做出充分安排之后,确保执行闭关继续承担以下义务:a.立即取消在实行的隔离检查措施;b.保证不入侵古巴。我确信其他西半球国家也不会准备这样做。”[6](95)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肯尼迪做出不惜一战的姿态,目标绝对不是战争。而是以美国战略力量的优势向苏联施压,同时又赋予前景诸多可能性,为赫鲁晓夫留下回旋的空间。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当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向我们通报说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对他进行了非正式的访问,罗伯特声称,‘总统自己不知道如何摆脱困境,而军方向他施加压力,力主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总统非常困难’,‘你们应该考虑到我们国家制度的特点,总统很是为难,即使他不愿意,不希望战争,一场无法挽回的灾祸可能在违背他意愿的情况下发生,因此,总统请求说‘请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难题’”。[11](2171)不难看出,肯尼迪在向苏联施加压力的同时,始终也没有放弃外交努力,在剑拔弩张时刻,他与赫鲁晓夫有着畅通的外交渠道和密集的书信往来。26日,肯尼迪收到了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一个解决危机的方案,即“只要美国政府保证不入侵古巴并解除封锁,那么苏联就从古巴撤回导弹,与此同时,他也警告说,如果出现战争,苏联已经做好了准备”,“10月27日肯尼迪致函赫鲁晓夫,信中表示,苏联必须中断,拆除在古巴的进攻性导弹基地工程,撤走导弹。作为交换,美国政府将停止隔离封锁行动,并保证不入侵古巴”。[10](271)同日,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信中指出,“我们同意从古巴撤出您认为是进攻性的手段。并在联合国宣布这项保证。美国代表要发表声明:美国方面考虑到苏联的安全和焦虑,将从土耳其撤出自己的这种手段”。肯尼迪于当日回复了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在联合国的观察和监督下把部署在古巴的武器系统撤出,并保证不再把他们运入古巴,美国同意马上取消现在的隔离措施,提供不进攻古巴的保证”。[6](91)赫鲁晓夫在27日晚至28日,一直讨论对肯尼迪的回信问题,气氛紧张到甚至最后部分没有校完,就开始广播了。赫鲁晓夫在回信中说:“苏联已经给自己的军官下达了指示,中止那些您视为进攻性的在古巴的导弹工程建设,并将设备拆卸回国。”[12](295)
四、余论
“战争边缘策略”说到底就是一种威胁增量所带来的效用,同边际递减规律一样,这种效用也是递减的。因为随着威胁的增加,突破常量前提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从而对前景的不可控制性增加。所以,这一策略的要义在于:第一,这种安全或者危险的边缘不是一个悬崖,而是一个斜坡,它是慢慢变得越来越陡峭的;第二,要置对方对前景的反应具有不确定性。基辛格对不确定性威慑作了精辟的论述:首先,就是要使对手(1)对于我们是否抵抗不能肯定;(2)对于我们抵抗的程度或方法不能肯定。其次,设定的“可以容许的”不确定的范围的最低限度必须是不包括让步或进行微弱的抵抗以致鼓励侵略的可能性,最高限度必须是不发出使人相信或者如果被人相信会引起先发制人的攻击的威胁。[13](69−71)
“战争边缘策略”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每一步都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和转机。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制造危险性,以达到符合自己一方利益的某种转机。它不是纯粹的或不留余地的军事行动,也不属于单纯的外交行动,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边缘”行动,且存在一种动态的行动轨迹,施动双方通过变量的调换,以寻求轨迹上的某一点,这一点足以满足自己的效用,而不至于边际收益的负增长,并促使谈判有得以进行的可能。纵观美苏在加勒比海上的危机事件可以看到,美苏双方一直在战争的边缘上滑动,却始终未能脱离一条既定的轨迹。原因在于在这个不断变动的轨迹上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便是核时代塑造的。“在核时代之前,政治家实际上是处于一种赌徒的地位——一个颇具理性的赌徒,也就是说,他愿意拿出其一部分东西和人类资源去冒险。如果他赢了,他的冒险就会被认为是正当的;如果他输了,他也没有把一切输光。换句话说,他的失败是可以忍受的。但是这种作为外交政策的手段的暴力和外交政策的目的之间的合理关系,已经被全面的核战争的可能性摧毁了。”[14](280)
注释:
① 国内有学者撰文指出国际危机管理中的决策并不都是完全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的,而且特别分析了肯尼迪的决策行为,原因是最高决策者的行为往往受到国际权力因素与国内官僚政治的影响。详见参考文献[1].
② 危机管理的决策模式主要有6种值得关注,除了理性行为体模式外,还有组织过程模式、官僚政治模式、领袖和非理性行为体模式、精英态度和错觉模式以及集体动力模式。详见参考文献[2].
[1] 荣正通, 胡礼忠. 国际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J]. 国际论坛, 2007, (1): 1−5.
[2] 杨洁勉. 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 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3] 罗伯特·吉尔平.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4] 柳植. 一场惊心动魄的核对抗——美苏解密档案展示的古巴导弹危机[J]. 百年潮, 2003, (3): 63−69.
[5] zak personal memorandum to N. S. Khrushchev[Z].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中心档案, 140962.
[6]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FRUS)·1961-1963·Volume XI·Cuba [Z].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7] 韩洪文. 美国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初步反应[J]. 军事历史, 1997, (5): 32−37.
[8] dobrynin .personal memorandum to N. S. Khrushchev[Z].华东师大冷战史中心资料室, 221062.
[9] 阿瑟·施莱辛格. 一千天: 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M].北京:三联书店, 1981.
[10] 孙恒. 肯尼迪传[M]. 北京: 华侨出版社, 2007.
[11] 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三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2] 方连庆. 国际关系史·战后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3] 亨利·基辛格. 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2.
[14] Hans J. Morgenthau. Western Values and Total War, Commentary [M].New York: Commentary Inc., 1961.
Kennedy’s “brink-of-war strategy” in Cuban missile crisis between the U.S. and Soviet Union in 1962
ZHANG Hong, LIU Huibao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Cuban Missile Crisis in 1962 was the most serious direct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S.A. during the Cold War, when President Kennedy took “brink-of-war strategy” characterized by forces, risks, self-restraints and being ready to negotiate. During the crisis,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to pursue the boundary of negotiations. The nuclear age leads ways to handle international crisis to revolution. Under the constant conditions of the nuclear age, both players of the game controlled their marginal benefits in order to reach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and thus ease the crisis.
Kennedy; Khrushchev; brink-of-war strategy; Cuban Missile Crisis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S.A.; international crisis; marginal cost principle
book=16,ebook=215
D815.5
A
1672-3104(2010)04−0035−05
[编辑: 颜关明]
2010−02−04
张红(1978−),女,安徽东至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大国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