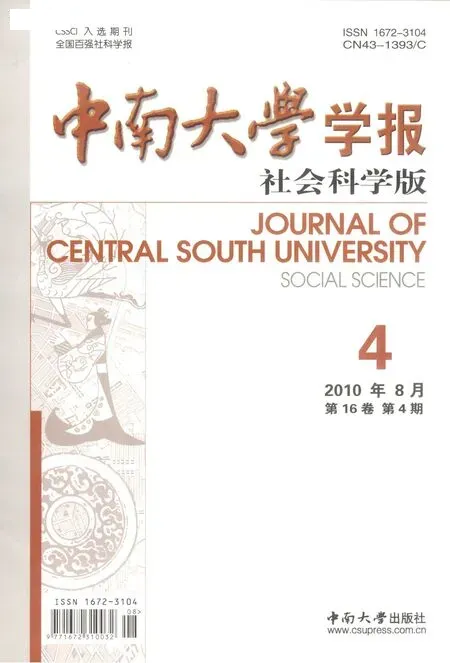经与权的统一:孟子之礼再考察
李友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经与权的统一:孟子之礼再考察
李友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孔子、郭店儒简强调礼本于情、礼以情为据。孟子受礼学历史传统尤其是郭店儒简思想的影响,同时因其礼学主要根于其性论,而性论所彰显的人之自主性、能动性与向善性,致使在以“男女授受不亲”为大常原则的同时,又主张“嫂溺援之以手”的权变性与灵活性,从而体现了礼仪与人情的典范式结合,是经与权的统一。对于礼而言,我们应该既要行乎表,更要谨于内,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得将礼之功能真正而完全地发挥出来,以达致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目标,使礼由礼仪之礼而向礼义之礼转进。所以,任何礼文仪节的背后都存在着深层次的礼意,都是人之恭敬、爱憎等情感的适当表达,因而谨守礼节亦必须以内在的情实为根基,否则就会流于肤浅形式;相反,只要有助于真情实感的表达,也不必过于拘泥于某种固有的形式规定,可以因情而变通,此当是对于孟子“经与权”之礼学思想的合理诠释。
豊;禮;郭店儒简;孟子;礼仪;礼义
从哲学史、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尽管孟子的学术兴趣主要着力于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之处,但是他的思想却是受了“即生言性”理论视角的影响的,其对于人禽之间的共性亦未避而不谈与断然否定。实际上,他的性善论思想即是以人禽之间的相同性为起点的,如果没有对于人禽之间共性的充分了解,就难以对于人禽之间的差异性有着如此深刻的认识。换句话说,尽管孟子多关注人禽之别与人的道德性,但他还是承认人与禽兽之间是有着很多相同的地方的。所以,由此可知孟子并没有完全摆脱从自然本性来看待人性、即生言性的思维模式,只不过虽然他亦承认人性是生而有之的,但他不把生而有之的所有本性都看作人性,而只把人有别于禽兽,决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部分天赋本性看作人性罢了。
同样,在礼学方面,孟子亦未能完全摆脱或者说是自觉接受了历史传统尤其是郭店儒简思想所带来的影响,因而他在以“男女授受不亲”为大常原则的同时,又主张“嫂溺援之以手”的权变性与灵活性,从而体现了其于哲学史、思想史上礼仪与人情的典范式结合,是经与权的统一。
当然,在他的思想体系当中,礼并非似荀子那样多指外在的礼仪制度,而更多的侧重于内在的仁义礼智之礼,是谓礼义。很显然,这种特点自与他的性论思想相关联,是对其性论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与深化,因为,孟子之礼本来就是源于其心的四端之一的,是其性论内容的一部分。故而,我们从对礼的文字考辨入手来研究与其性论密切相关且于哲学史、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礼学、礼论,并以哲学史、思想史的学术视角来审视之。
一、礼字考辨
礼字,于古文中通常会有两样写法:一为“豊”,一为“禮”。那么,这时有个问题就出现了,礼字于古文中为何通常会有这两样写法,在它们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而在其背后又会有着怎样的思想变化与文化内涵? 这是我们在对其进行考辨的过程当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惟有立足于哲学史、思想史的视野高度,才能更好地来解释与揭示这些问题,从而对于礼学思想于史上的传承与演变作出更好的梳理与探讨。
当然,这是仅从笼统意义上而言的。如果再仔细研究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字体、字形演变之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礼字于甲文一期、[1](15818片)三期[1](3629片)当中,其字形均不从示,字形皆为豊。不仅如此,礼于卜辞亦不从示,①字象两玉盛于豆中,以示献于神主,乞求佑福。本义是事神致福。[2](13)故而,《说文》亦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诚如上文所言,既然礼字于甲文一期、三期以及卜辞当中其字形皆不从示,②[3](15)那么礼字为何先不从示而后来又从示呢? 这是个很有意思亦值得研究的古文字现象。
从字体结构上来看,“豊”与“禮”之间的最大差别便是有无“示”之部件,因而,对其的考察与辨析自是从“示”字本身开始。示,甲文字形为或,学界多释为设杆以祭天,以象征神祇或象神主牌位形。与之相似,陈济先生亦认为,在卜辞祭祀占卜当中,示为天神、地祇、先公、先王之通称。卜辞亦用I(壬)、(工)为示。[2](7)或许,正是因为甲文“示”字多与祭天祀神有关,因而《说文》便将其注为:“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由此可见,从示之“禮”字多与其时祭天事神之仪轨相关。因而,此“禮”字当是殷商时期浓厚的宗教氛围之反映与表现。与之不同的是,“豊”并不从示,且多现于甲文一、三期与卜辞当中,从时间上来看,它的出现要比“禮”字早一些,其出现的时间当在殷商前期或者更早。毕竟,祭天祀神的礼仪制度与文化并非自始即有的,其出现、发展与演变必定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以说“豊”之出现要早于“禮”当是可信之论。③[4](45)
二、郭店简:礼作于情
上文,我们对礼字作了比较简单的考释,并对于“豊”与“禮”之间的差异性进行了一定的区分与辨别。接下来,我们就要着手解决礼于史上的起源问题了。对于这个问题,学界的看法并不尽一致。下面,我们就将对此细疏之。
关于礼的起源,《礼记·礼运》曾明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也就是说,礼的最初乃始于饮食活动。在原始时代,人们把黍米放在石板上用火烘熟,把小猪放在火上烧烤,在地上挖坑盛水当作酒缸,然后用手捧着饮用;抟泥烧制鼓槌,瓦框蒙皮做鼓,即便是这样简陋,亦可以向鬼神致自心之诚敬。既然其时之工艺、器皿皆如此简单、简陋,那为何还可以经此而向鬼神致敬呢? 盖远古之人,内心少受染着而较为纯净,又对于鬼神深信不疑,因之而于内心深生诚意,从而此“诚”在祭祀鬼神的活动当中便可进一步生发为“敬”,故可向鬼神致敬。于此可知,传世文献对于礼之起源的看法,无外乎宗教信仰(主要表现为事神致福)[5](15)与人情[6](442)。其实,尽管学者多从差异性来看待鬼神信仰与人情,但这两者亦非全然不同。实际上,礼本是因人情表达、呈现之需要而出现的,即便是学者所常言的鬼神信仰,其各种繁杂祭祀仪式的出现亦是因人向鬼神表达、呈现内心之诚而制定的,④[7](30)故而《礼记·郊特牲》云:“君再拜稽首,肉袒,亲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尽也”。⑤所以,《礼记·乐记》才会总结性地宣称:“著诚去伪,礼之大经。”
只不过,本于人情而制定的礼仪,当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了一种仪式化的规则的时候,它便具有了不容置疑的权威,从而亦就渐渐远离了个人的情与知;当这种情形随着类似观念的不断累积与叠加,久而久之就在人们那里形成了心理定势与历史传统,在这种历史情境下,人们就不再追问它的依据何在。[8](132)盖因为此,后世的人们便以为礼本于宗教信仰与鬼神祭祀,⑥殊不知,即便是宗教信仰与鬼神祭祀亦是因人情、人心之需而生的。所以,礼的起源,从表面上看是源于宗教信仰与鬼神祭祀,但从根本上而言,实源于人情。因而,礼的出现,实乃源于人情也。
《管子•心术上》云:“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郭店简《性自命出》则曰:“礼作于情”(简18);《语丛(二)》亦曰:“情生於眚,礼生于情。”(简1)可见,其时的人们对于礼源于情的说法还是深以为然的,而且对于人情的考量亦是制礼过程当中所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礼记·礼运》就曾把人情作为制礼的依据与目的:“夫礼,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所以说,礼源于情的说法并非突现之物,而是源自影响深远的历史传统。
我们知道,古人在相见、聘问等重要场合,常常执币帛以表诚敬,比如《周礼·天官·大宰》即云:“六曰币帛之式。”对此,郑注:“所以赠劳宾客者。”《阳货》亦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将其注为:“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可见,币帛对于古人的日常交往与人情往来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同时亦是人际情性之表征。所以,文献典籍对此亦一再申述:
幣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离志必有以逾也。(上博简《诗论》简20)
币帛,所以为信与征也,其词宜道也。(郭店简《性自命出》简22)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礼记·曲礼上》)
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礼记·坊记》)
礼之先币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后禄也。(《礼记·坊记》)
这说明币帛之于古人并非仅为实物,而且还富含强烈而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文化内涵,同时亦是人情往来之载体与表征。当然,此亦与礼源于情大有关联。言及礼,我们将无法绕开孔子对于礼的态度与主张。据前文研究我们知道,孔子之思想体系是以其仁学为根基的;同样,作为他的礼学思想,孔子亦是立足于其仁学来审视与探讨的。正因为孔子主张把礼建立在仁的基础之上,所以才会有“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之慨叹。⑦故而,当孔子在具体说明礼之依据的时候,仁的原则就表现为了内在的情感。[9](75)也就是说,在孔子的眼里,人们内心真实不虚的情感便成为了其制礼、行礼之根本依据,所以他一再告诫他的弟子:“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显然,孔子所注重的并不是礼的外在形式,而是其背后的本质,所以虽然在他这里还没有像郭店儒简那样去强调“情”对于“礼”的重要性,但是在他的思想里的确出现了明显的重情特征。
当然,孔子、郭店儒简一再强调礼本于情、礼以情为据,实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时代特色有着莫大的关系。
据文献可知,春秋以降,随着王权的式微,礼崩乐坏遂成为普遍现象。周礼亦渐渐失去了往日对于人们的普遍约束力。因而,各诸侯国在争权夺利、攻城掠地的过程中对周礼屡僭不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礼原先所含的人情与实意便不复存在,往昔用以表征人情厚重之礼遂变成了各诸侯谋取利益与外交斗争之功利性工具,此时的礼已是有名无实。换句话说,礼在此时已逐渐沦为一种形式,且日渐繁缛与精细,这也表明了礼的不切实际与僵化衰败。[10](66)这时的“礼”多和“仪”连在一起,偏重于外在形式,而对人情实意则有所漠视,此亦与其时争权夺利、社会失序、道德沦丧之社会背景有关。在这种情境下,有些明智之士便洞察到了问题之所在,进而力主把礼的发展重新拉回到本于情之正常而合理的轨道上来,《左传·昭公二年》有言:“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从而将偏于外在形式之礼与人之品德——忠信联系在了一起;《国语·周语上》则云:“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于此,显然将礼之外延大大扩大了,除了原有对于外在礼仪形式的指向性之外,还将人的重要道德品性都纳入到了礼的规范之中。因而,自此可知,春秋晚期人们对于礼关注的重心已渐渐由外在仪式规定向人伦道德转进了。盖因为此,所以孔子在总结春秋以来礼的变化的时候,就特别注重发掘礼的内在精神,即礼之伦理原则与道德内涵,故而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显然,在他看来,礼乐绝不仅是玉帛钟鼓一类的外在形式,更是对于人情的表征与彰显。[10](72)同样,作于战国前期的郭店楚简亦当是对于其时社会现象与历史情状的映现与反拨,是对“礼之文”的深入批判与有力舍弃,更是对先前“礼之本”的回归。
或许,正是因为郭店简文原作者目睹了当时社会堪忧之现状而有感而发,从而在郭店简中一再强调与赞肯人们那自然而然的真实不伪之情性的可贵。《性自命出》说:“信,青之方也。青出于眚”(简 40),即是对于人之真情的赞肯。简50~51亦曰:“凡人青为可悦也。苟以其青,虽过不恶;不以其青,虽难不贵。苟有其青,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于此,对于真情、实情的肯定与重视更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将其看成了与人交往、做事的出发点与行为依据。
另外,郭店儒简还对那种有意地为孝、为悌的过分行为进行了强烈地谴责与批判:“为孝,此非孝也;为悌,此非悌也。不可为也,而不可不为也。为之,此非也。弗为,此非也。”(《语丛一》简55~58)所以《语丛三》即明言:“父孝子爱,非有为也。”(简 8)不仅如此,即便是那些故意行义、为善的行为也都不是真正的义和善,这正是《语丛一》所同样强烈反对与批判的:“义无能伪也。”(简53)“有察善,无为善。”(简84)总之,“人之不能以伪也”(《性自命出》简37),否则“求其心有伪也,弗得之矣”。(同上)由此可知,郭店儒简对于人们那些“有为”、“人为”的行为是持否定与批判态度的,因为刻意去做、有意为之的行为都是违反人们自然情性的,因而是虚伪与不真实的,“儒家所重视的是真实而无矫饰的自然情感,这才是人的本真存在。”[11]
三、孟子礼辨:经与权
正如我们于前文中所说,孟子之礼虽对历史传统有所继承,然而,由于其礼学主要根于其性论,而且其礼即源于其心的四端之一的,实为其性论内容的一部分,因而,其礼实由仁义礼智之礼生发、延伸而来。换句话说,其礼论乃是其性论的生发,而其性论则为其礼论的根基。总体而论,孟子之礼既是礼学于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因而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其礼之常即多因于此;⑧同时,因其性论所彰显的人之自主性、能动性与向善性,致使其礼又具有相应的权变性与灵活性。于是,孟子之礼因在经与权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张力,从而使其已经具备了能够得以流传后世的某些普适性之因素与价值。可以说,孟子之礼实为礼仪与人情的典范式结合,是经与权的统一。
当然,最能体现孟子之礼经与权关系的典型性话语便是:
淳于髠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
显见,淳于髡与孟子之间的这段对话字数虽不甚多,然,所包涵之内容与意蕴却让人有很多话要说。从淳于髡的问话可知,作为一种常礼男女不能亲自用手来接送东西(“男女授受不亲”为状语后置句式,实乃“男女不亲授受”),这自是由过去所沿承下来的,并很可能至此已成为了一种影响人们心理至深之传统,所以他才会向孟子有此一问。当然,淳氏此问并不是其发问的真正目的,它不过是其引诱孟子上当的逻辑圈套罢了,他当然知道孟子会给出肯定的答复,因而接下来的一问才是他真正想问的,⑨亦是其心中最大的疑惑。只不过,淳氏的问法让人不由地想起了孟子与告子之间的论辩,⑩他与孟子向告子发难的做法如出一辙。只是,孟子与告子所论辩的内容是到底何为人之性,而于此辩驳的则是礼之外延的问题。从孟子对礼的创造性理解来看,此时的孟子其性论当已较为成熟,起码比其与告子辩论的时候要成熟得多。他对于“嫂溺不援”的做法斥之为“豺狼”,而对“嫂溺援之以手”则称之为“权也”,由此可知,他对“嫂溺援之以手”所持的认肯之态度无疑源自于其性善论,盖因为此,所以他才会将“嫂溺不援”的做法斥之为“豺狼”,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其性论当中的恻隐之心与是非之心相背离的。因而,从时间上来看,孟子与告子之辩当早于其与淳于髡之辩。
事实上,淳于髡之困惑亦是其时多数人的困惑,这说明当时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将礼仅仅视为外在的形式与规定,而对礼之包容性与开放性有着更多的心理期待。所以,淳氏才会提出“嫂溺则援之以手乎”的疑问,实际上,由此他已经意识到了礼之形式与规定的保守性、僵化性与人之情性之间的冲突以及协调的可能性了。就哲学史、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孟子生活的时代发出了向“礼之本”回归的声音,乃是时代要求与现实需要的结果。
盖因为此,所以郭店儒简便先于孟子发出了时代的声音:“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后之序则宜道也。”(《性自命出》简18~19)简文的意思是说,礼的制作本始于人情;因而,如果有变化,则要根据事物的形势权宜处之,其先后顺序当以合宜为依据。换句话说,郭店儒家所强调的与之后的孟子所主张的,从根本上而言并无二致:虽然礼为人行为、处事之规范,但礼不离人情,因而,若有变化则当以实际形势与合宜为根本之依据与目的。所以,孟子才掷地有声地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显然,睿智的孟子亦已洞见到了礼仪与人情、形势变化之间所存在的冲突,以及化解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即“权也”。由此,原本于春秋晚期因其时社会背景与现实需要而使当时的人们过于注重礼的外在形式与规定,从而使其流于诸侯之间谋取利益与外交斗争的工具与牺牲品,礼于这一时期遂成为礼仪之礼,后又经由孔子、郭店儒简原作者及孟子等人的不懈纠偏之努力,而使其渐渐向“本于人情”回归,从而使礼又由礼仪之礼而向礼义之礼转进,而这一转进的最终完成则是在孟子那里实现的。
据前所述,孟子之礼论虽对历史传统有所沿承,但主要还是源自于其性论,不仅如此,因为其性论还将礼与义联系了起来。当然,礼与义本皆有外在之指向性,但于孟子,礼与义却被内化为了人之心性的内容。因而,对于孟子而言,礼与义在其性论基础上便实现了对于外在与内在两种思维向度的彰显,而关于这两种思维向度的关系,约略可以和经与权之关系相当。
然而,尽管对于礼仪与人情、形势变化之间的冲突,孟子提出了以“权”为化解之道,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孟子没有了所坚守的根本之原则与底线,本来经与权就是辩证地存在着的,因而任何权变都不会没有一定的限制与规定的,否则,孟子便成了孔子所斥之“乡愿”了。其实,孟子所言之“经”,从表面上看为外在之礼仪形式与规定,但从根本上而言,则实为人之道德本心,具体到《孟子》文本上而言,则可以用“义”来论之,《孟子•离娄下》即明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对此,朱子释曰:“大人言行,不先期于信果,但义之所在,则必从之,卒亦未尝不信果也。尹氏云:‘主于义,则信果在其中矣;主于信果,则未必合义。’”[12](298)其义甚明。对于孟子而言,言与行皆为人之外在表现,与人之内心并无直接、必然之联系,因而,他才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义与言、行就不同了,它乃为心之端长养、扩展之产物,是人性内容的一部分,就具体实践而言,它实为人之动机与目标,因而,孟子宣称“唯义所在”。可见,孟子“并非是提倡人们言行不一,而是坚持信的道德标准,使守信建立在坚实的道德正义基础之上”,[13](90)其所注重的恰恰是人的行为动机,而不是人的行为过程与最终效果,此与西方哲学家康德所强调的“绝对律令”思想是有着相似之处的。
总之,从哲学史、思想史的角度而言,礼之内涵与外延既包括外在的威仪、礼仪,亦包括内心的敬畏、诚敬,两者共同统一于礼之中,进而又共同支撑着礼,须臾不可分离。对于礼而言,我们应该既要行乎表,更要谨于内,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得将礼之功能真正而完全地发挥出来,以达致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目标,此正如王夫之所说得那样,“君子秉礼以修己,先王制礼以治人,皆原本于内外交尽之盛德,而器非虚设。”[14](582)所以,任何礼文仪节的背后都存在着深层次的礼意,都是人之恭敬、爱憎等情感的适当表达,因而谨守礼节亦必须以内在的情实为根基,否则就会流于肤浅形式;相反,只要有助于真情实感的表达,也不必过于拘泥于某种固有的形式规定,可以因情而变通,此当是对于孟子“经与权”之礼学思想的合理诠释。
注释:
① 据王国维先生《观堂集林》的考证,殷墟卜辞中已习见“礼”字,作“”。又、、、实一字,特所出有先后而已。
② 陈济先生认为,“卜辞用豊为禮”。
③ 据何琳仪先生研究,九里墩鼓座上所刻有的六国古文“礼”字与《说文》古文“礼”字字形基本相同,均从“示”,为左右结构,很显然,后者为小篆文,前者虽已基本被篆化但仍呈现为金文的某些特点。相关字体字形可详见参考文献[4].
④ 王公山先生亦说:“由于祭祀之人,对神的恭敬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这些礼仪自始至终,一直是诚心诚意,没有丝毫的做作,惟恐亵渎神灵而所求无果。仪式的背后,确实能够反映出上古先人对待神灵的态度,那就是真诚而不虚伪。”
⑤《礼记•礼器》曰:“君子之于礼也,有所竭情尽慎,致其敬而诚若。”《礼记•曲礼上》亦曰:“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其意近是。
⑥ 许氏《说文》即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当属此类情况。
⑦《礼记•礼器》亦有言:“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盖源于此。
⑧《荀子·天论》即有言:“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于此,由荀子将礼义与日月、水火、珠玉相提并论可知,礼对于人之日常生活与行为践行是何其重要,无怪乎将其视为大常。
⑨ 不仅如此,他还希望凭借此问能够得以实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目的。
⑩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
[1] 郭沫若. 甲骨文合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2] 马如森. 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7.
[3] 陈济. 甲骨文字形字典[Z].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4.
[4] 何琳仪. 战国文字通论(订补)[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5] 王国维. 释礼·观堂集林·卷六·王国维遗书·一[M].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6] 李珥. 圣学辑要·二[C]//栗谷全书·一·卷二十. 汉城: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 1985.
[7] 王公山. 先秦儒家诚信思想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8]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C]//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9] 王博. 早期儒家仁义说的研究[C]//赵敦华. 哲学门·总第十一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0] 李亚彬. 道德哲学之维——孟子荀子人性论比较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11] 蒙培元. 人是情感的存在——儒家哲学再阐释[J]. 社会科学战线, 2003, (2): 1−8.
[12]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3] 傅礼白. 中华伦理范畴——信[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4] 王夫之. 船山全书·第四册[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6.
Flexibility of doctrine vs reality—a research on Mencius’ Li
LI Yougu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Confucius, Guodian Rujian regarded sentiment as Li’s(礼). Mencius was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y and tradition, especially Guodian Rujian, while its main roots are in their study of ritual theory, which it reflected activity and goodness. So, he didn’t only insist on the principle of “not deliver something by hand”, but also the variability and flexibility of “rescuing somebody by hand”. For the ceremony, we must move in the inner, then function better which should be real and ritual played out completel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nfucian “Saint and Emperor”. Therefore, what behind Li exists the appropriat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The contrary of Li, they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expression of true feelings, which not adhere too rigidly, and which should be the most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Li of “Jing and Quan”.
Li; Li; Guodian Rujian; Mencius; courtesy; righteousness
book=16,ebook=209
B2222.5
A
1672-3104(2010)04−0005−05
[编辑: 颜关明]
2009−12−22
李友广(1978−),男,山东莒县人,中国人民大学200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先秦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