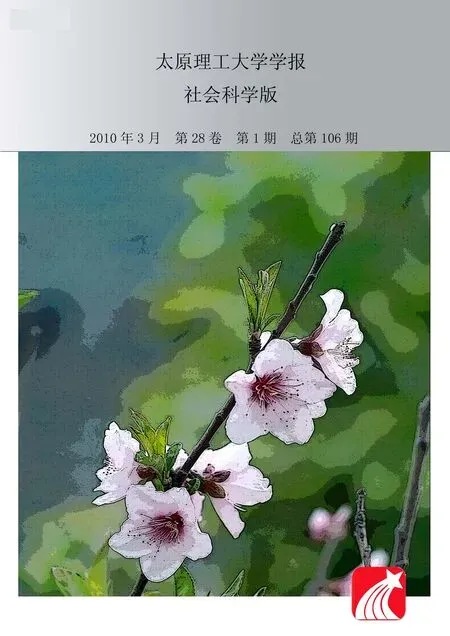中国传统社会中“户”的法律意义
周子良
(山西大学 法学院,山西 太原030006)
户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普遍而又长期存在的现象,而且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张晋藩先生所著《清代民法综论》[1]、李志敏先生的《中国古代民法》[2]、姚秀兰女士的《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3]与张晋藩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法通史》[4]、叶孝信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法史》[5]、孔庆明等先生编著的《中国民法史》[6]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户的法律意义,还有一些相关研究。[7-8]此外,台湾的戴炎辉先生,日本的仁井田 陞先生、滋贺秀三先生[9]等也关注过户的法律性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对“户”的含义及其在法律上的存在形式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户的含义
在解析中国传统法律中 “户” 的含义之前,应当对“家”的含义作一初步的分析。
(一)家的含义
中国古代的家不仅是国之基础,而且是古代中国人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港湾。[10]若抛开家,就无法理解中国社会。
古代中国的家是一个范围难以确定而又具有多重含义的范畴。就家的范围而言,可伸可缩。家可以很小,也可以大到数不清,天下可成一家。[11](p26-27)就家的含义,《辞源》和《辞海》分别有11和14种解释。虽然在不同的语境下,家有不同的内容,但其最基本的含义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
广义的家,指家族、宗族。何谓家族、宗族?《尔雅·释亲》云:“父之党为宗族。”家族和宗族均由同一始祖的男系后裔所构成,因此,“家族,又称宗族。……家族就是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若干世代相聚在一起,按照一定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12](p1)家族有大有小,形式多样,但无论什么样的家族,都是由狭义上的家所构成。《北魏令》:“百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北齐河清三年令》:“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百家为族党。”由此可知,族由家成。
狭义的家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家庭大致相同。家主要指家庭,应该是家的本义。“家”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说文·家》中说:“家,居也。从宀,豭省声。”但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不赞同许慎的说法。虽然许慎与段玉裁对家有某些不同的理解,但都承认家指“居”,许慎认为家“从宀”,而段氏则主张家“从豕”。段氏认为,家之本义“乃豕之居也”,但此论值得商榷。从家的字形看,家就是屋下有豕。罗常培先生推测说:“中国初民时代的‘家’大概是上层住人,下层养猪。”[13](p10)此种观点是有道理的。
推想古人造字的本意,应当是假借“豕之居”而指“人之居”,即家庭。《玉篇·宀部》:“家,人所居,通曰家。”西周初年,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了以“家”计数的记载。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令簋》铭文云:“(王)姜商(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诗经·国风·桃夭》里的“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曰:“有夫有妇然后为家”。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田法》,在记载战国前和战国时授田的情况时说:“五十家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14]其中的家,均指家庭。不过,中国早期乃至中国古代的家庭一般要包括父母、自己和子女三代人。瞿同祖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大概一个家庭只包括祖父母,及其已婚的儿子和未婚的孙儿女,祖父母逝世则同辈兄弟分居,家庭只包括父母及其子女,在子女未婚嫁以前很少超过五六口以上的。”[15],[注]但也有家有百口的现象。《魏书·卢玄传》载:卢玄之家“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不过,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并非多数。见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卷13)[M].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将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家大致分为了家族和家庭,但也要看到,中国古代“最小的家族也可以等于家庭”[11](p39),家族与家庭有时会重叠在一起。
中国古代狭义之家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因婚姻、血缘或收养等关系,由祖父母、父母和已婚或未婚子孙等组成,拥有一定数量财产的团体。家主要由亲属成员组成,但也不限于完全都是亲属成员。家庭内的成员同居共财,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11(p39),15,16]家庭不仅是生育单位,还是生产和消费单位。
从广义上来看,家还是古代国家的基础。国只是家的放大,君则是父的延伸,忠即是孝的位移,故此,儒家强调“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悌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其中,孝又是核心。在中国古人看来,孝不仅限于生前对父母或祖先的“养”和“敬”,还包括父母或祖先死后的“葬”与“祭”。[注]以永佃制为例,佃户永佃到的土地,其用途也不限于耕作,还可以作为家族的坟地。将父母或祖先葬在自己永佃的土地里,或自己认为的风水宝地里是孝的又一种表现。例如明代崇祯八年(1635年)的一份卖山契。详见卞利.江西地区永佃权产生的时间问题考辨[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3):74。中国古代也不缺乏“为权利而斗争”的事实,但都是为自家而不是个人的权益而斗争。如佃农反对“增祖夺佃”的行为。参见明末福建的海澄县志[Z].乾隆时的湘潭县志[Z].湖南省例成案[Z].道光时江西的石城县志[Z].同时,还应当看到,中国古代重视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国治、天下平。
(二)户的含义
户之本义指单扇门。《说文·户》云:“户,护也,半门曰户。象形。凡户之属皆从户。”《辞源·户部》释“户”云:“一扇为户,两扇为门。”至晚到西周时,户具有了家的意义。《周易·讼》云:“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三百户即是指三百家。《辞源·户部》释“户”也说:“一家谓一户。”由此至明代中期以前,家与户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
最早解释户的法律应当是秦律。《秦简·法律答问》载,如果奴隶犯盗窃和其他类似犯罪,因奴隶是主人的财产,隶属于主人,所以,主人应当连坐,负刑事责任;若主人犯罪,因奴隶不是户内成员,所以奴隶不被连坐,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可(何)谓‘室人’?可(何)谓‘同居’?‘同居’,独户母之谓(殹)也。‘室人’者,一室,尽当坐罪人之谓(殹)也。” 即“独户母,一户中同母的人。《唐律疏议》卷十六:‘称同居亲属者,谓同居共财者。’与简文不同。”[17](p238)也就是说,同居是指一户之内同母的人。唐人颜师古在解释汉代的“同居”时说:“同居,谓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见与同居业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财也。”“同居”指父母、妻子以及兄弟、兄弟之子等同籍同财者。“同财”与“大功”相连,“大功之亲,谓同财者也。”因此,秦代的户可理解为,由同籍同财共居的父母、妻子及兄弟、兄弟之子等家庭成员所组成的亲属团体。家庭与户基本相同。
唐律也是家、户相释。如《唐律疏议·名例律》“犯徒应役家无兼丁”条《疏议》曰:“‘而家无兼丁者’,谓户内全无兼丁。”《大清律·户律》“脱漏户口”条:“凡一(家曰)户,全不附籍(若),有(田应出)赋役者,家长杖一百。”一家即是一户。沈之奇在《大清律辑注》中也说:“计家而言之曰户,计人而言之曰口。”

有户,即有户主。户主,皆由家长(或尊长)为之,代表一户从事各种法律活动。《晋书·食货志》载:“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这说明户主既可以是丁男,也可由成年妇女及次丁男充任。
女子为户主者称之为“女户”。《律疏·户婚律》“脱漏户口增减年状”条、《宋刑统·户婚律》“脱漏增减户口”门,都有“若户内并无男夫,直以女人为户”之规定。即只有在户内无男夫的情况下,妇女才可以为户主。从唐代神龙三年(707年)高昌县崇化乡的点籍样,也能看到这一规定。[19](p468-477)户内女子分为大女、中女和小女,女户主一般由年长的大女为之,“户主大女陈思香,年卅,丁寡。口大小总三,丁寡一,丁女一,黄女一。”无大女则由中女为之,无中女,则由小女任之:“户主小女曹阿面子,年拾三,小女。口大小总二,小女二。”[19]( p469)(标点均由笔者所加)
虽然家与户的内容大致相当,但在某些情况下,家庭与户也并非完全相同。
第一,一人(丁)很难算作一个家庭,但却可以成为一户,《魏书·薛虎子传》:“小户者一丁而已”。《律疏·户婚》:“纵一身亦为一户”。
第二,对于分家与分户,法律有不同的规定。依据《律疏·户婚律》“子孙别籍异财”条,祖父母(高祖父母、曾祖父母在世亦同)、父母在世,而子孙另立户籍、分家析产者,处徒刑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子孙另立户籍以及将子孙非法过继给他人为嗣者,处徒刑二年;子孙不处罚。《疏议》解释说:若祖父母、父母做主,令子孙另立户籍以及将子孙非法过继给他人为嗣者,处徒刑二年,子孙不处罚。这里只说另立户籍,而不提令子孙分家析产,这表明若祖父母、父母令子孙分家析产,不受处罚。要言之,无论是子孙要另立户籍,还是祖父母、父母令子孙另立户籍,其行为主体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如果是祖父母、父母令子孙分家析产,祖父母、父母以及子孙都不受处罚。
第三,家中的人口、财产与户内的人数和财产不一定相同或相等。家中的人口和财产只有经官方登记才能成为户内的人口和财产,也正因此,没有经过官方登记的人口和财产,尤其是财产,很难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若事先不入户籍,即使子女、妻妾也不得享有分割家产的权利。
第四,户有时包含若干家庭。每当社会变革(或动荡)、户籍混乱时,户与家也不尽相同。如北魏初年,实行“宗主督护”制,任命豪强为宗主,督护百姓,导致“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公罔私”[20], “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21]不过,那“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的现象是“籍贯不实”的表现,为国家法律所禁止。
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并非只是为了人口管理,更具有征派赋役的功能。从明朝的“一条鞭法”到清朝的“摊丁入亩”,土地逐渐成为赋税征收的主要依据或惟一标准,先前户籍中家庭人口登记的功能渐次减退,国家典册中的一些“户”,或以田立户,或以丁立户,而不是以家立户,家与户逐步分离。
第五,更值得注意的是,家是自然形成的,户则是国家运用权力建构起来的。[注]参阅布迪厄和朱爱岚等观点:“当前对中国农村仍适用的户的定义,同样是通过国家权力的运作从内部建构起来的。”“对中国户的分析是个被优先选取的主题,因为它在当代中国是由‘官方’建构起来的。” 见[加]朱爱岚.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M].胡玉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31.国家通过编制户籍,将户内人口和财产登记在户的名下,使户承担起国家赋税和社会控制的重任。户的公法性质非常明显。虽然户的产生是出于公法上的需要,但同时法律也赋予户享有户内成员的人身权和户内财产的财产权。
有关户与家庭的区别还可参考《辞海》的相关解释。不过,明代中叶之前,户与家基本相同,户以家立、因家立户是古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有学者指出,明初黄册中的户对应于现实中的单个家庭,一户即一家。[7](p245)
明代中期之后,户的构成要素和性质逐渐发生了大的变化,明代里甲制下的“里长—甲首”关系渐渐变为清代图甲制下的“总户—子户”关系,而且总户与子户间的关系相当复杂。[7](p264-268)但是,尽管明代中叶以后,家、户逐渐分离,户“不再仅仅是家庭的户籍登记单位,而可以是单纯的田地赋税的登记单位”[3](p73),“只是由于一般地说,对于某一特定的‘户’拥有支配权并在其中承担纳税责任的,是一定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并由于‘户’本来是指一定的社会群体这样一种渊源关系,才习惯地用户名来指称一定的社会群体。”[7](p258)由于“子户”、“花户”的不明之处甚多[8](p500),也许可以这样说,无论“户”这个“户头”被什么样的社会群体(实体)拥有和支配,拥有和支配这个“户头”的社会群体(实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是以户的名义来进行。[7(p223、224、252、255),8(p499),18(p1126、1128、1129、1148、1150、1248、1414、1440)],[注]明代中期以前,人和土地财产是构成户的两大要素,并且以人为主,土地处于从属的地位;户一般代表一个家庭,是一个相当确定的社会单位(或社会群体)。明代中期之后,特别是在清代的图甲制下,户也可以包括两个以上家庭,户的名称也可以用来指宗族或族内房系,称为“户族”,户的构成要素也主要不是人和土地财产,而是田产与税额,户主要变为以土地为基本内容的课税客体或税额登记单位,类似于银行帐户的登记单位,即“户头”。参见文献[7],252-260页。但也应当注意,在一般情况下,并非所有的家庭与户都完全分离,而没有关联。参见大清律·户律[Z].“脱漏户口”条;沈之奇.大清律辑注[M].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将户理解为:明代中期以前,户是中国古代社会国家为了掌握人口、财产与征派赋役,以家庭为基础而建构的,具有法律性质的最基本的单位;明代中期之后,家与户逐渐分离,户主要成为田地与赋税的登记单位,但另一方面,土地财产的实际所有者,应当还是以户的名义从事土地的买卖、出租等民事活动,申言之,从事各种民事活动的主要主体,应当还是户而不是个人。明代中期之前,虽然户与家庭(狭义上的家)的内容基本相同,但两者之间也存在某些差别而不能完全等量齐观;再者,中国古代的“家”的含义具有不确定性,家可以指家族、家庭、家产、户(家户),而户则通过官府的登记而有较确定的含义和范围。
二、户的种类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编户是国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不同的人被编入不同的户籍,“普天之下谁不编户?”户也随朝代更替、社会变迁而产生了不同的种类和称谓。
两汉之前,户的名称比较单一,一般统称为“户”、“人户”、“民户”。若按职业和身份划分,两汉户的种类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农户,或称民户。农户主要由自耕农、半自耕农和大小地主组成。二是宗室贵族户。汉代有管理宗室贵族事务的专门机构“宗正”,其职责是“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其户籍称“宗室名籍”、宗籍。三是有市籍的市户。西汉时,凡在官府设立的市场中营业的商人都有专门的户籍,即市籍,不过,到东汉,商人已不见有无市籍之区别。[22](p213,215)
根据财产的多少,汉代的户可分为上户、中户和下户三种(等)。上户资产在50万钱以上,中户资产在10万钱左右,下户资产多不满万钱。[23](p7-8)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户的种类和名称明显增加。曹魏时期,曹操将控制下的人民分为农户、屯田户、兵户等。北魏时,除了统治者直接控制的编户外,还出现了名称和种类繁多的“杂役之户”、“百杂之户”,统称为杂户。其中,有隶属于寺院团体的僧祇户,有为寺院所领的佛图户(寺户),以及与国家有着密切人身依附关系的依附户:军户、营户、乐户、隶户、府户、屯户、牧户、盐户、监户、驿户、伎作户(包括细茧户、绫罗户、工户、金户等手工技艺户)、平齐户等。所有杂户都各有专属的户籍,其地位高于官私奴婢而低于编户。
北魏的杂户主要来源于反叛者、战俘、被掳掠的人口和罪犯的家属子孙等。这与北周的情形大致相同。北周《大律》规定:“盗、贼及谋反、大逆、降、叛、恶逆罪当流者,皆甄一房配为杂户。”北魏的营户多来自反抗统治的北方少数民族,他们被迁置各地后,在军队的掌控下从事农业、畜牧和手工业等劳动。
隶户与平齐户主要是从别国掳掠来的民户。隶户多来自西凉,《隋书·刑法志》载:“(北)魏虏西凉之人,没入名为隶户。”隶户主要从事各种杂役,地位低下,常与奴隶一起被赏赐臣下。平齐户是北魏在对宋战争中所俘掠,并被强迁至魏都附近的齐郡人户,地位低于僧祇户、佛图户。
北魏出现的杂户直到北齐才被废除。杂户又重新成为编户,获得更多的自由,摆脱了卑贱的地位。
虽然北齐在放免法令后已“无复杂户”,但在唐代,由罪犯的家属而变成的杂户依然存在。作为官贱民,杂户的户籍隶属于州县官府,其地位低于编户而高于官奴婢和番户。
番户是属于官户的罪役户,其户籍隶属于所服役的州县官府。作为官贱民,官户来源于罪犯及其家属、官奴婢的赦免。地位仅高于官奴婢而低于杂户和编户。虽然番户包括在官户中,但官户与番户也有某些差别。
除杂户、官户外,唐代的官贱民还包括工户、乐户和太常音声人等。工户是隶属于朝廷少府监的手工业户;乐户为隶属于朝廷太常寺、从事乐舞的官贱户;太常音声人是原附籍于太常寺而唐代改为属于州县官府的乐户,其地位较高。虽然太常音声人也属于官贱民,但其地位高于其他官贱民而仅次于良人编户。
唐代的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其中“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而附于主人的户籍之内。据《唐大中四年(850)10月沙州令狐进达申请户口牒》载,在户主令狐进达的户内,还包括奴与婢。[24](p566)其中,“宜”为婢、“进子”为奴。部曲“谓私家所有”。部曲之籍编入主人的户籍。奴婢、部曲无户籍,即没有独立的人格。
唐代的人户比较复杂,主要包括地主、自耕农、手工业者和商人。[25](p116)这些人户根据资产,分为不同的户等。唐初,国家的编户分为上户、中户(次户)和下户三等。贞观之后,唐代的九等户分别为上上户、上中户、上下户、中上户、中中户、中下户、下上户、下中户、下下户。根据居住地的不同,唐代的编户又分为主户与客户。凡是土著原籍人户称为主户,而因战乱、赋役、灾荒等逃亡异乡的客籍民户为客户。但到唐德宗实行“两税法”后,取消了主客户的区别。晚唐,再次出现主户与客户,但晚唐的客户是指佃户而非客籍他乡的民户。
在唐代主客户存在的时期,主户又分为课户与不课户。凡主户内负担国家税役人丁的人户,即为“课户”;无田产或依法免除税役的人户为“不课户”。课户负担沉重的赋役,主要有租、调、役、杂徭。
北宋以降,户种类的划分标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总的趋势是由以身份区别为主到职业划分为主、从看重人身关系到重视家庭资产的变化。但这并不是说宋代以后就没有身份的区别和人身的依附关系,而是说职业和资产成为划分户种的主要标准。
两宋的编户主要分主户和客户两类。这时的主客户主要以有无土地加以分别,主、客之间也常因有无土地而发生变化。主户拥有土地,相应也承担国家的赋役。主户又分乡(村)户与坊郭户两类。乡户的主体是自耕农户,此外还包括半自耕农户、地主、匠户、亭户(即灶户,以海水煮的正盐缴公的盐户)、锅户(以海水煮的浮盐卖给商贩的盐户)、井户(以井水制盐之民户)、茶户、机户、船户、茧户以及女户和一些官户、形势户。
官户指有官品、免除徭役的人户。这与南朝、隋、唐时的官户(即罪役户)不同。形势户是宋代“立别籍,通判专掌督之”,在仕籍的文武官员和州县豪强人户的统称。[26]坊郭户亦称城郭户,是指居住在州、县、镇内的手工业者、商贾和城市人户。
客户即佃户,无论乡村还是城市都有客户。前者称为乡村客户,后者名为坊郭客户。这里的主、客户,与晚唐的主、客户相近,但两宋的客户,其人身依附关系较前代大为减弱,其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即使客居他乡,也能很快取得国家编户的资格。公元1021年,诏曰:“诸州县自今招来户口,及创居入中开垦荒田者,许依格式申入户籍,无得以客户增数。” 客户取得编户资格后,就与主户一样在法律上取得了受国家平等保护的地位。同时,还应当明确的是,尽管两宋的户种繁多,但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因职业而不是由身份来体现的。
元代的户种也主要依据资产和职业加以区分。按每户占有土地的数量,民户被分为三等。依职业分,元代的户主要有军户、民户、匠户、站户、医户、乐户、儒户、盐户、冶金户、葡萄户、打铺户、儒户、猎户、酒户和礼乐户等,统称为“诸色户计”。元代比较特殊的户种为“驱户”,是蒙古人在战争中俘获的汉人民户。他们有自己的户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负担国家的赋役,但他们为蒙古贵族所占有,不得与自由民通婚,其身份是农奴或奴隶。
明代,户的种类和名称依然繁多。《大明律·户律》规定:“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大明令·户令》:“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计,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此外,明代还有匠户、丐户(亦称堕民、怯邻户)、疍户(以打鱼或水上运输为业)。这些户类都是按职业划分而有不同的名称。若按以财产多少为依据,则户分为上、中、下三等,“户有上、中、下三等,盖通较其田宅、赀畜而定之”。[27]有学者统计,明初户的种类至少有80多种。[28]
在清代,主要有“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法律规定的军、民、驿、灶、医、卜、工、乐等诸色人户,只是某一户类的总称,在每一类的人户中又细分为更多的户种。如民户中除了一般农户外,还有佃户、茶户、织户、商户、船户、矿户、渔户、儒户、阴阳户等。灶户,亦称盐户,包括亭户、锅户、畦户、井户等。
三、结语
上文的梳理仅仅是对古代中国户的种类和名称所作的简要概括,而事实上的户种类与名称远比上文所述要丰富的多。但即使只是一个简略的观察,也能看到户在古代社会中普遍和长期存在的事实。在这些不同的户类里,包含着数量庞大的以家庭为基础而构成的户。
由上可知,在家的基础上,国家通过法律建构了一个社会主体——户,正是这些种类繁多、名称各异的户组成了纷繁复杂的古代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户作为国家征收赋税和社会控制的对象,再加之,户律的规范多以刑罚手段以保证实施,可以说,户具有公法的性质。此外,户在经过户籍登记后,不仅获得了公法上的主体资格,同时,国家也赋予了户以民事主体的资格,在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和民事活动中,户充分享有户(家)内的财产权和人身权,个人或户主(家长)的民事法律行为也主要是户的民事法律行为。换言之,户因登记而被赋予了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户的权益也因法律的确认而受到保护。户不仅是公法上的主体,还是私法,尤其是民事法上最主要的主体。在平等、和同、诚信和情理等民事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户从事着诸多的民事活动。
参考文献:
[1] 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 李志敏.中国古代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
[3] 姚秀兰.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4] 张晋藩.中国民法通史[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5] 叶孝信.中国民法史[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6] 孔庆明,胡留元,孙季平.中国民法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7]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8] [日]片山刚.清末珠江三角洲地区图甲表与宗族组织的改组[A].郑振满,译.叶显恩.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C].北京:中华书局,1992.
[9]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M].张建国,李 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0] 周子良,李 锋.中国近现代亲属法的历史考察及其当代启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43.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 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 M].北京:中华书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3]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
[14]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J].文物,1985,(4):27-37.
[15] 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
[16] 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76.
[1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Z].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18] 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9]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吐鲁番出土文书[Z].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20] (北齐)魏收.魏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1] (北齐)魏收.魏书·李冲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2] 林甘泉,童 超.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3] 邢 铁.户等制度史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4]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 录文(下)[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
[25] 王威海.中国户籍制度——历史与政治的分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26] 辞海(经济分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149.
[27]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河南[M].
[28] 栾成显.赋役黄册与明代等级身份[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