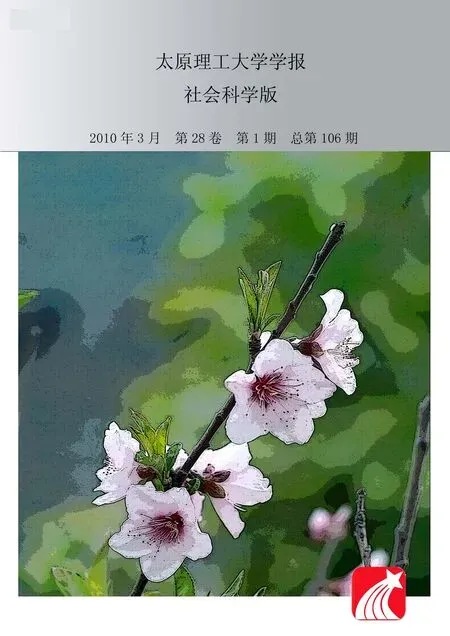评霍克斯小说《维斯尔杰克特》中语言、文本和意义的不确定性
谷野平
(1.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6029;2.北京语言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83)
一、引言
文学犹如一条虚构的河流反映着现实。在这条文学的长河中,优秀的作家闪烁着粼粼波光。当我们以断代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的时候,会吃惊地发现文学创作阶段的文本书写方式随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形态上、表达方式上或者甚至本体意义上的变化;每个时期总有几个作家在转折时期起着开先河和确定基调的作用。
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从自己的十四行诗、长诗、戏剧等划时代地转向了以人为本的文学创作,并取代了以神为描写对象的中世纪文学;丹尼尔·迪福开启了新古典主义时期英国现代小说的先河,以第一人称叙事和章回体形式确立了英国现代小说的基本框架,并在菲尔丁的笔下得以完善,忠实再现物质世界成为主基调;历经前期、中期和后期的浪漫主义诗人,用自己的诗行抒发着世间万物作用于内心的感受,特别是湖畔派诗人,他们回归自然,去寻求美和崇高,用细腻的笔触表现着心灵的狂喜;而后最优秀的传统作家奥斯丁将内心世界的描述与外部世界的描述结合起来,使传统小说达到了完美;现实主义时期的狄更斯用成长小说将小说重新转回到对物质世界的忠实描述;现代主义时期的伍尔芙和乔伊斯放弃了传统的物质主义转向了精神主义,在人类意识流动的河流中寻求人类精神的“火焰”,认为人类生活的中心是精神生活,而不是物质生活,他们用文本记述了以片段形式出现的人生经历,根据人类心理时间将人类的生活的本身以意识流动的顺序记述下来;美国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托马斯·品钦和约翰·巴思以及约翰·霍克斯受到西方后现代哲学等其他学科思想的影响,关注和实践文本本体,在使用戏仿和元小说创作的同时,将西方后现代哲学的精髓融入到他们的创作之中,结果在自我指涉的文本消解传统小说因素的尝试过程中,将文本的边缘无限扩大,文本本身呈现出了文本的内在性和不确定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
本文旨在以霍克斯小说《维斯尔杰克特》为例,说明“延异”和“播撒”在实现小说中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场形而上学”上使用了“延异”的概念,意为延缓和差异。“延异”可以用来对抗和消解罗格斯中心主义,造成语言变成了无止境的游戏的效果,同时语言本身也丧失了其终极意义。霍克斯将延异用在小说的许多概念之中,这充分说明作者主观上旨在对抗罗格斯中心主义的立场。他主观地促使能指滑动,使所指变得什么都是什么又都不是,这样就拖延了审视和确定的时间,造成语言乃至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也让读者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思考的时间;德里达的另外一个术语“播撒”是对“延异”的进一步扩展,指的是在语符的能指链中,由于“延异”的延缓和差异,意义的传播并不成直线形式延展,而是成四散播撒的形式展现出来,其功能是要不断瓦解文本,持续不断地揭露文本的零散和重复,标志着文本“超验所指”的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切都处于不确定性状态之下。
二、霍克斯小说的不确定性
霍克斯通过放弃传统小说因素的方式,将“情节、人物、背景和主题看成是小说真正的敌人”[1](p149),他的文本改变了读者的期待,可以说是文类上的重大改革,为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开启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小说从形式上看,每个小章节都可以单独成篇,删减任何一个小节都不会影响故事的整体,而传统小说的章节相互逻辑相连,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传统小说通常以线性叙事为主,而他的小说则在时空错置的同时,用意象或者颜色将各个章节或片断联系到一起,给读者以欣赏一幅画的感觉,在视觉上也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冲击效果;传统小说中的语言以散文(Prose)形式为主,作家或者叙事者有充分的抒情或者评论空间,而霍克斯的小说以杂文(Essay)形式出现,同时表现出强烈的诗歌色彩,其诗学语言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同时读者也忘我于诗歌的欣赏之中,忘却了故事情节的连贯,因此还得重新阅读他的小说,在字里行间寻找到各个章节和片段的连接物。霍克斯小说的各个部分不再由因果或者逻辑联系,而是通过意象和色彩之间的关联,这种抒情杂文体酷似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文体。霍克斯小说的语言方面,在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上都做了很多改造,双重或多重指涉造成文本出现了不确定性,这样,他的文本丧失了先前文学文本的那种人文关怀,读者的阅读变成了文本二次加工或者再创作的过程,在感到沮丧和无所适从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享受到了重新创作文本的快感。在他的一些小说中,传统文学的那种业已形成的理解方法和意义的期待只能是星星点点地显露出来,要想找到文本的本身,读者要拨开层层迷雾,发挥自己的想像和再创作能力,才能找到文本的本身,然而最终文本却因读者而异。小说传统的因素对于传统的读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没有他们,似乎就没有小说的框架。而霍克斯就是故意这样“难为”读者,让读者放弃传统的阅读方法,给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方法,那就是在字里行间找出事件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表面上却是异象的联系或者用色彩联系。这种写作理念恰恰与德里达的“延异”和“撒播”在理念上不谋而合。他通过类似于“延异”、“撒播”等过火的游戏,造成了消解人们思想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效果,也解构了“二元对立”的宏大体系,更使得文本开始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中心,从而解构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2](p141),实现了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
三、《维斯尔杰克特》中精彩的语言游戏与松散的叙事结构
根据德里达的理论,有些词汇如“存在”和“事物”都是不准确的,暗示语言之外的不可改变的在场。因为它们是我们手里仅有的词语,所以我们必须抹掉它们,用以表明它们表达意义的不充分和不确切。文学创作中可以把它们划掉,也可以把它们放在括号中或者引号中。在小说《维斯尔杰克特》中,霍克斯使用如下方法消解了罗格斯中心主义:语言上,把表达确定意义的语言删除。将表达人在场的事物毁掉,比如说在哈罗尔的遗像上划上了很多道儿,达到辨认不出人形的程度,这种销毁现场的方式表明他既“在场”又“不在场”,从而构建了自己的语言游戏基础。霍克斯在小说中引进的“游戏就是对在场的瓦解”[3](p292),可以阻止和消解中心结构,“通过让中心或者起源的缺失和不在场,开始新的游戏”[3](p289)。
小说本身也参与了对本身结构的评论。叙事者麦克尔把人体比作中国式菜单,认为西式菜单为预先设置的东西,不能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亦不能公平地对食物作出评价。西方菜单是“固定的”,顶多能称之为一盘好菜,与此同时西方的菜单“囚禁”吃饭的人,不给人们留下选择的权利。相比之下,东方菜单给人们选择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可是这种自由选择有可能毁掉线性结构,因为选择意味着变化,变化意味着不连贯,不连贯在西方人看来恐怕意味着没品味。这种语言游戏的结果是小说《维斯尔杰克特》就像中国式菜单一样,每个章节独立成篇。叙事没有连续性,达不到传统小说的“最好的一盘菜”的效果,所以他的小说中叙事量有限,致使小说得不出结论。小说中的各个片断没有主次先后之分,读者可以随意翻到什么地方就可以开始阅读了,自主选择式的阅读可实现“万花筒”的效果。小说文本本身也可被看作是对人体的模仿,是对人体的暗喻,使菜单本身充满生机和让菜单内的内容更加鲜活。小说的解读犹如对美丽的人的形体的欣赏,从人的嘴开始到臀部结尾的一个长时间的讨论过程,这让一本书的文本看起来像个人的身体,可从头到尾观察事物[4](p11)。
罗兰·巴特认为作品和文本不同,在他看来“作品”指传统的、有清晰的边界的文本,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却是抽象的,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他认为读者在不同时间的参与再创作,会造成文本中边界的无限扩张,也会造成文本的意义的多样性。小说《维斯尔杰克特》文本犹如中国式的菜单,各部分独立成篇,不同文类的篇章叠加起来可以成为一个整体;而从哪部分开始阅读,都可以得到新的文本意义,文本整体意义都会有所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说,霍克斯的这部小说文本颠覆现存的体裁,超越了传统“阐释规则的界限”[5](p157)。
小说《维斯尔杰克特》是一个有关范·弗里特家族的谋杀的故事,侦破过程和结果犹如埃科的小说《玫瑰之名》中的那样,神秘、恐怖、没有结果。家族首领哈罗尔德·范·弗里特神秘的死去,范·弗里特家族的养子——时尚摄影师麦克尔展开调查,在此期间,麦克尔不断受到来自斯狄浦尔顿的三个妇女的诱惑,最后深陷情欲之中无法自拔,竟然变成了包括继母、继女在内的许多女人的情人,最后案子也调查不下去了,他成了女人的中心,也成了自己和他人的麻烦之源。在痛苦、快乐的混乱性爱中,他的生活被女人们撕扯成碎片,他迷失了自己。
小说文本正如他的生活一样混乱,它由片断构成,结构呈现出破碎状态,包括18世纪画家乔治·斯塔博兹的故事、麦克尔对时尚照片的描述和他童年时代的景色描写。所有这些都不断地打断叙事进程,这些碎片多得令人目不暇接,仅仅第一章就出现了12处之多,但总体上说这些碎片相互之间还是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后面的章节和前面的章节一样,碎片迭出,大大降低了读者的期待,可读性变得越来越弱。
像后现代主义小说放弃了现代主义小说以自我为中心那样,霍克斯也放弃了将主人公放在叙事中心,把语言变成主角。霍克斯灵活地使用了修辞手段,巧妙地玩弄着文字游戏,致使传统的小说因素在小说中处于次要地位。精挑细选的词汇让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延展了词汇意义,从而将意义“撒播”在文字的各个角落,从而拖延意义的解读。表面上看,这些词汇的使用没有规则,但是如果仔细看,那么就可以看出这些词汇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从而构成了另类叙事,它不以时间和情节的发展为基础,而是以词汇之间的关系为脉络,编织成相互连接的片片“锦缎”,最终成为小说本身。小说的句子中好多单词都可以构成内韵,而相互之间又可以在意义上做有机的补充,如:文本中的人名布斯(buse)与诡计(ruse)以及男女厕所名字的“men”和“women”等单词在句子中都可以让意义得到延伸,同时也在语音上构成内涵。
四、《维斯尔杰克特》中不确定的人物身份及其普遍指涉的猜想
叙事语言的改变造成叙事声音的改变,突出了人物身份的不确定性。麦克尔的声音在小说中有三个变体:以第三人称叙事的童年麦克尔、以第三人称叙事的乔治斯塔博兹和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成年麦克尔。不同的叙事声音凸现了小说主人公身份的虚构的特点,外加上有些片断根本就没有叙事者,纯粹由场景描述,这些都是文本的结构松散、虚构性增强和意义的不确定性。
主要人物和叙事者麦克尔的角色由于身份的不可靠而变得似乎无足轻重。小说第三部分的麦克尔在观看哈罗尔德的老照片后,驰骋自己的想像,精心编造足以以假乱真的故事,创造出一种能够让真实场景退居其次的语境。真假难辨的故事足以混淆真假,延缓真正意义的追寻,为小说意义的不确定性做了铺垫。
在小说的第一章,麦克尔曾两次问谁在说话,而叙事者则意味深长地回答说他不知道,更令人困解的是小说从头至尾就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主人公的身份不确定造成了文本开放的可能性,因为不同人讲述一个故事和一个人讲述一个故事在角度和动机上都有差异,结果小说的传统固定而封闭的结构让位于开放的松散的结构。麦克尔说自己“避免暗喻”,“更喜欢具体”[6](p159),然而与之相反,小说暗喻不断,甚至一开始就使用了暗喻:“妇女是一个视野,妇女是自己的一道亮丽风景”[6](p3)。又如:将人体称为菜单;小说的结构称为中国式的菜单;故事是噩梦[6](p106)。再如:他根据哈罗尔德的照片来编造故事,把精力没有放在调查案件上,结果案件没调查成,他转而落到了开始欣赏女人这道风景的地步,并坠入了多角恋爱的情网,侦破工作只能不了了之。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麦克尔的生活也变得不确定了,因为他同时要面对多个女人。
和叙事人物不确定一样,小说的背景也呈现出了不确定性。首先,小说的背景上有狩猎场景和乡村庄园,既像英格兰也像美国,但两者又都不是。“国家”、“妇女联谊会”或者“主教派会员”等词汇说明故事背景既不是美国,也不是英格兰,而是一个霍克斯凭自己想像造出来的社会。霍克斯与帕特立克·奥唐奈尔访谈时谈起人造背景,指出这是他审美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就是想要这些人造的,这些真正人造的东西,无论人想要从词中创造什么,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它被创造的痕迹。”[6](p111)他将这些痕迹故意播撒在小说的各个角落,造成背景的虚幻和不确定性。当然在“乌有乡”背景中的人的活动恐怕也是想像出来的。那些人行为古怪、反常,也不招人喜欢。他们处于阴影下,身影模糊,身份不确定。
小说中的主要声音发出者麦克尔当然也是个“人造”的人。他身份的问题在故事开始就彰显无遗。“我是谁?”这个问题让我们了解了麦克尔,同时也认识到了霍克斯的美学观点。麦克尔就像《白雪公主》中有窥淫癖的王子,偷窥到的信息比照相机捕捉的还要多。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身份缺失。比如麦克尔的爷爷沃尔特·T·范·弗里特身份缺失就非常典型,痴呆让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一个人在夜晚的街道上穿行,他的身份一点也表现不出来。沃尔特·T·范·弗里特再也不知道他是沃尔特·T·范·弗里特了。”[6](p20-21)他死后,被领养的孙子麦克尔搬进他的旧屋子,承袭了他不确定的身份。两个人物之间构成了某种对应:爷爷把五个妇女带到斯蒂普尔顿当情妇,而孙子则在时尚摄影中使用五个模特儿;爷爷在五个少女面前倍感无助,而孙子在女人面前一事无成;爷爷生命的最后想和一个女孩儿性交,孙子无意间阻止了这个企图,几年后,孙子遇上了同样的事情。那么小说中不同人物的身份重叠,命运相连,互为重复,互为补充,成为霍克斯小说的主要美学特点。小说中人物不确定,可是人物的互补却间接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也就是说所有的身份不确定的人叠加在一起,“制造”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人。
如果说在小说的初期阶段霍克斯把麦克尔与沃尔特·T·范·弗里特两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那么当麦克尔搬进沃尔特·T·范·弗里特的旧屋子时,二者之间的关系终结。小说中开始强调麦克尔和另外一个相对应的人的关系,那就是神秘莫测、心怀鬼胎的哈罗尔德。那么哈罗尔德的人物性格承袭了弗里特,也作为麦克尔性格的补充,从而看到了霍克斯的人物塑造的特点,即小说人物是互补性的、拼凑出来的、人造的人。这样霍克斯不断地在小说中提醒读者,他的人物既不是真实的人物,也不是完整的人物,是将人物放在一起才可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
总体上说,麦克尔的身份不清楚,但可以由小说中其他人物身份定义出来,这样的性格也具备了“这播撒一点,那里播撒一点”[7](p380)的“撒播”性质,也就是与他相对立的“他者”可以定义他的身份。麦克尔的身份获得来自于对立面的身份,反过来说,他的身份也可用来定义对立面人的身份。这种身份信息的播撒,一方面造成文本结构的松散和意义指向模糊,变成了一个有关不存在的人的不存在的故事;而在另一方面读者会意识到不确定性的人物加在一起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人,然而是人造的。那么我们能否把他们看成是人类的总和呢?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果人类的性格加在一起放在一个特定的人身上,那么我们说这个特定的人肯定是不存在的,这和霍克斯笔下的人物麦克尔的人物性格有着巨大的相似性。我们如果这样说,那么我们可能和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混淆在一起,但是即便是后现代主义强调个体,那么谁又能否认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呢?这样我们可以说霍克斯通过延异将痕迹撒播的战略,表现出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对抗性:传统小说是典型人物涵盖着小说人物和读者的潜在人格,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人物则是多个人物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物性格。后者的形成必须依靠播撒的力量,当然,叙事可能依赖多个人的参与。
五、结语
霍克斯的文本实践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不期而遇,有很大的相似性。“延异”和“播撒”等概念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说明霍克斯通过语言游戏造成了意义多样性的以语言为主角的文本;人物身份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人物针对性减弱,然而却导致了反向指涉了所有后现代人,间接地反映了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霍克斯这样做,将一头雾水的读者置于无助的状态之下。读者在历经能指链中的意义搭建起的隧道,会感知到经常隐匿着细微意义的、连作者都没有意识到的潜在前提和言外之意[8](p91);读者充分感受到文本的窒息、碎裂、无助和乏味,他们自由阅读快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霍克斯企图通过语言游戏把语言变成了主人公并实现文本的自我指涉,让文本本身变得扑朔迷离,通过读者的参与无限扩大,无限延展文本的边缘,从而实现文本意义的多样性和无限性;霍克斯也企图通过将模糊化的“人造”人物身份,通过“他者”的反衬,呈现出一个整合出来的身份缺失的个体人格,可是出于后现代主义者们的期待,身份的不确定性却间接导致了身份的人类整体指涉,达到“都是,又都不是”的效果。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当霍克斯摆脱了一切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之后,通过“能指”的“滑动”将所指从传统典型的个体或群体转向整个人类呢?毕竟,当我们将后现代文本外面所罩的幕障扒开的时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同样依然是活生生的人生,鉴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不确定性在后现代主义文本中只是一个形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Enck,John.John Hawkes:An Interview[J].Wisconsin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65,(6):144-155.
[2] 萨晓丽.过火的游戏——“剪刀手”威廉·巴勒斯的文本结构策略[J].当代外国文学,2009,(1):140-147.
[3] Barthes,Roland.The Pleasure of the Text[C].Richard Miller,Trans.Oxford:Blackwell,1990.
[4] McGrath,Patrick.Violent Horses and Violent Dreams[N].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88-08-07(11).
[5] Barthes,Roland.“From Work to Text.” Image-Music-Text[M].Stephen Heath,Trans.London:Fontana,1977.
[6] Hawkes,John.Whistlejacket[M].New York:Collier,1989.
[7] 王岳川.文艺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8] 李 松,董迎春.延异哲学:从“摧毁”到“解构”[J].长江学术,2008,(3):8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