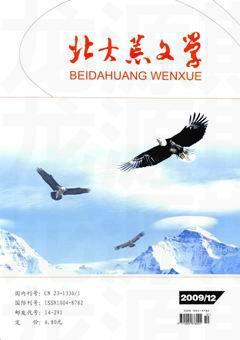议“荷塘月色”的积极与消极
张秀峰
高中教材中的《荷塘月色》一文,是历年来为学生们所喜爱的一篇美文,但是我们在长久的解读中,总是忽视了文章中对文人精神传承的理解。在《荷塘月色》中,朱自清先生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世外桃源”,用以表现内心的苦闷与对现实的不满,由此我们看出进步文人在白色恐怖时代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对黑暗的现实想“超然”又想“挣扎”的心迹。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先生于1927年7月创作的一篇借景抒情的散文。那时作者在清华大学教书,文章里描写的荷塘就在清华园,正值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作者也处于苦闷彷徨中,心中笼罩着“淡淡的哀愁”。他想投身革命,却有太多的顾虑和犹豫,于是只好选择了逃避。面对美景,先生内心虽有“淡淡的喜悦”,但这种苦闷的喜悦只是暂时的,所以他仍然在矛盾中挣扎。在如此复杂的心绪之下,先生借景抒情,写出了这篇著名的《荷塘月色》,在文中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用以暂时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
有人撰文说:“这几天心理颇不宁静”,主要是指朱自清爱妻被家务累垮了身体而愁闷,要借“月色、荷花和杨柳等自然景物来排解,”并已得短暂超脱而淡淡喜悦,可惜被“蝉声蛙声”闹了个不得宁静,终于“什么也没有”,这分析不能说没有些道理。问题在于,这时候,依常理,该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这荷塘月色中的自由美好,终归不属于我,我的自由美好在哪里?噢,只能从对妻的爱,对家庭的承担、对工作的投入、对黑暗现实的抗争中去寻找或创造。另一种呢,只会长叹一声:唉,荷香月色再好,终归于事无补,我只能回到病妻身边,回到问题成堆的家,回到沉重的工作室,回到残酷的黑暗现实中,这是无可夸何的事啊。这两种心思是积极的,是继续寻求超脱的不言败,后一种心思是消极的,妥协认命的。朱自清属于哪一种呢?他显然属于前者。
《荷塘月色》有个最突出的特点:静美。文章从“颇不宁静”开始,一直围绕“静”字展开,这是许多有关文章的共识。而笔者认为,文章不只是围绕“静”字展开,更是让“静”统领全篇,并未“失静”。“静”同“净”,是佛教的一种境界,也是人生的境界之一。古人推崇“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当代教育家魏书生老师上课,也爱先念念“松静匀乐”。朱自清大约是深得“静”之奥妙的。在《荷塘月色》中,朱自清既写宁静中的“荷塘月色”之美,也写“荷塘月色”中的柔静之美;既写自然景物的静谥之美,也写人在静夜的自然景物中所展现的情感思想之美——作者对自由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并且在“静”的表现手法上讲求变化,体现了一个文学大师的“高超”。或许高到极处,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大家对《荷塘月色》的鉴赏产生了种种分岐。分岐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失静”、是否“超脱”等问题,还有“出门”、“进门”、“蝉声”、“蛙声”等细节。
当读者陪着作者沉浸在无限静美的“荷塘月色”中时,突然听到蝉声与蛙声,听到作者感叹“我什么也没有”。这的确有点措手不及,有点睛天警雷,太不寻常了。特别是“我什么也没有”,如果不是疯话与傻话,是作家的正常话,已近于“失能”。一般说,无论你精神上或物质上怎么一贫如洗,也不至于“什么也没有”。怪不得有人要质疑那深夜的蝉声:“那时有蝉声吗?”“不可能有蝉声!”等等。也怪不得不少人失望地说:“其情与出门时一样,只能在无可奈何中不了了之”,只能重回“不宁静”了。也许,人们的这种姿态算是温和,宽容与尊敬作者的吧,没有将他与“非同寻常”联系在一起。如果视他为“非同寻常”,一般会有两种反应,这家伙要么在拿出非常的艺术,要么在发疯或发傻。人们的思维大约久已不用或少用吧,既想不到他的举动是非常的艺术,又有点善心、包容与对作家的爱戴,不肯将他与疯子或傻子联系起来,只当他没有从愁闷中走出或重新回到了愁闷中。在写法上,也不过是寻常的“动静结合”罢了。然而,笔者却要视它为平中出奇的祖来之笔。
不论是“月下荷塘”还是“塘上月色”,作者都在写其静美。当写到“荷塘四周”,作者就要离开荷塘、赏景就要达到高潮时,如果再继续以静写静,难免落入单调而平庸。文章至此必有点极限之举,何不以声写静呢?于是写出:“蝉声蛙声”蝉蛙之声真有些晴天霹雳了。但这意味着“失静”吗?当然不。这与“鸟鸣山更幽”同理,不过是用声视静,写出了更高更绝的静美。在此情况下,作者为何又说“我什么也没有”呢?笔者认为,他的“我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因为他随即就“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这是又一次超脱,这“实际上是对自己青年婚姻生活的美好回忆”(袁立权语)
这回忆的意味深奥吗?不。我们平素烦恼或恼恨某个人或某件事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想想这人和这事对自己有过的美好或益处,这样可自然减轻甚至消除对这人或这事的烦恼与憎恨。朱自清自然也不例外。当他再回到家里时,他看到的是“妻已睡熟好久了”。这“睡熟好久”的结局可忽略吗?应该不会也不能。从写作艺术的角度看,作为经典美文,朱自清的代表作之一,文章有个非同寻常的“凤头”,也该有个寻常非同的“豹尾”,才算和谐完美,达到真正的“回环照应、首尾圆合”。这“豹尾”自然是“睡熟”。妻的“睡熟”意味着“静”,这与妻在开头“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的“不静”相照应,更与“颇不宁静”相照应。而从文章主旨的角度看,“睡熟”更是非比寻常。人不会在担忧与焦虑中“睡熟”,不会在彷徨与苦闷中“睡熟”,更不会在痛苦与挣扎中“睡熟”。“睡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活环境的安适,或操劳奋斗的满足,或为今天明天做梦,或坦然面对一切而无所畏惧,等等。我们能说这是“其情与出门时一样,只好在无可奈何中不了了之”吗?能说作者是“带着无限惋惜和深深的遗憾之情”回到家吗?
美国作家莫利在散文《门》中指出:“开门和关门是严峻的生命流动的一部分。生命不会静止不动并听任我们孤寂无为。”是的,作家的生命没有孤寂无为,他感悟到“荷塘月色”中的无限静美,无限静美中的自由美好。这“自由美好”对心灵的影响是淋浴也是洗礼。月色是诗意的,也是强大的。“荷塘月色”给予人的既非“短暂超脱”或“片刻宁静”,也非永留你陶醉其中,而是启发你发现、欣赏自然或生活中美的存在,促使你萌生和开掘人生的智慧。在自然面前,人的一切显得微不足道,但人并不是无能的。自然再伟大,伟大的心灵亦可以自由到达。笔者想,这些看法,朱自清也该悟到了吧。否则,他不会借《荷塘月色》表达自己对自由美好的热烈追求,不会在“颇不宁静”中写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美丽诗文,不会表现“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高尚气节,不会成为被毛泽东称颂的“民主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