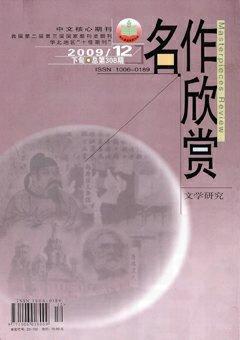西部民间伦理与西部乡土叙事
关键词:雪漠 生存状态 西部民间伦理 精神生态系统 创作视界
摘 要:雪漠的系列长篇以沙漠边缘沙湾村的普通农户老顺一家的日常生活为背景,真实地还原了西部农民的生存状态,叙写了现代性背景下普通农民痛苦而艰难的精神裂变的过程,揭示出西部贫穷的根源在于欲望的膨胀和西部人巨大深厚的精神惰性,而西部人的精神生态系统也限制了作者的创作视界。
20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西部乡土作家雪漠的长篇小说《大漠祭》,并在小说封面上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引起了评论家和读者的极大关注,小说不仅多次再版,还进入了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度小说排行榜,获得“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等,《猎原》获2004年度“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雪漠小说中充满艰辛与磨难的西部农村生活和西部农民自然原始、粗犷坚硬的个性,以及他们在苦难中顽强坚守的西部精神与伦理,深深震撼了读者的心灵,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奇陌生的审美想象空间,那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像田园牧歌一样充满了诗意,仿佛一缕清新的风滋润着那些沉溺于欲望之海中浮躁、焦渴的心灵。
一、西部民间伦理是维系西部农民生存的精神纽带
《大漠祭》之后,雪漠连续推出系列长篇《猎原》、《白虎关》等,以西部乡土叙事而备受文坛关注,这几部长篇都以腾格里沙漠边缘沙湾村的普通农户老顺一家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大漠祭》真实生动、饱含深情地叙写了西部农民艰难、严酷、悲凉的生存境遇和他们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在现代性背景下,沙湾村人那种类原始的生存方式和民间道德理念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明的侵袭,首先是自然生态因物欲的膨胀和生存的艰难而受到严重的破坏,并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现实生存,即使身兼三种身份——农民、牧民、猎人,依然难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与尊严,他们不得不继续向沙漠索取,向戈壁深处的沙窝去谋生存;在《猎原》中,他们还得应付那些偷猎者和外部文明所带来的外国投机者、手机、电视、碟机、明星照、进口面包车等现代化符号的诱惑,沙湾村已经不再是原生态的、孤立的西部乡土的“存在”了,它成了现代化观照下西部沙漠边缘的一个乡村。大漠这个浑厚、酷厉而又苍凉的文化意象,是即将逝去的一种文明形态和生存方式的象征,它沉寂千年,充满苦难又饱含温情,雪漠在新世纪的钟声里让世人看到了原始而又悲怆的存在,这群农民勤勉、诚实、顽强、豁达、坚韧地活着,西部的生存环境是阔大、雄浑、严峻而单调的,他们有生之艰难、死之无奈、病之痛苦,也不乏爱之甜蜜,尽管他们的观念有时显得保守封闭愚昧,但是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有足以在艰难环境中维系生存的强大的精神纽带。
《白虎关》延续了前两部的故事和人物命运,小说的线索是为猛子娶媳妇,猛子不断与村上的有夫之妇苟且让老顺觉得丢脸和亏欠了儿子,决定不惜代价为猛子说媳妇,夫妻俩还一厢情愿地想让莹儿嫁给猛子,既节省了彩礼,又可守住唯一的孙子。围绕这一中心事件,老顺家和莹儿娘家展开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而一切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一个“穷”字,而“穷”是相对的,作者尖锐地指出穷的根源在于人的欲望的膨胀。白虎关没发现金矿前,大家都穷,贫富悬殊并不太大,外面的世界对沙湾村的刺激远没有近在咫尺的黄金那样让人难以忍受,老顺等村民既无财力又无胆识去金窝子讨生活,艳羡、嫉妒、仇恨等情绪就在沙湾村逐渐蔓延,猛子和花球偷双福矿上的金沙被捉,被迫当沙娃又险些送了性命,于是,他和北柱掘了双福家的祖坟,俩人坟时的对话深刻揭示了部分农民内心的扭曲与矛盾,他们承认双福们的钱是“挣死挣活挣来的”,但双福们的富显出了他们的穷,双福给村里修学校、给村人发钱羞辱了他们,挑战了他们固有的价值观,反而加深了村人的仇恨。“二两酒喝一天”与“喝得起酒,喝不起时间”是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雪漠觉察到西部农民贫穷的文化心理根源和巨大深厚的精神惰性。仇富、掘人祖坟,从新旧道德的立场上看都是为人不齿的行为。双福女人秀秀打心眼里蔑视掘坟者,她说掘坟者“最终把自己心里的一种东西给掘了”;她认为双福是条“汉子”,“谁的坟,是谁自己掘的”。她对双福的评价是中肯的,尽管在《大漠祭》中,她拒不接受20万元的离婚费。她见识非凡,对人性的剖析透彻犀利,让人感佩之余心生畏惧,猛子觉得她“成精了”。秀秀是雪漠系列长篇中最具有现代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人物,虽然作者将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聚焦在她身上,使她处于生存的困境中,但她异常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自主意识还是让人觉得她在代作者立言。雪漠将她塑造成了沙湾村的“智者”或“旁观者”,另一个是孟八爷,但孟八爷是沉浸于其中的,他身上更多农牧文化的精神素质。
在《白虎关》中,雪漠在努力探索农村贫穷的根源,并将触角深入到人性的最隐秘阴暗的角落,他没有简单地将思索停留在外部社会,而是向文化心理的纵深处开掘,他的剖析是客观深刻而公允的,既无有意识的拔高,也没有韩少功式的夸张变形,他选择以原生态的生活真实震撼读者的心灵,并在事实上超越了《大漠祭》和《猎原》中对西部精神的歌咏,对农牧文明的盲目怀恋,显然,农牧文明的田园牧歌并不是抵抗现代工业文明的良药。他痛苦地发现将苦难崇高化的梦想已经无法抗衡现代物质文明对西部农民的强烈诱惑,西部农民的欲望在外来者或异质文明的刺激下正在畸形变态地膨胀,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颇具毁灭性的阻力,不仅阻碍经济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对人性善恶和人的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沙湾村那些损人不利己的思想行为,那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和陋习,以及人们对人性遭受践踏的那种熟视无睹,诸如换亲习俗,甘于贫穷,贪恋闲适,对女性人格尊严的肆意践踏等等,也许这才是西部农村贫穷的根本原因,这种价值观和文化心理才是阻碍人类进步的最大阻力。从这一层面看,小说立意高远,比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更加深刻厚重,发人深省,但是,由于作家地处西部,宣传力度不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小说相对松散的结构和散文化的笔法使小说的叙事节奏和故事性不及《湖光山色》,在可读性上略逊一筹。
二、西部农民精神生态系统艰难而痛苦的现代转型
如果说《大漠祭》和《猎原》中女性是情节发展重要元素的话,那么《白虎关》就是一部西部农村女性生存、挣扎与奋斗的悲歌,兰兰的自我意识在一系列灾难打击下开始觉醒。对婚姻、亲情、恋情先后绝望的她,把精神寄托在修行之上,而宗教也被庸俗功利的村人们亵渎,经过痛苦的反思,她毅然走出金刚亥母洞,决定自我救赎,她和莹儿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为各自兄弟娶妻的责任。在贫穷落后的西部农村,为自由、爱情、尊严而抗争在亲人眼里是荒唐的,五四新女性的追求竟显得那样奢侈。在现实中,当人对现世人生绝望时就会求助于宗教或神明,当作家无力解决现实人生的矛盾与困惑时就会下意识地选择由女性来承担灾难,激发或培育能够拯救世界的男性,张贤亮、张炜的大多数作品在小说情节发展的关键处,都让女人来拯救男人(肉体上或精神上),进而由男人来拯救世界,这种叙事模式早已被女性主义谴责和批判过。雪漠期望女性从经济上解放男性潜在的力量,帮助他们成长。难道金钱真的能拯救猛子懵懂混沌的心灵,难道富裕真的能改变白福赌博打老婆迷信愚昧残忍(他为生儿子遗弃并致女儿死命)的精神惰性吗?
我们承认雪漠小说那透骨的真实,西部农村的民间道德伦理规范有它的独特性和地域性,它对人的评价标准与现代城市有很大的差异,那始终是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勤劳肯干、诚实守信是男人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素质,其他的缺陷都可忽略不计,而女性却没有最基本的尊严和人权。现实如是,作家却不能仅仅做一个时代的记录者,而应站在全球化、现代性的高度对西部农村社会的变迁、人心的善恶进行审美的关照。雪漠扎根西部、书写西部,其心其情真切可感,但爱的方式似可商榷。鲁迅先生对童年时代的朋友闰土在同情之余更多的是批判,而雪漠却沉浸于西部人近乎原生态的精神生态系统之中,且影响了他对生存和生命本身的深层体验,影响了他对现代性关照下的西部农村现实生存与发展走向的准确把握。小说对西部生存方式和道德伦理的认同,对猛子等人的宽容,都限制了作者对思想文化的挖掘和艺术想象力的飞扬。猛子在系列长篇中经历了兄弟的生离死别,接受过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的思想教育,经历了偷情恋爱,亲眼目睹兰兰和莹儿的灾难与挣扎,偷过金沙和豆子,掘过双福家的祖坟,开过金窝子,参与过械斗等等,遍尝人间百味,却始终冥顽不灵。而见识非凡、心高气傲的秀秀缘何与他纠缠不清呢?是本能需要,还是为了报复丈夫的冷漠与背叛,或者是跟猛子之间产生了朦胧的爱情,好像都不是。秀秀无形中成为猛子成长的工具,秀秀的言行缺乏逻辑上的合理性和完整性。猛子的反思是成长的希望;而白福、花球、北柱、白狗、王秃子等却正在放逐着自己曾经坚守过的西部精神,或以暴制暴,或向泼皮无赖滑落,这使我们忧虑而恐惧。对他们的同情和怜悯,不仅削弱了小说的现实批判性,还使叙事陷入了无意义的循环。关注转型期西部农民如何活着固然重要,考察他们为什么这样活着,怎样活得更好,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神圣的使命。
面对冥顽不灵的猛子们,作者理性批判的锋芒消失了。在西部荒原上猛子们俯拾皆是,苍凉的荒漠还无力自发形成启蒙者,老顺、孟八爷、秀秀、莹儿似乎都无力承担,灵官还在漂泊的路上。猛子精神上的惰性是可怕的,他成长的艰难是由于作者对他的娇纵,对乡土的深沉眷恋影响了作者的价值判断,限制了小说人物和情节的设置。或许猛子的设置是为了揭示西部生存的艰难和西部人精神成长的曲折,猛子既没有许三多的幸运和机遇,也没有《奋斗》中那班80后的自负和优越。无论初衷如何,猛子都让人觉得如鲠在喉,他就像一块没有开化的顽石,物质和精神的贫乏使人的成长更加艰难,这或许就是猛子作为“这一个”的独特魅力吧。
三、雪漠如何超越西部人原生态的精神生态系统
雪漠习惯于在小说的前言或后记中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和审美价值取向,《猎原》的题记是“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①,《白虎关》有一篇很长的后记。雪漠对许多读者将《猎原》作为环保小说来读颇有微词,认为是误读。在文学阅读中产生“误读”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读者的思想深度和阅读水平有限,导致误读;一是小说本身无法完成作者所赋予的使命。《猎原》被误读应属于第二种情况,即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思想高度,文本无力承担,文本呈现的是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斗智斗勇的故事。唐达天(甘肃作家)的《沙尘暴》也叙述了人类如何与自然抗争,沙漠步步紧逼,不断侵蚀着人的生存空间,村人被迫移民新疆的悲壮与苍凉,作者对人与自然、对现代文明渴盼的急功近利与对故土深沉的眷恋、市场经济模式与传统小农经济等一系列矛盾的揭示,以及西部农民在外来经济文化冲击下的痛苦的精神裂变,都使读者无法将它作为一部环保小说来对待。《猎原》的叙事拖沓冗长,线索单一,人物的传奇性冲淡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故事性、抒情性、地域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却削弱了小说思想的深刻性。
雪漠说:“我仅仅是想定格一种即将逝去的存在。”②作者的创作理想和审美追求自然无可厚非,巴尔扎克曾说自己是法国社会和时代的记录员,贾平凹也曾在《废都》中真实深刻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所经历的精神与肉体裂变的过程,小说因表现力和性描写等问题招致非议,也给作者带来烦恼。雪漠的确写活了“一户农民”,但这种原生态的、“活化石”式的生存模式在现代化进程中注定是要消亡的,记录之外如何评价?是站在全球化或者至少站在中国现代化的视野下,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来观照它,还是站在沙漠的边缘或者西部的某一高处来审视它、怀恋它?李建军对《废都》的批评很多都是中肯的,如果作者能超越现实生存层面,进入存在与文化层面对庄之蝶的人生进行审美观照,小说就会向《红楼梦》和《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经典再靠近一步。小说的格局要大,作家的精神境界和创作视界就要更加高远。雪漠和贾平凹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还有打磨、锻造的必要和空间。
雪漠表现的是一种“静默地忍受”的道德,老顺的口头禅是“老天爷能给,老子就能受”,但是,隐忍并不能带来现代化,也不能阻止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乡土文明消亡的趋势,如何积极面对,是雪漠和“老顺们”共同的难题。早在2004年,雷达先生就注意到雪漠小说创作视界褊狭的问题,他指出:“除了沙湾这个小社会之外,雪漠还能知道多少东西?他会写沙湾小社会,会不会写之外的大社会?或者能不能把沙湾小社会放到大社会中去看?我觉得,他需要一种东西文化撞击后的眼光。”③遗憾的是,《白虎关》并没有完成这种超越。雪漠表示老顺系列已经完成,以后的创作将有新的格局,但能否超越自己,关键在于作者能否在文化心理和精神层面完成对西部农民原生态的精神生态系统和伦理规范的超越,站在全球化和人类性的高度审视和关照现代化进程中的西部乡土和农民。近年来,雪漠醉心研究佛教文化,他的研究能否对全球化经济大潮下人的精神信仰危机有所裨益,并与他已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相交融,成为其文学创作的精神文化资源,还很难预测。
作者简介:李清霞,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
① 雪漠:《猎原》题记,见《猎原》扉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② 雪漠:《白虎关》后记,见《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
③ 雷达:《雪漠小说的意义》,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6月18日第8版。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