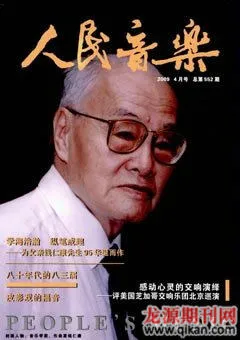1937年吕骥的北平、绥远之行
时光进入了1936年的初冬,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下已经度过了5年的艰苦岁月,民族生存危在旦夕。盘踞在我国张北、百灵庙一带的“伪蒙古军政府”助桀为虐,接受日本侵略者的大批军用物资支援和日本指挥官的扶持,伺机向绥远地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及以西地区)扩张。
11月5日,贪心不足蛇吞象的日本侵略者,在亲日的“伪蒙古军政府”所在地嘉卜寺(今化德)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集中主要兵力先进犯绥东,占领红格尔图(即四子王旗的锡拉木伦庙,俗称大庙)后,进一步攻占归绥(今呼和浩特)。
10天后,日伪军联合起来,果然对红格尔图发动了攻势。
绥远省政府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傅作义将军(1895—1974)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不断高涨的全民族抗战热潮推动下,亲临平地泉(今集宁)前线,指挥四个多团的兵力,迎击气焰嚣张的日伪军,连续击退了他们多次进攻,迫使他们不得不退守商都。
不甘失败的日伪军,很快又重新集结起来,将兵力部署于多伦、商都、百灵庙一带,日军还增加了200多名指挥官,临阵指挥,企图卷土重来。
红格尔图一战的胜利,给中国军队以极大鼓舞。傅作义将军决定一鼓作气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给蠢蠢欲动的日伪军以狠狠打击。11月23日夜,35军以一个骑兵团和211旅的三个步兵团的兵力,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在山炮、装甲车配合下,主动向百灵庙地区发起奇袭,24日,一举收复了百灵庙,歼灭伪盟军第二军第七师大部。12月2日,又击退了日伪军4000余人的多次反扑,歼敌700余人,百灵庙战役大获全胜。
1937年1月8日,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写道,百灵庙战役大获全胜,在缴获的战利品中,除“军用品(子弹20万发、汽油千箱)无以数计外,并有万袋白面及白糖,罐头食品数百箱”。又说,“如果提及日寇的阴谋,飞机坦克就是最好的铁证。不只这样,这次所获的战利品里面,还有好些秘密文件。在日寇特务机关长住的房子里,找到了大批的日文、蒙文、汉文和日蒙、日汉蒙合印的书籍、小册子、印刷品等等。……尚有中国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十余厚册,中国所有军队的名单,官长自营以上的名字籍贯履历,其他文件不可数计,此外还有日人所设的无线电台,这可见日寇阴谋的一斑了。”
绥远抗战的百灵庙大捷,是日本入侵中国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辉煌胜利。消息传到上海,万众欢腾。为祝贺绥远抗战的胜利,声援绥远前线的将士们,吕骥等救亡歌咏运动的领导者们,在上海市总商会礼堂组织了一场规模盛大的“援绥音乐会”。参加演出的有:法商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任光领导的“森森乐队”,上海音专夏国琼的钢琴独奏,歌唱家郎毓秀、蔡绍序等人的独(重)唱,常学墉(即任虹)、石人望主持的“光明”、“联合”两个口琴队,丁珰(即丁致中)的二胡独奏,张捨之的小提琴独奏,何士德指挥的圣乐团——洪钟歌咏团的合唱,以及住在大场镇以张劲夫为团长(亦称校长)的“山海工学团”的孩子们……
谁也没有想到,音乐会被“山海工学团”的孩子们推向了高潮。
穿着农民粗布衣、打着赤脚的孩子们走上了舞台,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十几个人站成一排,在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指挥下,唱起了《谁说我们年纪小》。天真稚气的小脸,银铃般的歌声,以及那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头,使在场的每个人都激动不已。当他们唱到“谁说我们年纪小,万恶的敌人要我们来打倒,陈腐的旧社会要我们来改造”时,全场沸腾了,歌声伴着掌声,掌声和着歌声,犹如万钧雷霆,撼动着每个人的心,许多人激动得流出了泪水……
2005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人民音乐家吕骥传》及书后的附录一“吕骥年表”,在写到这次音乐会时的记述,“陶行知领导的大场山海工学团的儿童们演唱儿童歌曲《只怕不抵抗》”(见该书第162页),是不准确的。一、据史料记载,当时“山海工学团”的领导早已不是陶行知,而是张劲夫团长(亦称校长);二、当年参加过“援绥音乐会”的“山海工学团”小团员、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应彬(即杨石)在散文集《春草集》(1984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中回忆,当时演唱的是应凯作词、贺绿汀作曲的《谁说我们年纪小》。
“援绥音乐会”是上海音乐界空前大团结、大统一、大联合的一次音乐盛会,演出的全部收入捐给了绥远抗战的将士们。百灵庙大捷的消息激励着全国军民的爱国热情,各地、各界人士都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捐款援绥。有的学生集体停伙一日,把省下来的钱寄往绥远前线。有的教师联合起来捐出一日薪援绥。全国各地的演出活动层出不穷,他们把演出的收入纷纷寄往绥远前线。甚至连监狱里的犯人也联合起来,停伙三日,用省下来的伙食费劳军。在归绥,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截至1937年初,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竟达300多万银元。这样一个团结坚强的民族,早已注定了日本侵略者必然失败的下场。
1937年2月,为慰劳绥远前线的抗战将士,上海地下党再次决定,以“新安旅行团”为主,组织一支“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劳团”,北上归绥。
这已是上海地下党第三次派人参加或组织赴绥远前线慰劳团了。第一次,是1936年12月中旬,由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率领的“上海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劳团”,赴归绥劳军。团员中有三名“新旅”派出的儿童代表张俊鑫(张早)、曹维东、左义华(左林)。随团赴绥的还有戏剧家崔嵬。因为那次带去了由吕骥作曲(《新编“九一八”小调》)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由崔嵬、陈波儿、张俊鑫合演。第二次,是1937年1月中旬,再次从“新旅”抽调三名儿童代表张杰、程昌林、童常北上,参加在北平组建的“平、津、沪三市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劳团”。这次,已是第三次,是以“新旅”为主组成的“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劳团”。
在以往的许多材料中,包括《人民音乐家吕骥传》及书后的附录一“吕骥年表”,分不清这三次赴绥慰劳团的组织情况及参与人员,总是把三次混为一谈。《人民音乐家吕骥传》中写道?押“1937年1月间,上海和北平文化界组织了‘上海、北平文化界慰问团’赴绥远慰问抗日将士。新安旅行团参加了这个慰问团,吕骥、崔嵬也同行。”并说“吕骥于1月底到达北平。”(见该书第28页)这是最典型的“混为一谈”,并将慰劳团的名称及吕骥到达北平的时间都作了错误记载。该书后的附录一“吕骥年表”还说,“在崔嵬的介绍下吕骥随新安儿童旅行团于1月底到达北平。”(见该书第163页)一句话里有三处失误:一、“新安旅行团”虽由儿童组成,但准确的名称是“新安旅行团”?熏并无“儿童”二字;二、吕骥不是“在崔嵬的介绍下”,“随新安儿童旅行团”北上的,而是以团长身份率领该团北上;三、吕骥到达北平的时间,也不是1月底。
1937年2月3日,由上海文化界地下党组织指派吕骥为团长、“新安旅行团”负责人之一的汪达之为副团长的“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劳团”,从上海出发。为节省经费,他们从十六铺码头乘船北上,到达天津塘沽港后,由天津转车赴北平。为躲避路上敌伪关卡的检查,他们所带的慰劳品、书籍、电影器材等,早已由第二批抽调北上的张杰、程昌林、童常三人,于1月中旬乘火车直接押运北平。
“慰劳团”出发那天,麦新、孟波等“歌曲研究会”的同仁们到十六铺码头来为吕骥送行。麦新还带来了二百本刚刚再版的《大众歌声》(第一辑)送给慰劳团,并对吕骥说,他也很想离开上海,到抗战前线去。果然,在吕骥走后不久,同年9月25日,麦新参加了以钱亦石为队长的一支“战地服务队”离开了上海,与刘田夫、石凌鹤、杨应彬、孙慎、吉联抗等人,到张发奎任总司令的第八集团军做抗战宣传工作,活动于江、浙、粤、赣、鄂等地,后到延安。抗战胜利后,转赴东北,直至他长眠在辽阔的科尔沁草原,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上海。
2月6日,“慰劳团”一行抵达敌伪控制的塘沽港。上岸后,立即转车赴北平。
在平期间,“慰劳团”先是住在位于长安街上的“艺文中学”,后搬到宣武门内未英胡同的“育英中学”。
北平历来是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心。在北平的日子里,吕骥有意把救亡歌咏运动与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结合起来。在“北平学联”帮助下,很快由各校抽调出来的学生运动骨干组成了“北平学联合唱团”,教他们演唱《五月的鲜花》、《新女性》以及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等。
“学联合唱团”的成员们返校后,又组织起各种形式的合唱团或歌咏队。吕骥又联合各校的合唱(歌咏)团(队),组成了“北平歌咏团联合会”(简称“歌联”),使救亡歌咏运动很快在学生中间传播开来,并很快波及到军民之中。
3月14日,“慰劳团”离平赴归绥。临行前,吕骥为即将在归绥举行的“绥远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和祝捷阅兵典礼”,谱写了一首挽歌《敬挽阵亡将士》。歌词是由被钱玄同和刘半农戏称为“诗孩”的著名诗人孙席珍(1903—1984)撰写。在西去的列车上,吕骥将挽歌抄在一块白布上,挂在“闷罐”车里,一路教团员们演唱。
这时的归绥,已经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个慰劳团、演出团、救护队等,挤得满满的,大小旅社和饭店都住满了人。他们到达后,绥远省政府只好安排他们住在归绥中学的教室里,并特派该校的霍校长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每天用一辆大客车,专门接送他们到绥远大饭店去吃饭。
第二天,在霍校长陪同下,吕骥和慰劳团全体成员去省政府谒见了傅作义将军。当年参加过慰劳团的“新旅”小团员黄中一,在回忆文章《在内蒙古大草原》①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代表上海文化界和后方千百万少年儿童向他表示了敬意和慰问。傅将军身材高大魁梧,非常英俊,和我们讲话的时候很和蔼可亲。他见我们新旅团员年龄幼小、十几岁就立志跑遍全国宣传抗日救亡,现在又到冰天雪地的塞北前线来慰劳,很是感动。……我们拿出题词簿请他为我们题词留念。他叫副官取来纸笔,不假思索,就刚劲有力地写了两行字:‘行万里路,聪明了你们的耳目;读万卷书,增进了你们的知识。’”
3月15日,在归绥大教场(并非《人民音乐家吕骥传》及附录一“吕骥年表”中所说的“烈士公园”)举行隆重、肃穆的“绥远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和祝捷阅兵典礼”。绥远省政府主席、35军军长傅作义将军,坐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吕骥也坐在主席台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慰劳、演出、救护团体以及归绥军民近三万人参加了大会。汪精卫、阎锡山也专程赶来,参加追悼、阅兵活动。
那天,狂风肆虐,黄沙蔽日,会场的气氛格外肃穆、庄严。追悼仪式开始,“新旅”的孩子们唱起了哀婉的《敬挽阵亡将士》歌:
荒沙里,敌人的炮声未息,
你们已经战死。
今天,全国军民已经觉醒,
我要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
安息吧,勇士,
你们的英名永远不灭,不灭。
接着,汪达之宣读了《上海文化界致绥远前线抗日将士书》,献了锦旗和慰问品。“新旅”还向傅作义将军献了银盾。
追悼活动后,举行了雄壮的阅兵典礼。大会结束后,慰劳团立即开始了慰劳活动。连续几天,他们跑遍了归绥各伤兵医院慰问伤兵,给他们唱歌、读报、讲时事,替他们写家信。慰劳之余,他们还参观了民生渠,游览了名胜古迹昭君墓。黄中一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吕骥同志得了肺炎,住进了省立医院。那次北上他的行李非常简单,只带了一条很小的被子,他说这是鸭绒的,盖了很暖和,但是毕竟太小了一点,夜里受冻,再加上工作劳累,就得了肺炎。团体派我和几个小团员轮流着去医院看望服侍他。”②短短几句话里一再提到吕骥“得了肺炎”。
《人民音乐家吕骥传》在写到这个细节时说,“3月17日,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将他(指吕骥)送医院治疗,诊断为患急性胃炎。”(见该书第29页)该书后面的附录一“吕骥年表”说,“追悼会后,吕骥终因工作过劳和水土不服患急性胃炎病倒了,于3月17日被省政府送进一个天主教医院医治。”(见该书第164页)一个说傅作义送吕骥住院,一个说省政府送吕骥住院。一本两说。
那么,吕骥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住的又是哪所医院呢?
当时在归绥,医术较好、设备较齐全的医院,只有两所。一所是黄中一讲的“绥远省立医院”;一所是《人民音乐家吕骥传》及“附录一”所讲的那所“天主教医院”。当时,它的名字也不叫“天主教医院”,而是天主教会开办的名叫“归绥公医院”,后改名为“公教医院”。省政府会不会绕过自己管辖的“省立医院”,送吕骥去住一所“天主教医院”呢?我认为黄中一的回忆“住进了省立医院”是真实的,因为他亲自护理过吕骥,这样的记忆是不大容易忘记的。如果吕骥真的住过“天主教医院”,那也只能是在“省立医院”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不得不将吕骥转入这所医术设备稍好一点的“归绥公医院”。那么,吕骥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呢?
《人民音乐家吕骥传》及附录一“吕骥年表”认为吕骥得的是“急性胃炎”。“附录一”还对吕骥的病情作了这样的描述:“吕骥病情相当严重,以至神甫到他的病床前做了临终祈祷,在他胸前放了一个小十字架。”(见该书第164页)按天主教习俗,为病人“做了临终祈祷”,并在胸前放了小十字架,说明吕骥已经病危。这也恰好证明黄中一的回忆是准确的,吕骥得的是肺炎,而不是胃炎。稍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再严重的胃炎,只要没有穿孔,停食两天,即可缓解,很少危及生命。吕骥作为一个南方人,第一次来到冰天雪地的塞北,所带行李又很单薄,夜里偶感风寒,得了肺炎。当时消炎药又奇缺,致使肺部大面积感染,高烧不止,当然危及生命。看来,亲自护理过吕骥的黄中一回忆是可信的。
直到4月中旬,吕骥的病情基本稳定,便在“新旅”两位小团员张早、左义华护送下,返回北平。
4月末,基本康复,又立即投入到救亡歌咏运动之中。
5月4日,是“五四”运动十八周年纪念日。北平各界学生在“清华大学”新建的体育馆内,举行纪念大会。“北平学联”安排吕骥在大会开始前,教唱救亡歌曲。他指挥大家学唱与麦新共同创作于1936年末的《保卫马德里》。这首歌曾在章乃器、钱俊瑞创办的半月刊《现世界》上发表(上海引擎出版社印行),并翻译成世界语、西班牙语,以及英、法、德、意、日、苏联等国文字,寄往世界各地,有着广泛影响。与会的近千名爱国学生,在吕骥指挥下,群情激昂,歌声嘹亮。正在大家唱得起劲时,突然一群国民党分子闯进会场。他们一边无理驱赶学生代表,一边呼喊:“唱什么唱?中国还未保卫好,保卫什么马德里?”双方发生冲突,大打出手。吕骥在进步学生李伟(军旅作曲家,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护送下,迅速离开会场。大会无果而终。
5月末,日本侵略者大举增兵华北,处心积虑地策动“华北自治”。战云密布在北平上空,吕骥感到工作难以开展,便再次离平赴归绥。
这次,他是以绥远省政府特聘的“音乐教授”身份,到归绥一带开展音乐工作的,没有再与“新旅”一起行动。此时的“新旅”正由五原一带继续西进,活动于乌加河两岸、临河、杭锦后旗、陕坝等地。
吕骥在归绥,先到“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组织的歌咏团去教唱救亡歌曲,并多次到“蒙旗师范学校”(不是《人民音乐家吕骥传》中所说的“蒙藏学校”,“蒙藏学校”在北平)去上音乐课,到35军军乐队去搞调研,在官兵们中间教唱救亡歌曲。他还跑遍了武川、土默特左旗、达拉特旗等好几个旗、镇,搜集整理了大量绥远地区的民歌。并将其中较好的六首,以《短歌》为题,发表在缪天瑞主编的《音乐教育》(1937年9、10月合刊)上。其中一首,后来成为马思聪创作著名小提琴曲《思乡曲》的主要素材。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的形势变得愈发严峻。吕骥决定离绥赴晋,向傅作义将军辞行。傅将军再三挽留未果,只好送他四十元川资,与之话别。
吕骥搭乘35军的军用卡车,冒着盛夏的酷暑,经凉城、左云,到达山西大同。几天后,又由大同乘火车,经朔州、忻州继续南下,8月初,到达太原。
五台山——清凉山,只一步之遥。吕骥站在烽火弥漫的五台山上,向着清凉山的方向眺望,他仿佛看到了清凉山上那巍巍宝塔的身影,心中向往着革命圣地延安………
①②陈强、陈明等编《烽火五万里——新安旅行团》,1983年出版。
乔书田原吉林省歌剧舞剧院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编剧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