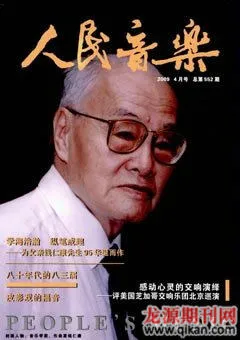多元文化视角的乐器文化因素
乐器文化因素的研究属于乐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乐器学领域同词源学及语义学相关,联系着乐器的历史和地理文化分布。①乐器是历史与文化的活的载体,是音乐发展的确凿见证。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经济一体化、信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音乐呈现出西方和东方、现代和传统、外来和本土、兼容和并存的状态。本文从乐器文化的地域性因素、代表性因素、认同性因素三个方面对乐器文化因素进行诠释。
一、乐器文化的地域性因素
乐器是体现该民族该地域音乐文化的一种代名词,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中产生不同的乐器,同时乐器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
以中国音乐较典型的乐器组为例,其体现了乐器文化的地域性因素。如:中国传统乐器中的天津十番乐“粗十番”;福建南音的“上四管、下四管”等等。
天津十番乐中的“粗十番”?熏也称为“清十番”或“素十番”,即表示只用打击乐器演奏锣鼓乐?熏而不加任何管弦乐器演奏。“天津十番”最初是由苏南传入天津的?熏在多年传承和研习过程中?熏受到天津地方语言、风土人情、北方人性格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熏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天津十番。“粗十番”锣鼓乐铿锵有力的敲击声,显现出北方人粗犷豪放的性格和特征,在音调上低沉苍劲,这和天津地方语言有着较紧密的联系,天津方言的语调多为平降调,因此在唱念锣鼓经时?熏习惯于把“七”“仓”“扎”等锣鼓经用较重的降调来念诵,进一步增加了音调与力度变化的感染力②,因而更具有北方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地处中国东南海隅的福建,东临大海,西、北、中部临山脉,这在交通闭塞的古代,给福建造成与世隔绝的另一番天地。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很好地保存了传入福建地域的音乐形式,如福建南音上四管中的琵琶演奏,至今还是延续了唐朝时期的演奏手法与抱持方法,演奏手法仍用手指甲演奏,抱持仍为横抱,在音品方面南琶只有九品或十品,只能满足演奏福建南音的旋律。③南音中的洞箫与当代所使用的箫在形制与演奏上也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继承了古尺八、宋尺八精华的乐器。结构上南音洞箫保留了唐代六孔尺八的规制,音域从d—b2,拥有两个八度和一个五度音;造型上又吸收了宋尺八的特长,以竹的十目九节和一目两孔为标准,下部无底;长度上恰好与明清两代营造尺的一尺八寸相当,尺八到了明代又有一如今天的南音洞箫这种规制的进步。演奏讲究端坐、挺胸。左手拇指按后孔,食指、中指(或无名指)按后孔,右手拇指把稳乐器,食指、中指、无名指掌握三、四、五孔;左右手臂展起,成凤凰展翅之势④,与今演奏形式不同,颇具古风。南音体现了福建文化自古多山、交通不便的地域性因素,为中国音乐保留了“一部活的音乐史”⑤,是华夏传统音乐的“活化石”。⑥
有些地区的乐器不仅涉及乐器的原生物质形态?熏而且还同该地的自然生态、地理环境和经济文化方式结合紧密。⑦如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呼伦贝尔呈交错状态分布着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林业、牧业和农业是其主要的生产方式。自然地理条件有所差异:北部,地处大兴安岭北麓森林腹地,人烟稀少而苔藓、石蕊丰富,是鄂温克族游猎和饲养训鹿之地,在此环境下形成了山林型的萨满鼓,即鼓体沉重、粗犷,鼓圈宽大,为“上圆下尖”之蛋卵形,鼓面为鹿皮蒙制,鼓的制作材料为木、皮、铁,鼓槌粗短,为木板槌体面附带毛兽皮;西部,地跨森林、草甸草原和干旱草原三个地带,多为天然牧场,在此环境下形成了草原型萨满鼓,即鼓体轻便,鼓圈较小,为圆形,鼓面为羊皮,鼓的制作材料主要为木、皮,鼓绳为三根,鼓槌细长多为狍腿加工制作;东、南部山地、丘陵、河谷、平原兼具,体现出林牧农结合的特点,形成了混合形态的萨满鼓,即鼓圈为圆形或蛋卵形,木框,鼓面为鹿皮蒙制,鼓绳为八根,鼓槌为狍腿加工制作。⑧在同一个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呼伦贝尔地区里其乐器就有此差异性,可见地域性差异对乐器形制影响之大。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有迷人的“会说话”的乐器:如凉山彝族的青年男女用来谈情说爱的口弦;苗族用来问路、聊天的芦笙;傣族商贩用来与买主讨价还价的葫芦丝等等;⑨鄂伦春族狩猎时还有专为诱捕鹿的鹿哨;⑩西南各少数民族可模拟鸟雀鸣唱的口弦;“骑在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如马嘶鸣的马头琴等。这些乐器都是在其地域里产生并发展的,蕴涵着该地域的文化内涵。
全世界有很多属热带雨林气候的国家盛产竹子,而反映在乐器上,即产生了大量的竹制乐器。如:在南美洲安第斯高原上,印地安人的代表性乐器具有竹制的盖纳竖笛,他们还采用竹子和其他植物茎制成各种尺寸和规格的排箫。在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巨大的竹排箫是他们的典型乐器。在东南亚,有各种竹笛竹箫,还有摇奏的安格隆竹筒琴和用手指弹拨的竹皮弦琴(是一种竹筒表面挑起竹皮为琴弦的自娱性乐器);印度尼西亚的甘邦竹琴、缅甸的帕德拉竹琴、柬埔寨的罗奈特竹琴、越南的德朗竹琴和菲律宾的达姆加底琴等,{11}这些竹制乐器都体现了竹文化的地域性因素。竹乐器在中国的西南、东南地区屡见不鲜,如苗族的芦笙、芒筒等;台湾高山族的口簧琴(过去所称的口弦),台湾高山族音乐学者巴奈·母路于1997年夏参加了在奥地利举办的国际口簧艺术季,巴奈·母路带去的阿美人制作的口簧琴因其为竹子制作且多簧而引起西方音乐家的扼腕惊叹:“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多簧的竹片口簧琴,而且是活体的生态,你们不能使它消失,这是你们对人类应该承担的责任。”{12}现此乐器仍在高山族阿美人中使用并保存,成为高山族乐器史活的实物见证。
二、乐器文化的代表性因素
乐器是用来了解当地音乐文化的一种代名词,不同的音乐文化联系着不同的代表性乐器,而这些乐器也被用于了解一个音乐文化的切入点。
就乐器组而言,二十世纪初期的乐器分类学者大都注意到古代中国以乐器材料为划分依据的“八音”?熏他们认为这个整体性的乐器分类反映了古代中国关于世界的概念?熏含有宇宙的威力和要素,背后所蕴藏的是有机哲学下的一个现象。因为早期中国是农业社会,一切以农为中心,中国产生了最早的四分法:丝、金、革、竹。秋天,以钟等金属乐器,将帅鸣金收兵,秋气收敛,方位在西;冬季,以鼓宣告太阳重行前进,方位在北;春季,万物更新,竹经严冬而长绿,如日出东方,方位在东;夏季,蚕吐丝成蛹,适演奏丝弦乐器,方位在南。而当时人类靠天生活,乃有各种祭祀,向八个方位舞蹈,分以不同乐器来掌握,则扩展为八种乐器分类,{13}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14}澳洲学者克托米的观点?熏早期的“八音”?穴及另一种相关的四分法?雪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分类法,它们同季节、风水、政治权力和人类福祉观念有关。{15}此种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乐器分类组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因素。文化代表性因素的乐器组在古希腊也存在,如古希腊将音乐与天体的运行作了关联,音乐是由恒星与行星运转所创造出来的,柏拉图认为音乐的本质在反映心灵的意向,认为“多样性”会造成有害的影响,例如弦数太多的弦乐器,音域太广的乐器都是不好的。古希腊与印度一样,将乐器与神作关联性的描述,如七弦琴与阿波罗神相关联等等。{16}这些关于乐器组的分类体现了国家文化的思想代表,同时也成为这些思想的载体。
从独立乐器来看,中国的古琴、日本的琵琶、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Gamelan)等都是各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乐器。这些“代表性”乐器因其文化及社会中的特殊角色而受到民族音乐学者的注目(Baumann 2001)。{17}每一乐器都在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产生而且发展,是民族文化因素的反映,如:中国的古琴作为中国传统乐器的代表,主要在于无品而适应于中国传统音乐的音组织形态——带腔的音。古琴的七弦乐器构造中的无品正为音高的变化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其吟、揉、绰、注等演奏手法的运用,又适合着“音高、力度、音色的某种变化”,从而使琴的演奏与中国传统音乐的音组织紧相吻合。此后,许多乐器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承继着这一“无品、音腔”模式,如:胡琴类乐器和三弦等。古琴音乐又奠定了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学紧密相关的基础。琴歌乃是音乐与诗词相结合的产物。千百年来所积累有大量琴曲,如:《高山流水》、《潇湘水云》、《广陵散》、《龙朔操》、《阳关三叠》等,这些琴曲都与一定的文学题材或文学形象相联系,这也成为中国传统器乐曲发展的一个主流。{18}黄翔鹏先生曾指出:“古琴音乐和昆曲历来被看作保存着中国古代音乐的两大宝库。”{19}“古琴音乐对中国音乐史说来类似钢琴文献对于欧洲音乐史的意义。因为它在历史上实际曾吸收、保存汉魏清商乐、南北朝隋唐俗乐大曲和唐宋以来诗、词乐的某些精华。”{20}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第23号决议,将古琴艺术列为世界遗产。2003年11月7日,该组织宣布古琴艺术为世界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如此更奠定了古琴在中国的代表性地位。古琴贯穿几千年来泱泱大国的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乐器。
日本琵琶是日本的代表性乐器,日本琵琶是在唐代?穴平安朝初期?雪由中国传入日本后作为雅乐管弦乐合奏中的一种主要乐器而被运用的。日本琵琶为四弦、四柱?熏 腹板?穴面板?雪 上开有对称的两个半月形发音孔称半月?熏 腹板中央靠近复手处有一个横约10—12厘米长的用皮革蒙着的地方,叫做拨面或拨皮,拨面上画有美丽的图案。颈部有四个柱?穴即品位?雪。琴弦至今仍用绢丝搓成,从左至右、由粗而细分别称为第一弦、第二弦、第三弦、第四弦。抱持方法至今仍是唐宋时期的首向左上方的斜抱。用右手拿拨击弦弹奏,是唐代拨弹法的保存。演奏时有拨手、一拨、掬?穴又称反拨?雪、搔手等演奏技巧。{21}这些与当时传入日本时的形制与演奏方法基本一致。日本琵琶演奏起来音色古朴、深厚,具有对古老传统原样继承的特色,因其在日本保留了一千多年来传统的琵琶形制、琵琶演奏方法而成为日本的代表性乐器。
另外还有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Gamelan)、印度的Table等等乐器同样也是历史悠久,以其独特的音色与民族魅力,在其国家内保存发展并成为具有代表性因素的乐器。
三、乐器文化的认同性因素
亚欧之间国家与亚洲之间国家乐器的交流,使得音乐织体横向性思维和多声性纵向性思维互相借鉴,{22}乐器文化的认同性在国家之间不断深化,在认同中改造、在改造中认同是乐器文化认同性因素的主旨,同时延伸到亚欧之间音乐思维的认同。
亚洲与欧洲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十六世纪起,对其他文明(阿拉伯、中国、印度、印第安和非洲)的发现和征服为欧洲带来了其他文明的乐器实物,同时也为中国、日本、印度等非欧国家带来了欧洲的乐器。如钢琴、小提琴进入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不但得到了认同而且得到很好的发展。“乐器之王”钢琴在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不但将国外的乐曲演绎得很好,而且自进入中国起就有大量具有中国民族音乐元素的乐曲产生,赋予了其中国文化特色,如钢琴曲《牧童短笛》《采茶扑蝶》等。年轻的钢琴家也证明了对于异文化乐器钢琴的接受程度:郎朗、李云迪继前辈演奏家在当代国际舞台上绽露出中华民族的锋芒。小提琴为欧洲乐器中的“皇后”,传入中国后,一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赋予了其中华民族的精神而成为千古绝唱。在当代,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考级制度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对于钢琴、小提琴这些欧洲乐器的认同和发展程度。
法国著名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在自己的作品中力图从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Gamelan)音乐中吸取灵感创造出一种静止、无发展、沉思的适合印象主义风格的音乐,管弦乐《大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十九世纪初的莱佛士起先后有几代西方音乐家对印度尼西亚的传统音乐进行研究,使得甘美兰在世界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23}
俄国人德米特里·卡林?穴Dmitri Kalinin?雪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世界音乐中心”由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赞助向日本音乐家学习日本音乐与日本筝(Koto?雪的演奏,他不仅曾为日本乐器创作了日本风格的作品,而且于2003年9月25日晚在天津音乐学院演奏厅举办了“三国演绎中日传统音乐——中、日、俄音乐家联袂演出”音乐会,在中国二胡、琵琶及日本尺八的伴奏下,他依照日本传统音乐的演奏形式?穴铺毛毯、筝触地、脱鞋跪坐?雪演奏了三首乐曲,均用日语边弹边唱。令人称道的是一位俄罗斯人居然把日本筝和歌谣弹唱得如此地道。此举突破了单一的欧洲-苏联音乐教育模式,批判“单一进化论”和“欧洲文化中心论”,拓展为“多元化”的音乐教学模式。此现象或许可以作为“它山之石”,以平等的目光与身份进入世界音乐平台,突破单一模式,使乐器使用更加多元化。{24}
亚洲之间的国家自古以来交往甚多,以中国与日本的交往为例。日本是一个不长于乐器的国家,其乐器绝大部分来源于中国,或经由我国传入印度、西亚等国的乐器。田边尚雄在《日本音乐史》中称:“在原始民族中,有广泛使用乐器的民族;也有极少使用乐器的民族,而其代之的是有着丰富的、旋律自由的民谣。我们把前者称着为长于乐器的民族,把后者称着长于声乐的民族。古代中国和埃及等国属前者,日本属后者”,{25}庆幸的是,传入日本的乐器得到了认同性并成为日本的传统音乐,乐器保存完整并应用广泛,在传习中有严格的教习制度,使其更好地得以保存。
王耀华教授的《三弦艺术论》中主要论述了中国三弦及其音乐、日本冲绳三线及其音乐、中国三弦音乐与日本冲绳三线音乐之比较研究,通过三弦这一乐器为主线对两地之间存在的历史关系、文化交流、音乐形态的各个方面进行论述,把中国与日本冲绳置于世界、亚洲这一大格局之中,从日本冲绳与日本本土、朝鲜、中国、东南亚的多重历史关系,来认识中国与日本冲绳的关系;从中国与日本冲绳的全部音乐中来研究三弦、三线及其音乐,从文化整体来研究音乐与乐器,以明确音乐在文化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26}同样说明了同一乐器在不同国家的认同性。
日本筝(Koto)是在中国的唐代时期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穴公元八世纪左右?雪,因此,在形制及演奏方法上传承了唐筝的一些特点。中国作曲家唐建平创作的日本筝曲《自鸣》,是应日本筝演奏家松村小姐委约而作的,该曲的“自鸣”来自于中国敦煌壁画的“不鼓自鸣”,该曲在乐器定弦方面首次采用了非音阶定弦法和特殊的记谱法。既不用中国音阶,也不用日本音阶,而是将十三根弦分为三组,每组四个半音,加上演奏中的按弦、颤音和划奏,这种音乐便形成一种全新的音响韵律。他的记谱方式很独特,码左方弦与码右方弦都作琴弦使用,乐谱分作码左方弦和码右方弦两行记谱,使原本不多的琴弦翻了一倍。全曲力图表现一种无拘无束的艺术创作精神,音乐节奏自由?穴不记拍?雪,从容、深邃、韵味悠长,带着一种特有的东方文化精神,给人以无尽的遐想。{27}此举说明了乐器文化的互为认同并进一步发展。
亚欧之间国家与亚洲之间国家乐器的交流,使音乐思维互相借鉴,使乐器文化的认同性在国家之间不断深化,在认同中改造、在改造中认同是乐器文化认同性因素的主旨,同时延伸到亚欧之间音乐思维的认同。乐器是人类音乐发展的实物见证与文化载体,“乐器是迄今历史上唯一可以把握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它对音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28}
①见萨克斯1929年所做研究《乐器的精神及发展》,转引自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之乐器学》,《音乐研究》2000年第1期,第55页。②王满《天津十番中的“粗十番”套曲》,《天籁》2005年第1期,第85—86页。
③这些特点与今天普遍使用的右手五指带假指甲演奏、竖抱、二十四品或二十五品的北琶形成鲜明的对比。
④王耀华《福建南音初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75页。
⑤赵沨《为泉州历史文化中心题词》,1987年春。
⑥黄翔鹏《“弦管”题外谈》,《中国音乐》1984年第2期。
⑦杨民康《中西乐器和音乐分类法的多维关系比较研究》,《黄钟》2006年第3期,第99页。
⑧刘桂腾《呼伦贝尔萨满鼓之类型——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族萨满乐器的地域文化特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21—28页。
⑨白兴发《“乐器说话”在南方少数民族社会中的应用》,《音乐探索》2003年第4期,第22页。
⑩田联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280页。
{11}陈自明《关于“竹乐器”的思考》,《艺术科技》1995年第3期,第32页。
{12}刘冬《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记福建师大的台湾高山族博士生巴奈·母路》,《福建民族》2000年第3期,第30页。
{13}郑德渊《乐器分类体系》,《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4期,第72—74页。{14}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穴上册?雪,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15}“八音”分类虽然早已被国外学术界所认识?熏但并未像印度分类系统那样被后世采用为世界性的分类法标准。
{16}同{13},第72页。
{17}蔡灿煌 《音乐物质文化研究(乐器学)的新途径——乐器的传记性案例及乐器博物馆案例》,《音乐艺术》2006年第1期,第118页。
{18}王耀华主编《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3—24页。
{19}黄翔鹏《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与发展》,《中国音乐学》1998年第4期。
{20}转引自同{19},第87页。
{21}孙丽伟《福建南音琵琶与日本琵琶比较两题》,《音乐研究》1998年第2期,第30—34页。
{22}在音乐上有两种不同的音乐思维:一个是亚洲的音乐织体横向性思维;一个是欧洲的音乐织体多声性纵向性思维。
{23}奚泰来《竹摇神韵 鼓瑟天籁——浅谈印尼的传统音乐甘美兰》,《合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28页。
{24}唐朴林《俄国人·日本筝和歌谣》,《天籁》2003年第4期,第73页。
{25}徐元勇《日本传统音乐中使用的乐器》,《交响》1996年第1期,第10页。
{26}王耀华《三弦艺术论》(上、中、下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27}李吉提《玲珑塔中话玲珑——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首届年度新作品音乐会有感》,《人民音乐》2003年第5期,第10页。
{28}?眼德?演C.萨克斯著,俞人豪译《比较音乐学——异国文化的音乐》,董维松、沈洽编《民族音乐学译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6月版,第56—57页。
何丽丽 聊城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