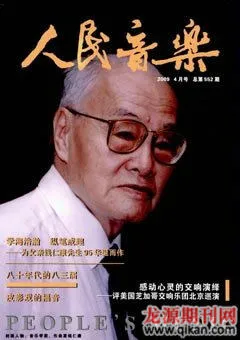《名歌手》中的“瓦格纳寓言”
爱尔兰戏剧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创作了一部名为《瓦格纳寓言》的著作,以对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的四联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1864)的描述与分析为基础,揭示其中如“主导动机”般错综的象征性手法,在探析作曲家本人思想观念的同时,将整部歌剧作品诠释为一部透视社会文化的“寓言”。实际上,用“寓言”手段表达自己的人生观以及艺术观一直是瓦格纳惯用的手法,其结果是他的作品不但在音乐界显示出分量和影响,同时也冲击着整个文化领域。在他的作品中,除了《尼伯龙根的指环》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859)由于突出体现歌剧改革精神而尤为引人注目之外,还有一部独特的作品非常值得研读,那就是《纽伦堡的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1867)。故事描述了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社会艺术生活的一个侧面:“工匠歌手”博格纳许诺要将自己的女儿埃娃嫁于一位歌唱比赛的获胜者,因此埃娃的恋人:年轻骑士瓦尔特决心参赛,虽然他没有遵循旧有的歌唱“规则”而遭到以贝克迈赛为代表的“师傅”们的反对,但是在同样身为“师傅”的鞋匠萨克斯的帮助下,以更加新颖而优美的音乐赢得了比赛胜利。
作为瓦格纳成熟阶段唯一喜剧性质的歌剧、唯一直接在情节内容上诠释个人歌剧改革理念的歌剧、唯一与“传统音乐技法”靠近的歌剧、唯一在声乐与器乐比例上表现均衡的歌剧,《名歌手》可谓是作曲家艺术生涯中各类因素的一个特殊整合结果,其独有的轻松笔调不但证明了一向亲近悲剧性风格的瓦格纳灵魂中的“另一个世界”,还让人们感受到同一作曲家在处理不同题材时的多样性与可能性。确切地说,不能够清晰准确地认识《名歌手》,就不能完整了解瓦格纳创作的全部实质。
一、多重文化因素的聚合
1.西方文化双重源头的体现
瓦格纳坚信十九世纪流行的“艺术综合”观念来自古希腊的艺术精神:“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艺术问题上不是结合希腊的艺术来进行考虑,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①,并认为自己的歌剧也是“集诗歌、戏剧与表演为一体”的古希腊戏剧形式的再现。瓦格纳对古希腊戏剧理念的继承是全方位的,他不但像古希腊戏剧家一样集诗人、剧作家与音乐家于一身,在题材上也像古希腊戏剧一样热衷于神话故事,只不过惯常采用的不是古希腊神话而是“德意志各族人民的乡土传说”②。“寓言式”的表现手法也与古希腊戏剧充满隐喻与象征色彩的陈述方式相近,这使他几乎成为十九世纪音乐领域一位新的“伊索”。《名歌手》的最初脚本构思于《唐豪塞》(1845)之后,音乐完成于《特里斯坦》之后,两次从悲剧到喜剧的创作连接不但在形式上遵循了古希腊戏剧创作悲喜剧交替的习惯,也表现出作曲家可与古希腊戏剧家相媲美的自由游弋于两种戏剧精神之间的才能。尽管德国哲学家尼采(Nietzsche,1844—1900)认为瓦格纳是“自埃斯库罗斯之后的酒神颂戏剧家”③,但充满温暖情感与希望梦想的《名歌手》却是一部具有典型“日神”精神的作品,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就引用了《名歌手》第三幕中萨克斯对瓦尔特解释诗歌与梦的关系的剧词来阐发他心目中的“日神”精神。这证明喜爱悲剧形式的瓦格纳同样重视古希腊人对“美与智慧”以及现实中健康愉悦生活的追求,正像他在著作中所表达的,其全部工作的目标就是效仿古希腊文明的精髓:创造“又壮健又优美的人类”④,这也正是《名歌手》表现的主题。
对于基督教观念的认识,瓦格纳表现得十分矛盾复杂,虽然他在《艺术与革命》等著作中对其进行批判,甚至说“伪善根本就是全部基督教从过去的各个世纪直到我们今天的最突出的特征,也是它的本来面目”⑤,但是大量歌剧作品又表现出基督教理念的强势渗透以及他本人对基督教信仰一种天然的敬畏态度,甚至将基督教确认为人性挣扎与灵魂救赎的最终希望。相比之下《名歌手》中的基督教因素表现出一种平和状态,它是作为历史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出现的:歌剧情节安排在“圣约翰节”⑥的前日与当天,第一幕开场就是人们在教堂中歌唱赞美施洗约翰的场景,这段伴有管风琴的合唱优美而宁静,几乎再现了十六世纪教堂中的虔诚气氛。“圣约翰节”这天还是主人公萨克斯的“命名日”⑦,在许多信仰虔诚的地区,“命名日”是远比生日重要的私人庆祝日,它显现出基督教在人们生活中喜悦而温暖的一面。另外,作品中部分角色的名字是来自基督教传统,女主人公“埃娃”就是德语中的“夏娃”——《圣经》中上帝创造的第一位人类女性,而萨克斯的徒弟“大卫”的名字则来自《圣经》中记载的一位具有超常音乐天赋的领导者,舒曼将自己虚构的艺术家团体称为“大卫同盟”,就是以这位《圣经》人物作为自己向代表庸俗保守势力的“非利士人”进攻的旗帜。而《名歌手》具有双重含义的“大卫”也不时闪现,第一幕中埃娃将瓦尔特喻为“图画里的大卫”,第三幕中瓦尔特得到的代表“师傅”荣誉的金链上也镌刻着大卫的形象。
2.德国历史文化的承继
中世纪民间世俗音乐是德国音乐领域的最早繁荣阶段,其代表是以各个市民行会工匠为主体的“工匠歌手”⑧,一个从“学徒”开始的手艺人要经过层层测试才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师傅”——这不但要求本行业的技艺高超,在歌唱方面也要达到相当的水准。“工匠歌手”的中心就是纽伦堡,《名歌手》主人公的原型也来自当年最为著名的“工匠”音乐家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1494—1576),据说正是他的创作给已经陷于呆板的“工匠歌手”创作带来了活力和新风格。历史上的萨克斯虽然生活在与马丁·路德同一时期的文艺复兴“变革时代”,“人文主义”情怀已经在德国各地开始蔓延,但是由于纽伦堡在宗教改革大潮当中受到的冲击较小,文化发展也相对平稳,歌剧中“圣约翰节”与“命名日”的背景证明这个城市当时还遵从天主教而非“新教”传统,明显带有更多的中世纪遗韵。关于《名歌手》的喜剧色彩,许多人都认为与德国文化的深沉气质不符,不过尼采在这一点上自有独特见地,他认为《名歌手》表现出了一种在马丁·路德、贝多芬与瓦格纳心灵中共同存在的“德国乐天精神”,是一种“由单纯的心地、深情的爱、认真的思考和开玩笑的雅兴混合而成的金光灿灿的佳酿”⑨,从这个意义上说,《名歌手》正是德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个性侧面的表达。
从情节构架上看,《名歌手》与韦伯的《魔弹射手》十分类似,它们都描写了主人公为获得爱情与荣誉而参加竞赛,情节也都设置在比赛前日到比赛当天,并使用三幕结构先后表现主人公在比赛前受挫——反面角色尽情发挥主人公在众人面前获得胜利的整体安排。两部歌剧还都表现出对民众地位的重视,无论是射击还是歌唱比赛都像是民众的盛大聚会,而《名歌手》第三幕中各行会成员的合唱与《魔弹射手》第三幕中著名的“猎人合唱”一样充满了对生活与工作的热爱,似乎是瓦格纳在向韦伯这位德国民族歌剧的先行者深深致敬。
3.个人生活的点滴闪现
《名歌手》中的部分细节与瓦格纳个人生活还具有一定关联,歌剧第二幕中博格纳所说的“如果有人要做些不寻常的事情,总会有人要说些话来反对”⑩,以及萨克斯所感叹的“生来能当大师的人,在大师伙里的处境最最坏”,都是瓦格纳对个人境遇的有感而发。另外,歌剧中含蓄地表现了萨克斯与埃娃之间的纯洁情感,这种“是爱而不是欲望”的情感在瓦格纳的作品中相当罕见,而它的描写被认为与瓦格纳生命中的一位重要女性、1849年革命之后流亡瑞士期间结识的玛蒂尔德·维森东克具有一定关联。此外,创作《名歌手》时的瓦格纳已经开始受到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而摆脱了困窘处境,在这部作为圣诞礼物赠送给国王的歌剧中,博格纳唱到“在德国宽广的国土上,慷慨解囊扶植艺术唯有我们多”,让人不免联想到其中暗含的对国王的一种特殊歌颂。
二、“寓言”式表达与改革理念的呈现
1.角色与场景的“寓言”
在《名歌手》完成的年代,瓦格纳虽然已经在欧洲成为艺术界的权威,但是他具有独特观念的创作对许多人来说还是很难理解,这也使他一直遭受着各方面的质疑甚至敌意的对待。《名歌手》中的萨克斯是深谙传统、受人尊敬的“师傅”,而瓦尔特是对传统规则并不了解的“新锐创造者”,正是二人的合作最终推动了“工匠歌手”音乐的革新与进步。对瓦格纳来说,这两个角色如同舒曼为自己的多重性格所设计的两个代表人物“弗洛列斯坦”与“约塞比乌斯”一样可分可合,他们不但分别代表了瓦格纳性格中沉稳与激进的不同侧面,其形象融合也象征了瓦格纳在当时艺术领域“大师与革新者”的双重身份。其中萨克斯更是一位几乎具有完美形象的人物,这个集智慧、练达、勇气、温情、幽默于一身的角色,在歌剧中阐发了大量的艺术观念,几乎成为瓦格纳的思想代言人。《名歌手》中唯一的所谓“反面角色”是贝克迈赛,这个已经拥有“师傅”身份的人参加歌唱比赛的目的并非“艺术”或者“爱情”,而是希望借此成为博格纳的女婿而继承他的可观家财,在作品中他被设计成了带有相当滑稽色彩的人物。众所周知这个角色是瓦格纳用来象征和调侃奥地利美学家、音乐评论家汉斯力克(Hanslick,1825—1904)的,有资料记录瓦格纳甚至在起初的脚本设计中将这个人物称为“汉斯·力克”或“维特·汉斯力克”。对于这位论敌撰文批判自己“把音乐看成是一种用歌声和弦乐来唤起的鸦片醉梦”{11},以及将自己的歌剧视为“音乐上的一个不堪设想的怪物”{12},瓦格纳使用了一种独特的回击方式,歌剧中将贝克迈赛定位为一个“师傅”级别的人物,就是意味着瓦格纳首先承认他对传统规则的“权威性”,之后再用喜剧性的手段更直观地向观众证明:拒绝接受新的理念是一种荒谬可笑的行为。据说汉斯力克对此感到深恶痛绝,从不惧怕论战的他不能忍受的应该是这种带有居高临下意味的嘲弄。如果抛开艺术观念的孰是孰非的话,这个细节倒是十九世纪艺术领域中一个颇为有趣的花絮。
在第一幕行会“师傅”的聚会中,萨克斯提出应该让“人民”在艺术评判中起到重要作用:“明智的做法应该是,人们每年对规则要进行一次检验,看看它们是否因屈服于习惯势力,落入俗套丧失了新鲜和生命力。看看它是否跟上了自然的脚步未陈旧。而这只能让那些百姓,不懂规则表的人来告诉你。”实际上,瓦格纳早就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过这种思想:“人民作为艺术作品制约的力量”{13},是真正具有创造力的群体。《名歌手》在许多场景中都表现了作曲家关于创作与规则关系的理念,第一幕中萨克斯对瓦尔特歌唱的评价是新颖但不混乱:“虽然离开了我们的轨道,但他跨着坚定的脚步不离目标”。第二幕中贝克迈赛为讨好埃娃而演唱了一首小夜曲,其旋律是从由序曲中出现的“爱的情景的动机”发展变化而来,但是自以为“懂得所有规则”的贝克迈赛却在规则的束缚下将原本流畅动人的旋律演绎得十分蹩脚。第三幕“比赛”一场中,又是这个贝克迈赛只注意押韵而使自己语意混乱——这些都象征了某些艺术家只注重“规则”而放弃了艺术表现中更重要的东西:内容的丰富和谐与情感的真挚表达。对于创作与传统的关联,《名歌手》首先抱有开放的态度,这在第一幕中大师们询问瓦尔特的师承时已经表现出来。瓦尔特认为自己的老师是通过书本神交于心的中古游吟诗人瓦尔特和“伟大的自然”,这也是未受过系统音乐学院教育的瓦格纳认为自己秉承古希腊精神的一种象征。就另一方面瓦格纳又强调了传统的重要性,当作品末尾瓦尔特获胜后却不愿接受“师傅”称号时,萨克斯劝告他的一段话十分令人动容:“不要轻视师傅们,您应该尊敬他们的艺术!他们受到赞扬的地方,也是您从他们那里丰富受益的地方!……德国的艺术有今天,大师的功绩不可磨灭。”作品中的一些段落也相应做出证明:从圣咏式合唱到乐队中的对位以及持续低音手法,从进行曲风格的音乐到民间风格的圆舞曲,从琉特琴伴奏小夜曲到中世纪风格的歌谣等等。尤其是大卫演唱的“圣约翰在约旦河边”的中世纪风格歌谣,朴实又有韵味,如同德彪西在他的《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中为梅丽桑德创作的那段中世纪游吟诗人风格的歌调一样,都表现出这些“前卫”人物呼应传统的一个侧面。正如瓦格纳著作中曾引用过的古希腊先贤的话“不尊重他的过去的人民是没有未来的”{14},《名歌手》表达的也是这样一种思想。
2.个人歌剧改革理念的呈现
瓦格纳曾经说过:“存在于歌剧这个艺术品种中的错误就是,表现的手段(音乐)被当成了目的,而表现的目的(戏剧)却被当成了手段”{15},音乐家应该用音乐去实现“最高的诗的意图”{16}。尽管格鲁克在歌剧领域的第一次改革就是强调音乐应该为戏剧情节的完整表现而服务,不过在瓦格纳看来,他的改革只是“在音乐上作曲家对歌唱家的专横的反抗”{17},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歌手的炫技,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歌剧不自然的结构方式。而瓦格纳的改革在具体措施上提出了更加复杂的要求,歌剧体裁也前所未有地达到了“完整戏剧表现”的状态。
许多人都认为《名歌手》是一部剧情比音乐更多体现“改革”精神的作品,实际上,《名歌手》音乐的总体设计和表现方式与大部分改革特征是完全吻合的,这首先表现在《名歌手》采用的“无终旋律”方式上,所谓“无终旋律”是瓦格纳为了更完整地表现戏剧情节、避免作品成为“戏剧性的套曲”{18}而主张打破传统分曲歌剧形式中以咏叹调与宣叙调为基础的结构安排而将整幕音乐连续起来的一种表现方式,《名歌手》中“无终旋律”手法的应用是十分明确的,其中也有几段优美唱段,但与传统“咏叹调”相比,更像柏辽兹的标题交响曲《哈罗尔德在意大利》中的中提琴“固定乐思”与传统协奏曲中的“华彩段”之间的区别,不再是炫技意义的音乐,而是充满细腻情感的优美朴素歌唱。其次,“突出器乐”是瓦格纳所有歌剧作品的特征,《名歌手》也不例外,除第一幕与第三幕都设置了具有相当分量的前奏曲外,唱段部分声乐与乐队配合和情绪表达也能让人们感受到伊索尔德“爱与死”中显示的力量。不过《名歌手》的整体器乐安排比瓦格纳的其它作品显得更有节制,音乐没有超越剧情之上的倾向,也显得更加接近瓦格纳“音乐为戏剧服务”的理想。此外,从序曲开始,《名歌手》每个场景都有丰富的“主导动机”出现,瓦格纳也一如既往地利用这些动机来编织和表达剧情的发展。瓦格纳还在《名歌手》中进行了动机的“自我引用”,作品第二幕与第三幕中出现了《特里斯坦》中“伊索尔德”与“马克王”动机的变形形式,这从一个侧面渗透出瓦格纳对自己另一部力作的极大珍视。《名歌手》与瓦格纳改革措施最不接近之处就体现在“调性突破”方面,一部使用喜剧性手法描写和平时代人们艺术追求的作品,当然不像以往创作那样需要半音化的复杂行进、尖锐的音响以及调性频繁转换和延迟解决所带来的紧张度与不稳定感,这也是音乐为戏剧服务的必然结果。不过《名歌手》毕竟已经是瓦格纳创作后期的作品,音乐不可能退回完全“传统”的风格状态中,其和声技法“包含着丰富的半音进行的中间声部,也包含着丰富的和引人入胜的新颖的转折”{19},从听觉直觉上就能够感受到其中非传统的和声风格与色彩。
时至今日,距《名歌手》首演已经整整过去一百四十个年头,全世界有更多的歌剧听众欣赏到了这部温暖明亮的作品。这部作品之所以令人感动,也不仅仅由于它是一个多种文化因素的综合成果或者改革理念的优秀代表,而且还归功于其中所显现出的充满“健与美”的情感表达,这其中容纳了恋人之间的温情、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也表现出人们对过去艺术的尊敬以及对崭新艺术的欢迎。就像瓦尔特在歌剧第一幕中唱到的“爱的旗帜是神圣的”以及瓦格纳在著作中所说的“最高的人类的需要则是爱”{20},《名歌手》正是这样一部充满欢欣与希望的“爱的寓言”。
①瓦格纳《艺术与革命》,选自《瓦格纳论音乐》,廖辅叔译,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P4。
②瓦格纳《歌剧与戏剧》,选自《瓦格纳论音乐》,廖辅叔译,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P318。
③尼采《瓦格纳在拜洛伊特》,选自《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P139。
④同①,P26。
⑤同①,P11。
⑥“圣约翰”也称“施洗约翰”,是基督教创建年代的重要人物。
⑦天主教以及正教的信徒纪念与自己同名的圣徒的节日。
⑧实际上将“Meistersinger”译为“名歌手”并不确切,准确译法应为“工匠歌手”或者是“师傅歌手”,而“名歌手”的翻译结果不但倾向音译,也包含着一种赞美与崇敬的意味。
⑨尼采《瓦格纳在拜洛伊特》,选自《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P149。
{10}本文中所有的剧词都引自《瓦格纳戏剧全集》,高中甫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
{11}汉斯力克《论音乐的美》,杨业治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P14。
{12}同{11},P46。
{13}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品》,选自《瓦格纳论音乐》,廖辅叔译,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P44。
{14}瓦格纳《未来的艺术家行当》,选自《瓦格纳论音乐》,廖辅叔译,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P178。
{15}瓦格纳《歌剧与戏剧》,选自《瓦格纳论音乐》,廖辅叔译,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P203。
{16}同②,P469。
{17}同②,P209。
{18}同②,P204。
{19}格奥尔格·克内普勒《十九世纪音乐史》,王昭仁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P600。
{20}同{13},P61。
殷 遐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