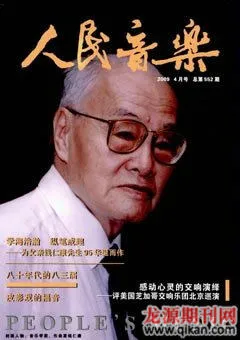八十年代的八三届
十年动乱以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撤销“四人帮”为其样板团培养接班人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恢复被“砸烂”的艺术院校建制。停课闹革命、下放劳动锻炼的师生返校复课。1977年恢复高考。中央音乐学院在全国招生,原拟招收135名新生,却有一万七千多人报考。经过初试,发现招收人数与报考人数差距太大。许多有音乐才能的优秀青年不能入学。同年12月,七位教师联名给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写信,反映此种情况,请求扩大招生名额,获得批准。此次共招收322名新生。以往作曲系每次招收新生常在10名左右,这次招收了30多名新生,是前所未有的。他们1978年入学,1983年毕业,形成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庞大的八三届毕业生群体。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把全党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结束了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①对教育的干扰与制约。学校教学秩序稳定。经过十年动乱折磨的教师们恢复教学工作以后,以极高的敬业精神按照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进行教学。从千万人中遴选出来的渴望学习的作曲系新生,入学以后表现出极高的学习热情与主动性。从完成作业中受益,丰富了音乐知识,培养了音乐创作的基本技能,却又不为课业所囿,尽量扩大视野。多方自学祖国丰富悠久的文化遗产。从诗经、楚辞、诗、词、文、赋学习中弥补文化修养的欠缺,也从中积蓄音乐创作的素材。原课程中缺少对我国民族乐器的研究,他们便多方面对民族乐器的性能作研究,对古代民族器乐曲遗产亦有所涉猎。
长期以来,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音乐被奉为音乐院校学习的经典。而二十世纪的西方现代音乐却被作为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腐朽形式主义音乐遭到批判,是严禁涉猎的禁区。闯入这个禁区将受到严厉批判,甚至被划为“右派”。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较为宽松的文艺政策,解除了束缚文艺发展的一些条条框框,要求全面继承并发展中外古今一切优秀遗产。北京、上海、武汉等音乐院校的一些教师先后着手研究西方现代音乐,其成果在各种刊物上登载。中央音乐学院创办了《外国音乐参考资料》(后改为《世界音乐》)双月刊②,专门登载有关西方现代音乐流派、作曲家、作品研究、现代音乐写作技法译文。有关现代音乐的一些专著也逐渐问世。同学们自学研究西方现代音乐有了一片园地,这弥补了课程中缺少现代音乐的不足。研究现代音乐一时成为一种风气。
在此种氛围中,英国剑桥大学音乐教授、曼彻斯特乐派的现代音乐作曲家戈尔(Alexander Goehn)来华讲学。自1980年5月20日至6月11日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从一位现代音乐作曲家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论述西方现代音乐的发展。在序言中,他先就二十世纪之初西方音乐的形成,其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起伏变化,及有代表性的作曲家间相互关系等作概括的叙述,为现代音乐的发展勾勒一个总的轮廓。继而依次对德彪西(Claude Debussy)、勋伯格(Schoenberg Arnold)、韦伯恩(Anton Webern)、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梅西安(Oliver Messiaen)等作曲家的生平及创作进行系统论述。结合作品分析,阐明其创作思想,独特的音乐风格,以及写作技法的创新。涉及印象派的音乐风格,以及写作技法的创新。涉及印象派的和声、音阶调式、乐曲结构特点,十二音序列技法,独特的节奏处理,有限移位调式的运用等问题。而对当时健在的布列兹(Pierre Boulez)、斯托克豪森(Julius Stockhausen)、卡特(Elliott Carter)、利盖蒂(Andras Ligeti)等人的作品因难分析,只作简要介绍,附带涉及波兰的潘德雷茨基(Krzysztof Penderecki)和美国的凯奇(John Cage)等现代作曲家。与此同时还为一些同学上了作曲个别课。经过这次学习,同学们对西方现代音乐有了较系统的了解。
这些同学都是十几、二十岁的人。抗日战争时期,强寇入侵,国家危亡、民族危亡,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同声高唱救亡歌曲,轰轰烈烈的抗敌歌咏运动时代离他们已经遥远。十七年的文艺发展已被“四人帮”作为文艺黑线下的产物批判。他们目睹的是十年动乱中文艺专制政策扼杀文艺创作,一切文艺活动都被强制归附其反动的政治需求。在这一段学习中看到了当前世界音乐发展的大致轮廓,视野开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政策比较宽松,鼓励文艺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倡创新。他们每个人都在考虑作为中国作曲家应该走什么样的创作道路。在校学习期间已显露出创作的主动性与旺盛的创作活力。
1980年学校为参加全国交响乐创作评奖征集作品。他们入学不久,尚未进入交响音乐创作的学习阶段,参赛的都是课外自己创作的作品。数量不多,水平也不算高。指挥家黄飞立教授发现谭盾的《离骚》虽然结构凌乱,但乐思较丰富,有加工修改的基础,在老师指导下作了较大的修改。1981年参赛,在全国第一届交响音乐创作评奖中获鼓励奖。1982年他又把弦乐四重奏《风雅颂》寄往德国,参加韦伯室内乐创作比赛,获二等奖。这是中国作曲家最早在国际音乐创作比赛中获奖的作品,受到社会关注。
学校经常组织音乐创作比赛。其中的优秀作品在《音乐创作》季刊上发表。1982年江定仙教授在其中见到瞿小松发表的小提琴曲《恋》③,盛赞作者的创作才能。同年鲍晋书、汪镇平、瞿小松、叶小纲、郭文景、张小夫、陈远林、艾立群、陈怡、张丽达、刘索拉等在四年级学生作品音乐会中演出了歌曲、小提琴、双簧管、单簧管、钢琴、竖琴独奏曲及弦乐四重奏曲。四年级已是大学学习的最后阶段,从中表现出他们在校学习期间的创作面貌。这些作品共同显露一种求新的倾向,受到关注。
1983年他们大学毕业,形成一个活力充沛的青年作曲家群体,崛起于中国乐坛,掀起一阵前所未有的波澜。
1984年陈远林、陈怡、朱世瑞、谭盾、周龙等人组织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实验组,与中国唱片社联合举办电子音乐会,要在电子音乐领域中开拓出中国的领地。音乐会演出了《昊》、《吹打》、《中国民歌二首》、《补天》、《游园惊梦》、《三月》、《森吉德马》、《宇宙之光》等作品。同年瞿小松在文化部与中国音乐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主办的中国交响音乐新作品专场中演出了四乐章的管弦乐曲《山与土风》。其为动画片《悍牛与牧童》的配乐引起广泛的注意。
1985年4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为振兴民族音乐,繁荣新创作,探索新风格新理论,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民乐系联合举办的“探索与追求”活动中,演出了谭盾中国器乐作品专场音乐会。5月又演出了青年作曲家民族器乐新作品音乐会。两场音乐会共演出谭盾、周龙、瞿小松、俞逊发、朱世瑞、陈怡等青年作曲家创作的民族乐器独奏、重奏、小合奏、声乐与民族乐器曲、组合打击乐独奏、大合奏、打击乐与民族管弦协奏曲等19首新型民族器乐曲,这是民族器乐曲创作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国民族器乐曲长久以来多出自民族乐器演奏家之手,作曲家极少问津。青年作曲家研究民族乐器性能之后,从作曲专业角度出发创作的民族器乐曲有了新的素质。品种繁多,结构新颖,使民族器乐曲创作进入一个新时期。在这两场音乐会中“八三届”毕业的青年作曲家开始集体展示出他们锐意求新的创作倾向,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同年11月中央音乐学院主办了谭盾研究生毕业作品交响音乐会,启开了1985至1988年举办毕业交响作品音乐会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中国音协创作委员会与中央音乐学院先后举办了叶小纲、陈怡、瞿小松、郭文景的毕业交响音乐会。上海音乐学院及四川音乐学院并与创作委员会联合,共同举办了许舒亚、何训田的毕业作品交响音乐会。陈其钢、张小夫、张丽达的毕业音乐会要晚一些。马剑平的毕业音乐会已延迟到1991年才举办。陈远林的毕业音乐会是由电子合成器与人声演出的诗剧。每场音乐会演出四五部作品,共演出交响曲、协奏曲、序曲、弦乐合奏曲、室内管弦乐曲以及一些非常规组合的作品三十余部,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自从上个世纪前期西方专业音乐创作输入我国到八十年代,建立在大小调功能体系上的西方作曲技法,一直为我国专业音乐创作所遵循。作品的体裁、品种大致不出这个体系所涉及的范围,创作风格比较单一。马思聪、谭小麟等老一辈作曲家引进一些西方现代音乐创作的观念及写作技法,未能改变上述状态。这些青年作曲家因受西方音乐早已越过古典的创作体系另辟蹊径的启示,以活力充沛的群体力量跳出功能圈,自寻创作道路。他们相互启发,相互促进,又张扬个性,回避雷同。借鉴西方,又不直接引用西方的现代技法(郭文景、许舒亚用十二音技法写小提琴协奏曲是较少见的范例)。在探索中未忘记向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找依据,为我国专业音乐创作开辟出一片新领域。
这些音乐会中已很难见到建立在大小调功能体系上的曲调与和声。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由自然音体系转向半音体系写作。何训田更创立了自己的任意律与对位法。传统的曲式已被新的乐思突破,传统的规范已不再被遵循。交响曲多由一、二乐章组成,没有典范的四乐章交响套曲,三乐章的协奏已属仅见。传统的管弦乐队中常因附加新的乐器或乐器组而有新的色彩。人声常在交响音乐中占主导地位。打击乐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常用边缘音域的高低音求得特殊效果。民族乐器已逐渐消除与西洋乐器音律、音色、音量、演奏方式的差异而结合运用。传统的管弦乐队之外,更出现一些新的乐器组合。电子音乐更是我国前所未有的品种。音乐表现的范围从现实引向遥远的洪荒时代的梦幻。这样的音乐不同于西方现代音乐,也不同于我国既有的音乐作品,是一种新的中国音乐作品。
新不等于好。新事物常与有缺陷、不完美相伴。若再加上求奇,问题就更复杂了。但求新亦有突破束缚、促发展、求扩展的一面。这些青年作曲家创作发轫之始,在朝气蓬勃的激情中创作的作品,多数都在老师指导下反复修改过。不宜用好与不好作简单概括。其得失可由群众评议,亦须经时间筛选。时至今日,《乐队及三种固定音色的间奏》(人声、低音单簧管、低音大管),后改名《道极力》、第二交响乐《地平线》、为混合室内乐队而作的《Mong Dong》(原美术片《悍牛与牧童》配乐)、室内管弦乐《多耶》、交响曲《蜀道难》等作品都还是作曲家重点保留的曲目,有些还多次在国内外演出。
创作的繁荣引发了演出的繁荣。新作品系列问世培养了一代新型民族乐器演奏家。他们是:李萌、姜小青(古筝),王健、陈涛(箫),赵家珍(古琴),吴蛮、刘桂莲(琵琶),杨守成(笙),何建国、李聪农、王建华、孟小亮(打击乐),刘月宁、黄河(扬琴),姜建华(二胡),谈龙健(三弦),张云龙(唢呐),包健(管),张维良(尺八)等(据相关音乐会节目单记载),还有民族管弦乐队指挥王甫建。探索性的民乐新作品须看谱演奏,还有很多新的演奏技法。习惯背谱演奏的民族器乐演奏家多不适应。有了这些新人的参与,作曲家的新作品才能演出。他们不仅参加演奏民乐曲,还经常担任管弦乐中民族乐器声部的演出。管弦乐新作品演出的指挥家除韩中杰、郑小瑛、陈燮阳等中老年指挥家之外,还有青年指挥家邵恩、陈佐湟、水兰、胡咏言等。他们有机会连续处理那么多新作品首演,在其中积累经验迅速成长,是青年指挥家极难得的机遇。一些青年声乐家、钢琴家、大提琴家、小提琴家等也为这些新作品的问世做出了贡献,并从中受益。这些青年音乐家绝大多数都是“八三届”的毕业生。
新型作品连续问世,在我国音乐界掀起轩然大波,推动了音乐评论的空前繁荣④。一时论家蜂起,论争纷纭。对新作品支持与反对的文章界线分明。争论涉及不同文艺观点的碰撞及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较宽松文艺政策不同态度的对立。争论的语言犀利,直言不讳。有批评亦有反批评,更有对反批评的批评。问题在激烈的争论中逐渐深入。一些青年理论家(其中包括“八三届”毕业生)在争论中成长。所幸并未发生因文得咎的事例。争论中有些意气用事,应属正常辩论范围。吕骥在《当代音乐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说:“争论可能非常激烈,观点对立可能非常尖锐。但不能因此损害彼此之间的感情。”“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彼此之间的争论,最后的目的是求得真理。”⑤这种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宽松的文艺政策指引下才能出现。
争论的另一焦点是新时期出现流行歌曲的问题。我国自古就有广泛流传的歌曲《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高雅的《阳春·白雪》和“引商刻羽”式的,在极少数人中传播的,有音阶调式变化的探索性歌曲,形成完整的音乐金字塔。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流行歌曲创作,差不多和西方专业音乐创作输入我国同时产生。抗日战争爆发,流行歌曲受到批评,至1949年后在大陆才销声匿迹,一直延续到80年代。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有多方面的艺术需求,流行歌曲发展起来是很自然的事。其中出现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应当批判,其格调应不断提高。但作为一个音乐品种自应有自由发展,探索性的音乐创作受到重视,而阳春白雪档次的作品极少问世。音乐金字塔处于中空状态。在西方,探索性的音乐作品只在极少数人中传播。因为有几百年留传下来的大量音乐经典作品,多数人的音乐生活仍可丰富多彩,我国没有这份遗产。要丰富我们的音乐生活,只能仰仗外国音乐作品,时常听到乐队指挥家呼吁急需可供经常演出的有持久艺术魅力的中国作品,这样的作品实在太少。
西方现代音乐自20世纪初兴起,各种新思想、新流派、新技法相继问世。几十年间都已先后完成了发展音乐的历史使命。到80年代,其创新的活力已显衰竭。戈尔教授已经举不出更多值得他全面深入论述的大师级代表人物。正当此时,我国现代音乐兴起。1988年前后,“八三届”毕业的青年作曲家纷纷出国继续深造或从事各种音乐活动。它们的作品在欧洲的音乐节、音乐会中演出,或在电视台播放,受到很高的赞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宽松的文艺政策指引下,青年作曲家在成长。中老年作曲家迈着自己坚实的步伐为民族音乐建设贡献毕生精力。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音乐各流派的兴衰中吸取教益。处理好音乐创作与听众的关系,写作技法与音乐表现的关系,使音乐艺术沿着宽广道路持久发展。今日的中国音乐文化已得到前所未有的大普及。在此基础上,可以期望我国的音乐为世界乐坛做出应有的贡献。
①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②中央音乐学院创作研究室主编的《外国音乐参考资料》双月刊1978年5月创刊,1985年10月改名《世界音乐》,1986年8月停刊。
③《音乐创作》1982年第1期。
④参看李西安主编中国现代音乐争鸣文选《一石激起千层浪》上、下集。
⑤《人民音乐》1987年第12期。
⑥汉·刘向《新序》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王震亚 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中国音协第四届创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音乐创作》原主编
(责任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