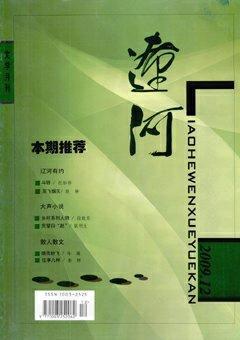冬天里的母亲
崔新月
小村隆冬的早晨,从梦乡里那三两片飘飞的雪花开始。常常是刚刚从睡梦中醒来,还没等睁开眼睛,早已感觉到鼻子冻得冰凉,吸一下,呼吸已经不再顺畅,真冷。然后是母亲瑟瑟索索下炕的声音。睁眼看看,窗玻璃上凝结了厚厚一层霜花。我知道,外面早已经是滴水成冰。我便蜷缩在被窝里,等母亲把炕烧热再钻出被窝穿衣洗脸。
这当然是稍微长大一些的情景。在这之前,关于冬天清晨的记忆是这样的,我穿上一件小棉袄,跪在窗前,用手在冰花上写字或者画画,兼用嘴哈气,让窗玻璃透出一点光亮,好看清楚窗外阴冷的天色。梦里的雪花并没有真的飘落,但我常常看见母亲推开门外的雪,从院子里的雪堆底下掏出一捆玉米秸或者几根干柴,急匆匆地回家,留下一个个歪歪扭扭的脚印。我看见她的短发随风飘起,像极了泥墙上在寒风中抖动的枯草。然后听见灶间风箱拉动的声音,听见母亲被烟雾呛得大声咳嗽的声音,偶尔听见柴火燃烧的噼噼啪啪的声音。透过朦胧的窗玻璃,我可以看到远处树枝在风中使劲摇摆着,可以看到前方几户人家屋顶上刚一露头就被风吹得无影无踪的炊烟。我的嘴里哈出的那点热气并没有让窗玻璃明亮起来,反而更加朦胧,直到什么也看不清,我想再重新弄出一点光亮,但是双手早已经冻得冰凉,便再钻进被窝。原本凉透的炕竟然有些热气,真好。只要有母亲在,我的冬天就不再寒冷。
过了一些时候,母亲带着一身凉气走进来,喊我们穿衣洗脸吃饭。虽然那饭菜没有任何值得期待的,但毕竟能够填饱肚子,而且能暖暖身子啊。吃完早饭,把碗筷收拾下去,冬闲时节没有什么事情,母亲就爬上炕,拉一床褥子盖在腿上。我看见她的身体仍然在发抖。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母亲或许是冻透了,我无法想象,她是怎么用自己温润的双手去握住冻得冰凉的家什的,无法想象,她在那一瞬间脸色是不是冻得铁青,她的牙齿是不是一直在打战。我想,那个时候的母亲一定是冻透了,以至于多年之后,每到冬天,她总是那样瑟瑟索索地走路或者做事,她那单薄的身躯必定经受不住寒风的侵袭,早已经变成寒风中的一片枯叶了。那个时候还算年轻的母亲,却已经永远留在了冬天。
留在冬天的母亲似乎很怕冷。或许是冰冻从她的指尖偷偷溜进她的身体,然后把她的原本沸腾的热血冻成了冰河。即使是坐在滚烫的火炕上,她的血液里也流淌着冰碴,那些无法融化的冰碴一定会刺痛母亲的筋骨。所以,我还记得,即使是春天来临,总还是有春寒料峭的时候,见我们想要早早脱了冬衣,母亲总是厉声劝阻,告诉我们春捂秋冻,千万别着凉。可是到了秋天,母亲却也是早早地穿上厚厚的衣服,在秋雨连绵的日子里总还是腰酸腿疼得整夜睡不着。
很多时候,我没有注意到母亲的冷,很多时候,我只是注意到了我自己匆匆行走的脚步,从冬天走到春秋,从童年走向成年,从儿子走成父亲。我就这样走着,看我的儿子咿呀学语,继而一天天茁壮起来。可是看看母亲,她还在冬天里冻着。我用再厚重的羽绒服包住她,也已经化不开她身体里的冰层。即便是如今,我带着妻儿回乡,冬夜在母亲炕头享受着大火炕的舒适和惬意,清晨醒来,母亲也总是不知何时就早早下地,依旧用那瑟瑟索索的声音烧炕,煮饭,然后喊儿孙起来穿衣洗脸吃饭。我以一个孩子的视角看着走在冬天里的母亲,看她的皱纹一道道延伸到岁月深处,一直延伸到我的记忆里。
只要有母亲在,我的冬天就不再寒冷。
可是母亲呢,她是不是把自己燃成了一捆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