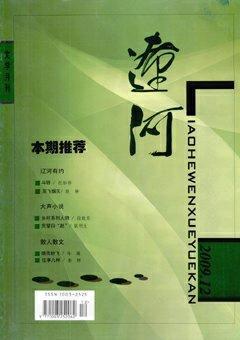坛子
秦 峰
我去一个叫打铁巷的地方。
打铁巷里以前都是打铁的,现在只剩一家了。我来这不是要打什么铁器。我的确收藏了一把藏刀,一位挚友赠予我的,还没开刃。我希望有一天能佩戴它,身着唐装,去纽约的街头显摆。
打铁巷里藏着家酒坊,一到巷口就觉得香气袭人。老板见我拎着塑料壶过来,脸上立刻堆满笑意,他递来一支迎客松香烟,并给我点上。我告诉他前段时间高兴,这段时间心烦,所以酒喝得快。
他打酒的工夫,从里间走出一位十三四岁的女孩,我一看就知道是他女儿。她打量我一眼,也没喊叔叔,只问是用这塑料壶装酒吗。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我使这个酒壶好几年了。老板笑眯眯地告诉我,女儿都被她妈惯坏啦。
她觉得爸爸对顾客不负责,天气热用塑料壶装酒,会产生化学反应,味道也会变差的,没有哪家酒厂用塑料瓶装酒卖。女孩的解释令我惭愧,我枉有二十几年酒龄,赶紧向她请教储酒的独门诀窍。她指指店里的大酒坛子,毫不客气地说我想玄乎了。她介绍道,玻璃瓶也行,最好是坛子,呶!像这样的……
我认真凝视着几个大缸般的坛子。老板似乎看透我的心思,他说,这些坛子都是从老家托运来的,又都是大的,要不然就送给我一只了。
我拎着酒回家,走在路上就有了心事。酒需要坛子装的问题,还真没考虑过。现在,它由一个陌生女孩提出来,我就很在乎了。我那么爱酒,决不能再委屈我的酒了。
几天后我公休。揣着这月薪水,我决定去买个坛子。我这样想,如果我爱的酒是皇帝,那么我相中的某个坛子,就该是深宫大殿。皇帝不住进宫殿,不就成没落皇帝了,有损龙颜和帝威。
来到一家杂货铺,我说想买一只坛子。老板指指里面,讨好地问我是腌咸菜吧。我不悦地告诉他,买坛子不是腌咸菜,是要装酒。老板无奈地耸耸肩。
它们杂乱地堆在一起,模样丑陋,做工粗糙。我暗想,这种坛子恐怕也只配腌腌咸菜给穷人过日子。显然,我不允许我的酒住进这样的地方。
我打算去一家大超市。路过古玩街,街上的人似鱼游着。他们游在空气中。我忽然看见一个蹲在水底的“鱼”。一条美人鱼。四周还围了些“咸鱼”。
古玩街的氛围很容易使人恍惚。这是一个装腔作势的时代,没有英雄只有流氓。这是我一位铁友的名言。如今,这家伙正混在深圳。
那年,我不想去任何地方,我觉得家乡最好,甘愿沐浴在单位温暖的阳光里。对漂泊无定的生活,我举棋不定。至少,在这个城市,我还有一个结实的小窝。朋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骂我肉头,让我就待在这等死吧。我们打起来,打得脸上都挂了彩。后来打累了,就握手言和。坐下来,继续喝酒,从中午喝到深夜,直到把我的塑料壶喝空。黎明时,他背着一只破包裹,失魂落魄地上了出租车,像一条丧家的犬,直奔火车站。我没空送他,我正跟一个女人在床上纠缠。
一个古玩贩子居高临下,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就像在絮叨什么冤屈。美人鱼显然不配合,十分麻木。她一身休闲打扮,紧抱一个坛子。那坛子白底黑彩,依稀画有人、牛、犬。犬跟在人身后。人举着个鞭子。牛在犁地。远处,隐现着青山碧水。是典型的中国山水画风格。坛口给人感觉深不可测,似乎藏匿着一个秘密。
我觉得她在等我。我很想买个坛子,她却在这卖坛子。只是,她如何也不像古玩营生的人。她忽地站起来,仍然不说卖,也不说不卖。文物贩子急得眼睛在冒火。
我拨开人墙冲进去,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说,妹妹!咱不卖了,你缺钱,哥给你。
像一个从天而降的外星人,我的出现使她异常吃惊。我把眼睛对着文物贩子和人群横扫一遍。人群无聊地散开。文物贩子边走边打手机,还回头不断地张望。
她镇定下来,冷冷地问我是谁,问谁是我妹。我告诉她,就凭她一个外地人,那个文物贩子非把她吃得骨头渣都不剩,做我妹还吃亏了。我叫她赶快走,不然会有麻烦的。她被我震了,眼神里却不服气,她说外地人怎么了,她不怕。我夸她有种,问她这坛子要多少钱,我买了。
她坚定地说,不卖!并让我别演戏了,她认为我们是一伙的。
我转身就走,并呵斥她不要跟着我。走了一段距离,我发觉她竟尾随过来。快要走出街口,我突然回头,她躲闪不及,与我目光碰到一起,她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她问我是不是生气了。我说都不认识你,生的什么气呢。她十分好奇,我演的那一出,到底是什么把戏。
我迅速把她带出古玩街,走到一个隐秘的地方,才坦然告诉她是怕她吃亏,我很喜欢这个坛子,担心被文物贩子抢去。我指着刚开进古玩街口的一辆奥迪说,好险,幸亏我们早走一步,不然就走不出古玩街了,除非把坛子留下,而且我肯定帮不了任何忙。
她说光天化日的怕什么,而且她会誓死保卫坛子的。我夸她勇敢,并告诉她车上是一群无赖势力。暗地里,这条街上,他们说了算。文物水分大得很,真真假假,贵贱之分,只是一念之差。那个古玩贩子是个白痴,他拿不下她,又不想让别家吃掉,才打电话讨好他们老大。这条街上有那么多古玩老板,却只有这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跟她过招,就是因为没人敢坏规矩。我很清楚,这是一条容易滋生事端的街。
她说凭什么相信我呢。老实讲,我也不知道凭什么。我不想再与她争论,就告诉她除古玩街,她现在可以去她想去的任何地方了。我刚说再见,她就急忙拉住我,问我是否真想要这个坛子。我认真告诉她,最近确实想得到一个坛子。
当她听说我不是收藏,而要用来装酒时,眼睛瞪得夸张,把音调拖长喊我亲哥。我说装酒怎么了。她叫我猜刚才贩子出的价钱。我故意说两百,她摇摇头说我是个白痴。我说两千,她气得骂我冒牌货。我皱着眉说不猜了没意思,她蔑视地看着我,说那人出两万,可她没松口,那人有眼无珠。
我突然就没了底气,如实说买不起这坛子,我只想得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酒坛子。我说完就走。她问我去哪里。我说回家。她竟柔声问,可否带她去我家。我真怀疑自己听错,我说哪能带她一个女的回家呢。
她觉得我是怕老婆的男人,我禁不住笑了。她问我笑什么。我说我还没有老婆,她是否还敢跟我走呢。她似乎很无奈,说方才被我这么一搅和,似乎这个城市里只有我一个好人了。她说,起码我还没有让她感到不安全。我能嗅出其中嘲讽的味道,但还是觉得很受用,反让我不知该怎么反驳了。
她之所以要卖这个坛子,是因为她的钱花光了,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她委屈地指指坛子,说出来两个星期了,身边就剩下这个坛子,她确实很犹豫和矛盾。因为还差一天的房钱,她的身份证被抵押在前台,多亏旅馆好心的小姐帮忙,要不然,她昨晚就露宿街头了。而且,她前天就把手机贱卖了,她还不想绝食。她向上帝发誓,她不是编戏,请我一定相信她。
我让她别误会,我真没那个意思。我问她为什么不跟亲人联系,难道不怕家里着急吗。她丝毫都不忌讳,喃喃地说自己属于离家出走,来这鬼地方找个混蛋,可这混蛋好像消失了,电话也消失了。因为仓促等意想不到的原因,她没料到事情会这样糟糕。她更不想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一个闺中密友。
为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她使了一些优美漂亮的手势,因此,我听得还算有味。我问她难道就不怕我是坏人吗。她狡黠地问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我微笑着把视线转移到天空。我觉得沉默是最好的回答。
来到旅馆,我一看就傻了。这是一家具有涉外性质的宾馆,根本不是她说的什么旅,什么馆。我替她在前台结了账,赎回了身份证。我做贼般瞟了一眼证件,看到笔画茂盛的三个字,陈蒹葭。她很敏感,迅速把身份证收起来,我很遗憾没看见住址和日期。
走在马路上。她说,她可不想跟一个陌生人回家。我说,我叫郑钢,难道我现在还是陌生人。她说,知道名感觉就不一样了。我问她名字,她瞪我一眼,说我不地道,明知故问。我挠挠头皮说自己不是圣人,向她表示歉意。
陈蒹葭站在客厅中央,十分忧伤地叹她命运不济,说她陈某人竟流落到一个狗窝。我的屋子确实很脏乱,这使我无话可说。陈蒹葭像教徒安放圣像一样,终于给坛子找到一个还算安全的地方,并声明只是暂存我家,它还姓陈。我叫她十二分放心,它一百年都姓陈。她白了我一眼。
我烧了两个菜一个汤,加上带回来的熟食,看上去也蛮丰盛的。她可能饿坏了,捏了一块就吃,并夸我手艺不错。她说原来单身还可以提高厨艺。她可能发觉说漏了什么,马上打住了。我问她喝酒还是喝饮料。她指指白酒,竟大呼小叫起来,说我不会居心不良吧,并指出我开始可是喊她妹妹的。
我其实是个有脾气的人,但在一个娇蛮可爱的女性面前,也不便发作。我不悦地甩给她一瓶饮料,就自斟自饮起来。陈蒹葭觉得我喝酒的样子很沉醉。
我确实喜欢喝酒,这首先感谢我爹的遗传,其次感谢我的血液,在对待酒的态度上,它宽容大度,也和平友善。我五岁时,在祖母的乡村里,在她老人家盛大的生日宴席上,在我父亲的纵容下,我敬了祖母一杯乡下产的烧酒。祖母很高兴,皱纹笑得像开了花。我还表演了一套郑氏醉拳。全场目瞪口呆。因为我的出彩,父亲很是虚荣了一把,他站在秋季的天空下,精神得像一棵钻天白杨。
我觉得,喝酒可以忘掉一个世界,也可以创造一个世界。我满嘴酒气地告诉她,酒像神,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神,那么酒就是我的神。陈蒹葭笑嘻嘻地很佩服,说这句话经典,可以上央视做广告了。
后来,我就不吭声地看她。她瞪我一眼,埋怨我干吗直勾勾地望她。她说自己可不是烧酒,并扬言她是烈女,如果我胆敢冒犯她,她一定会咬死我。
我对她的高度警惕表示赞美,但对她会咬死我不感兴趣,我只是觉得,她……陈蒹葭柳眉一挑,示意我不要吞吞吐吐。我感觉她是一位有钱人家的小姐,至少也是个金领。她哈哈大笑,说自己祖上三代贫农,而她只是个普通的穷小姐。我冷笑说,穷小姐会舍得随便卖手机,会舍得随便卖古董,会舍得随便住五星级宾馆。她驳斥说那只是一个破手机、破坛子,住宾馆是因为她懂得善待自己。而她总不能为了装穷,就露宿荒郊野外吧。
我严正声明,她的所谓破坛子,我保守估计应不低于五万六万。我觉得她走路的姿态,说话的派头,以及身上的高档香水味,都具有典型贵族小姐的做派。她脸上表情顿时凝固了,她认为我主观臆造。我又列举她的名字陈蒹葭,我说,这可不像普通老百姓家起的名。她用低低略带嘲讽的语气说我太聪明,劝我该去当侦探做间谍。
我不再说话,仍冷冷地审视她。她觉得我的样子是想绑架她。我扑哧笑了。她没笑,只把筷子一丢,说我是个虚伪的人,再不相信我不懂什么古玩的鬼话了。她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突然就神经质地问我可有电脑,她必须得马上上网。我指指卧室,并告诉她电脑密码是酒的拼音。
我用余光瞟了瞟屋角的坛子,它依然保持着精灵般的矜持和冷静。大约半个小时,她出来了,看起来很沮丧失落。我问她在搞什么名堂,我的电脑里可是有隐私的。
她没理会我的调侃,竟蹲在地板上啜泣起来,就跟先前蹲在古玩街的地上一样。我必须得诅咒她所要寻找的那个混蛋。否则,我会觉得自己也是个混蛋了。她扬起通红的眼告诉我,说那混蛋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认识他三年了,他怎么能骗她呢。
我有些明白她跟那混蛋的性质了。她说,那混蛋也像我这样喝酒。她觉得像我们这样喝酒的人,应该不是坏人。我认为她的逻辑很有问题,好像她是说,世上像我这样喝酒的人都很善良一样。
她像个现代祥林嫂,开始反复絮叨一个跟情爱有关的主题,主角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混蛋。我能感到,从她嘴唇里吐出的混蛋二字,绝对质变了。他曾经许诺,条件成熟时,他会离开那个他不喜欢的女人,然后今生只陪她。
有一天黄昏,她匆匆路过北京天坛,在古玩市场遇到一个女人,并一眼看上了那个坛子。那女人一袭黑衣,举止典雅,神情高贵。她说自己是旗人,这个坛子是祖上传下来的,不是为了救急,万万不敢卖的。黑衣女人忧郁动人的眼神,彻底打动了陈蒹葭。
她忽然惦起那个男人,一个狂热迷恋坛子和罐子的男人。他的家除了书和酒,就是坛坛罐罐。他可以对着一个精美的坛子或罐子看上三天三夜,他说对陈蒹葭也是这样。这个坛子精巧得浑然天成,陈蒹葭觉得它不是空的,那里盛着她今生的爱情。她觉得,整个北京都被她的爱情感动了。陈蒹葭花高价买下坛子,用一块碎花蓝布裹好,小心翼翼地抱着,就像怀抱自己一生的幸福。
她跟他说,要送他一件特别的生日礼物,等忙过这个月,她就来看他。一个月后,她携着坛子过来。男人说好去车站接她,陈蒹葭等了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就像一个世纪。可,男人没来。
不得已,陈蒹葭寻到那个著名的湖边。她内心非常忐忑不安,毕竟是第一次登门。她鼓足勇气敲开门,可谁能想到,这幢别墅已换了主人。她一下子傻了,急忙打听这家人的去向,主人说好像移民欧洲了,她一听脑子就懵了。他可以说不爱她,也可以说从来都没有真正爱过她,她肯定不会怪他的。她真的不会怪他的,可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结束呢。
这是我第一次耐心听,除母亲外另一个女人的啰嗦。我不清楚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这对陈蒹葭确实很残酷。说实话,这种纯情故事已经对我失去毒性。
陈蒹葭大老远过来,就是想送给他一个坛子,并不想要求什么,她突然觉得自己很傻。我有个预感,她是想用坛子装住那人的心。男人并不知道陈蒹葭要送他一个坛子,但他已感到危险的降临,他可能不想继续游戏了……
我这样分析,使她非常愤怒。我说,这只是我的感觉,也许是错的;我觉得婚姻里的女人最精明,而爱情中的女人最傻。
我后句话切中要害。她开始沉默,沉默得叫我恐惧。忧伤和绝望淹没了她。
她竟要陪我喝酒。我连连摆手,她却觉得我怕了,奚落我是个胆小鬼。我问她难道不怕。她嘿嘿花痴般笑着,眼神迷离地说,这句话听着开始像坏人了。
后来一切,被酒渲染得顺理成章。这是个疯狂的夜晚,她的火热和缠绵,使我亦死亦生。我喝了很多酒,只觉得非常冲动,我没完没了地吻她,要她,就像不要命地喝酒。陈蒹葭像一片云彩,温柔地迎着我。
她说我很贪婪,真想咬死我。我气喘吁吁地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
清晨的阳光,从窗帘洇进来。一些虚幻的气息,在房间里蔓延。
我太困了,睡得像死人。陈蒹葭早飘得没有影踪。我还能闻见她隔夜的气息,这是能杀人的气息,我已经被她杀过了。一根长发在枕边静静躺着,我拾了起来,举着逆光而望,它就像金线闪闪。
她写了纸条,从我钱包取了一千块钱。陈蒹葭说,从我醒来开始,这个坛子就改姓郑了。她叫我用它装酒,要我好好喝酒。她说昨夜只是一场梦,现在我们都醒了。
看着这个亦仙亦邪的酒坛子,我突然感到一种遥远的虚幻和缥缈。我觉得昨天的事情,好像发生在五百年以前。我得了便宜,又卖了乖。我开始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不是子虚乌有的。
我打长途跟二伯说得了一件宝贝。二伯是另一座城市的资深瓷器收藏家。二伯风尘仆仆地乘火车过来。
二伯先远远打量坛子,然后才通过放大镜,十分冷静地察看坛子。看了很久,他才说:小钢,从艺术上看,它白底黑釉,画彩虽有些黯淡,但仍可窥见当年浓烈的质地,纹饰图案简洁精巧,与主图构成含蓄、粗犷之美。坛口有一处小小的磨痕,我怀疑是主人打酒时用的酒提子磨损的。
从细微处看,局部布满一些开裂的小纹片,坛子的底部,本是满釉,很可惜脱落了一半,这是由于年代久了所致。在时间上,我想最晚也是明末。这是典型北方窑风格。天下民窑在磁洲,这是河北磁窑烧制的酒坛,是大户人家定制的私人藏品,这个坛子是民窑中的精品。
我强压住欢喜,不敢打断他的思路。
二伯再次沉默。他的意识肯定正徜徉在几百年前的某个时刻。他又想了一会,从口袋拿出一把小刀,在坛子的破损处,小心刮下一些粉末。它们就像古代的时间,被二伯的目光所击碎,纷纷洒落到一张白色硬纸上,二伯通过放大镜仔细观察。他皱着眉,好像先前某个细节或秘密就隐匿其中。
我都不敢呼吸了。
二伯忽然俯下身,像猎犬般嗅那粉末,并用食指和拇指轻轻捻着,捻着。捻了好大一会,二伯终于舒口气,安心地喝了口茶。他慢条斯理地说,这个坛子价值连城肯定不可能,可价值连房应不为过,问我可信。我兴奋地站起来说,我信,专家的话还能不信。
可是,二伯语气一转,忽然就愤怒地告诉我,这坛子是个赝品!只是做得太逼真了,一般人很难辨出它的真伪。坛子表面可以做旧,但历经几百年的材质是假不了的,这就叫表里不一。
我呆若木鸡。
二伯生气地骂我不懂装懂。我不知该说什么,也不好解释什么,只好对他老人家傻笑,我说二伯您喝酒,我敬您,我向您老赔罪。我站起来,咕咚一声,就把一大杯酒喝到见底。
下午,二伯败兴而归。
我后来去了一座临江城市,遇见一位贤淑女性,并毫不犹豫娶了她。那只坛子在数次迁徙辗转中终于遗失,我奇怪竟没有太多难过。我觉得,我把它放生了。
我仍然喜欢喝小作坊做的烧酒。我的运气很好,我所住过的城市附近,总能寻到这样的小酒坊,它总能点缀亮堂我的生活,使我倍感亲切安详。我早已明白,我的酒不是皇帝,它也不需住什么深宫大殿,我和我的酒都是平民,我们都热爱简单质朴的生活。
一个叫刀郎的西部歌手,躲在我的音响里,唱一首叫《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歌。我的城市并没落雪,落雪的季节已经过去。可我凭感知,觉得雪正飘下来,在我心中纷纷扬扬。
从阳台望过去,天空蓝得很傻。路上,行人不多。路面有落叶,不多的行人从落叶上踩过。这是春天的落叶,香樟树的叶子。我喝着酒,觉得心里有沙沙声在响,就像风拂过旷野,又像许多蚕在我耳畔吞食着桑叶。我感到时间哗哗地从我头顶砸下来。
我不怀疑二伯的说法,但我始终觉得,陈蒹葭是个受害者。她为了一千块钱骗我,这更没有道理,而当时我的钱包里有两千多块钱。一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人,很容易失去理智,臆想出一些虚幻,什么疯狂都干得出来。她当然看不出那个坛子是个赝品,就如看不出那个男人是个赝品一样。
我宁愿相信,这是个货真价实的明朝酒坛子;就如相信陈蒹葭给我的那一夜,是情深意切的一样。我后悔不该把二伯请来,这个坛子的真实价值,其实只跟情感有关,它是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宫大殿,繁华或萧索,热闹或寂寞。
我倒出一杯酒,喝着喝着,我的眼睛湿了。妻子小声问我怎么了,我说,狗日的酒呛了我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