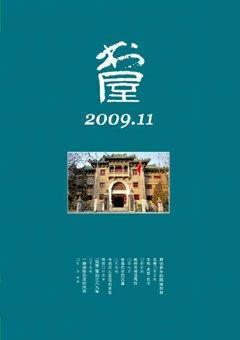徐志摩惹祸的三篇序跋
彭林祥
现代文学三十年期间,文事论争层出不穷,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炎生先生著的《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就梳理出了现代文学三十年间共九十次文学论争,由此可见新文学文坛文事论争发生的密度。而作家间论争总是需要由头,或者说是导火线。在笔者收集整理新文学序跋的过程中,发现许多新文学序跋常常充当了文坛论争的导火线。拙文仅以徐志摩所写的三篇序跋为例,梳理因序跋所引起的三次文事论争。
1923年7月7日的《时事新报·学灯》刊登了徐志摩的诗作《康桥西野暮色》,这是一首没有标点的诗作,诗前有一段小序,专门对诗作有无圈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小序中,徐志摩有这样的话:
我常以为文字无论韵散的圈点并非绝对必要。我们口里说笔上写得清利晓畅的时候,段落语气自然分明,何必多添枝叶去加点画。……真好文字其实没有圈点的必要……我胆敢主张一部分的诗文废弃圈点。
争论由此引发。7月13日,《晨报副刊》上登出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十地的《废新圈点问题》,他质问徐志摩:不知西洋的“圣经贤传”上有无圈点?弥尔顿一流的妄人所编的不说也罢,不知道像徐先生一样有教化的西洋绅士们所看的古书,是否都用散字母排成平方一块的版本?徐先生的书库里一定有不少没有圈点的西洋“圣经贤传”,何妨请用铜版印一页在《学灯》上,给我们长点见识呢?另一篇是松年的《圈点问题的联想》,也对徐志摩的小序中的关于圈点的主张提出了批评:“我们每叹一部好书没有圈点,但世间也会有叹息痛恨于一部好书可惜有了圈点的人。”稍后的7月18日,《晨报副刊》上又登出了黄汝翼的《废弃新圈点问题》,对徐志摩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并把徐的观点奚落称为“徐志摩定律”。徐志摩实在不堪他们的诘问和讽刺,在看到黄汝翼文章的当天,他就写了致伏庐(指《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一封公开信》,此信在22日的《晨报副刊》登出。在信中,他申明:
我相信我并不无条件的废弃圈点,至少我自己是实行圈点的一个人。一半是我自己的笔滑,一半也许是读者看文字太认真了,想不到我一年前随兴写下的,竟变成了什么“主张”。不,我并不主张废弃圈点……
他在申明自己主张的同时,也承认了自己笔滑。但因前面几篇批评他的文章的发表,徐又对《晨报副刊》的编辑方针提起了意见:
所以我劝你,伏庐,选稿时应得有一个标准:揣详附会乃至凭空造谎都不碍事,只要有趣味——只要是“美的”——这是编辑先生,我想,对于读者应负的责任。
这是针对作为编辑的孙伏园,责怪编辑为什么要发批评自己的文章,这就得罪了孙伏园。所以在徐的公开信的后面,作为编辑的孙伏园写了《伏庐后记》,对于徐志摩的意见进行了反驳。《后记》中首先就批评徐志摩:“辩论而至于教训记者,这是下下策。”最后,孙伏园反唇相讥道:“平常作者被人驳倒无可申诉却迁怒于编辑的窠臼,这是大文学家们不屑为的。”
徐志摩与鲁迅的结怨,也是缘于他的一篇小序。1924年12月1日,《语丝》第三期出版,刊有徐志摩的译诗《死尸》(波特莱尔作),前面有他写的一小序,他提出了自己的“神秘文艺论”:“诗的真妙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接下来,他又有这样的话:
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鸭,树林里冒的烟,朋友的信,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燐,巷口那只石狮子,我昨夜的梦……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无一不是音乐,你就把我送进疯人院去,我还是咬定牙龈认账的。是的,都是音乐——庄周说的天籁地籁人籁,全是的。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朵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你能数一二三四能雇洋车能做白话诗或是整理国故的那一点子机灵儿真是细小有限的可怜哪——生命大着,天地大着,你的灵性大着。
这篇小序引起了鲁迅的反感。半月之后,在《语丝》第五期上刊出了鲁迅的《“音乐”?》。文中开始就说,因夜里睡不着,坐起来点灯看《语丝》,不幸就看见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谈。接着,他马上纠正,不是神秘谈,而是看到了音乐先生的关于音乐的高论。但是,对于鲁迅来说,他这样皮粗耳笨的人能听到天籁地籁人籁,却没有听到徐先生所谓的绝妙的音乐。所以,他这样调侃徐志摩:“我不幸终于难免成为一个苦韧的非Mystic了,怨谁呢。只能恭颂志摩先生的福气大,能听到这许多‘绝妙的音乐而已。”但是,他又笔锋一转,讽刺道:“但倘若有不知道自怨自艾的人,想将这位先生‘送进疯人院去,我可要拼命反对,尽力呼冤的——虽然将音乐送进音乐里去,从干脆的Mystic看来并不算什么一回事。”最后,鲁迅意味深长地反问:“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
不难看出,鲁迅显然不同意徐志摩的神秘主义的文艺观,而徐志摩对音乐的看法,也让他不敢苟同,这是两种不同的文艺观的交锋。所以,他就写了这篇略带戏谑和讽刺的妙文与徐志摩争鸣。十年之后,鲁迅在《〈集外集〉序》中还提及到此事:“我其实不喜欢做新诗的……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了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就果然不来了。”
1925年9月,徐志摩开始主持《晨报副刊》的编务,改版为《晨报副镌》,10月1日出版第一期。但是就是在第一期里,徐志摩又是一篇序跋惹了祸。在这一期发表的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后面,徐志摩随手写了几句跋语,其中一句是:“还有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一并致谢。”这一句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是由凌叔华画的。这一笔误自然给了人口实。一周后,《京报副刊》上就刊出了重余(陈学昭)写的《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文中指出,偌大的北京城,学者专家随处皆是,但是为什么都没有发现窃贼呢?作者很想看到有人发出点声息,但是使我等得耐烦了。文章末尾,作者只好自己来点明这幅画是剽窃琵亚词侣的:
琵亚词侣是英国人,他现在已变为臭腐,已变为泥土,总之是不会亲自出马说话的了!但这样大胆是妥当的吗?万一有彼邦的人士生着如我的性格一样者,一入目对于这个“似曾相识”起了追究,若竟作大问题似的思索起来,岂不???我觉得难受!
可是仔细想想我又何必着急替人家难受?反正人家有这样的本领做这样的事,呀哟!真——算了罢!!!
这一指责针对凌叔华,徐志摩知道事情闹大了,当天便写信给《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请求将此信刊出,说明事情经过,为凌女士辩诬。10月9日,《京报副刊》刊出了徐的信。信的开头就交代:“这回《晨报副刊》篇首的图案是琵亚词侣的原稿,我选定了请凌叔华女士摹下来制版的……幸亏我不是存心做贼,一点也不虚心,赶快来声明吧,”但是,徐又在信中也对质疑者表达了不满,在他看来,“琵亚词侣的黑白素绘图案,就比如我们何子贞、张廉卿的字,是最不可错误的作品,稍微知道西欧画事的谁不认识谁不爱他?”言外之意即是,你以为别人剽窃,实际上是你自己孤陋寡闻而已。
自然这幅画很快就被撤下来了。到10月17日出第九期时,就换上闻一多画的刊头。但是,此误会并没有完。在1926年年初,鲁迅在《不是信》中还提起此事,说陈西滢以为是他揭发了凌叔华剽窃琵亚词侣的画,才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整节的抄袭了日本学者盐谷温的书。凌叔华也不甘休,在《关于〈说有这么一回事〉的信并一点小事》(刊于1926年5月5日《晨报副刊》)发泄了自己的不满:“哪晓得因此却惹动了好几位大文豪小文人,顺笔附笔的写上凌○○女士抄袭比斯侣大家,种种笑话,说我个人事小,占去有用的刊物篇幅事大呀!因此我总觉得那是憾事,后来就请副刊撤去这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