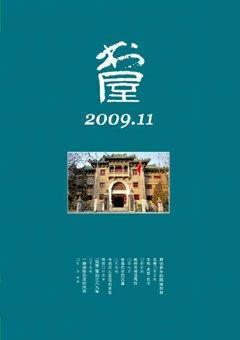热爱老大哥与奥威尔
杨光祖
还没有放寒假,但学校里已经很寂静了,单位也没有人叫你去开会,天气也渐渐地冷了。我懒得出门,就缩在被窝里读书。这几天读的就是奥威尔。很奇怪,以前我很反感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根本没有读过他的一本书。大概是从别人处听说他写的是政治小说吧。可是无意之中,读了《动物农庄》,我被震撼了。这岂是“政治小说”所能概括的?而且当时读这本书,还是儿子的原因。2008年7月我们去杭州,在友人吴玄兄的办公室,儿子读了几页《动物农庄》,就被终止了,因为我们要返回了。但他一直记着这本小说,我找了好长时间,从一个特价书店买了一册。他看完后,我也随意翻了,我现在经常与儿子一起读书。这一翻,不得了,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很奇怪,好多东西你一旦发现,就像踩着弹簧一样,很快就上去了。他说完,我想了想,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就如奥威尔,一旦喜欢,就非常投入,从网络、书店买了他全部的代表作。这几天就一直读《1984》。读着读着就忘记了周围的世界。
今天下午,家里人都出去了,我又钻进被窝,读《1984》。电脑里放着音乐:吴莉的古筝《寒鸦戏水》,忧伤轻曼的音乐给我许多的伤感,有一种文化人的轻愁。在这个音乐里读《1984》最合适。而今天我读的正好是男女主人公在政治高压下的偷情部分,文字真是太妙了。我不知道董乐山是何许人也,但他的译笔无可挑剔,非常符合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和艺术品位。从“文革”走出来的人还有如许美妙的文笔,与这样古典的情致,让我对他这个人也有了极大的好奇。从谷歌搜索,知道他1924年生,浙江宁波人,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专业。难怪!好多疑问也就冰释了。看他的照片,那么风流潇洒,很有气质的一个人。长期从事西方尤其美国文学文化研究,1999年病逝于北京。
奥威尔出生于英国中产阶级,虽然家庭贫穷,但那种优秀的教育和家庭熏陶,对他的小说写作影响至巨。他说过,英国人的阶级在舌头上。他本想混迹街头流浪汉中,可警察一听他的口音,就非常客气地请他这位绅士不要胡闹。而那些流浪汉也不信任他。正是在这种阶级文化的撕扯中,他才有着别人没有的感觉,创作出如此优秀的小说。不像我们当代的很多文学,总是有一种小流氓味道,对汉语的高雅、典雅、韵律都一无所知,也没有丝毫文体感觉,你能想象出他们还能写出什么文学来?翻译奥威尔这样一个人的作品,董乐山就是最佳人选了。傅惟慈翻译的《动物农庄》,也不错,但那种气质那种情调,他并没有翻译出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1984》可以说是一部政治小说,但这样说本身就限制了他的生长,它其实是不断在生长的,在有心的读者那里,它是可以持续生长的。我们以前的阐释主要关注它的政治性,反极权性。如果说《动物农庄》更接近一部政治小说,一部批判反思极权的小说,那么《1984》则意义大得多,它其实已经触及人性的深处,人的一种文化养成,人对文化的需求,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所谓的极权主义就是要抹杀人的所有欲望,把人变成工具,在他们内心,根本没有历史,没有记忆,没有感情,没有思维,没有人性,没有文化,没有情趣,没有韵律,没有品位,总之,凡是与一个优秀的人有关的东西都不应该具备。这是以前的所谓专制无法做到的,而现代化却给极权主义以高科技的支持,其文化领导权的威力那是以前的帝王想都想不到的。
《1984》里在真理部工作的温斯顿,在小说司工作的裘莉亚,他们经过了多年的极权教育,每天生活在电幕、窃听器、同事、领导、警察等的严密监控之下,但他们的内心却越来越向往一种自由的生活,一种人的生活。他们在办公室道貌岸然地甚至非常政治化地生活着,工作着。但在极其有限的私人空间,他们却不愿意遗忘,他们不断地触摸和回忆历史,他们对历史留下来的遗物,那么感兴趣,甚至不惜以死亡为代价来换取片刻的温馨。他们互相爱着,爱得那么深,这在那个仇视爱情、仇视性欲的社会,真是大逆不道。小说里他们通过非常曲折的道路,到达野外的一处隐秘丛林里,在那里他们真正的热恋了。那一段描写真如天籁之音。我这里就不征引了,有心的读者可以自己去读。看来,人作为人,毕竟是不同于物的。
最后他们终于被逮捕了,说“终于”,是因为他们做的一切其实都在人家的掌控之中。经过多少次的折磨、恐惧、毒打、教育,他们终于都“觉悟”了。只是最后在心底还保留了一点私人感情,所谓的爱情吧。可即便这一点,也不让你留存。在101室,他们最后都完全地彻底地心甘情愿地投降了,他们终于被改造成功了,整个一个人都是那么“纯洁”。奥勃良说:“你最后投降,要出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并不因为异端分子抗拒我们才毁灭他;只要他抗拒一天,我们就不毁灭他。我们要改造他,争取他的内心,使他脱胎换骨。我们要把他的一切邪念和幻觉都统统烧掉;我们要把他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不仅仅是在外表上,而且是在内心里真心诚意站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在杀死他之前也要把他改造成为我们的人。我们不能容许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不论多么隐秘,多么不发生作用,居然有一个错误思想存在。甚至在死的时候,我们也不容许有任何脱离正规的思想。”
这种对人性的压抑、异化,不仅是极权的要求,就是现在的现代化、高科技、后现代主义,不是也如此吗?福柯说,人类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大监狱,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监控之中。我想,这可能是人类的原罪吧?不是仅仅只有极权社会才有,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我们要把你挤空,然后再用我们自己把你填满”。在这里,权力很关键。“权力就在于给人带来痛苦和耻辱。权力就在于把人类思想撕得粉碎,然后按你自己所选择的样子把它粘合起来”。其实,我们想一想,任何权力都是会膨胀的,都是想把人变成真正的工具,没有感情的工具。这里,最关键的就是感情,有感情就证明你的自由,心灵的自由。
小说结尾写道温斯顿回到了友爱部,一切都已原谅,他的灵魂洁白如雪。“他走在白色瓷砖的走廊里,觉得像走在阳光中一样,后面跟着一个武装的警卫。等待已久的子弹穿进了他的脑袋”。他鼻梁两侧流下了带着酒气的泪。但是没有事,“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读到这里,我的心里很难受,一种从来没有的难受。到现在为止,只有两部小说读到最后,给我很不愉快的感觉。一部是《红楼梦》,一部就是《1984》,前者让我绝望,甚至一种幻灭感,而后者给我一种恶心,一种绝望的厌恶,甚至还有一点认同这种恶心的情感。或者说读《红楼梦》让人虚无,不知所在,而阅读《1984》却让人有点进入迷狂,并勾起了读《象棋的故事》的感受:一种一边阅读一边自我克制的痛苦,似乎自己也要进入那种癫狂。我真不知道,欧洲作家怎么有这种魔鬼般的力量?他们如果不是天使,就是魔鬼,作品里的那种力量超过了人的承受能力。
我读完此书,正好是一个冬日的下午,看着阳光从窗外流走,我知道我不会再关注这种书,这种事了。我的眼泪想流下来,却被一种绝望般的厌恶所挤走。想起除却巫山,想起曾经沧海,我忽然明白了许多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