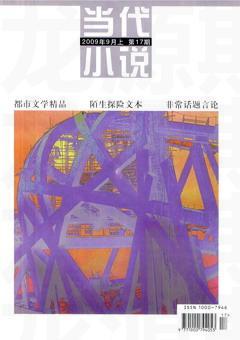火色鸟(短篇)
赵胡子
一
我记得那件事发生的前些天,我总会梦见一个样子很奇怪的东西。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只奇怪的鸟。它通体赤红,浑身燃烧,像个绅士一样抖着一条竖起来的尾巴,焦急地在我家的院子里踱着。我觉得它好像要跟我说话。我瞅着它豌豆一样大的绿眼睛,咕咕地唤着,探着身正要向它凑上去,它雉鸡一样精瘦的身子突然一耸,翅膀猛地一展,啊地叫了一声,不见了。我梦见了一只身上会着火的鸟。天亮了我跟他们说,可他们每次的反应都很冷淡。我知道要是再说的话有人一定会朝我发火,我只要说上两遍,有人一定就会冲上来瞪着眼睛想揍我。我不敢跟他们啰嗦,就跟小草说。小草听了,很忧郁,说,是吗?那它到咱家院子里来干啥啊,它一定是饿了吧。小草说着就拎了棒苞米,掰着往院子里撒苞米豆。对了,就是苞米豆。
我又梦见那只火色鸟了,我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在它叫了一声就要不见了的时候,我手一舞,醒了。半夜了,顶棚上的灯还亮着,我嗅着好像有一股不祥的气息,接着,听到爸爸“嗯哼”了一声,说:“这事我已经决定了,就叫小草去!这个仇不报我咽不下这口气。”
小草是我的妹妹,七岁了。爸爸说叫小草去干什么,我不明白,但后面的话我觉得懂了。这些天,我们家被住在前面的二疙瘩欺负了。二疙瘩这次翻新房子,后抻一步把我们家门口的进出道霸占了。爸爸咽不下这口气,不停地上访。可二疙瘩在公社建筑队当头头,财大得势,早就把上面下来的干部们喂饱了。今天上面的干部们又来了,爸爸跟他们大吵了一场,骂咧咧地从队上回来,一憋劲把二疙瘩家的后墙刨了个大口子。二疙瘩气坏了,跑出来一锤子就把爸爸的头敲了个大窟窿。“这个仇不报我咽不下这口气。”爸爸又说了一句。我揉了揉惺忪的眼看了一眼,爸爸侧着身朝外躺着,头上缠着一圈沤着黑血的灰布条。爸爸糟乱而又狼藉的后头很像一片磨掉了毛的癞狗腚。我正要笑,这时候,炕那头传来了妈妈叹着气,给小草摆弄枕头的声音。
我又想起刚才做的那个梦了,说:“我梦见那只会着火的鸟了。”
爸爸厌恶地瞪了我一眼,说:“睡你的觉吧。”
我也不知一下子怎么来了勇气,生气地说:“你们要叫小草到哪里?我真的梦见那只会着火的鸟了,它就在咱家的院子里。”
“你这个傻子!你简直是个丧门星!”大概是我的脾气把爸爸激怒了,他转过身来,吼了一声,扬起一只巴掌就要扇,却被妈妈制止住了。妈妈说:
“你不要再打了,他知道什么呢。”
爸爸气哼哼地,又回了身。
他们说得没错。是的,我是个傻子。他们说我五岁那年掉进薯窖里被人吊上来,就再没长脑子,而我今年十岁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叫我傻子,我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傻。我知道吃,知道喝。还有,我做起事来很喜欢动脑子。我经常很费脑子地去想不傻的人会是什么样。想得头疼。
二
我又梦见那只火色鸟了,但它刚一落下就立即飞走了,接着,我迷迷糊糊地觉得脸痒得像爬上条虫子。我一激灵,醒了。我看到小草正咯咯地笑着,拿着根狗尾巴草在我脸上撩拨。
于是,我生气了,大叫着,说:“你又给我把火色鸟吓跑了。”
小草见我醒了,收起狗尾巴草,说:“哥,我要去做侍女了。”
我的话你没听见吗?你又把火色鸟吓跑了!我对小草撩醒我的梦有些生气,嘟哝了句,想继续睡,忽然“咯噔”一下想起了晚上他们说要小草到什么地方去,一下子又跳起来,说,什么?你说你要做什么?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小草说,我要去做侍女了,去给小先生做侍女。
“原来他们要把你送给小先生啊。”我说。我惊措地张了一下眼睛,眼颊有些生疼。我用手指抠着眼屎,一边抠着,一边又张了张眼,说:“原来他们要把你送给小先生做侍女啊。”
小草对我这个不雅观的动作已经习惯了,她把手里的狗尾巴草缠在指头上开始系花。她咧着嘴笑着,说:“哥,你知道小先生是谁吗,我给小先生做侍女好不好啊。”
我想了想,说:“不好。”
小草说:“哥,我给小先生做侍女怎么不好啊。”
我说:“我不知道。”
我开始很费劲地去想小先生是谁。
我对小草说给小先生做侍女不好没用,这不单是说我是一个傻子,因为小草得听爸爸的话。小草说要她给小先生做侍女是爸爸早晨告诉的。爸爸说要是她去给小先生做侍女,下次我们家再跟二疙瘩打官司,小先生就答应帮助我们家。小先生说他的功能可以让上面下来的人倒过嘴来帮着我们说话。小草说着,把系在头上的花整了整,捏着系起来的狗尾巴草花也插上去,歪着头,咧着嘴又笑起来,说:“哥,爸爸说要给我做新衣裳呢,你说我漂亮吗?”
我说:“我不知道。”
小草对我呓语一样的应答有些急,她用袄袖擦了擦我嘴角流下来的涎水,摇晃着我的头。我一愣怔,回过神了。小草说,哥,你想起小先生是谁了吗?我说,没有。小草说,爸爸说要给我做新衣裳,你说好看吗?我说,他们要给你做新衣裳啊,他们都给你做新衣裳了。我和小草正说着,这时候,我听到了妈妈叫我们下去吃饭的声音。我胡乱穿上衣裳下去了。
我下到正间,看到长条桌上的苞米饼子已经端上了。爸爸已经坐下,他头上缠着的灰布条让血沤得愈发恶心和吓人。爸爸灰着脸正抽烟,妈妈蓬着乱发,正趴在锅灶上往盆里舀什么。我挨着爸爸坐下,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妈妈舀满了小盆,端下来。我嘘地一声,眼睛一下子亮了。
我说:“你们做了面疙瘩汤啊。”
爸爸仍抽着烟,没有理我。妈妈挨着小草在我们对面坐下,开始舀汤,她先给小草舀了一碗,接着,给我,给爸爸。妈妈的眼睛有些肿,看样子刚才哭过。
我见他们都不理我,又生气了,大起声又说了一句:“你们为什么要做面疙瘩汤啊。”
我的话把爸爸惹烦了,他瞪起眼,朝我吼了一声:“你就不能闭上嘴!你这个傻子!”
我毫不示弱,说:“你们要把小草送给小先生干什么!”
“你不闭上嘴不行啊!你这个傻子!”爸爸终于被我激怒了,他扬起巴掌猛地一抡,啪地一声把我手里的面疙瘩汤碗打翻了,接着,又吼:“你这个傻子不用吃了!饿死你算了!”
“这日子真没法过了。”妈妈从端下面疙瘩汤到现在,一直抑郁着脸不说话。这时候,她站起来,捂着眼跑了。
我和小草哇地一声哭了。
我有两三天没有梦到火色鸟了。我想,它肯定是让我们家不祥的气息吓着了。
我觉得我们家不祥的气息越来越浓了。爸爸现在一天几趟地跑大队,回到家就不停地抽烟,莫名其妙地发火。爸爸越来越喜欢发火,就连我这个傻子也怕他了。今天早上,他们给小草做的新衣裳拿来了。小草试了试,很高兴。小草问我她的新衣服好看不好看。我说,不好。小草很生气,一努嘴,把系在头上的花也摘下来撂了。说实话,我也想说些漂亮话,可我是一个傻子,傻子是一般不说假话的。我觉得小草的新衣裳一点都不好,一身的绿,小草穿着像个媒婆。当然,还有些怪怪的感觉,我说不出来。中午,爸爸跟妈妈嘟哝了几句,妈妈听了身子有些哆嗦。我觉得这也很不祥。我想问妈妈刚才爸爸给她说什么了,见爸爸死灰着脸,就没敢问。但很快妈妈开始行动了,她蓬着乱发,从碗柜里端出一碗干枣,洗了洗,给了我和小草一人一小把,接着,支起面案,吭哧着从锅灶角里搬出一大盆发得冒沿的面,倒在上面就揉捏着忙起来。妈妈一定把队上一年分的麦子都磨成了面,妈妈什么时候发了这么一大盆面?我和小草都惊呆了。等爸爸走了,我问妈妈:“你发这么大的面要做什么。”妈妈说:“给你和妹妹做饽饽吃。”妈妈说着,背过身抹了一下眼。他们会做饽饽给我和小草吃?他们为什么要做饽饽给我和小草吃?我才不信呢。
整整一个下午,妈妈一直闷着头做饽饽。她做了一个嵌满干枣和一条“龙咬元”圣物的“大枣山”,又做了一面案各式各样的水果和看起来很像动物,蒸熟了,又涂得花花绿绿的很好看。可我觉得这也怪怪的。我好像要想起什么了,于是,我问:“你说你到底做这些饽饽干什么?”
妈妈没直答,说:“妈妈以后一定给你做饽饽吃。”妈妈说着揪起块破布擦了擦手,蹲下去搂着小草抹起了泪。
我说:“我知道你给谁做饽饽,你一定是给小先生做的。”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来了。这几天让我费尽脑子也想不起来的一个疑问终于被我想清了。我一把夺过小草手里刚蒸熟的小面什,连同我的,一起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我朝小草叫:“你不要给小先生做侍女了。”
我觉得头麻麻的,脸也凉了,浑身突起了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我歇斯底里地叫起来:“这是一个阴谋!”
我终于把这个疑问想清了。我觉得好多问题都明白了。我知道这些天为什么梦到火色鸟了,它一定是奉了上帝的旨意来告诉我这个阴谋。它只告诉我一个傻子,它知道那些不傻的人其实不可靠。可这几天我再没有梦到火色鸟,我想,有很多事情的征兆,往往在事情发生的那一刻,反而又都不明显了。这是规律上的一个表现。我要制止这个阴谋,不然,就来不及了。
整整一个傍晚,我一直在琢磨着这样一个问题。
我知道一个人要计划成功一件事首先要冷静,于是,晚饭的时候我强制着把自己的焦躁压下去,故意装出了一幅咧着嘴流涎水的傻相麻痹他们。晚饭后,趁着爸爸在呲牙咧嘴地让妈妈给他往破头上换灰布条,我拽了拽小草的衣后襟把她叫出去。
我严肃地对小草说:“你不要给小先生做侍女了,这是一个阴谋。”
小草把下午那个小面什又捡回来了,拿在手里,玩着,说:“哥,你知道小先生是谁了?”
我说:“小先生就是小神仙。”我想告诉小草小先生并不只是一个跳大神的人,听说他唱神的时候对扮做侍女的小女孩都要脱光衣裳去附身,有好几个做过圣女的小女孩已经不明不白地死了。我知道小草听不懂,就说:“你要是去的话,你肯定就没命了。”
小草听了我的话,全身哆嗦了一下,我拉着小草拼命跑起来。我一边跑着,一边继续吓唬,说,今天晚上你要是再不逃出来,你明天肯定也就没命了。我们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只觉得甩过去的风响得像耳朵里钻进一只抖着翅膀的大头峰。我们起初好像听到爸爸扯着嗓子骂了几声,但很快听不见了。我拉着小草朝山上跑。后来,我们实在跑不动了,这才停了下来。“我们跑哪儿了?”小草一腚坐下去,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也喘着气,说:“我们上山了。”我说着,向四周看了看,黑魆魆的啥也看不清楚,远得跟天边一样的村子隐隐约约亮着灯,像天上散落下来的几颗星星。
我们找了块凹陷的地方坐下来。小草手里的小面什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系在头上的花也跑丢了。她跑上凹顶找了找,又佝偻着身子回来了。小草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她说:“哥,我怕。”
我说:“不怕,有我呢。”说实话,我才不怕呢。现在天黑了没有人,没有人的天再黑也比不上人的阴谋黑。我说着,把小草搂到怀里。我觉得小草的身子也在不停地颤抖。我们就这样坐着,一会儿看天上的星星,一会儿听山蚂蚱伸懒腰时抖腿展翅发出来声音。我们被这些美妙的景象熏醉了,小草的身子也不颤抖了。后来,我们骂二疙瘩把我们家门口的进出道霸占了,也得意地庆幸自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我疑问那些请小先生问神的人,他们比我还傻。他们明明知道要死人,却又要不顾命地去请小先生问神。他们肯定遇到人活着比付出死还要难受的事情了。这个疑问,我没有跟小草说。我们又想起火色鸟了,小草说:“哥,今晚要是我也能梦到火色鸟就好了。”
我说:“我们是火色鸟救出来的,它就在我们周围。”
我说着,看了小草一眼,她的眼睛亮亮的。我仰起脸向上看了看,上面无边无际,密密麻麻地开满了一辈子都数不清的星花。
后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不知不觉睡着了。是小草先睡的。我不敢睡。我现在害怕梦到那只火色鸟了。它来了,就证明我们的计划失败了,他们的阴谋又得逞了。本来小草问我的时候我就想这样说,可我一动脑子就安慰了她。后来,我挺不住,也困了。它真的就来了。它依然那样,通体赤红,浑身燃烧,像个绅士一样抖着一条竖起来的尾巴,焦躁地围着我们不停地转着,瞪着豌豆一样大的绿眼睛,啊啊地叫着。它肯定是看到我们刚才拼了命地逃跑,扇着翅膀跟来了。它不放心,跟着保护我们来了。我尽量朝着吉利的方面想,挥着手,跟它招呼,说,我把他们的阴谋止住了,我们的计划成功了。我要它不要急了,正要说些好听的话取悦它,可它突然疯了一样抖着嘴上来啄我。我推挡着,躲闪着,最后,我被它的不可理喻激怒了,喝斥着,滚开!你滚开!我不想见到你!我骂它是一个不祥的东西,捡起石子开始掷它。它掀着翅膀,腾跳着。终于,它也被我的粗暴激怒了,精瘦的身子一抖,翅膀一展,扑上来狠狠地啄了我一口。跟着,我听到半空里霹雷似地响起了一声吼:“妈个巴子你再跑!”
我“啊”地一声,醒了。
三
他们的阴谋果然得逞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们的行动就开始了。爸爸怕被人家看见笑话,早早就把独轮车准备好了,还铺上了块破毯子,硬拖着把小草绑上了。小草就穿着那身绿衣裳,头上还系着花,脸上抹满了妈妈用来涂饽饽的红颜色,挣扎着,哭叫着:“我不去!我不去!”妈妈蓬着乱发,也哭。这时候,小草的嘴就被爸爸堵上了。他们就这样,独轮车上一边绑着小草,一边绑着妈妈昨天做的大饽饽,乘着暗色急急忙忙推走了。那天他们送小草的时候我没看到,但当时的情景肯定就这样。当时小草肯定也哭着叫我救命了,她肯定哭着,叫:“哥,哥,你快来救我。”可是,我帮不上忙。我怎么了?我不知道。我迷迷糊糊的,一点儿劲儿也使不上。我又看到那只火色鸟了。它通体赤红,浑身燃烧,像个绅士一样抖着一条竖起来的尾巴,焦急地围着我转着。它没有因为我昨晚冥顽不化就不再管我。它瞪着豌豆一样大的绿眼睛啊啊叫着,用整个身体扑上来撞我。它要用死来撞醒我,可我一点反应也没有,就像死了一样一动也不动。后来,我还是被它撞醒了。
“我在哪?”
我问了自己一句。我不知道。我迷迷糊糊地,觉得天好像已经大亮。身上很疼,动了动,我的手被反绑着了。跟着,闻到了一股恶臭,我的感觉就在这个时候被激活了,我的头胀得快要裂开,鼻子里疼得要命,嗓子也火辣辣的。我张了张嘴,嗓子疼得说不出话,却听到谁在哼哼,接着,身上又被生硬地踩了一下。我一睁眼,看到瘦花猪正烦躁地向我蹶着一个后腚,一恶心,蹭着石墙爬起来。
我想起来了,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了。昨天晚上,我不知好歹地跟火色鸟较劲的时候,它狠狠地啄了我一口。我被爸爸踹了一脚,醒了,跟着听到半空里霹雷似的响起一声吼,惊恐间,又看到灯影里支着两张熟悉的脸……他们的阴谋又得逞了。是小草跑丢的头花和小面什帮了他们的忙。他们把我抓回来绑了一宿,我也吼了一宿。天蒙蒙亮,爸爸狞狰着脸,气汹汹地抓着棍子来到我跟前,说:
“你说你还叫不叫!”
我的嗓子烂了。我瞪着眼,盯着他昨晚刚换上灰布条就又沤了血的破头,用带着血丝的声音,含糊不清地吼:“这是一个阴谋!”
爸爸火了,劈头盖脸地就抽起来。他边抽着,边嗷嗷地叫着:“傻子!你这个傻子!我今天要除掉你这个傻子!”
我是一头傻驴,爸爸越是抽打,我越要挣扎,越要吼。这时候,妈妈蓬着乱发扑上来要夺棍子。她肿着眼,哭着,抓扯着爸爸,尖叫着朝他吼:“这日子我也不过了!”“你去死吧!”爸爸狠狠地扇了她一掌,一抡胳膊又抽了一棍子。她一捂脸,哭着跑了。爸爸把我提溜起来扔进猪圈,我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全都想起来了。
我蹭着石墙向外看了看,院子里空得好像死过人。
“小草死了。小草死了。”我呜噜着,挣扎着身体要爬出去,跳了跳,眼前一黑,又昏了。
我又醒过来了。我在哪儿?我又这样问自己。我觉得自己真傻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反反复复总是搞不清楚。我迷迷糊糊地,好像刚才又梦到那只火色鸟了,它垂着头,哈着眼,一副丧尽气的样子。我嗅了嗅,那股恶臭没有那么浓了,可有种声音搅得我头还胀。我听了听,好像有人在哭。不错,是小草在哭。我一愣,坐了起来。
我看到小草在里间妈啊哥啊地哭。
我用吐着血丝的声音,呜噜着,说:“你怎么回来啦?你没死啊?”
小草穿着绿衣裳,头上的花又不见了,她涕啊泪啊的淌花了脸,哭着说:“哥,妈妈死了。”
我一惊慌忙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跑过去。
天啊,是妈妈,妈妈咋会死了啊。我看到妈妈死挺着躺在炕上,嘴角和鼻子里淌出一股血丝。妈妈蓬乱的头发里绞满水草。她瞪着眼睛,好像看见了恐怖的东西似的盯着顶棚。妈妈在刚才送小草去的路上,闷不出声地一头跳进水库了。妈妈真死了。妈妈在一天也不想多过了的大清早真的不过了。
我呜噜着,也妈啊一声哭了。
我哭着,呜噜着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过了啊?爸爸哭丧着脸,蹲在墙旮旯里狠着劲抽烟。我哭着,又呜噜着问火色鸟,既然上帝派了它来拯救,可妈妈为什么还要不过了啊?我净问一些傻问题。我模糊间看到它又来了。它跳上炕展开翅膀,妈妈笑着从炕上坐起来,轻盈地坐在了上面。它翅膀一扇,托起妈妈飞走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几十年了,我想像这样奇怪的异物已经不需要再来拯救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