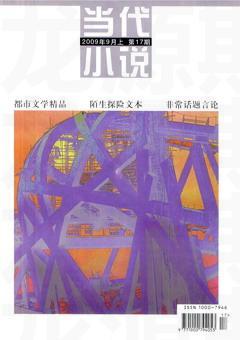流落到丰浦(短篇)
何 也
一
“我老家丰浦电视台招聘男主播已经半年了,一直没人应聘,我觉得阿猛哥你真的很合适。”
说这话的是和廖阿猛只有一面之交的丰浦姑娘瑶婷。听瑶婷说话的口气,电视台台长不是她哥哥就是她表叔。刚好瑶婷要回丰浦结婚,廖阿猛便有点稀里糊涂地跟着她来了。
等赶到丰浦才知道,电视台男主播已经上班五个月了。当时的瑶婷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做了天底下最傻最蠢的一件事。通讯如此发达的21世纪,要打听核实并非难事,但她却冒失地把廖阿猛给带来了。
大概要和瑶婷结婚的男人是她的理想人选吧,所以她这时候的为难和尴尬就全都写在脸上了。由于她不负责任的一个自以为是,把廖阿猛带到丰浦,结果希望落空。她好心办了坏事。廖阿猛转眼间便成了她随时准备甩手的包袱。
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基本上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
这情景岂是廖阿猛愿意看到的。也怪自己太轻信,按说他这个70后的老男,凡事总抱着碰运气的想法,这样的结果可算是自找的。
从电视台出来。走了八九百米,也就到丰浦廊桥了。
周遭是滚滚热浪,可一站在古色古香的廊桥上,午后的风似乎是裹着水雾的,一下就把你凉透了。望着桥下摇晃着满满当当的绿波,居然使廖阿猛的情绪从严酷的现实中摆脱出不少。
“瑶婷,别让你父母等急了,赶快回家去吧。我随便找个落脚点,打短工挣点路费,过几天我就离开丰浦走人了。”
大概瑶婷正需要廖阿猛有个态度,所以听他这么一说,跟他握一下手就顾自走了。
望着瑶婷匆匆离去的背影,廖阿猛的心比廊桥上吹的风还要凉。他被她一个善意的由头,便懵懵懂懂地流落到地生人不熟的异乡来了。
不过的确有点奇怪,站在这廊桥上,廖阿猛的心情转眼就又从迫在眉睫的食宿问题上摆脱出来。环顾廊桥周遭的景致,如果人有个前世,他的前世大概来过此地,否则的话为什么会感到似曾相识?置身于此。怎么会一颗心神神道道的就像在梦幻之中?
桥头砌了两米见方一面粉壁,绘的是以廊桥为中心的景区示意图。东头矗立着丰浦的标志性建筑——旋转楼,旋转楼后是县城新区。西边是一株百年老榕,要进入一片老街区的哨唇口,沿伏壶河西岸的一溜河房街,以及河房街吊脚楼下的十九渡。桥下是伏壶河,流到百米外与花溪汇合,然后流激浪涌飞波溅沫地向东流去。合流处的正前方就是高佬洲——高佬洲上的木房子、点缀其间的小洋房和金碧辉煌的姜太公庙。
廖阿猛以为自己至少在梦中来过此地。站在廊桥上,他或多或少给自己虚构了前世今生的某种牵连与慨叹。
高中毕业后廖阿猛在外漂泊多年,每到一处他都感触良多,但都没有丰浦这个地方的特别。这个地方似乎要把他带进说不清道不明的过去。
二
廖阿猛站在廊桥上痴痴地呆了十几二十分钟,瑶婷的弟弟给他打来了电话。
瑶婷匆匆离去,但她心里并没有放下和她结伴而来的一个异乡男子。刚才望着她离去的背影时,看来他廖阿猛是误解她了。
在瑶婷弟弟杏生的帮助下,廖阿猛在废弃的怡红公园里以每月百元租了一个单间。杏生临走时,塞给他一个装有300元钱的信封——“我姐姐说,以前跟你借的钱先还一部分,其余的你需要时再送过来。”
瑶婷何曾向他借过钱?这个善良的姑娘为了帮他廖阿猛竟用了这样狡黠的心思!
本来,300元钱足够廖阿猛离开丰浦。可房子已经租下来。还有——恰恰因为这300元钱,让他觉得不该一走了之,在这世上,他先是由西漂向北,又由北一步步往东南方向漂,感到要找个落足或归宿之地,谈何容易。既如此,又何妨在丰浦这个地方住一阵子?
三
杏生走后房东说:“前面租房的也是一个后生,退房才两天。由于离开匆促,日常物件来不及带走——你只要不嫌弃,便都是用得上的。”
廖阿猛自是巴不得,应承着暗暗叫好。此刻提箱里除了一台手提电脑、一面床单和替换衣服,他几乎一无所有。廖阿猛跟房东签了合约,接过院门和房门的钥匙,房东便离开了。杏生塞给廖阿猛——他姐姐的“还款”后,也离开了。
看得出,怡红公园至少有一半建在冲积地之上。在高佬洲西南方向的斜对面,中间隔着那条花溪。
公园被废弃。怕是由于低洼地势,每年都要频繁遭受洪水肆扰的缘故。地面上沉积着从上游冲刷下来的废脏物,久不清理又杂草丛生,无形中增添了岁月的破败与荒芜。倒是十多株高大的相思树长得郁郁葱葱的,几乎把整座公园覆盖了。
廖阿猛租住的房间,建在背朝花溪的围墙上。支撑一排五个房间的,是石围墙和靠前的六根水泥柱子。房东为了安全或独立,给这排鸟笼般的房子砌了简陋的院墙。院子的铁栅门可以伸出手去倒锁院门。上完楼梯便是走廊,第一个房间充当公共卫生间和盥洗室。
廖阿猛租住的是最东头的房间。
房间里的床铺桌椅、脸盆提桶虽然凌乱倒还干净。多年谋生在外,见了各色人等,所以一眼便看出退房刚走的肯定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后生(丰浦人把小伙子称作后生),因为房间里没有残留一星半点暮沉老者或病人的恹恹之气。
往后窗一望,花溪与伏壶河的合流,以及高佬洲均近在眼前。廖阿猛设想一下,这座废弃公园应该在廊桥的西南方向上。
四
廖阿猛将就睡了一夜,隔天醒来到街上吃了早餐,谋生一事更觉茫然,于是决定给租房作一次彻底的打扫,把免费得来的“家当”重新摆设一番。
清理中,廖阿猛竟意外从铺盖中抖出长达7页的一封信。信是男孩写给女孩的,要么写完后便被大意裹进铺盖,还自以为找不到了;要么觉得没有必要寄出这封信了,便随手一丢不了了之。
收信的女孩叫亚丽,写信的男孩叫丁缅。电话、短信、伊妹儿、QQ,当代通讯如此便利,这个叫丁缅的男孩竟有难得的耐心写这封长信。
男孩的口气亲昵而深情。这封信写了他俩相识相亲相爱的动人点滴,而核心内容是丁缅决定要不告而别,至于什么原因他没有写明。信到最后丁缅说:“亲爱的亚丽,你我从相识到恋爱,时间不长,可你我的深情绝非海枯石烂可以比拟!情深爱切中,总使我在睡梦里呼喊着你的名字——亚丽!可现实却容不下你我这样的爱!为了避免在分别时肝肠寸断,我决定不告而别!亚丽,别恨我的辜负,为了我们的爱,你一定要好好珍重!你赐予我的无限美好,若有来生,我情愿当牛做马报答你!”
廖阿猛读完信,难免叹息一番。
这封信没有寄出去。但男孩离开了。女孩还不知道她爱着的男孩为什么会突然的一天就不告而别了。
当然他俩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告知对方。比如发一次短信。
从信中的那股火热劲看,这对深深相爱的男孩女孩,肯定属于80后一代人。
看起来还不错,廖阿猛蜗居一隅,偏僻而又荒凉,可心中、跟前却拥有一
个小小的世界。关于自己,也关乎他人。
五
丰浦县城是个人口不足10万的小山城。要不是亲历、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里的形胜会如此震撼廖阿猛的内心。丰浦的交通和通讯与各地一样四通八达。但这里的外来工极少,在街上走的基本上是熟头熟脸的本地人,说的也是当地方言。用工的廉价让廖阿猛这个多少怀揣着发财梦的外乡人倒吸了一口气。
难怪房租那么便宜,即使花极少一点钱也可以在路边小摊饱餐一顿当地小吃。
好你个瑶婷,竟把堂堂的廖阿猛诱到丰浦修心养性来了!
几天了,廖阿猛知道希望渺茫,但也没有停止在丰浦的大街小巷转来转去,样子像一个调研民俗的工作者。
这天下午廖阿猛百无聊赖的,出公园朝南走去——那儿有一座通往高佬洲的石拱桥。这座桥建的年头不长。桥头勒碑称:花溪桥,建于惠心桥原址之上。60年前,匪首谢山河控制了丰浦及邻近数十个乡镇,立高佬洲为大本营,为阻绝交通捣毁惠心桥。今获政府批准,由姜太公庙众香客集资得以复建。改称花溪桥。
高佬洲是一座三面临水的小山冈。不临水的西北向是陡峭的山崖。
廖阿猛穿梭于高佬洲破败的木房子之间,时而望一眼对面的木制廊桥,旋转楼:时而望一眼斜对面废弃的怡红公园,以及他租住的那个房间和那面小窗。廖阿猛跟一个中年男子打听说:“60年前匪首谢山河捣毁惠心桥这个通道,那么,进出高佬洲怎么办?”中年男子说:“谢山河建了一溜河房街,每间河房的吊脚楼下都是一个渡口,共十九渡,外人要上高佬洲只能通过搭渡,为了控制和收费,艄公都是武艺出众的谢山河手下。”
引起廖阿猛对高佬洲好奇的是那座姜太公庙。他通过住处的小窗望见,这座姜太公庙并没有什么特别,香客也不过断断续续三三两两,但它却彻夜亮着灯,彻夜有香客前来烧香上供或求签问圣。进来一见也与别处无异。不同的是这儿没人叫卖香纸烛,香客也相当随便,有的上供还愿,有的只烧香点烛,有的不过来庙里逛一逛。年轻人则干脆不烧香不上供,仅折腿跪在蒲团上磕个头便抽签去了。姜太公庙的签牌是72片,72片的签牌不用说配72首签诗。签诗贴在墙上,庙祝免费解签。
这儿是除了个别深山荒庙外惟一没有商业运作的一座庙,不由得让人顿生好感。
廖阿猛也是年轻人,所以只折腿跪在蒲团上磕了一个头,掷了珓,见是阴阳卦,便摇签筒去了。他抽到的是22签,签诗云:
客自云游朝夕至,
青山着意绿水流。
惊心入梦原非此,
因了前缘此间来。
廖阿猛蓦地一惊,不禁对座上被香烟熏得乌黑发亮的姜子牙塑像肃然恭敬起来。至少,这签应了他来丰浦时那种奠名其妙的心境。
廖阿猛跟庙祝打听说:“这签诗随意而灵动,不同于各地签诗的晦涩和引经据典,不知这签诗可有特别的出处?”庙祝说:“姜太公庙原本有一套签诗。此刻用的签诗出自曾经占据高佬洲的匪首谢山河之手。”
又是那个匪首谢山河!
廖阿猛说:“可不敢小看这个匪首谢山河了,连神明都采用了他的诗作!”庙祝说:“匪首谢山河恶贯满盈的,最终被县宪兵队和警察大队合围射杀在高佬洲上。由于这个缘故,几十年来一直想换上原本的签诗,只是奇怪得很,每次正珓证愿,姜太公都不予通过。”
六
有一次约了三两朋友去游玩某处形胜,结果观感大不相同。廖阿猛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那些差别。此刻他对丰浦的讶异,却不知道给予别人的是什么样的心境。
傍晚廖阿猛离开高佬洲,到街上吃一碗当地称作“米筛目”的小吃。它其实就是长盈寸、筷子粗的粳条。只是当它加上少许油炸葱花、白米醋、芹菜末和辣酱。其滋味便令人刮目相看了。这种好感,就像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
回到租房已是掌灯时分。
打开门亮了灯,看见有人从门下塞进一封信。空白信封,也没有封口。由于有前面的“悬念”,廖阿猛便迫不及待打开看了。
——这封信果然是那个亚丽姑娘写给丁缅的。
丁缅:不知何故你就是不想见我,难道你为了和我中断联系才换手机号码的吗?我前天来过,打开院门进来了,可你把房锁换了!——我不明白,你何至于要如此决绝,门也不让进了?
我知道今天也肯定见不到你,看了这封信,你一定要给我打个电话,在此前我们已经到了分不清你我的关系了。为何没有半点前兆你便音讯全无,如同从人间蒸发了一样?试问,你为何要让我如此痛心?我太可怜了,居然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出错,我想只有见面才能解决问题——丁缅,就算我求你了!
廖阿猛躺在被石围墙和水泥柱子撑起的房间里,看了这封信,设想这对恋爱男女的情形,可出现在脑海里的画面却是形单影只的瑶婷。廖阿猛吓了一跳,也不知道瑶婷此刻在哪里,到底婚结得怎么样了。
七
县城不大,但廖阿猛必须打瑶婷或她弟弟杏生的手机才能知道她的住址。
瑶婷是回家结婚的,在这期间冒昧出现一个外乡男子,理智告诉廖阿猛这个电话他无论如何打不得,
廖阿猛乘电梯上了旋转楼,买了3元一杯茶,坐在观景茶座上缓缓旋转两周,看了丰浦县城的全景,然后下楼去十九渡。在他差不多要失望时,才由一个农具店的胖女人拉开梯口的吊门,让他走下磴道。廖阿猛坐在水面那一级磴道上,此刻河房街吊脚楼下停靠小船的十九个渡口,既没有艄公也没有小船。只有裹着水雾的风,满满当当的水,还有廊桥下由花岗岩条石砌起的桥墩。
廖阿猛对胖女人经营传统农具深感不解。一打听才明白,原来是为了增强景点的可看性,十九渡上的十九家店铺基本上按照70年前的样子布置店面,政府发给相应补贴,生意是可做可不做的。难怪从旋转楼到十九渡,让他感觉就像从当代走回解放前。廖阿猛对胖女人说,要是他来经营她这家店面,他会去订制一批微型的传统农家器具供游客选购,把微型的农家具当工艺品卖给顾客,肯定是抢手生意。店主一时间有点懵然。大概是胖女人正在权衡,如果她把生意做好了,政府不予补贴了,她到底是得还是失。
过后廖阿猛才知道,在他去旋转楼和十九渡的时段,前后有两个人来叫过租房的门。
八
胖女人能在废弃公园的租房找到廖阿猛,要么说明县城小,要么说明胖女人不一般。胖女人叫邢秀秀(她的名字和身材是两码事:互通姓名后廖阿猛便称她秀姐)。秀姐采纳了他的建议,同时要聘廖阿猛当她的店员,包吃。月薪600元。末了她说:“等生意做红火了,再给你加薪。”
如果廖阿猛在上海或广州。月薪的起点应该是5000元。可他此刻在丰浦,他敢说秀姐的农具店一个月的营业额也不超过几千元。要不是政府给予补贴,她怕连房租也付不起。
廖阿猛到河房街的农具店上班的第二天,秀姐便进山去订制微型农家具了。他再三交代。微型农家具只是型
号变小,制作材料不变,更不能减少其中任何一道工序,以保证其可用的真实性。比如水车,同样能车水;比如扬风机。同样能扬谷子之类。
三天后从深山出来的秀姐背着一个大包,打开一看,有犁、耙、扬风机,古式床、碗橱等十几种式样,基本符合要求。廖阿猛挑出耙和扬风机说:“这两件做得最靠谱。”
“这两件是我小姨丈和表弟的手艺。”秀姐说,“这父子俩的手艺那叫精,只要看一眼。没有不能做的!可如今丰浦的百姓基本不种五谷,改种水果了,农耕路打得像蜘蛛网。农具只要锄头、喷雾器和摩托车;做家具用预制板。只要一把铁锤、一副小电锯、一包钉子就成,父子俩憋着好手艺用不上,也不知道有多失落!”
廖阿猛建议把父子俩请出山来专门制作微型农家具,提供场所,包吃住,按件付酬。秀姐也觉得可行,但必须看看销路再作决定。
廖阿猛动手将原有的大件农具挪后。把玻璃柜台置前,朝外贴了名称:微缩农家具展销专柜:在墙上挂出这样一道广告语:微缩农家具,装饰当代居家新选择。
九
下班后,廖阿猛回到租房过夜。
廖阿猛本以为,与租房并排的另三个房间是搁空的,实际上是时不时地就有人人住,流动性较大,又不便打听他们是日租月租还是季租年租,所以见到的大都是生面孔。由于偏僻和简陋,租住的也差不多都是男性。所以这一天见隔壁房间有个姑娘出入,不免深感新鲜。这姑娘与别的邻居不同,一见廖阿猛回来她就过来敲门了。门刚开个缝,便听见她叫道:
“丁缅,我终于等到你了!”
一听这话廖阿猛已明白站门外的是亚丽姑娘了。可以想象的是,当她看见露面的是廖阿猛时,亚丽姑娘的神色就像是熊熊火焰被盖头浇了一盆冷水,在错愕间熄灭了,连表示一下歉意都没有,便回她的房间去了。
廖阿猛思量片刻,于是去敲隔壁房间的门。亚丽开门后。他直接把前后两封信一并递给她:说:“丁缅写给你的信,是我在整理房间时发现的,另一封是你写给丁缅的,正好物归原主。”廖阿猛接着解释说,“房间我租住半个多月了。我估计房锁是房东换的吧,与丁缅无关。他已经离开20天了。”
看得出亚丽急于要看丁缅写给她的信。摩阿猛不便打扰,于是回自己的房间。因为那两封信,所以亚丽一出现,廖阿猛便觉得自己好像也参与了他俩之间的一部分。这也就罢了,此刻的廖阿猛,还坐立难安,这就有点多管闲事的味道了。
目光透过后窗,望着高佬洲上的点点灯光,灯光下姜太公庙零星进出的香客:望着黑黝蹦的河面浪涌鱼鳞似的闪光,或以浮云相映衬时的一片醭白。仿佛听一次动人心弦的老歌,望着天地间的这种深邃与魅惑,他内心的温湿感觉就又铺陈开来了。
前天廖阿猛要离开高佬洲时,庙祝告诉他说,匪首谢山河被击毙时,手中就握着他在姜太公庙求到的一首签诗。这首5号签诗,当然也出自谢山河之手:
溪雨潺潺,
亦真亦幻。
雾柳邀弧光,
惊雷猛浪碾红尘。
在廖阿猛看来,这个无恶不作的匪首谢山河,他穷凶极恶的同时也挣扎于自己的内心,躲在高佬洲上某个枯寂的角落,凝望眼前的闪电雷鸣或凄风冷雨,生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从何而至的感叹。
说不定徘徊于丰浦廊桥这个三角地带的人,无一例外都会有某种宿命感吧?
不出廖阿猛所料,亚丽姑娘看完信便来到他房间。她请求廖阿猛原原本本复述一遍发现丁缅那封信的经过。廖阿猛如实奉告。大概亚丽姑娘相当熟悉房间里的这些物件与摆设,她眼睛里闪着泪光说:“我明天就到丁缅的老家找他去。”廖阿猛说:“本来我觉得丁缅应该会回来取走这些物件的。”
“不会的,”亚丽说,“丁缅是办了退房后离开的。这些物件大都是我给他添置的,我知道他在担心着什么,这些物件他干脆不要了,以免赌物恩人。”廖阿猛同:“亚丽你过后还回来吗——回来搬走这些物件?”
“隔壁房间的租期是一个月,我无论如何都要回租房一趟。”亚丽点头说,“但我不想取走这些物件,你有用处,我反而会心安一些。”
亚丽完完全全是一个南国姑娘,委婉而坚强,对爱情的执着使她的容貌变得生动起来。
十
秀姐静静等待着,不做声。但廖阿猛能感觉得到她的焦虑。
微型农家具的生意出现曙光,是这一天丰浦廊桥景区来了一支旅游团,逛河房街十九渡时他们看到这个小小的玻璃柜台,十几件微型农家具被一扫而光,甚至有几个游客留下款项和地址要求邮购。秀姐当下决定要把小姨丈和表弟请出山来专业制作。
(许多天后廖阿猛才知道,这个不起眼的秀姐居然是丰浦一个地产大亨的老婆。很显然这对夫妻的关系只是一种维持,秀姐的丈夫在沿海几座城市都经营有房地产,可她看起来连温饱都成问题。惊悉之时,让廖阿猛再次对丰浦这个地方感到不可理喻。)
秀姐二度进山后,廖阿猛接到瑶婷弟弟的电话。杏生很快便在农具店找到他。
回丰浦的瑶婷在结婚的那一天,在喜气洋洋的场合,男方以瑶婷“早已与他人私订终身”为由当众悔婚。瑶婷被击蒙了,当即说起胡话来,连亲戚朋友她也不认识了。授男方以把柄的还有,瑶婷意识模糊后,念叨最多的竟是“阿猛哥”这几个字。除了杏生,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阿猛哥是谁。而在瑶婷清醒时,就要求弟弟杏生必须为她带回丰浦的廖阿猛守口如瓶。所以杏生犹豫了好几天,一直不敢造次前来找廖阿猛,
听了这个意外的消息廖阿猛吓坏了。竟不知如何是好。廖阿猛和瑶婷连深交也谈不上,怎么疯了之后心中只有阿猛哥这几个字?
杏生要廖阿猛去看望一次他姐姐。廖阿猛二话不说关了店门便跟他走。
说来奇怪,瑶婷的家和租房、农具店不过咫尺之遥,廖阿猛也多次走过扶柳巷。却不曾与瑶婷碰过面。
扶柳巷是从哨唇口走进旧城区的小巷之一。无论过去如何,眼下的旧城区总是显得那样的晦气与忧郁。杏生安排了一个他父母都不在家的时间,让廖阿猛去探望他姐姐。但廖阿猛不知道自己是否来对了。那个阴暗的家是土木两层楼,很静也很闷,瑶婷自个羞怯地坐在那儿——她连自己不停念叨的阿猛哥也不认得了,杏生对瑶婷说:“姐姐,阿猛哥看你来了。”瑶婷自始至终都没有抬起目光,说:“这个阿猛哥是假的。”杏生失望至极说:“我姐姐已经这样子了,阿猛哥你不要见怪才好。”
廖阿猛鼓励杏生说:“姐姐会没事的,我们一起努力!”
经营时间关店门是做买卖的大忌,所以十几分钟后廖阿猛不得不离开扶柳巷。回到河房街的农具店。
十一
秀姐果然把小姨丈和表弟请出山来,租了一栋闲房当父子俩的制作车间。
已经没有自觉意识的瑶婷,居然会在谁也没有觉察的情况下,不声不响摸到河房街的农具店。她不像是来找他廖阿猛的,因为她已经不记得廖阿猛了。可她长时间不做声,在农具店
站或坐着,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临结婚那天被男方弃绝,经受不住打击的瑶婷疯了,几天时间便在这个山区县城传得沸沸扬扬。瑶婷失常后出现在口中的那个“男朋友”,也就是河房街农具店那个外乡人廖阿猛。秀姐仿佛要从瑶婷的脸上找出点什么,问道:“扶柳巷的瑶婷被男方悔婚,真的与你有关?”廖阿猛只好据实以告。听了来龙去脉,秀姐叹息说:“谁说不是孽障男女。”
由于议论与传闻,河房街农具店的生意反倒红火了不少。
几天里发生的事,似乎拉近了廖阿猛与丰浦之间的距离。
夜里廖阿猛回到租房,见隔壁亚丽的房间灯亮着。年纪轻轻的亚丽神色迷茫。她离开县城找到乡下。才知道丁缅并没有回老家。她此行了解到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原来丁家有遗传性心脏病,发病前个个身强力壮,但到了三十岁后的某天,一发病便意味着死亡。丁缅的爷爷、父亲、大哥都没有逃过这个定数。亚丽终于明白了丁缅的良苦用心。丁缅是为了不想连累她,选择在她面前黯然消失。
廖阿猛问亚丽以后怎么办,亚丽满脸是泪说:“无论如何我都想再见丁缅一面。”
十二
在廖阿猛迷迷糊糊的睡意之中,几次出现亚丽那张满是泪水的脸庞,接着又被一阵叫喊声惊醒了。
“好姐姐,黑灯瞎火的,你怎么可以睡到这里来!”在楼下院子外叫喊的,是杏生的声音。廖阿猛直奔下楼,见瑶婷当真是背靠铁栅门睡的,任凭弟弟杏生的叫喊。她都无动于衷。“阿猛哥,我都拿姐姐没办法了。”廖阿猛打开院门对杏生说:“这地里又脏又乱的,先把你姐姐哄到我房间再想办法。”瑶婷身上裹的似乎是一团没有警觉的困意,被一前一后推着拉着上了租房,如同回到家里,见了床铺便一骨碌软倒过去,杏生要姐姐坐起来,不想就在这转眼间瑶婷又在睡梦之中。
廖阿猛和杏生只好趴在桌子上瞌睡,一起守这个夜。
瑶婷是不让人理喻的,第二天夜间她又重蹈覆辙,阿猛只好跟隔壁房间的亚丽商量,让她俩睡在一起,他和杏生借睡亚丽的房间。
过后的几个夜,不讲理的瑶婷都是如此,她似乎只有在廖阿猛的租房才能睡得好。
十三
河房街农具店的生意不错,但种类偏少。读过三年美术专业的廖阿猛,决心再设计几款式样。秀姐当然是赞成的。就这样廖阿猛有了几天附近的实地考察。
不用说在这几天里,瑶婷和杏生姐弟俩都伴随左右走遍附近的山山水水。画下的水碓房、过山亭和望江楼等图纸,让秀姐的小姨丈和表弟大开眼界。从父子俩欣喜的目光里。秀姐几乎看到了顾客的激赏。
夜里从河房街的农具店下班,廖阿猛没有直接回租房,而是到秀姐的小姨丈和表弟的制作车间,和父子俩琢磨那几种新的设计。
直到夜深,廖阿猛在街上吃了夜宵,这才朝废弃的怡红公园走去。走到公园内相思树下,只觉跟前蹿出两道黑影,朝面门擂下的一拳砸了他的鼻子,顺势挑起的拳头铲翻了他的腮帮,侧面那个人飞来的一脚踢中他的腋窝,在他跪下瘫地的同时,感到又腥又成的液体哗哗地流了他一脸。
袭击廖阿猛的两个人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廖阿猛滚地的惨叫,惊动了守候在院子外的两个人。
这一天,及时护送廖阿猛到医院救治的是瑶婷、杏生姐弟俩和亚丽姑娘。
在医院耀眼的灯下,见廖阿猛浑身是血的一刹那,瑶婷打了个激灵,掩脸干呕一声,奇迹般地清醒了过来。一时间里,不明白自己为何会置身于这种场合,看一眼廖阿猛,看一眼亚丽姑娘和医生,竟心生虚怯地避开了众人的目光。
廖阿猛使眼色让杏生赶快带姐姐回家。这样,守候在身边的就只有亚丽姑娘了。
十四
由于只是外伤,仅鼻子和腮帮有点肿,翌日一早廖阿猛就出院回租房了。
本来亚丽觉得自己该走了。可廖阿猛受伤了,她决定留下陪廖阿猛几天。
丰浦的炎夏,并没有让人觉得特别地热。只是到了这一天午后,尽管天花板上的吊扇转得飞快,也赶不走租房里的暑气。
因为亚丽在身边,廖亚猛当然不敢短裤背心那样放肆,只寄希望天能下一场大雨。
亚丽也说:“太闷热了,能下一场大雨就好了。”
天遂人愿,挨到午后三点,终于噼噼啪啪地下起雨来了。这场雨和以往不同,起初是零零星星的,后来就又密又猛的了,持续的时间长得就像没个尽头似的。雨天加上廖阿猛行动不很方便,晚餐由亚丽打电话要了外卖。盒饭一送到,越下越来劲的雨就有铺天盖地的味道了。
亚丽说:“这雨要么不下,要么下疯了。”
到了入夜九时,他俩隐隐感到不对劲。廊桥一带亮起了恍若白昼的灯光。望一眼花溪,觉得不过是片刻之闻。花溪里已涨满了洪水。翻滚的白浪似乎就在眼皮底下。廖阿猛说:“河里涨大水了。”
亚丽不放心,开门一看,惊呼道:“天哪,院子被洪水淹没了!”
也许是不在意,在短短的时间里,孤零零的租房已无异于滠浮在洪水之中。
廖阿猛就像在自言自语:“这洪水,没理由涨得这么快。”
没完没了的下雨声,翻滚的洪浪声,廊桥一带嘈杂的喊叫声。似乎与眼皮底下的汪洋连成一片。
两个都是外地人,并不清楚这一天的暴雨是否正常,当地的水灾会厉害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支撑租房的围墙和柱子是否牢固。
“阿猛哥怎么办?我们被洪水包围了,出不去了!”
亚丽说这句话时,声音在微微颤抖。
“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么多的水!”廖阿猛明白自己接着又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
惊恐的两双眼睛,又同时看见有无数活物正从窗口那儿爬进屋来,门缝也是如此,红蚁,黑蚁,掉了翅膀的飞蛾,胖胖的暗青色的爬虫,毛毛虫,探头探脑的老鼠,小青蛇……漂浮于恶浪中的惶惶兽类。为了逃生,纷纷爬向这座洪水中的小屋。
两个人也顾不了许多了,差不多是穷凶极恶地往外驱赶击打了它们,手忙脚乱关严了门窗,连缝隙也用纸张或布条塞紧。
处理结束后,两个人都看见对方在上气接不上下气地喘息,亚丽嘴唇发青,哆嗦得厉害。
“这个时候。你我也太可怜了。”亚丽说,“偏偏像丁缅那样,还要想得很多很多。”
廖阿猛说:“亚丽,隔壁你的房间怕被爬虫们占领了。”
“我想通了,放弃了,不管了。”亚丽看了廖阿猛一眼说,“要是洪水不再涨,明天难道你还不想离开这儿?”
廖阿猛吃惊地望着身量单薄的亚丽姑娘,一时没有言语。
亚丽近过身来,抱住他说:“阿猛哥,要是我们能逃过这场洪水,我愿意随你去天涯海角。”
“别担心,相信我们不会有事的。”也许是共患难的心情吧,见此刻只有身心弱小的亚丽姑娘与自己相伴,在洪水滔天的天地间,廖阿猛发觉被亚丽视为依靠的自己,实际上无足轻重,更是渺小。
周围不是洪水就是异类,两个人也就情难自禁地偎依在一起了。
这是危难中紧紧的依偎,时间好
像是停顿了。亚丽的一双手不知道是急切还是慌乱,总之是身边的这个人被她握住了,放进她的身体里去了。廖阿猛没有想到,风雨和洪水竟促成了这样的“一次预谋”。
看起来雨小了些。但洪水还在涨,灰沉沉的天际依旧逼迫大地。
亚丽说:“阿猛哥,其实我们可以跟杏生或秀姐打个电话。”
对呀,这么长时间,竟没有想到要往外打求救电话!
廖阿猛打了杏生的手机,简要描绘了租房的危急处境。杏生说:“我姐姐对这场雨也很害怕,一直抓住我的手不放。我担心一旦扔下她,她又想不开了怎么办?”
廖阿猛和秀姐通上电话,说:“秀姐,我的住处被洪水包围了,洪水快涨到楼板了。”
那头的秀姐说:“是上游几座破水库怕出险情排水了,没事的,涨也涨了,洪水从来就没有淹没过你住的那座小房子。”
秀姐同样找到了推脱的理由。
扔了手里的手机,这下廖阿猛也就变得得理不饶人了。亚丽说:“瞧阿猛哥你有多凶猛,这房子不被洪水泡垮,也被你摇晃垮了。”
廖阿猛说:“垮了,我们就这样拥抱着,任由洪水送到东海去见龙王好了。”
十五
第二天,洪水退了,太阳又那么好地出来了。
租房底下的废弃公园,是洪水退后留下一片糟塌的烂滩涂。
房东穿高筒雨靴,拉管子接水冲走泥泞。总算把院门打开。上楼后到卫生间洗净雨靴,才来找他的房客:
“二位昨晚吓坏了吧?”
洪水已经退了,廖阿猛感到无话可说。
亚丽说:“岂止吓坏,要是洪水再涨,这房子垮了,命也没了!”
“不会的。”房东说。“我搭建这座房子时,楼板刚好和高佬洲姜太公庙的门口在同一水平上。历史上,再大的洪水也没有淹没过姜太公庙的檐台。”
“昨晚那吓人的情景,可不是体现在说的轻松!”亚丽好像不想轻易放过房东。
“也怪我忘了给你俩留电话号码了,只要说明在先,你俩就用不着担惊受怕了。”房东见怪不怪的。并没有在内心上受到谴责。
房东逐个查看后,廖阿猛要为亚丽清理房间,被房东阻止了。只见房东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硫磺,放在亚丽的房间里点燃后拉上门。房东说:“千万别强行赶它们走,以免留下不必要的脏东西。”
房东临离开时,朝他俩笑了笑。廖阿猛和亚丽当然明白房东的意思。
洪灾之夜,唤醒了人最原始的那种需要。
廖阿猛说:“亚丽,请问你现在还是昨夜的心思吗?”
“阿猛哥,对不起。”亚丽低下头来。
廖阿猛说:“我看得出来,你还想见丁缅一面。”
十六
廖阿猛跟秀姐告了半天假,然后动员亚丽一起去扶柳巷看望瑶婷。
经历了一场劫难,与廖阿猛已显得生分的瑶婷,仅为客人泡了茶便上楼躲开了。
杏生说:“不知道为什么,前天我姐姐见阿猛哥遭打后浑身是血,脑子倒一下子清醒了,可人却变得畏头畏尾地怕事胆小。”
大概坐了十几分钟,他俩便告辞了。廖阿猛到河房街上班,亚丽回租房去了。
“看洪水把你吓的!”见廖阿猛面部浮肿,秀姐,惊讶了一下。
廖阿猛说:“昨晚我住的房间就像漂浮在洪水中,我又不习水性。要是洪水再涨我就没命了。”
“打小开始几十年来,我就没见丰浦城区的水灾死过人。”
“我是外地人,哪晓得丰浦的水灾竟有这种人情味!”
“阿猛你还是跟我小姨丈和表弟住在一起吧。旧城区的房子破旧。可就是用不着担心安全问题。”
“除了发一次洪水,我并不觉得租房有什么不好。”真要放弃废弃公园里的租房。廖阿猛反倒有点不舍了。
因为废弃公园里遍地是糟蹋的烂滩涂,照明又基本荒废,所以廖阿猛天黑前就回租房了。
有个年轻后生在公园门口徘徊,探头探脑地往租房张望。见廖阿猛往公园里走,后生便停下脚步,目光盯住他的背影不放。上了二楼,隔壁房间的门是开的。亚丽坐在那儿阴沉着脸色。
廖阿猛说:“亚丽,公园门口有个后生,我想他八成是找你的吧?”
“随便一个人,与我什么相干!”亚丽的口气有点气急败坏。
看来彼此间已见过面。
廖阿猛说:“前些天我在高佬洲姜太公庙求了一签,且不说它是否灵验,单读那签诗就让我觉得服气了。——说来也许你不相信,这座庙24小时都有人烧香上供求签问圣。我走了大半中国,像姜太公庙这样完全开放的不是惟一也是凤毛麟角。”
廖阿猛接着说:“亚丽你要是想上姜太公庙求一签,我这就陪你去。”
廖阿猛很遗憾。等他俩走出公园,门口的后生早离开了。
看见姜太公庙几对年轻男女进进出出,似乎都是怀揣某种心愿来的。亚丽跪下来摇签筒。她求到的是54签。亚丽持签牌找庙祝去了。墙上第54号的签诗是:
来了去了,
去了来了,
此番光景又如何?
风雨没有事,
流水又兼程。
十七
廖阿猛在河房街做满一个月,领了工资,到扶柳巷还瑶婷300元。剩余的钱,已足够他离开丰浦。
也不知道廖阿猛的下一程要去哪里。
那个亚丽,会随他去天涯海角吗?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