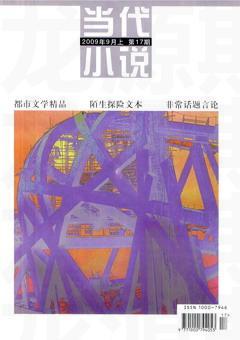冤孽(短篇)
罗锡文
轮船顶着风颠簸着,远远看去就像一只硕大的纸盒。风是从峡谷里横灌而来的,先是沿着江面低低地吼着,一条巨型蟒蛇般,当它一撞上轮船的时候,就猛地抬起头,船便剧烈摇晃起来,船上的男女就一阵阵尖叫。南娃感到船是在浪尖上跳来跳去,然后一个猛子似的落进码头的。他随一群急于下船的人拥到了出口,差点就被摔进江里。船疯牛一样挣扎和号叫之后。终于稳妥地停了下来,南娃随人群跑出船舱时,砂块般的雨点就砸了下来。码头和沿着又陡又长的石级才能看到的新市小镇立即被灰白的雨雾水帘遮蔽。
南娃飞快脱下衣衫,将一直抱在胸前的一包东西裹上,猫身夹胸,一溜儿冲进雨里,几乎是飞着上了石级,像一只落荒的豹子。冲进黑压压的街道,街道两旁黑压压的瓦屋子恍如随时会坍塌下来,眼下除了雨线密织细缝的一片烟外,他没见到一个人。在下四街,街两边的店铺亮着黄晕晕的光,饭馆的门口耷拉着一些杂物。穿过下四街,南娃看见前面一座青砖黑瓦的古老建筑,一只破烂的灯笼,活像一个吊死鬼。南娃终于站在了一家客栈门外,正寻思着可以躲躲雨了,不料从江上猛冲上来的风把漫天雨水横街刮脸地打来。他立即惊吓了,转身进了一家客栈。他在客栈石灰泥的地上刚站稳,一脸还是雨水模糊的时候,便听见一个女子低低的叫声,仿佛雨的深处吞没的一只被主人遗弃的野猫。虽是夏天。但经过这么一阵风雨折腾,南娃有些撑不住,牙齿咯咯磕着。他摊开双臂。左右看看,用力跺跺脚,水从身上流到腿上,被体温弄热了,腿上就有了条条毛绒绒的虫子在爬,酥痒难耐。面前是一个尖脸小嘴巧身的女子,皮肤白嫩嫩的。她好像对眼下这个粗鲁的半裸男人很恼火,比黑瓦还黑的眼睛压得很低。南娃咧开嘴,吃力地笑了笑,将手臂上的水使劲甩了出去,墙上便有了几条水印。像一条硕大的螟蚣。女子眼光越过窗台,盯着南娃的脚,又看看从他身上流下的水打湿的地面。南娃心下说:“这小阿婆怪我没长眼睛哪!”南娃又跺跺脚,鞋子发出呱呱的响声,鞋面上的几块污泥怎么也去不掉,他正欲捡一块瓦片将其刮去,从住宿登记室传来一个男人变腔拿调的声音:“老大,你死了么?有客人来了,你还愣着做啥?”南娃一乐:“一个老太监!”那声音紧接着又从宫廷深处钻了出来:“把客人带过来!老大,你耳朵塞木栓了?”南娃又想:“这杂种是谁?他会生出这个标致的小娘们儿?我呸!”
被叫着老大的女子狠狠地抿抿嘴,南娃想她咬牙齿倒好,别把舌头咬破了,想同那臭老爹吵架都不成呢。女子手一撩,额前鬓边的头发就整齐地往后贴去:“你……住宿吗?我们这儿很干净……”南娃心下说:“我可不干净。”这时,从楼上下来一个小个男子,接过女子的话说:“就住我们这儿吧,我们的客栈,在全新市都是最好的,”南娃站着不动:“这小女儿也是新市最好的哩!”主意打定,南娃就笑了笑,乍见女子瞥了一眼自己,眼珠儿落在他胸前,便低了头,才觉察自己没穿衣服,那胸肉长势极好,在宽宽的胸膛上凸着。他忙在胸上搓着,咯吱咯吱地响,一抬头,女子转身上楼去了。
一只圆实的脑袋从登记室的窗口滚了出来,脸上发光的赘肉褶成了几条线:“小幺哥,要住么?”见南娃不出声。便道,“你过来看看价格,随意选,贵的便宜的都有,包你满意。”话音落下,乍看南娃一脸嬉笑。一身黑肉,不像是有钱人,眉头便皱紧了,“小幺哥想好了?最便宜的是通铺,10元一铺。”他眼珠骨碌了一阵,身子往窗后一缩,“老大的,阎王爷招你了?客人累了,赶快下来招呼。长耳朵投有哇?你要磨死我啊!”
南娃将一张大钞扔在男人面前。
“住单问,还是……?”男人的脸从酱瓜变成了哈密瓜。
“嘿嘿!”南娃捏着下唇,将上唇凸出来,极似兔嘴。
“小幺哥好说,好说!单间!?”
南娃哈哈道:“单间,单间。单间!”弄得男人划破了收据,
南娃踏着嘎嘎响的楼梯上了四楼。两边墙上斑驳破败,口痰鼻涕脚印横行,南娃就想:除了那小娘们儿,都他妈脏,监狱都比这儿好。
晚饭后,暴雨停了。金沙江奔腾咆哮的声音使南娃听着极惬意,一个喊江人像是从云南那边过来的商贩,机动轮船的吼叫像一只老放不完肚中浊气的打屁虫。一弯清淡的月亮从乌黑的云层中滑出来,刚台利屋中的地板上便撤了一层劣质镁粉般亮晃起来。楼下车辆叭叭开过,街上积水扑哧分开,南娃立即就听到一个女人锐声的惨叫,继之又是一声山洪起蛟般的怒骂。南娃心下乐了:“呀,敢在大街上洗泥水澡的女人才是仙女哪!”在闷声中闯荡开去的金沙江和痤座山峰之中,是新市小镇,狭长、黝黑、朴拙,宛若一只梭子,嵌在山水罅隙中。入夜,灯火鬼祟闪着。往常时节欢喜夜游的人照例出来,吃火锅,唱卡拉OK,找上几个熟人没黑没白地聊开去,这梭子就在星月和山水间活灵灵地穿梭着。
女子提着一只绿色水瓶进来时,南娃正摊开四肢想她。衣服和裤子怪怪地晾在屋内的铁丝上,女子的头不慎碰到了。
南娃没有动弹,仍然像山里任何一个粗野放浪的小子一样叉开双腿躺着,腿根处一块大包,昏暗的光线中,挑逗地露在女子眼前。南娃笑着望着女子,手臂绕过脑袋,将其枕着。
女子将一盘蚊香放在桌上,说:“蚊子多。”
南娃本想说“新市的蚊子就是多,你们专养蚊子,成蚊子专业户了。”嘴上却道:“我已经领教了,都快成疙瘩人了。”
“那我替你点上吧。”蚊香点上了,又道,“蚊子,也不是都会咬人的。”女子转了身,却没立即走的意思。
南娃肚中一乐:“就像你这样的母蚊子要咬人的!”却对女子背影道,“不咬你罢了,可所有的蚊子都喜欢叮我。”
女子轻轻一笑。一方月光落到她脚上,脚就像钉在了地板上。
女子说:“蚊子也要看人,才咬的。”
南娃说:“都是母蚊子呢,我一进门,就嗡嗡呜呜地围着我转,它们是在等我哩。”
女子暗中羞了脸,出去了。
南娃有些失望地在床上挺了挺身子,又滚了滚,燥热上得身来,皮肉粘乎乎的,他看到了窗下那方浅浅的月光,一点一点的挪移,但他觉得它们一直都如水印一样印在那儿的,一厘一毫都未曾动过。
南娃侧身面对墙壁。墙上写满了诸路过客歪歪扭扭的留言和尊姓大名。几只脚印让南娃很快推测出是一个短小的胖子和一个精瘦的高个蹭上去的,在几只脚印之间,是一幅女人裸体图,私处被夸张地涂成一团黑,手法拙劣,人体都完全变形,乍看像一个森林妖魔,墙角处横着几条蚂蟥似的干物,南娃定睛一看,看出是鼻涕口痰的遗物,和楼梯处的一样,便恶了心,又将目光停留在留言上。其间有一打油诗,引得南娃念出声来:“我是仙家到此游,游来游去结冤仇。仇家是个烂婆娘,屁股大得如水牛。”
南娃一脚踹去,字迹仍清晰可见。他跳起来,呸呸几口,又踹了一阵,那些字仿佛是镏金的一般,镌在墙上越
发醒目。
当月光从窗边消失,落到街上时,南娃决定在这客栈多住几日。
南娃被一阵打骂声吵醒时,太阳已经离开东边的山头几竿子高了。同阳光叫骂声一同涌进房间的,还有车辆行人鼓噪后的尘灰。
南娃听出那是那猪头男人和女子的声音。南娃跑下楼去,客栈门口站着很多人。
女子站在登记室门口,手放在脸上,正凶凶地哭着。那滚圆男人拿着一根荆条,叫道:“我牙根都吧唧断了,你咋就不长记性?顾客就是我们的爹,我们的妈,得罪不起。可你,看看你都做了啥?我牙腔都磨出血来了,你咋不支起耳朵听个通泰?你还要不要我活了?”
女子头一点一点地哭着。
南娃问身边的人出了什么事。那人撇撇嘴,说早上有个旅客到登记室,要他寄存的行李,女子找遍了所有柜子,连旮旯都找遍了,也没找到那人的东西。这人就大吵大闹,说他的行李中放着大量的钞票和从美姑和雷波购买的银首饰。他对女子说,东西丢了,你们就得赔。女子吓着了。那人抓住女子胳膊,说不赔就得告她。女子突然想起什么,就到了那人的房间,结果在床下找到了他的皮包。原来那人睡昏头了,竟忘记了他的皮包放在哪儿了,女子要他打开皮包点数一下,里面的东西一件不少,只是没有银首饰,一问,他才说还没买。女子一生气,一脚就把那只皮包踢到了门外,一个旅客说了几句刺耳话,女子一盆水泼了去,那人一闪,就泼在刚从外面回来的胖男人身上。
“依我看,应该抽那家伙耳光,揍他一顿。张老板也真是、即使做女儿的使性子,可当老子的也没这种当法,哪能骂男娃娃一样骂女娃娃呢?那是人话吗?落在地上,大象都踩不烂,还打哩,你瞧他那荆棒子,他做老板将心做硬了,打女儿就跟打畜生一样狠,那是打女娃娃的东西吗?”
一个在客栈门口摆烟摊的妇人撇撇嘴,啐了一口:“就像是捡来的,想咋打就咋打,我那摈刀砍脑壳的,打儿子也没这么黑心肠的,”
那男子道:“张老板即使有儿子,怕也被他收拾得像个柿饼的。心黑哪,都黑得发光了,”
烟贩说:“真还没见过张老板这号拿女娃娃出气的男人。”
说话时,客栈老板又将荆棘条抽了过去,空气中响起了身体被抽打时发出的声音。几个人上来劝,被男人一顿骂,便退开了。几个年轻丑陋女子,想是平时与女子有过节,或是妒忌女子那漂亮腰身,但见女子挨打,脸上便绽出歪歪的笑意、撇着嘴在一边顾自看去。
“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了。”男人气咻咻地叫道,“今天不打烂你一块肉。老子就不姓张。”说罢,扬手又一荆条。突然,女子哇的叫了一声,扑上去,抓住了男人的手,叫道:“你打吧,你打吧,你把我打死了你就好过了。我是你生的。你恨我。你下得了手。你就把我打死吧。打死我,打死我就好过了!”女子疯狂地撕扯着男人的衣服。男人先是蒙了,险些被女子突如其来的阵势掼倒在地。但他很快就清醒过来,揪住女子的头发就朝墙上撞去。女子死死抓住男人的衣服,男人脚下一滑,两人就倒在了地上。
“这张老板可是咱新市百里地界内,打灯笼也难找的能人,当年打他婆娘也是这样狠,哪儿当人呐?都说他婆娘那癌症是骨头里长了瘤子,肾也衰了,可依我看哪,他婆娘那一身病,是被他给打出来的,给活活气出来的。婆娘死了,他还装着流猫尿。日他先人的,他婆娘不是被他打死的,我舔他屁眼儿,现在,轮到他亲生女儿。”一个中年男子说。
摆烟摊的妇人说:“他婆娘嫁过来时,多标致哟,可被他弄得,唉!”
一个年轻人说:“有多标致啊?是不是瓜子脸杨柳腰啊?”
妇人白了他一眼:“有多标致?你怕是没见过吧,说给你你也不知道,反正我们这里都说她是头号美人。她死的时候,就剩一个骨头架子了,一身干皮。”
年轻人吐了舌头:“这么造孽哦!”
中年男子说:“这姓张的也是白长了球卵卵,有本事揍男人去,专找女人斗狼,算什么东西?”
年轻人说:“他那样子又狠又恶,以前怕是可以做土匪的。”
妇人说:“当过兵的,逃兵!”
话音刚落,只见女子抓过男人掉在地上的荆条,劈头盖脑地朝男人挥去。
男人被女子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待他反应过来时,头上已被重重击了几下。
南娃推开面前的人,猛地冲上去。抓住女子的手,说:“跟我走!”没等女子说话,两人已经到了大街上。男人跑到客栈门口,正欲谩骂,两个人已经不见了踪影。他干咳了几声,根本没发生什么似的回到顾客登记室,扑打着身上的灰尘。众人各自散去。
“跑得了初一,跑不过十五!”男人喝了口苦丁茶,说道。
一个长期住在客栈,做药材和皮货生意的男人走上前来:“张老弟。你这是何苦呢?闹这么大,大家伙都看见的……那小子是谁?他,怎么,咳咳,他怎么把你女儿拉走了?他是干什么的?唉,何苦嘛!”
男人头也没抬,擦了根火柴,将烟点上。
“何苦呢?老弟。”
男人径自抽烟,不作搭理。
“那小子是谁?”
“是你爹!”男人吼道。生意人一吓,却也装出你这等粗鄙之人,不屑于和你理论的神气,背着手出去了。
南娃拉着女子跑到江边。码头上空空如也,几只铁壳船静静地泊在水湾。
“他真的是你爹?”南娃问。女子没有回答,她正为刚才被那男人抽打而难堪不已,脸上一道道红。南娃继续问道:
“他真的是你爹?”
女子坐在一根木头上,望着江中的漩涡,依旧不出声。
“我要宰了他!”南娃道。
女子抬头看看南娃,又很快低下头去。
南娃恶毒地咒骂了几声,把在水边饮水的几只鸡也给吓跑了。
女子低头哭了起来。
“跟我走!”南娃眼睛盯着江水,说。
女子肩膀微微颤动了一下。
“跟我走!”
“可……我……昨天你到我家客栈住宿,才认识你……”女子脸上的泪水都还挂着。
“那又怎么样?”南娃道,“我可不是你爹。”
“可……”
“你爹还是人么?他简直就是王八,是石头缝隙里炸出来的,没屁股眼儿,你还想跟着他过日子?”
“我还不认识你……不,是,是,还不,…”女子迟疑道,将衣角往下扯了扯。
南娃道:“说那些有什么用?我们不是很熟悉了么?昨天,今天,以后谁还管得了谁先谁后啊?跟我走!”
女子望着港口,一溜去宜宾的人正陆续来到那长长的石级上,说着话,或木然地瞪着江面。航船上已经有人在走动,高声地同岸上的人打着招呼。那面已经有些发白的红旗蔫蔫地耷拉在船的尾部。
女子很久了才说道:
“你叫什么?”
南娃说:“从小家里都叫我南娃,你就也这么叫吧。”
“哦!”
南娃突然想起了什么,便问:“你不是你爹亲生的?”
女子道:“你才不是你爹亲生的哩。”
南娃说:“你爹叫你老大,什么意思?”
“家里我排老大的,爹从来不叫我
名字,说叫来叫去塞牙缝,就叫老大顺口。”
“那你弟妹?”
“有一个弟弟,他死了,就死在金沙江里。你也看见了,爹拿我不上眼,恨到骨头里去了。除了他生来就是那副铁冷的心肠外,他恨我还有几件事,弟弟的死就是其中之一。”
“怎么说?”
“不是说了吗?弟弟的死。”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弟弟死了。”
“怎么说?”
女子咬了咬嘴唇。
“五年前,江里发大水,都快把港口上的防洪大堤都给淹了。弟弟和我就到江边来打捞从上游冲下来的东西。每年夏天,这儿都暴雨不断,暴雨来了,江里就涨水,江水就会从上面冲下来很多东西,木头啊,衣服啊,淹死的牲畜啦,南瓜啊什么的,镇上各家都要到江边来打捞。那天,弟弟和我捞到不少的东西。太阳很毒,连皮都快晒裂了。我累得撑不住了,就躲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就是那边,木材站往上去一点那块像癞蛤蟆的石头,看见了吗?就是那块石头下面,我在那儿躲太阳。弟弟也热得叫,干叫,身上的汗水弄得他像落了水。他把捞来的东西码好,和我打过招呼,就和几个人跑了,说是到西宁河里去洗澡。西宁河你知道吧?就是木材站后面,从吊桥下流到金沙江里的那条河。水可清亮了。如果我是男娃娃,我也会像弟弟一样脱光衣服到河里去的,我都快热得发疯了。等我凉快了,歇息得差不多了,弟弟却还没见回来,那么多东西我一个人可是扛不动的。我爬到石头上,喊弟弟的名字,那帮在凉水里泡着的男人只露出黑乎乎的头,好像听不到我的声音,而岸上几个光溜溜的男人听到我的喊叫,才发现弟弟不见了。我喊:‘是不是回去了?那几个人说没看见,刚才还在的,我又开始热得不行,弟弟又不见了,就很生气。突然一个小孩子尖叫道:‘张二的衣服都还在哪!我跳下去,跑到河滩上一看,果然是弟弟的衣服。我腿一软,站不起来了,完了。弟弟被水冲走了。西宁河在吊桥下面有一块很大的水荡,河水在那里旋转一圈后才流到金沙江。那水荡里的漩涡又多又急,又涨了大水,人看漩涡眼都要发花,弟弟一定是被漩涡给卷走了。我们沿着河滩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弟弟。我害怕极了。那天,爹把我腿都抽烂了,说是我害死弟弟的。爹没说错,我没看好弟弟,我害死了他……”
“也不全怪你!”
“话虽这么说,可弟弟还是不在了,我是做姐姐的,没管住他啊。爹为这事恨我也有他的道理。”
“屁!他哪来的混帐道理?你弟弟又不是你推下水的。”
女子凄然咧嘴一笑:“他找不到出气筒啊。妈妈就是在他气头上顶撞了他几句,他就把她打得几天起不了床。”
“宰了他!”
女子把头别向一边。
“告他也行!”
“告他?我妈都忍了,我又能做什么?况且他是我爹呀!”
“爹又怎么样?照样告他,告不了,就宰了他!”
“我……”
“其他的事,说说吧。”
女子肩膀微微地抖动了一下,眼睛里充满了一股雾水样的东西。此刻,江水平静下去,先前罩在江上的雾霭也稀薄开去,像被匠人摊开的棉絮,轻薄地横在江天之间。几块巨大的木头从上游冲来,在水面一上一下地浮荡着。一只水鸟站在最前面的那棵木头上悠闲地啄着翅膀,随木头一路漂去。
“不想说,就别说吧。”南娃将手中石头扔进江里,“不过,与你爹有关吗?”
女子撩撩头发,然后像清理往事一样用手轻轻地梳理着辫子。
“爹打我,久了,也就习惯了,我也认命了,那有什么法子呢?天生成的就是这命,就这样吧。”停顿了片刻,她叹了口气,“唉!”
南娃望着江对面的村子,想那边就是云南了,耳朵却专一地搜集着女子的声音。
“那个人是谁呢?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女子道。
南娃头也不回:“哪个人?什么那个人?”
女子说:“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是谁呢?怎么可能啊,那个人就死了,还是再也不到新市来了?”
南娃道:“那个人怎么了?把你怎么了不是?”
女子道:“我,怎么说呢?你,你说说,我怎么说呢?我连爹都不能告诉,你要我怎么说呢?那个人,该挨刀砍脑壳的!”
南娃迷惑地盯着女子,眼睛里说,你到底在说什么呢?那个挨刀砍脑壳的把你吃了?
“他是谁呢?”女子也迷惑了,“他坏了我。”
南娃立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女子道:“他坏了我,可就我一个人知道。但爹还是知道了,他知道了,那还了得啊?他就是因为那件事情,恨透了我。可是,是哪个狗日的告诉他的呢?是那个接刀砍脑壳的吗?不,不可能,他弄脏了我,会说出去吗?我跟他哪来的冤仇呢?”
南娃喉咙里咕哝了一声。
“那天夜里,爹又打我了,我疼,想我娘,就跑到江边来了。到了江边我就哭,哭够了,也乏了,想这辈子我是完了,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后来我就睡着了,靠在石头上睡着了,我睡眠很好,一倒下就睡得死活不知,很少做梦的。那天也是,我睡得很香。可在迷糊中,我感到身上不好受,有什么东西压着我,连出气都很困难。我想动,却动不了,胸口闷得慌。我猛然醒了,原来有个人正趴在我身上,光溜溜的,没穿衣服,不不,裤子是穿着的。我吓得手脚酸软,想叫也叫不出来,即使叫出来了,也没人听见,那地方距离镇上还远着呢。但我还是挣扎,尽力叫出来,但我拗不过那个男人,他可是有一把力气的。我看不清楚他的脸,只闻到一股酒气和汗水的馊味。他也没说话,很快就撕开了我的衣服。我哭了起来,他就把他喷着酒气的嘴堵在我嘴上。我没力气了,只是在他身上胡乱地抓着,狠狠地掐他的肉,他可结实了,抓他掐他,他都没事一样。我一定是把他给抓伤了的,也流了血的。我巴不得把他抓个稀烂,舌头也给他咬断。后来,我就不行了,我痛。他是一头野兽。事情完了后,他一句话没说,就溜了。我不敢问去,我那样子,新市的人一眼都能看穿的。我又哭了,身体痛得不行,我想自己快死了,什么也没了。那狗日的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糟蹋我呢?我,我……我除了摸到他腰上……除了他是……一个臭男人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了。半夜过后我才回到旅馆。那天幸好爹喝多了酒,早早睡了,我才敢回去睡觉,可第二天他就怒气冲冲地揪住我头发,把我从床上拖了下来,狠狠地把我揍了一顿。这次就像我娘被他打得浑身伤疤一样,我也是几天都起不了床。爹在打过后对我说:‘活够了吗?活够了就一根绳子解决了了事!跟你妈一样丢人现眼!你知道不,连你妈在阎王爷那儿也没脸说话,你比你妈还烂贱。往后,我看你怎么嫁人!没几天,镇上都知道了那天夜里发生的事,人人见了我就像见了耗子一样,舌头长舌头短个不停。爹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或者听到人提起这件事,就会打我,用最难听的话骂我。”
南娃嘴里嚼着草根,抬起头,翻着白眼。
“那个狗日的,他坏了我,脏了我,
还把事情张扬出去,你说说,那狗日的还算男人吗?哪天让我见到了他,我就杀了他!”
南娃看到了女子眼里的凶光,他说:“杀了他!”
女子说完了,眼睛却湿了起来,南娃离开了她的眼睛,看江上一个个巨大的漩涡,一块圆圆的鹅卵石在他掌心滚来滚去。
“跟我走!”南娃死死地拽着石头,“以后永远也不再回来了!”
女子异样地盯着他。
南娃说:“你再这样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跟我走,你是我的!”
女子说:“爹常说,他恨我,就权当没生我这个女儿一样。”
南娃说:“这不,跟我走,你们不是扯平了么?”
女子说:“那个狗日的,我要杀了他!”
南娃说:“好,杀了他。算了,把他忘掉吧,跟我走,你是我的。”
“……”
一声汽笛传来。两人回过头去,码头上已经站满了搭乘轮船下行的人。一条两层的客船正从下面开来,缓缓地,波浪撞在船舷上,又哗地荡开。
“走!”南娃跳了起来。
“我爹,他会不会在码头上?”女子幽幽地说。
“如果他在,我就把他扔到江里去!”
女子突然想起什么,说:“你的东西,还放在旅馆里。”
南娃摆摆手:“不要了,送给你爹吧,他连狗屎都当黄金宝贝的。”
“就这么走?”
南娃目光坚定:“就这么走,跟我走!”
“这,”女子犹豫道,“妥当吗?”
“有什么不妥当的?如果哪一天他发现我南娃是他女婿,他成了我岳父大人,说不定他会因为要了我的东西而舍不得宰我呐。”南娃大笑起来。
女子别开脸,两眼愁云。
“全镇的人都看见的,我们……”
“快,跟我走!”南娃厉声叫道。
女子将目光从江上收回来。她理了理头发将粗粗的辫子甩到背后,跟着南娃向码头走去。没人看他们,实际的情形是,根本就没人在意他们。女子将脸深深地埋着,跟在南娃身后。
船离开了码头,送行的人老鼠一样在码头的石级上爬行,黑黑的。女子在呜——呜——的汽笛声中将头藏在南娃的怀里。南娃轻轻地闻着女子的发香。
拐过一个弯,南娃说:“新市看不见了。”
女子仍然不肯抬起头来。她咬住了南娃的肉,南娃轻微地叫了一声。
坐在两人斜对面的是一个老尼姑,一张脸黄白相间。如同蚕蛹。她把两个年轻人的举动都看在眼里,蚕蛹便僵硬了。她望着江水,浑浊的江流翻卷着,将巨大的轮船负载着,颠着向下滑去,这老女人的心也被这般颠簸着,漂着,也就漂出她年轻时节的情节来。但那些情节还没在她意念中成型,就被她一个眼闭和深呼吸给压了下去。当她看到南娃拥着女子,也朝她这边看来的时候,她立即有些慌乱,忙站起来,匆匆走到船的另一边,寻了一个两人看不到的地方坐下了。
女子缩在南娃的怀里,要钻进他的身子里去似的。
日子缓慢地过去,金沙江也由混浊变得清澈明净,夜里,凉幽幽的空气从外面游到屋子里,使人不敢怠慢,得在身上加一层棉被,身子才能暖和,有时,湿润的风从江上吹来,冷不丁的就是一个寒颤,天蓝得让人舒心,又让人生出莫名的忧郁。
当秋天随一片片枯黄的叶掉下来时,女子也从金沙江下游某个地方回来了,掐指算算,她离开新市还不足两个月。
新市还是那副模样,青黑青黑的,像一个清瘦的老者。
她爹那时正在屋子里吧嗒吧嗒地拨着算盘算帐,嘴上一根粗大的旱烟,一只景德镇产的弯嘴紫砂壶放在一边,极似一只乌龟,替他守候着烟水和时间。他见了女子,脸上没任何表情,眼里平静如水缸里的泉水,仿佛她只是走了亲戚,或者到集市上买了柴米油盐回来,然后他依旧勾着头吧嗒吧嗒地拨打着算盘。女子正欲往楼上去,他叫道:“四楼十号房没开水了,你给端两瓶送去!”
女子转身去抹泪,男人什么也没看见,他扔掉烟蒂,蘸着唾液点数着钞票。
到了冬天,女子起不了床了。新市地方上难得见到下雪,倒是一日紧一日的江风将小镇裹在其中,一把手术刀似的一点一点地刮剥着房屋,远远看去,萎缩着的楼房仅仅剩下一副副骨架了。但家家户户买来枸杞大枣,合着辣椒生姜炖了大锅狗肉,老少围在一起喝烧酒,但女子没起床,只吃了一口她爹红烧的狗肉。冬至过了很久了,女子还是没起来。她爹倒是从一个云南商人那里得了五千块钱,便答应将女子嫁给他。因她卧床不起,只喝了订婚酒,婚礼便定在了开春。
女子听到金沙江水流的声音,像在听一片遥远的梦。她哆嗦不已,仿佛噩梦将她吞噬。她抓住被角的手沁出了冷汗,但她一直没有松开。一只鸟儿出现在窗口,她眼里立即亮丽起来。鸟儿见她欠起身来,便扑哧一声飞走了。她望着天花板,那些水渍勾画出一些抽象或十二分形象的图案使她眼睛发涩,她很快又死睡过去。
春天来临,女子便能起床了,能下楼来招呼旅客,为旅客端茶送水了。她爹依旧脸面冰冷,偶尔也训训她,有时也给她说几句地方掌故。她什么也没说的,只是笑了笑。她爹又从云南商人那里得到五千块钱,后者在三月初三那天就将她娶走了。
那个叫南娃的男子,又到哪里去了呢?原来那天夜里将女子糟蹋的人就是他。离开新市后的某天夜里,两人正兴奋得吭哧吭哧时,她抱住了他的腰,在那光溜溜的腰上,她摸到了一块长着毛的痣,当时她就觉得是摸到了一只坚硬的毛毛虫,而指尖告诉她,这硬物跟那黑夜里那男子腰上长的,是同一个东西,它们的主人是同一个人。
“他说死也不承认!祖宗八代,上天下地,都诅咒发誓了:说根本就不是他。不。就是他!要是他能承认,老老实实地承认,一切都好说,事情也不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至少,我不会离开他。”婚后,女子将南娃告诉了她的商人丈夫。
“他怎么会承认呢?”男人将口中的痰吞下肚去,“是男人,都不会承认的。”
黑暗中,女子侧过身去,背对着丈夫。丈夫的话将她彻底击人黑暗,她落下泪来,丈夫却在铺天盖地的呼噜声中睡下去。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