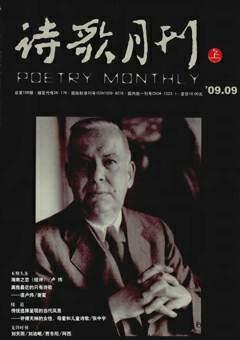刘洁岷的诗(9首)
刘洁岷
母亲节
碧绿的田野,朝向
灰黑的镜子般闪耀的池塘
我的母亲是我晚年的朋友
当她在一天将尽时定格在黄昏
从棉田一次次地归来
父亲节
我有个落落大方的朋友冤屈在牢狱里
八年后出来时已经厚颜无耻
我在世上白白走了一遭结果
我还是渴望把我带到我父亲的故乡
我到那儿小声念叨着父亲、父亲
我就像一个胖子那样开心
啤酒节
我们都需要一点点空虚使承诺新鲜
那醉的形状
火把节
突然感到需要和某物谈话
今天天气阴晦,许多青毛蛇
在寨子以外孵成
那年天气晴和,澜沧江以南,许多白蛇
都冲动了
那个人是见过的但此刻
在摆舞中离得很远
(全寨的人和路过的人
都加入进来,形成一条
很长的舞动着的人龙)
那个人没有见过叫什么
“叶多多”或“绣绣”,此刻
在同一城市同一小区
以古法泡茶
默默地恳求,仿佛遇见
黯淡将灭的火把下
那个眼神中残留我旧情的拉祜女子
空缺
我像火车似的在别的大街上走动
面孔,分布在车载电视画面中
黑色的线人弯曲食指
扣击窗帘起伏飞扬的玻璃
每一扇掠过的窗口
都陈列着我的母亲
为我整理的从小到大的
作业和照片
而许多滚烫的眼睛
都涌向广告和节日促销人员
我对歌曲过敏,阳光下
街心公园的草地微凉
我想找到一个水波中的
潜在的影像,或者
像一只巨大白净柔软的手
从长睡中醒来的动物
荆州东门水饺馆
东门右边,我曾和一位同事坐在浅草中
东门的左边,我曾和一个秀气的女子
在星光的夜晚骑车而过
东门以内修葺一新
红旗和彩旗飘飘
道路宽广,著名的监狱
已经整体搬迁
站在黄金堂站点
赭红的“东门饺子馆”下
这几个字迹它没有变
我想到“老”了
刚才在宾阳楼下的门洞里
迎头碰见几十年不见的故乡小学的
班长韦小敏,那是安排好的吗
我们进入饺子馆坐定
周围全是吃东门水饺长大的男女
有几个赤膊纹身的青年
对着我们笑眯眯
笑眯眯的
这是安排好的吗
店内没有装修过照旧
没个服务员,也是安排好了的
包饺子的大妈
在包着韭菜饺子,三十年
她们只包韭菜饺子
这是安排好了的
卤菜的口味丝毫未变
藕和海带,猪蹄顺风鸡爪
品种也没有改变
洗碗的水池,煮锅的布局
都被安排得没有变化
只是,我感到有点
什么老了
需要她们为我们
安排好周围
吃水饺的群众,并
为我们解释店里不变的老规矩
和口味,纹身小弟的女友
匆匆帮我们拿来碗筷
把我们安排在
靠近角落
有风扇的位置
慢慢,一口
一口地
吃完命中剩余的几个
东门韭菜水饺
当我们离去
当高柳的相机镜头
对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大妈
她们雪白整齐
或暗黄凸凹,但
显露出全部牙齿的形象
似乎在大声
急切地告诉我们
无论多少年月
古荆州东门都在
东门水饺馆也还坐落在
黄金堂,包水饺大妈
还满面皱纹地
坐在案板前开怀大笑
青海湖
水的对岸是山
圣洁的地方
神迹所在,那是
可以用双臂飞到的地方
巨大的水与人
之间
有小动物
在恐惧中渐渐形成
某年秋,潜江,森林公园
那天一片很小的森林里共有
皱巴巴的7个人,其中一个
很老了这老头总是怀疑另外6个人
喜欢和他一块呆着,其他的
也各自有点点这样的
想法,几乎雷同
他们举着电量不足的相机
他们有时行走,有时挂在树上
还冷不丁地匍匐在落满落叶的草丛中
一头水牛在一条静止的小河边
打着盹,醒来的时候
像苏瓷瓷一样害羞
他们在自己寂静的身体上感到
城市、村庄和小镇,临近了秋天
——垂危的父亲在明媚的阳台上钓鱼
外祖母的鬼魂在菜市场喧闹的边缘
陷入了棕红和蓝色三角形的假寐
没有意外,也没什么结局
女儿发来的诗
不是我不说而是我觉得
没有必要虽然
你们很关心我我也爱你们
但我终究还是一个人,我常常
想把自己封闭我发现
心里有些不正常的压抑
我很想长年累月地待在学校
我非常讨厌自己,因为
很不满意
我讨厌自己的性格,是它让我
拉开了与她们的距离以及
与我自己的距离
你不知道我是个极其胆怯、拘谨的
人,想要冲破那些压抑不喜欢
这样的生活所以想努力改变
我不会因为有人比我差就
高兴,我在乎平等,我把这看得
比有些东西要重得多
创作短言:诗歌是对语言世界的发现或重新发明,既不是在模仿实在之物也不是为了表现梦幻遐想,而是一种旨在揭示内心生活和语言内在奥秘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