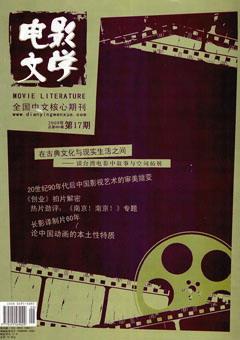从影视作品角度比较中西法律文化
曾金鹤 陈诗文
[摘要]法律与影视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法律用严谨的规则和逻辑阐释生活,影视用光影声色生动形象地展现生活。本文从影视和法律的相关性、研究法律文化的意义出发,通过对影视作品中的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权力意识与权利意识、理性意识与感性意识三个方面的比较来阐述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影视作品;法律文化:差异
一、影视和法律的相关性
法律通常是教条刻板和理性思维的象征,影视文学则是多姿多彩和浪漫感性的代表,法律与影视的确有很多不同。但是法律和影视却有一个共通点:即法律与影视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法律用严谨的规则和逻辑阐释生活,影视用光影声色生动形象地展现生活。
影视是银幕上的生活,从各个侧面影射甚至细致刻画社会、历史和人生,是真实生活的再现,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生活本身。影视可能涉及各种法律问题,譬如,展示人类文化中理性部分的法庭审判,法律人的生活、冲突、纠纷的解决,甚至是演绎一段真实的法律故事,以最贴近民众的方式展示正义的实现,或者揭示实现正义的艰辛。影视为法律分析提供了生动形象、活泼有趣的素材,通过影视可以揭示出深刻的法理。影视反映了社会生活,展示了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法律,体现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知和理解,因此影视可以是法律人与社会公众实现沟通的另一种途径。
二、研究法律文化的意义
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建设有重要意义,因为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对法治建设更是具有全面性的影响。国内著名学者李交发教授在其著作《法律文化散论》中说到:“从深层意义上说,法律文化是法治扎根的土壤,是一切法律制度和思想赖以存在、运作的条件,同时还是制度和思想不断创新的活水源泉。”法律制度在实施中是否有效依赖于两个方面的支持,一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支持,一是文化学意义上的支持。其中文化学上的支持就是看这种法律制度背后的价值、意义、态度和思维是否同立法者、司法者以及守法者的文化观念相适应。
三、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
在个人权利和群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给出的是个人向家庭让步的群体意识答案,而西方社会文化给出的则是个人权利至上,至少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个体意识的答案。影片《刮痧》是体现在个人权利和群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中西法律文化所折射出的差异的最佳范本。
《刮痧》的故事发生在美国中部密西西比河畔的圣路易斯市。该影片主角许大同在美国,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但随后降临的意外事件却使许大同从梦中惊醒:他五岁的儿子丹尼斯闹肚子发烧,来美国探亲的爷爷不懂药物上的英文说明,便以中国民间传统的刮痧疗法为小孙子治病,而这成了许大同虐待儿童的证据。随之,接连不断的灾难噩梦般地降临,原本美好幸福的家庭转眼间变得支离破碎,许大同一家努力了多年以为已经实现了的“美国梦”被这场从天而降的官司彻底击碎。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美国的法律给许大同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究其给许大同带来厄运的根本原因是许大同那些用中国式的思维来生搬硬套地认知美国法律,从而做出的种种不符合“国情”的举动。显而易见,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许大同,虽然从表面上看已经步入了美国社会,甚至成为美国社会的佼佼者。可事实上,他仍是一个有着“中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的现实处境与未来憧憬的巨大反差,无形中为我们揭示了中西方法律文化在观念上的差异。
从美国法律文化强调个性与中国法律文化强调家族的两极来看,许大同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美国司法机关对他家庭内部事务的干涉,在中国,
“清官难断家务事”显得天经地义,但这一思维习惯,却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两千多年的儒学家庭观、家族观在中国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不可撼摇。中国古代通常也是以家庭或家族划分社会单位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律的惩处对象便不仅仅是针对个人,而是家庭甚至家族的连坐;其后独尊儒术,也处处强调家的重要性,他们把国比喻成一个大家庭,称之为国家。正如高旭东先生所言,“儒家以孝为逻辑起点,而建构了一个父慈子孝的和乐家庭,天下国家不过是这一和乐家庭的合情合理的延伸和扩大,这就是君仁臣忠的礼乐之国。”
从文化根源上来讲,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内核的迥异形成了中国法律文化强调家族性与美国法律文化强调个性的分野。
四、权力意识与权利意识
《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就形象地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几千年来“命令——眼从”的权力特性在人们的冲突、痛苦和情感抑制中造成一种内在的、主观的变化,使人们以一种新的法律的视角去看待生活和现实。这部电影的结局是当她想要“说法”时得不到“说法”,当她不想再要时却又突然降临了,而这个“说法”也不是她最初想要的“说法”。秋菊其实是要“礼”的说法,而不是要“法”网的说法。这个“礼”的说法并不是要真正地冲破权力的束缚,也不是要彻底与权力的决裂,而是在不破坏这张权力的基础上,给她以适当的妥协和让步。即在中国传统社会观念里,法和权力是一体的。法首先意味着一种“权力关系”,一种“命令——服从”关系,甚至于中国人会把执法者的话都当作法本身去执行。这种“命令——服从”关系不仅存在于国家和政府的政治运作之中,而且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种形态之中:习惯、利益、情感、理想等。按照韦伯的理论,存在于这种“命令——服从”关系中的各种不同的服从动机表明,每一种真正的统治形式中都包含有最起码的自愿服从的成分,但只此不足以构成真正的统治,必须还要有“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自愿服从与信仰体系共同构成了统治系统或称权威系统;在群体(家庭、团体、民族、国家)中,则体现为一种“命令一服从”的权力关系。
美国电影《费城故事》则体现了西方人为捍卫权利而不惜做生命一搏的精神。影片以一种严肃、真诚、庄重态度向观众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天赋人权”,任何人都不能以不正当的理由侵犯他人的正当利益,纵使他们是被边缘化的艾滋病患者。在美国社会,《权利法案》被视为为弱者提供的可以抗衡强权的法律武器,使他们有能力反抗加诸于他们头上的不公正行为,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美国人对法律的尊重“如爱父母”,因为“个人从法律力量的增强中看到个人的利益”。“个人主义”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社会历史之中,成为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其实,“广义地说,个人主义的概念是描写这样一种学说:认为个人利益是或者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一切价值、权利和义务都来源于个人。它强调个人的能动性、独立、行动和利益。美国人认为,作为一个人都应该具有独立性、责任心和自尊心,具备了这些,也才不负作为一个人而受到关注和尊重。”在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中,它强调的不是牺牲个人利益去服从群体利益,不是把个人利益溶化到群体利益中去,更不是大公无私,而是通过集体合
作的形式和群体的力量来实现个人利益。“在西方人的心目中,高扬个人主义的旗帜、摆脱群体的羁绊所获得的独立、自由、民主高于一切。”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这种意识上的差别其实体现了两类民族不同的“人观”之间的精神分离。在西方人看来,人都是具有理性的独立的个人。他们的法定义特别强调法的本质是理性、正义,是权利或公共幸福。而在中国古人看来,人都是嗷嗷待甫的婴儿或蚩蚩待教的群氓,无所谓独立的人格。对待这样的“动物”,当然只能是“临之以威”。
五、理性意识与感性意识
中西方法律文化在观念上的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分野,在意识上的权利意识与权力意识的较量,都是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实质而产生的。西方文化的理性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性意识的背离使中西方法律文化的精神形成迥异的特征,分别指示了两种文化各自不同的发展之路。
《刮痧》是中西法律文化在理性和感性差异的又一范例。影片中的许大同吃的另一个亏就是自己所注重的情感因素在美国法律强调事实与证据的作风面前是那么的无力与无助。中国社会是靠关系网组织起来的,这一点不容置疑。一方面是中国古老的封闭经济限制了人们的交际圈,有限的圈子必然导致会被主观地予以放大并得到重视,并用友情、爱情、亲情、伦理血缘之情,甚至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里之情去精心地编织与呵护这个圈子。在中国人眼中万能的人情在美国人眼里也只是一个参考而已,甚至连儿童福利院和法官都怀疑许大同有虐待儿子的倾向。最终宣告许大同的人情法律观无效的首先是法官对他智商的怀疑,其次是法官理性地告诉他用美国的理性法律观来解决问题——“找一个官方医生,用简练的,一个老法官能看懂的英文来说明刮痧”,也就是提供事实与证据。坚信人情法律观的许大同并没有就此失去对人情观的信仰,他放弃了去寻找刮痧的证据,而是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法庭上深情的陈述演讲上,结果,他动情的演说被法官和控方律师一致地认为是“精彩的表演”。以至于后来,许大同毫无顾忌地顶替他父亲说是他本人给儿子刮痧的,大同从福利院“偷”儿子到机场与即将回国的爷爷见面以及为了在圣诞夜与家人团聚,大同冒着被逮捕的危险。虽然大同爱子心切,但却拿不出证据来证明刮痧是中国的传统治疗法,无论他怎样用语言来表达他是多么爱自己的儿子,都打动不了法官的心。法律只需要证据,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每一种纠纷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他们看重的是事实和证据。大同最终还是被判决与自己的儿子隔离,这一判决虽然缺乏人情味,但是从依法办事的角度来看,法院的判决却是正确的,只是广大中国观众接受不了,情感还是站在不守法的许大同这一边而已。直到最后,是昆兰用事实证明了许大同的清白,而不是许大同的人情感动了法官。但冷静下来想一想,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这场法律文化的较量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代表着中国法文化中的感性观的许大同与代表西方法律文化的理性观的美国法律之间的又一次真正叫板。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比较得知:法这种规范以个人为本位,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权利。整个西方文明的历史,就是个性不断解放、个人权利不断发展的历史。而中国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是在其自身独特的理沦构架下存在并发展起来的,并以儒家纲常伦理学说的正统思想为理论根据,中国传统思想中把法律视为人类的规范体系,并将之与礼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令法屈从于礼、屈从于家族伦理。这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和对规范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两种法律文化的巨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