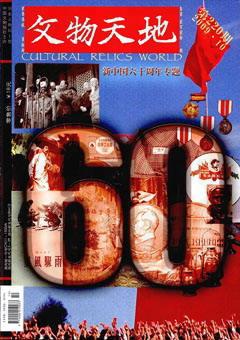法乳圆融 随缘自喜
赵 强

西藏地接中亚和印巴次大陆,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西藏佛教艺术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元明时期的藏传佛教艺术主要受到三大艺术因素的影响:一是来自东印度波罗艺术的美学和图像学方面的准则;二是源自加德满都河谷地区的艺术传承;三是来自北京(大都)的元代西天梵相艺术风格。除了汉藏交融的西天梵相艺术在中国宫廷自成一格之外,元明以来的卫藏地区造像艺术即多受前二支的艺术风格所影响。特别是卫藏地区,印度波罗王朝(8—12世纪中期)以及属于波罗系统的尼泊尔艺术传统是其最主要的艺术灵感的源头,这类风格一般被称作是“印度尼泊尔”风格。这尊15世纪初期的释迦牟尼佛紫檀造像就是这一风格的代表性作品。
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者”,佛为“佛陀”之略,意为“觉者”。其形象以诞生、成道、转法轮,涅桀四相为世尊造像的典型样态,最为常见的即是此成道相。事实上,佛陀的具体形象经由“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等等基于宗教理念与审美传统的规范和美化,标志了佛教由兴盛的“正法时代”步入“像法时代”衰微趋向的开端,而从人文的角度,它却奏响了人类艺术史上至为辉煌的乐章。正如此像,它遵循了古印度的造像模式,即佛像须具备的“相好”标准:波罗式的仪容与发髻,顶有肉髻,宝珠顶严,额广平正,眉间毫相,眉如初月,眼广长,鼻高不现孔,耳轮垂等等。螺发和双唇分别施以石青、红色,以表现佛陀“螺发右旋,其色青绀”“唇如频婆果之色”的容颜。眼睑曲线优美,目光下敛,似在俯视芸芸众生。特别是面部的神态,慈祥大睿,体现出智善合一的佛性。肩胸宽厚,肢体修长,腰部细敛。腰身比例合度,给人以挺拔之感。面部及肢身皆以金色矿物胶彩作漆绘。身着袒右肩袈裟,采用藏式写实技法,仅在衣缘处雕刻数道边际线,衣纹简约流畅,使得像身优美的曲线得以展现,犹若曹衣出水,显然受到萨尔那特表现手法的影响。袈裟上的纹饰,亦通绘了明初西藏造像所常见的卷草纹。卷草纹又称卷枝纹,其与缠枝纹最大的不同处,在于卷草纹仅出现抽象的枝茎或草蔓的圆形或波状延续线条,不出现写实的花卉或果实。由于缠枝纹写实性较强,而卷草纹则颇具抽象性,以至于在卷草纹中由诸多草蔓卷起的饼图纹与其内的辐射状草芒,视觉上会看似法轮图案。由于寺内藏香及酥油灯的长期熏炙,佛像表层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包浆,色泽醇厚而自然。手的造型保持波罗艺术传统,手掌较大,手指纤长而略有弯曲。右手垂放右膝,指尖向下,结“触地印”,也称“降魔印”;左手平置右足上,结“禅定印”;坐姿为右腿在外左腿在内的全跏趺式,称“降伏坐”或“降魔坐”,概括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降魔与成道的两个情节。这是“释迦八相”中最具代表性的造型。在藏传佛教造像中,释迦牟尼佛的造型应用此式者尤多,《造像量度经》更以此姿态作为一切佛像的模式样本。
此像尽管题材单纯,但在艺术表现上却显露出高度综合的艺术风格,其艺术构成也比较丰富,是东印度、尼?自尔以及西藏三种艺术因素的融汇,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还要阐明的是,此像的雕造者应是卫藏地区的藏族艺术家,他们汲取了不同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甚至是艺术理念,并在创作上显示出他们特有的综合能力。整躯造像体量硕大,结构上为木造接合。像身与莲座系用不同材质分体雕造再榫接而成。台座的仰莲瓣圆润饱满,上缘雕刻圆浑的连珠纹,既富于装饰色彩,又给人以敦实稳固之感。
难得的是造像内部装脏无损。明初以来的世间诸宝及出世间的殊胜法物封存其中,自有其不可思议的福德与加持力,令人心生欢喜,由衷赞叹。正所谓:法乳圆融,随缘自喜。福慧皈依,肃穆巡礼。稽首心诚,花雨满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