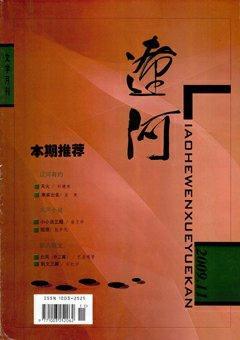声音
李维宇
一朵夜来香骤然在暮色里开放。短暂得只有几秒,便展开得如一盏小灯,挑着黄色丝绸般的花瓣。我是可以听见它开放的声音的,在临海的一座别墅里,四周安静,只有不同植物抖动茎叶的细微声音。惊诧于它瞬间制造的美丽,就像我突然登临这座陌生小岛而感受到的亲切一样。是的,声音,我应该从它开始记录,从一朵花、从一次倾听开始。
落日挂在几株向日葵上方,绚烂得有些不真实。那些披着金光的云彩在蓝天里拉起霓裳,仿佛海滩上摊开的渔网,漫漫收拢再慢慢在夜色下消失。那些向日葵的笑脸是你面向我的心情么?在落日的余晖中,想象着有一种美好悄悄抵临,像对面盛开的芙蓉花,带着一抹羞红,一种向上的妩媚与妖娆。这些植物的颜色应该就是它们的声音。金黄的灿烂,粉红的娇羞,仿佛向我发出的邀请又或是期待。
是了,就是这片海了。沿着别墅前的柏油路一直走再右拐,一片海扑面而开。与其说这是黄昏里的一次邀约,倒不如说是一次预谋好的迎向。将自己融入扑面的咸腥海风中,才知道海并不遥远,也不是平常所说的遥望中的不可企及。我是如此兴奋地靠近它、倾听它,又迫切地想融入于它。
视线被一艘破旧的小船牵住。不知它的归属,也不知它的航向。斑驳的船体让人想象着它的沧桑。每一条船都有属于自己的命运,也都有属于自己破海而行的声音。现在,它安静地躺在沙滩上,任凭游人频频为它拍照。它是这片海的一个标志,也是迎向我们的一面旗帜。船的桅杆上挂着一面红旗,有些破旧。飘动着的褪了色的布条让人想到它的经历,想到它的每一次出航与回程。这是一艘木质的小船,散发着一丝霉味。也只有旧船才会有这样的味道,带着海的咸腥。一艘船也是时光的线条,每一次航行都是时光之海里的一次跃动。谁会知道那一次次的航程里,时光之手是如何悄悄改变着它的容颜,而它又是如何穿越时光穿越海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复又回还的。
我是想登上这艘木船的,但终没能如愿。我怕我的登临会压坏了它本就破旧了的船身,也怕自己不经意的抚弄会剥离它身体上一些关于时间的印记。我远远望着它,就像远远望着一个瓷器,不可碰触。我相信这艘船应该载着海的声音。从遥远到遥远,从此处到彼处。关于船,有许多记忆。有沉在海底的浪漫无奈也有破浪出航时的惊喜。当它安静地躺在这里,面向游人,它已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小船。它是大海的一只手,是漫长海岸线的一处延伸。它默默展示着海的博大与深邃,又把海的温情浪掷在沙滩边,牵动众多视线。在淡淡月色照耀下,它油漆剥落的船身及挂着水藻的缆绳,裸露着它陌生却不孤独的灵魂。
是什么突然炸响于夜空呢?我不能不惊异于这海边燃起的烟花了。在海岸线的一角,它们的巨大声响让我突然忘记了海的苍茫。在海的上空,它们短暂地绚丽,又迅速地消失。我想到空旷,那种绚丽后的空旷与苍茫。我站在一处人少的沙滩边观看烟花,海水在脚边轻拍着。这是触手可及的海,是瞬间就可以覆盖我的海。可是我不怕。从我伫立的地方向右侧看,便是一团一团燃起的烟花,伴着快节奏的“的士高”音乐。那是一片欢乐的海洋,与我有些距离。而对面是一些直立的灯,光影投射在平静的海面,随着海一波一波地涌动。在海上,若是看到灯火,那一定是岸了。即使有再大的雾,只要看到这些光亮,就仿佛听到母亲的召唤,便不会迷失航向,找到自己的岸。所以,我喜欢海上的灯,喜欢看它们投在海面上的光影。那些长长的光影仿佛母亲延伸过来的手臂,摇着我,随着海的呼吸安睡。可是我多么不愿意就这样沉沉睡去啊。我被一盏跳动着的灯盏吸引。它先是远距离地闪动,让我以为那是一只航行在黑夜海上的小船。可随着它的临近,渐渐看出那仅仅是一盏灯,是一位赶海老人手里握着的一盏灯。我是飞奔着跑向这盏灯的,就像飞蛾扑火般不顾一切。我看到一张脸庞,被灯光映着的皱纹里漾着亲切的微笑。在如此博大的海面前,我相信一切距离都在慢慢消失,就像面对眼前的陌生老人。虽然我们从不相识,但我却把他当成父亲一样的人,从他挥动的手势中体会温馨。他把灯照在退了潮的水面上,指引我看躲在卵石中的小鱼。我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去,可是一条条鱼迅速地从指缝间逃离。我有些气馁,老人却大声地一边笑一边告诉我去捉鱼的头部。依着他的话,真的捉到了几条小鱼。可是迅即我们又都放了它们。鱼总是要在海里游动的,就像我们人要行走于尘世,做自己的事情一样。它们也有自己的命运,我为什么要突然改变它们呢?在我捕捉到它们的同时,它们的同伴会不会发出求救或者危险的信息呢?在如此博大的海里,这些呼唤是不是微弱得如同一粒沙,细小而尖锐,却又很真实呢?
复又静静地伫立在海边。望着苍茫的水面,望着被水波斩断的一截截的光影,我相信那些水波里一定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此刻的我,也许正成为它故事里的一个小小配角,不重要却也不可缺。这时,一位像我一样在海边伫立很久的人靠近我,“你在等谁呢?”突然的问话让我惊讶。是啊,我在等谁呢?是这片海么?还是一些关于海的声音,一些来自遥远又让我期待的声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