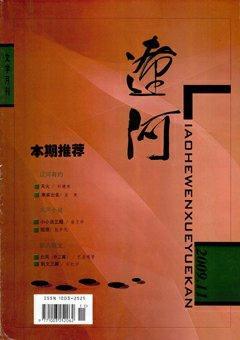未名松(外一篇)
刘云峰
距宽甸县城南行大约20公里是毛甸子镇。镇北头公路边的河套里有一道奇异的景观:光秃秃的砬子头呈乌龟状,斜坡向下探伸,距水面一米许。其水平如镜,酷似乌龟引颈戏水者。尤为奇特的是,乌龟颈项顶端兀立着一株青松。松高约三米左右,粗似碗口。松下无土,显然其根植石间却不见些许缝隙。其根深几许?何以摄取营养?树龄若许年?均为未解。其蔚为壮观,令人遐思不已。
早先,宽甸去丹东的公路绕经长甸。201国道开通后,取捷径路过毛甸子,直奔丹东。这道奇异景观便更多地展现在路人视野。然而,却多为“走车观花”者。从这奇异的岩松边路过时,人们会指点着相互提醒说,你看!你看!汽车便飞驰而过,留下来的是更加美妙的遐想。少有近前观赏者。
偶尔有一次去丹东赶礼,回来的时候我打乘私家车。开车的朋友路过岩松时便停下来刷车洗脸。我心窃喜,终于可以近距离观赏岩松了。然而,我们所处的位置仍是其对过的河套边,只能隔岸观赏了。还好,透过平静的水面,可以鉴赏到乌龟岩和岩上松的倒影。视觉上的这种享受,把我越发带进了梦幻般的奇异境界,让我的心态也有些许满足。其实,绕过对岸也只是咫尺之间的事,我却难为情向朋友启齿,让其等我片刻。在纷纭的事态中,岩松与我就又一次失之交臂了。要上车走的时候,乌龟岩后壁的岩洞中有几只鸽子大小的无名灰鸟飞出来又进去了。原生态的境界。
我是经常往返丹东与县城之间的。每次路过那里,我都要在车里掉过头,长时间流连它。它生命的底色是几铺炕面积大小的秃砬子,着实让人的生命律动不已。冬雪覆盖着大地的时候,唯独那苍松下的秃砬子色彩依旧,岩上的雪会瞬间消融的。雨霁天晴时,松下的秃砬子也绝不显得氤氲与潮湿,秃砬子一点土都存不住,又何以能存下水呢?伏天,会有一群孩子光着屁股在河里洗澡。上岸后,会在松下的砬子上哈趴着烙肚皮,晒太阳。春秋冬夏,年复一年,这棵松树都独自傲然挺立着,也许,它昭示着生命的神奇。
出于好奇,有几次遇到毛甸子人我向他们打听过,这里有没有什么美丽的传说。比如,王子与公主,仙子与书生。他们醒过腔后,大都嘲笑我迂腐,一个光秃秃的破砬子头连一点土星都没有,一棵孤零零的干巴松树能有什么传说?除非是吃饱了饭撑得慌。他们只告诉我,那里叫“老鳖汀”。而我却依然固执认为,辽东古代历属边塞,缺乏中原文化的沉淀。让这样奇异的景观埋没了。
世间被埋没的宝藏大都离不开泥土。唯独这老鳖汀的岩上松却为岁月的裸者。然而,它从土地里裸露出来的同时,却又在人们的心目中视野里被埋没掉。
千山可怜松的生命为三百多年。与之比对,从状态上看毛甸子“老鳖汀”的岩上松起码要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毋庸多言,原来它是被丰厚的沃土覆盖着。而随着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岁月流逝,土没有了,而它却依然傲然挺立在岩头之上,生机盎然地活着,去见证着岁月沧桑。这不能不说是生命的奇迹。抑或,它要向人间昭示着什么。
世间,大凡人们发现了被埋没的东西,它的曾经被埋没便都是暂时的。尽管其间很漫长。我幻想着有一天,毛甸子的乌龟岩和岩上松会被开发为旅游景点的。而它现在却没有名字。为其取名就成为我由来已久的奢望。而物以人传,却又是世俗生活中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我一无名鼠辈,即使为其取下名字,也是很难流传的。弄不好,就会把这一神奇美妙的景点“糟败”了。再者,我发现有的风景旅游区,本来就有着很好的名字,可开发者硬是给改了。把其原有的文化底蕴弄没了。有的地名,本来挺好,而当政者硬要改,弄得看不清其历史沿革。取名和改名的学问老大。
可不给这秃砬子和岩上松取名,我又经常向人谈起它,表述起来就极不方便。思忖再三,我给它取了个临时名字,叫“未名松”,自己用。
房后有棵大梨树
三间草房。房上苫着厚厚的草渐渐腐朽了,间或便生长着一层嫩绿的青苔,却也不漏雨。浑然一色的黄泥墙,从墙根到屋脊下,似乎涂抹着庄户人家的全部生活,再无其他色彩。屋檐下的釜台,每日三遍升腾着袅袅炊烟,在昭示着农人的生存图景。
这便是我童年记忆里的祖宅。而记忆最深刻的还是房后的那棵大梨树。
春天的脚步还没有真正践踏到大地上,天空还飘洒着小雪,树的枝头上却摇曳出浓浓的春意来。一对喜鹊叽叽喳喳,在枝头跳跃嬉戏。它们不辞辛劳,衔来小棍、碎麻和牛马羊的杂毛在枝头做窝繁衍了。每年如此。伴随着春的脚步,人们在田间行走不时地便会轰起一大群一大群的小鸟来,铺天盖地。那是鸟的迁徙,它们便会在大梨树上作暂短的栖息。树的枝头便结满了初春的动感。
夏天便呼啦一下来到了大梨树上。雪白的梨花绽放在树的枝头,也绽放在我童稚的心里。梨花飘落着雪花的韵致,洋洋洒洒让我的思绪随风飘荡起来。我依偎在奶奶的怀抱里,乘着阴凉,睡着了。伴随着奶奶的摇篮曲,梨花一瓣一瓣地飘进了我的梦乡。
秋的丰实,那是大梨树的承载。 “卸梨”就如同某种民俗中的庆典,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父亲洋溢着笑脸,手持一根长长的木杆,灵巧地向树上攀缘着。我们在树下仰视着父亲,父亲的形体竟然显得小起来,而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却愈发地高大,仿佛童话中的部落首领。父亲轻巧地在树杈上跺着脚或双手绷着树杈摇曳着,梨子便噼里啪啦纷纷落下。我们姐弟兄妹们把梨子捡得满满的一大筐又一大筐。自家吃不了便分送给亲戚和乡邻们,亲情和乡情便在大梨树下飘洒开来。
这似乎是一棵再平凡不过的大梨树了,关于它的记忆也就极其平凡。而那却是我们庭院里唯一的一道风景。唯一也许便是单调,树下玩赏腻了,便背着大人同弟兄们往树上爬。就真的有所发现。其实这是一棵歪脖子大梨树。半截腰骤然拐弯处的一侧有一个碗口粗细的筒,筒很深,筒壁周围的木质腐朽成缃黄色,大梨树原来是长在筒的上面。我便耳目一新,也就产生了新的玩法,同弟兄们爬上去藏东西。而很快又玩腻了,我便向爷爷探究树筒的成因。爷爷便向我述说了那一段梨树的沧桑:
荒乱时过兵。不同的队伍住营的方法不一样。八路军全住在老百姓家,不睡炕,炕留给主人睡,睡地下,挤得满满的。走的时候院落和屋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国军装备好,不睡百姓家,睡帐篷。帐篷的外围要用物件围成一个大圈子。一个“南蛮子”小兵便去砍房后的大梨树,挡圈子。爷爷腆着脸同小兵求情说,果木树金贵,能不能换砍别的树?小兵却不讲理,叽里呱啦把爷爷臭骂了一顿,说爷爷不支持国军革命,给了爷爷两杵子,继续砍。爷爷不服劲,去找了国军营长。营长把小兵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又给了他两“脖溜子”,教育他尊重老百姓的利益。大梨树原来两个大杈,此刻已被砍掉了一个,另一个便保住了。爷爷讲得目光炯然,充满着英雄气概。我便又耳目一新了,觉得大梨树上似乎蒙蔽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大梨树遮天蔽日,房后的菜园不长菜了。父亲想砍掉大梨树,爷爷不让,说,是家的风水。大梨树便又保留了下来。
从老家搬走后,我始终有一种漂泊感。思绪却长期停留在大梨树下。将近半个世纪了,脑海里绽放的依然是大梨树的花朵,飘荡的依然是大梨树的落叶,味觉里回味的依然是梨子的香甜。
山里人童年的生活似乎很单调。而单调给我的却是专注,大梨树下的记忆碎片丰实着我。关于社会、人生的思索也许都源于大梨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