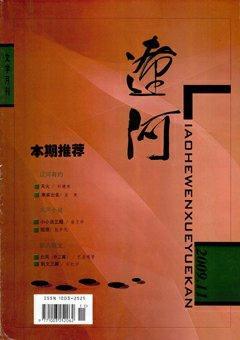北风(外二篇)
巴音博罗
风娘娘,送风来。
骑着毛驴自东来。
拿着口袋洒风来。
——民谣
整整一夜,老北风那个白毛怪兽蹲在门外号叫。像牛吼、马嘶,像那条瘸腿老狼仰天呜咽。
整整一夜,这幽魂一样的北风在村庄周边游荡,它无赖一样拍打别人的门环,醉汉一样在小学校操场上打滚,尘土飞扬地打滚,最后还顺手抓走了马寡妇窗户外的烂塑料布……
我蜷缩在被窝里。我能感觉到这所房子正漂浮在白浪滔天的海洋上,一会儿陷入巨浪的谷底。一会儿又被掀到陡峭可怖的山尖。树林在黑暗中被一只狂暴的巨掌折断,群山在远方轰隆作响,仿佛一只快被擂击得崩裂的牛皮大鼓。
我瑟瑟发抖,炉火忽明忽暗,像是一位垂亡者的眼神。而风正大声狂笑着,大踏步穿过积着脏雪的田野踉跄而来,并把悬挂光秃秃树梢的半轮残月撞得叮当乱响。风啊,像个莽汉,像个杀人如麻的土匪,又像个撩开冬夜厚重幕布,前来抢亲的痴情郎——他跺脚、瞪眼、胡乱发着脾气;他叹气、捶胸、一边嘟哝一边拔出腰间那口青森森的砍刀张牙舞爪扑向前来……
直到天光大亮,黛色穹空下的村庄被冬阳的手一寸寸摸暖。远山面目一新,像是饰妆的新娘。道路也刚刚被风修改过,并将一位猎人的脚印深深埋葬,而家家草屋瓦房边悄然伫立的烟囱,此时则一边咳嗽,一边将缕缕淡青色的烟斜斜地送给天神。
雄鸡高啼,此起彼伏一会儿就叫成一片。马和牛在牲口棚里沉默,被风梳理过的鬃毛稍稍有些零乱。猪在矮矮的猪圈里哼叽,冻得硬邦邦的木槽里的猪食又难看又肮脏。只有梦,那刚逝不久的梦境被一夜北风吹得澄净明泽,大河对面山尖的坚冰一样在灰暗的阳光下闪闪烁烁。
就这样直到半晌午,我在村街上寂寂而行。村庄似乎刚刚苏醒,慢慢活动着僵硬的筋骨。风又来了,风把我的脸吹得缓缓凹进去,使我的眼眶变得更加深陷,像是一个陷阱。
我的身体变成弓形,渐渐有些举步维艰。我几乎喘不上气来,我听见我那破损的心脏仿佛一台年久失修的发动机,风把我的帽子一把揪走,扔给站在一边颤抖不止的一棵小树,风把我的头发揉乱,又一根根拔掉。我捂着伤口落荒而逃,摇摇晃晃,拼尽全力,终于重新躲进屋里。
我快要昏厥过去了。我听见门被风凶狠地摔打着,窗户咔咔作响,连窗棂上的玻璃都被风的强力吹得渐渐凹进来。但是却没破碎。
大地在战栗,晕黄色的太阳在风挥动的纱幔中黯然无光。风使原野上的电线发出呜呜怪叫,也把电线里的声音拉得越来越紧,宛如再一用力,就能将声音折断!一只鹰在村庄上空双目紧闭,一动不动。钩形的头和爪之间,此刻也没有弑杀和诡辩,它顽固、坚持,终于崩溃一样被风扔得远远的,一下扔到山那头的野河滩上了。
我心惊胆寒地坐在椅子上,我觉得风早已把我的骨节与骨节之间拉脱臼了。我瘫软如泥,脑子像个被盗空的仓库,不能思考,也不能瞌睡。像个无生的白痴或傻瓜。
而房子仍然在摇晃,连房基都在簌簌作响。刚才,在我出去游逛时,整栋房子一定被北风那只老野兽粗暴地移动或虐待过了。现在房子低眉顺眼,连大气也不敢出,听凭那恶徒的摆布。
房子开始缓慢倾斜,餐桌上的玻璃器皿和碗橱里的瓷盘先后掉落、跌碎,棚顶的白炽灯在剧烈的晃荡中尖叫一声,蓦然熄灭。水缸、木箱、立柜和米桶都在纷纷呼救,而灶膛中鬼火一样的余烬,忽然噗地一下,灰飞烟灭了……
平原上的落日
平原上的落日就像京戏中的老生唱腔一样旷茫和苍凉,好多次我从省城回老家,正好是夕阳西下的黄昏时分,舒适宽敞的长途大客车在辽阔苍茫的高速公路上疾驰,仿佛小船在风平浪静的湖面上闲闲漂泊,除了些许轻微的颠簸和发动机的嗡鸣,几乎感觉不到那风驰电掣般速度的威力,放眼车窗外广袤无边的冬日的旷野,一派北国惯有的黑土平原的静穆与寥远。
长久以来,在我和落日之间,似乎达到了某种默契。坐车时我总是习惯性的选择右侧靠窗的位置,为的是有机缘能与那老友般的自然景象有个交流的享受(有时,如果不能达到这么个小小心愿,我会宁愿忍饥挨冻等待下一趟车,这似乎成了我内心的某种秘密)。
而此时此刻,落日正像一位睿智、达观的老者,信步向西天一步步行进。我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她绚烂的背影,在高速行驶的车厢里,我与落日之间虽然相隔万里之遥,但是,我俩倒常常能相视会心一笑。我们默然无声,纹丝不动,只有公路边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飞也似的向后移去。
车厢里的人们正昏昏欲睡。我把目光放在原野上偶尔闪过的逐渐灰暗的村舍、道路或暮霭里缓慢移动的行人身上。我看见一辆三轮拖拉机正无声地向零乱的村庄驶去。开车的是一青年壮汉,而坐在车厢板上的却是两个扎着花头巾的乡村女子。他们是收工回家么?我猜测他们正在往家里赶,因为眼下正是村妇们煮晚饭的时辰,家家烟囱里都冒出一缕缕淡淡的饮烟。饮烟在向晚的微风中被吹得稍稍有些歪斜,并且一律被夕晖染成了橘红色。
黝黑的平原深处,另一对骑自行车的农人也正缓缓往这边赶,(由于光线晦暗,他们几乎被我忽略掉)。我仔细眺望,发现坐在后车座上的女子,正把两只手紧紧搂住骑车男人的腰,同样扎着头巾的脑袋也惬意地倚靠在男人宽阔的背上。
夕阳在跟着车子奔跑,我发现夕阳简直无所不在。
夕阳给整个大地都涂上一层柔和温情的油彩。只要你有耐心,仔细去睃巡,总能在一小垛遗弃在田畴上的苞米秸的干枯的叶子上,在一小块冻严实了的鱼塘的冰面上,在沼泽地中央一大丛野芦苇的白穗中,在一排排电线杆的瓷轴或细长的铁线上,在猛然闪过的一条宽阔大河的白茫茫的激流冰缝的涌动里,夕阳总是给我们留下那梦一般绚丽的光泽。
车厢这时倏忽一暗,落日仿佛一颗熟透的果子,猛然加快了脚步,向起伏不定的地平线坠落。而在此之前,落日是由耀眼的灿烂逐渐过渡到温和的平实的。这一过程极像某个伟人向平民的角色互换,或一个帝王,一个被大众追捧的神向芸芸众生的还原,当那层光泽缓缓消逝,人们会从他们身上读到沧海桑田、世事苍凉的戏剧性的历史感。
这是对的,一个人失去外在的伪装,才能显露其朴素的内心,才可以与我们注视和交流,才能以仁厚的广博对待世事万物。我在与落日的无声对白中,总是能读懂她眼中流露的苦闷与惆怅,读懂她由如日中天时的辉煌到卸去重负日薄西山时那灵魂上的欣悦与松弛。她好像落回土地的一枚榛果,为肉体的归宿寻找到了安歇之地。
蓦然,一只暮鸟啼叫着,一耸一耸越过幽暗的大地向静默下来的西天飞去,我似乎嗅到了一种灰烬般的气味弥散开来,耳畔同时响起挽歌似的合唱,落日沉入了地平线之后,莽莽苍苍的东北大平原在青带子一样的高速公路两畔,如同终于平和下来的晚潮后的大海,而车厢里良久无言的我,此刻则完全成了一条沉入梦乡的鱼。
草香
世人皆爱鲜花的芬芳,我却独喜草香。
上小学时,学校开始向学生征集各种东西。因是乡村小学,所收之物自然离不开农副产品:粮食啦,蔬菜啦,冬季生炉火的木柴啦,野花椒粒儿啦,天麻、细辛等野生药材啦,晚秋的大茧啦……等等。除此之外,春秋上学时,我们还要左肩背书包,右肩挎土筐,为学校的农用田捡拾牲畜屙的粪便(那是少年时代的我最讨厌的一项劳动)。记得走在崎岖难行的山路上,我们十几个小伙伴一边匆匆赶路,一边双眼贼溜溜四下睃巡,偶遇牲口遗下的粪便,便飞也似抢上去。因为那个饥饿的年代,牛啦、羊啦、毛驴和马骡这些牲畜是断断不允许农民自己饲养的,大牲畜都归了公社和生产队,普通农家养几只鸡鸭都受限制(口粮少得很),所以路上的粪便也极难遇上。我常常因为难以完成任务被老师责骂得哭鼻子。好在这些繁重的“苦役”中还有一项我比较喜欢的,那就是每年八月。给学校喂养的牲畜割秋草。
草哩,是靰轆草,榛柴秧子或毛毛狗。八月骄阳似火,我和几个小伙伴各自荷了镰,扣顶草帽便进了山。我们自然知晓哪旮旯草势丰盛,草质肥美,我专挑一丛丛一簇簇的毛毛狗下镰,其他草种我总因个人好恶而懒得眷顾。
那时阳光如瀑,白白地眩目着。山陡林疏,崖岩森森。耳听得水响却见不到那细如麻绳的山溪,我将唾沫吐在手心,甩开背着的干粮和外衣,紧紧腰带,便伏身低头刷刷刷地割将起来。
草儿又柔软又韧性,汁浆在草茎中流淌,手臂借助腰劲风卷残云地反向一搂,便有清郁的馨香扑面而来,透过鼻息和肚腹,一直沁入到小小的心脾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香气啊,多少年逝去后我仍然能嗅到它的余味,它入心入肺的精灵之气。仿若一场带着母性体息的薄雾,又似若有若无的一场淅淅春雨。我总是在这一瞬间闭一闭眼,身子像被什么打了一下似的,我紧慢吸上几口。又徐徐吐出口浊气,全身便如洗过似的,真是清爽得不得了。
这时,山雀子在林梢上咕咕……咕咕地啼唤着,草蝇和蜜蜂也嗡嗡然于周边。一条青花蛇悄然游走于岩缝间,好像清凉的涧水。而一枚蓦然跌落的松果,沿着山石嶙峋的阳坡一直滚到幽深潮湿的沟底,恰好挡住了一队举着树叶铿锵前进的蚂蚁的去路。
就这样日影西斜,转眼到了半下晌,伙伴们正相互吆喝着躺下小憩。我啃了半块玉米饼,又寻到那只闻其声的山溪饱饮一顿,这才一屁股坐下来懒懒地胡思乱想。脊梁上的汗早已把破了几个口子的布衫浸透了,山风吹来,脊梁便凉丝丝地。我索性把布衫扒下,挂在矮灌木丛上(我讨厌汗,汗那东西不光咬人,也咬衣裳哩,因为被汗经常浸过的布衫,一点也不禁刮磨)。
而八月的天真是蓝得可以啊。看久了,仿佛能把人和心智整个融化进去似的。我斜躺在那儿呆呆望着高高穹隆,以及穹窿上偶尔路过的云朵,嘴里无聊地嚼着一根随手折来的毛毛狗草茎,遐想着迷雾一般的未来岁月。草汁有点淡淡的苦味,又有点清新的甜,就如同山里孩子的命。我若无所思慢慢地咀嚼着,直到碧绿的汁液染满嘴丫……
通常我要割整整十大捆才能收工回家。草儿割回后,剩下的工作就是摊在空地上晒晾了。但是初秋的九月常常淫雨连绵,如果一垛垛草捆不及时避雨,就会因潮气捂困而腐烂霉败,变成毫无用处的黑灰色朽草,那时不仅牲畜们不吃,连生火也燃不起火苗,真正成了百无一用的废物了。所以整个九月,我都会照顾宝贝似的精心看管那些渐渐褪去绿意的草儿。直到它们充分吸收阳光之后,变成黄灿灿的金色干草。
啊,那是一些多么美丽柔净的干草啊!草秆又轻又软,散发着温润如玉的光泽。草叶和草茎被牙齿嚼咬之后,你会品尝到一种甘冽的清香(这时候的草香宛如被窖封、腌制或酿造之后的纯净和憨厚,而不是青草时代的尖利和刺激了)。草的味道真像一坛封制百年的老酒。而喜滋滋的我哩,也真恨不能变成牛啦、羊啦、马啦或撅嘴的毛驴子,美美地享受一顿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