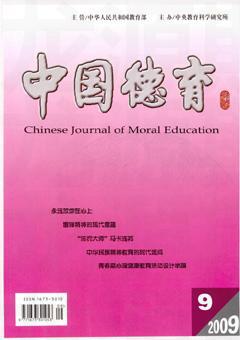民族精神教育笔谈
郑富兴
编者按 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是指民族传统文化中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教育部规定从2004年开始,每年9月为“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各地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以中华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教育为重点,集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所以,研究民族精神,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期特辟专栏就民族精神教育进行理论探讨,以期进一步引起大家对这一话题的理论研究兴趣,也为大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实践提供借鉴。
关于民族精神教育的责任主体性
我国的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但是过去那个没有自我、强调牺牲的时代让人们对民族精神产生了一些消极的认识。就学校教育而言,正如英国学者约翰•怀特指出的,如果国家缺乏对个人自由的信仰,那么,为国家的教育就是真正的为“国家”的教育,这会导向极权主义。这种思想就是强调“必须教育孩子们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个并不存在的超个人的实体。实际上这是欺骗人的。为的是让人们相信存在着一个‘国家,国家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因此为了国家的利益要牺牲他们自己”。现在有些人认为,强调民族精神会限制个人的自由和自主,忽视个人的价值与幸福。随着人们的主体意识逐渐确立与增强,人们对于强调群体至上的民族精神似乎表现得越来越淡漠。
但是,社会民众的民族精神并没有丧失。汶川大地震中人们的自发救援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精神对于拯救处于危难之中的民族有着重要价值。地震灾难中的自救行为和自发的援助行为正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许多西方媒体都认为,感动世界的正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善良、勇敢、坚韧不拔,在以往任何灾难中都未曾看到过像中国这样的举国动员的能力、勇往直前的决心和强大的团结互助的精神。正是勤劳、勇敢、坚强、乐观的民族精神维系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生生不息。
民族精神是维系一个民族群体生存与延续的核心价值,但是民族精神教育针对的是个体,民族精神教育的实质是培养一个国家里的青少年对本民族倡导的价值的自愿认同,因此,民族精神教育要在个体层面获得内在支持。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依据法国思想家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对个体层面的民族精神教育,也即民族精神教育的责任主体性进行探讨,从而挖掘出个体化社会中民族精神教育的新意义。
列维纳斯的伦理学思想致力于思考主体与他者的伦理关系,故而被称之为“他者伦理学”。“他者伦理学”的形成源于列维纳斯对西方哲学的“同一化”特点的批判。列维纳斯从西方哲学中寻找到了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社会暴行的思想根源,那就是“把他者还原为同一”的权力哲学。这种“同一化”的特点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操纵与被操纵的工具性关系。列维纳斯认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在起源上和根本上是伦理性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一种为他者负责的关系。列维纳斯虽然强调他者,但是他并不否认主体性,只是否认为己的、自我中心的主体性,他从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的角度主张一种“为他”的主体性,一种责任主体观。这种“为他”的主体性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形成的,为他人承担责任正是自己主体性的表现。从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来审视主体性,意味着“为他性”就是主体性的展现。一个人的主体性就是主动为他人承担责任的自主性与能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主体性也就表现得越强烈。所以,主体性不是对他人的支配能力,而是一种为他者承担责任的能力。这就是责任主体性的含义。当然,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具有普遍性,没有特地针对民族这一特殊的共同体,但它仍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民族精神是处理个体与其他民族成员的关系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的共同特征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即不是人与人的你争我夺,而是互助互帮,为了群体的共同生存而相互负责。人的自由、自主不是要摆脱这些责任和民族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按列维纳斯的观点,人的主体性并非遗世独立、一枝独秀,而是在人与人的互助互帮之中得到展现。只有在交往关系中才会产生真正的主体性。无视别人的自我独立、自主自由并不是真正的主体性。那种主体性针对传统社会群体力量对于个人的精神压制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主体对抗结构性压制的关系运用于平等个体之间的交往关系时,往往会产生扭曲,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操纵与同一化。主体性在于主体的人性力量的显示。主体性的强弱程度体现为主体自身的力量大小。就同一民族而言,个体的主体性大小取决于个人为民族中的他人承担的责任,即承担的责任越大,彰显的主体性越强。比如,民族英雄就是主体性得到最大彰显的人。如果一个人自私自利,即使他能够独立思考,自我辩护,却只能是一个主体性缺乏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精神正是个人主体性的集中体现。
但是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不具有足够的主体性,或者自甘“奴性”,因而就认为自己不用“为他”,这是否合理呢?这就意味着民族精神最后要靠个体的良知决断来支撑,也就是说,为了防止受到良心的谴责,为了避免压在心头的负罪感、愧疚感,个人也要勇敢地承担起为民族共同体中他人的责任。这实质就是强调良心的最后防线。我要为他人负责,因为民族里的我们是一种共存的关系。只有意识到这些,才能真正改进民族精神教育,使人们获得个体内在支持的基础。
在个体化社会里,责任主体观含有一种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即列维纳斯所说的:他人对我恳求,需要我回应,我对他人具有责任。如果学校教育只以增进个人幸福为目的,那么个体成长的过程中可能始终认为幸福便是一切。其教育结果就是培养出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人人追求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忽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其结果就是削弱民族凝聚力与民族精神。所以,英国学者安迪•格林强调,尽管学校教育在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公民意识方面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已被相对弱化了,但是教育促进社会稳定和团结的功能仍然很重要,尤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化作用下。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本身就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
我们强调人的主体性不是自我的独立,而是对他人的帮助,对于他人的过错、灾难承担自我的责任。这种责任是集体的责任,哪怕这种过错不是自己的罪行。对于民族其他成员或同胞承担无限的责任,正是自我主体性的体现。责任越大,自己的主体性彰显得更突出。这种责任主体性是能够维系群体生存的个体基础。因此,个体化社会里民族精神教育的新意义在于一种责任主体性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