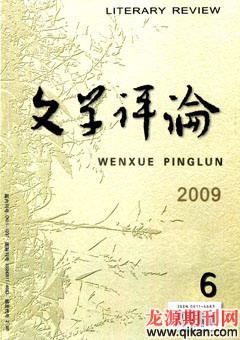中国当代文艺学知识建构中的焦虑意识及其价值诉求
段吉方
内容提要: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的理论重建和价值重建除了从文学整体思维方式入手探索理论转型道路之外,更应该重新理解当代文学经验中的“文学性”问题。在媒介与技术、视觉与图象面前,“文学性”问题仍然作为一种思想底色与文化原质起到重要的作用,当代文艺学研究仍然具有严肃对待当代“文学性”问题的接受语境的能力。
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问题引发了诸多的争论,学者们殊途同归地发现了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随着社会语境与文学生态的变换,中国当代文艺学面临着多种学术资源融汇与整合的压力,更面临着当代文化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在文学理念、思维形式、研究方法、话语体系、表达方式等方面面临着时代与自身理论生命力的双重挑战,由此出现了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的危机与焦虑。本文试图探索这种“焦虑”的背景与成因,以期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走出焦虑的“危机”提供一种思考的方式。
一、“文艺学危机论”:一个反讽的命题
“文艺学危机论”是当下文艺学界广泛讨论的命题。所谓的。危机”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随着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向纵深发展,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知识话语、运思方式和理论思维正日益失去对现实文化经验的解析能力,文艺学知识生产和建构已不适合当代文化经验的突变,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与人们现代文化体验间的距离日益明显,出现了“理论消亡论”的危机。(2)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崛起,中国审美文化现实快速进入了一个极度感性化、肉身化和平面化的历史时段,审美文化研究越来越体现出把握当下文化体验的优势,文艺学研究面临文化研究的挑战。(3)当代技术与传媒力量日益发达,传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面l临着电子媒介的挑战,出现了所谓的“文学消亡论”。(4)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影响了文艺学知识建构和传授方式,文艺学研究存在着“宏大叙事”的困境,文艺学知识生产和建构面临自身理论生命力的危机。
“文艺学危机论”是一个“反讽性”的命题,其“反讽性”就体现在它是在“繁荣”的假象中展现出了种种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仅仅来自异域文化思潮与理论思潮的压力,还在于理论话语的深入遭到了有效性和共识性的挑战,知识生产和知识建构与当代审美文化现实之间出现了裂隙。这些困境一方面影响了文学理论问题本身的探讨,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当代文学研究格局中文学理论乃至文艺学学科的生命力。目前学者们迫切要求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收效甚微,甚至让困境愈演愈烈。为什么“文艺学危机论”会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文艺学知识话语繁荣的时刻?这是首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从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现实来看,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论断。从整体上看,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论争与建设,如人性论主题的重新确立、文艺学方法论的突破、文艺学主体性问题的论争等等,中国当代文艺学逐渐摆脱了长期以来极左语境对文艺观念的禁锢,开始努力建构自己的品格,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但是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到如今,文艺学研究也并没有完全规避知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诸多问题,对单一性政治阐释观念的逆转在短时期内强化了文本审美特性意识的同时,也在审美复杂性问题的认识基点上出现了文学本体论研究的困境。而且随着西方文论的融入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当代深入,这说明当代文艺学研究在多重历史语境中还面临着一定的话语压力和困境,而从当代文艺学研究现状而言,理论观念和思维方法层面上的痼疾也导致了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层面上的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在整合多种文论资源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话语的过程中存在着知识生产上的重复倾向,知识建构过程在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难以实现根本性的变革,二是文艺学研究对具体的文学生产、文学理解与文学接受层面上的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把握,文艺学知识的逻辑建构和表达难以在现实文化语境的变迁及文学经验的裂变中展现知识更新的能力;三是对文学的政治阐释语境的突破不排除矫枉过正的倾向,使得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建构的整体观念与当代现实文化经验的裂隙不断加大,也使文艺学内部知识的更新与研究范式的转换出现了面对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困难。这些困境集中体现了中国当代文艺学在逻辑建构与理论效应上的两难,既无法忽略多重的理论资源又难以找到创造性融会贯通的道路,既无法回避当下文学经验的现实性又无法找到在整体上把握现实文化经验的有效途径,因此它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如何应对理论的危机与困境问题,而且还涉及如何理解当代文艺学的学科定位、当代文艺学研究如何面对文学理论知识系统中的古典意识和古典情结等复杂的问题,特别是现当代文论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与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建立有效的交流机制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文艺学危机论”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文艺学研究的焦虑意识。
二、文艺学研究的焦虑意识及其表现
文艺学研究的焦虑不同于通常的“文学的焦虑”。“文学的焦虑”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它是一种特殊的时代病。即使在文学高昂的时代,比如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时代、20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以及现代主义文学时代,文学的焦虑也是存在的。文学的焦虑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文化矛盾。在文化上升时期,作为社会个体的作家知识分子困囿于时代大潮的风云变幻,他们的焦虑既是一种文化上的困惑,也是一种哲学上的思考,还表达了一种特殊的精神使命感。歌德、雨果、波德莱尔、左拉、王尔德、本雅明、卡夫卡、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都在特有的文化时代表现过这种焦虑。在特殊的文化时代,“文学的焦虑”体现了作家作为一名社会知识分子特有的文化期待,展现了文学家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忧患意识以及自身精神存在的价值标识。正像美国作家福克纳所说,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职责就是能够表达时代的怜悯、希望、勇气和抗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才是不朽的。文艺学研究的焦虑却传达了不同的讯息,它恰恰体现了文学理论思考的混乱和飘移,体现了文艺学研究在某个时代失去了把握文学生态与文学生产的敏锐性和恰当性。目前这种趋势虽然也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特别是有些典型的文学理论探讨试图在规避这种危机和焦虑,但往往是在理论问题的深入中面临着更深入的危机挑战。我们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为例来说明。
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一个引起了较多关注的理论观念,它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在整合当代多种文论资源中重新进行理论建构的努力,其最大的理论价值是在突破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思维方式的同时,在文艺学的理论观念、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有很大的进步,使文学理论话语基本上摆脱了长期以来制约理论观念深入和思想方法创新的工具理性,在思维方式上则打破了传统文学反映论的僵化观念,从而在理论研究过程中比较注重哲
学基础与理论问题的思辨、文学理论建构与文学事实的变异、理论范式的演进与当代视野的融合等更深层次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的出版、再版、修订以及大范围的使用为标志,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进一步得以推进。《文学理论教程》进一步强调了文学研究在对象、内容和形式上的特殊性,并充分考虑到文学创作在主体层面上的能动性、精神心理层面上的无意识特性以及语言符号运用上的个别性,从反映的对象、反映的目的、反映的形式等方面更加深入地探究了文学的本质属性问题。从而使当代文艺学研究在理论建构与知识话语层面上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还体现了对多种文论资源整合的努力,如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对古代文论与西方现当代文论都有借鉴与引入,如“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文学作品的本文层次和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抒情性作品”这些章节对中国古代文论观念引入较多一“文学创造的主体与客体”、“叙事性作品”、“文学风格”、“文学接受”等对西方文论有较多的借鉴。还有就是较多地展现了本土理论的色彩。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对具体的西方的审美意识形态观念没有过多地引进,甚至对有明显类似理论观念的英国学者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没有涉及,而是体现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者基于中国特有审美文化观念的理论建构,如钱中文先生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就是如此。
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同样引发了很多争论。在这个争论中,研究者大都从马列原著中援引观点来说明自己的理由,都能从经典文献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论述,但学者们的争论并没有对“审美意识形态”与中国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和知识建构的具体过程作深入探讨。而就实际而言,虽然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当代文艺学知识建构与知识生产有很大的推进,但也存在一定的缺憾。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体现了对多种文论资源整合的努力,但在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文艺学知识的表达中,多种文论资源仍然与具体的理论问题存在着阐释的间隔,在有些内容上,古、今、中、西文论只是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和理论证明的材料,这些资源的引入恰恰掩盖了对具体文学理论问题的当代思考。而且,古、今、中、西各种资源各种材料太过庞杂,使理论的思考有淹没在文献材料中的弊病。这说明,这样一种理论观念仍然是在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压力下进行的探索,它的时代性仍然不是很鲜明。其次是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对当代文学生产的意识形态特征没有透彻的说明,而是过多地强调了个人化的审美体验,在文本解析过程中过多地强调了个案性和片段性的审美感受,却忽视了社会政治、经济、媒介变革、社会结构等复杂意识形态变革对文学的影响。最后,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在文学的审美性问题上做了很出色的理论研究,强调文学的“无功利”,“形象性”与“情感性”的特点,但是在对当代审美文化现实的阐释中,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和概念化的缺陷,我们看不到像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文学理论:导论》中那样的对英国文学意识形态性所作的出色的批评分析,而且,某些概念内涵模糊,某些原理重复论证、循环论证也比较突出。比如,在对待文学的“理性”这个问题上,不但没有明确界定“理性”的概念,而且没有指明“理性”与稍后的“认识性”有何区别。在阐述文学的“理性”特征时,论述者这样表达:“从审美意识形态角度看,文学仍然必须依赖理性。只不过,理性在这里是以特殊形式存在的。但是,如果借此以为文学仅仅依赖形象便可进行,那就会大谬不然。”接下来,论述者并没有深刻论述那种以特殊方式存在的“理性”是什么,特别是没有指明文学形象中蕴涵的这种理性与意识形态性有什么关系。因此,综合来看,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在具体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理念化”的趋向,理论建构与审美经验的分析仍然难以找到有效的融合途径,对多重理论资源的整合努力也暴露出了当代文艺学所面对的理论压力,其理论建构的努力引起了当代文论中的“反本质主义”的质疑,而对文学审美特性的重视则引起了文艺学“去政治化”的辩论。这说明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若想成为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和知识建构的合理甚至唯一形式仍然要进行一定的理论突围。这个突围不仅仅是对国内学界质疑之声的呼应,更是对当代迫切的理论问题与现实文化问题的深度探索。
相比“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呼声则更加展现了“雷声大、雨点小”的趋势。这种呼声开始于1996年左右,虽然早在争论刚开始的时候,就有学者宣告了它的结束,但这十年中,学者们围绕着它进行的争论却一直继续。有的学者不但明确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可能的而且提出了转换的方法、方案…。但就现实情形而言,我们并没有看到古代文论转换后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建构过程的深度变革。这里面有一个难点,那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特有的交流媒介和语意转换方式问题。中国古代文论在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传统中浸濡良久,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审美交流机制。自五四以后,中国文学语言革命性的断裂已经形成,完全恢复古文论基于诗性语言系统的交流机制断不可能,以古代文论中的诗性语言来阐释现代审美问题只能是一种“应用性”的“修饰”,“诗性语言”难以真正成为一种本体论的观念注人文艺学知识生产过程之中,而且,现代西方文论中对语言本体功能和语言形而上学意义的解构更在这方面造成了困难,所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即使有方法有方案,也难以真正带来文艺学内部的知识更新和研究范式的转换,充其量是一种“旧话新说”,至少,这十年间,还没有见到任何有说服力和启发性的“转换成果”。
人们在谈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时有一个语境,那就是中国文论的“失语”问题。现在看来,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清理的问题。究竟存不存在“失语”?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其实一直是主动引进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我们引进西方文论为了什么呢?实事求是地说,是借鉴和参考。至于在借鉴和参考中我们的研究出现了什么问题,如片面崇拜西方文论,生搬硬套全面引入西方概念解读文学作品,那只能是我们的理论应用和理论理解出了问题,在这方面,情绪性地拒斥西方文论资源并非解决我们理论难题的方法,而恰恰暴露了文艺学研究的危机与焦虑。这种焦虑一方面是显示了知识生产与建构中观念的混乱性和个人性,二是显示了知识生产的表面化和随意性,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普遍存在“接着说”的就事论事倾向。前不久刚刚偃旗息鼓的“文学死亡论”再度证明了这种趋势。
在J.希利斯·米勒引出了这个话题之后,中国学者明显地展现了积极参与世界性文学论争的“对话渴望”,但是,具体的论争仍然是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假定”的问题论域中进行的。金惠敏先生指出,中国学者对米勒的发言有所误读和误解,而且米勒的论断也有模棱两可的地方”,童庆炳先生也发现,米勒的说法后来有了转变“,这
说明米勒的论断有多少严谨性原本就值得怀疑。在笔者看来,米勒提出的这个问题有较多的经验分析色彩,他的“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观点不但非常极端和武断,而且缺乏明显的学理依据。中国学者在迎战米勒观点时,对他的直接的观点“在媒介时代,文学是否会消亡”均有正面的呼应,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呼应恰恰不是米勒所强调的重点,米勒提出的问题是随着媒介与技术的日益发达.传统的文学表达方式和文学体验方式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文学生产、文学研究将面临新的现代转换的挑战,而这恰恰也是当代中国的文学现实。就当下来说,信息网络时代与图像审美风潮的兴起,感性阅读与大话文学等种种实用娱乐形式日益威胁文化经典与理智思考的空间,文学生产与文学研究的命运的确令人堪忧。在这种情形下,“文学死亡论”不仅是一个论断,也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并不是说文学在现时代“已经”死亡,而是说有某种“东西”让我们警觉文学正在接近“死亡”,这才是值得理论界认真讨论的问题。在回应了米勒的论断之后,中国文艺学界这方面并未继续深入讨论下去,米勒警觉的意识并没有引发中国当代文艺学界深入探索有效的文学应对方案,倒是“将死”的阴疆加重了理论研究的焦虑心态。目前,关于“文学死亡论”的讨论已经渐渐冷却,但“文艺学危机论”所产生的焦虑意识还是存在,当代文艺学研究在危机面前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文学未来普遍的自信与乐观,更需要的是文艺学研究的价值重建精神和文学理论面向当代文学实践的真正的超越性姿态。
三、文艺学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中的
价值重建策略及其现实遭遇
在“文学危机论”和“文学死亡论”面前,有的学者提出:“文学边缘化不等于文学终结”,文学是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只要人类的情感还需要表现、舒泄,那么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就仍然能够生存下去”。也有的学者认为,媒介与技术的发展,使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在向社会各个文化层面渗透中仍然会获得新的存在形态”;图像社会的出现,文学受到威胁,但“图像社会”的出现尚不足以使文学消亡,“文学的未来将为它自己优越而深刻的本性所指引”。这些乐观的探索固然重要,但正像有的学者提出的那样,当代文艺学面临的危机不只是表层的、文学形态意义上的危机,更根本的还是文学本质或文学精神意义上的危机,是一种深层的危机,表现为传统文学所培养起来的文学性阅读的弱化,理性思维与想象感悟能力的萎缩,尤其是精神审美超越性的丧失。
在这种情形下,当代文学艺研究的理论重建和价值重建呼声是很高的,当前文艺学研究中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审美意识形态的论争”、“日常生活审美化”、“反本质主义”都有这种明显的价值诉求。这种价值诉求除了从文学整体思维方式人手探索当代文艺学研究的转型道路之外,同时也涉及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关于当代“文学性”问题的解释与接受的新的趋向。其中“反本质主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所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显。
“反本质主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涉及了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中的一些核心问题,比如文艺学知识格局的陈陈相因、文艺学知识体系的凝固封闭、文艺学知识培养与传授机制的困境、文艺学研究方法的陈旧与失效等等,这种思考与其说是展现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的本体论困惑,倒不如说是体现了普遍化与本质化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建构格局与当代“文学性”问题的接受语境的差距,其中隐含的是对当代“文学性”接受问题的强烈关注。学者们希望进一步将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建构历史化、个性化与细节化,希望在当代文化生态与文化格局中拓展文学理论问题。在这方面,“反本质主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所提出的问题有深刻的理论启发和思想启迪,对当代“文学性”问题的接受语境也有深刻的理论思考。但是,就现实而言,“反本质主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也仍然无法整体把握当代文学经验深层裂变的现实,这两种思考方式在文学经验层面上也存在一定的阐释“瓶颈”。当代文学经验的裂变是在媒介文化、视觉文化、消费文化导致传统文学研究的边界泛化与非经典化过程中造成的,“反本质主义”在扭转传统文艺学研究的本体论思维方式上有一定的冲击力,但在深入当代“文学性”接受事实空间的问题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在把握当代文学经验裂变的具体过程上还没有展现让人信服的实践,因此,以反本质主义思维作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的主打思维还不太现实。
坚持“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研究”的学者强调文学研究融人消费文化大背景,强调以文化研究“回归日常生活”,但以文化研究全然取代文艺学研究的策略也未必可取,以文化研究的眼光检视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缺陷也未必令人信服。“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科形态和研究视野,关注既定社会的文化构成与文化裂变,重视社会文化系统中的新兴文化事物与文化主体,这些对传统的文学研究构成挑战与压力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压力是文化研究学科的学术研究辐射力的正当结果,无论是英国伯明翰学派,还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的文化研究并没有坚持取代文学研究。在文化研究的层面上,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学发展规律、文学的语言特性、文学批评原则等等问题并非完全是一种理论的“虚构”。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早已形成了自己的集中的问题领域,文学本质特性、文学发展规律、文学语言特性、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文学阅读与文学接受,文学批评与实践,这些文学理论问题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文学经验的发展会体现出不同发展的路向,文学精神、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文化、文学与宗教、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媒介等等相关学科交流与渗透也使得文学理论问题研究有不断解决的问题,笼统地以文化研究挑战与颠覆传统的文学研究并非能够对这些问题有根本性的深入探讨。
但是,“反本质主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引出的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文学性”问题却应该引起关注,这也是解决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焦虑意识乃至更深入地探索理论重建与价值重建问题的关键所在。面对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文学性”问题,除了在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等方面有所深化之外,更应该具体面对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文学性”问题接受语境的变化。这个接受语境的变化就是当代文学经验中关于“文学性”的理解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变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娱乐和实用为中心的当代文学经验在“文学性”问题的理解上感官化和消费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文学经验的感官化强化的是当代“文学性”理解上的非理性倾向,所谓“三还原”(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逃避”(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三超越”(超越逻辑、超越语法、超越理性)、“不及物写作”、“下半身写作”、“美女作家”、“身体叙事”、“肉身冲动”等
等就是其集中的表现。文学经验的消费化则直接促使了消费文化的崛起和文学接受的娱乐倾向。市场和消费使文学变成了一种享受的东西,也使“文学性”变成了“娱乐之死”的载体。文学经验的感官化和消费化进一步在社会文化生态中制造了文学经验中的实用主义和媚俗主义,也损伤了传统“文学性”问题所包含的经典意识和精英意识。在这种变化面前,“非理性主义”带给当代文学理论“文学性”问题的不是思维方式与文学观念的解放,而是道德失范价值失衡的非理性冲动,中国当代消费文化缔造的也不一定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很有可能就是日常生活的“庸俗化”。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要突破困境,走出危机,就不能不重视这种当代文学理论在“文学性”问题上的深重变革与矛盾,类似于“反本质主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探索也不应该仅仅是在理论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构方式上继续文学本体论层面上的突围,而更应该关注当代文学经验中“文学性”问题的现实趋向。
在面对当代文学经验中“文学性”问题的变革时,很多研究者把这种情形归结为媒体变革与视觉转向中所产生的异质性文化因素的促发,因此出现了种种“媒介威胁论”和“视觉转向论”。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虽然媒介文化有着极强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媒介时代的来临,为各种异质文化因素的成长提供了可能,也为当代“文学性”问题的接受语境缔造了感官化和非理性化的审美变异的空间,但不影响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文学性”问题仍然有深入人心的可能。而当代文化中的视觉转向问题也并非是当代文学经验中的“文学性”问题变革的唯一结论,而是它的一种展现方式。在媒介与技术、视觉与图像面前。“文学性”问题仍然作为一种思想底色与文化原质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虽然当代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性”问题发生了重要的变革,但当代文艺学研究仍然具有严肃对待当代“文学性”问题的接受语境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在价值重建的努力中走出焦虑意识就不能忽视当代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性”问题的现实境遇,以强化文学理论把握现实文学经验的能力。在这方面,“反本质主义”文学观念不应该是罢黜文学本体追问的理由,“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不应该是过分张扬感性审美兜售欲望与娱乐的口实。当代文艺学研究步人困境并非是接近黄昏,种种可贵的探索仍在继续,危机不是退却的理由,困境不是改换门庭的借口,焦虑与压力是客观的现实,但也正是理论探索的动力,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宣告“理论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