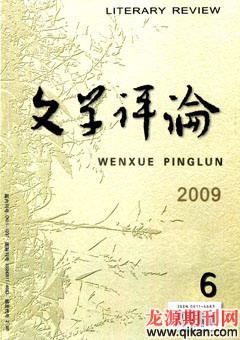论悲剧的美育作用
俞樟华 熊元义
内容提要:悲剧可以培养人的历史意识、担当意识和超越意识。既要发扬光大中国近现代美学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的传统,也要在美育实践中高度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
当前中国有些文艺家在文艺创作中日益广泛地搀人了单调、无聊的成分。这种“恶性娱乐化”倾向在突出感官娱乐的功能的同时抑制了文艺的其它功能。这些单调、无聊的成分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批判的,它满足和迎合人们心灵的那个低贱部分,养肥了这个低贱部分。匈牙利文艺批评家卢卡契曾经尖锐地指出:“过去的伟大小说把重大人性的描述同娱乐和紧张结合在一起,而在现代艺术中则日益广泛地搀入了单调、无聊的成分。”这种堕落的现代艺术在我们这个躲避崇高和娱乐至死的时代日益泛滥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当前中国悲剧创作的缺席不过是中国近现代美学传统的断裂。
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上,那些为中国近现代美学奠定基础的前驱为救亡图存所进行的启蒙运动是高度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的。1904年,蒋观云以“中国之演剧界”为题在引进西方的悲剧概念的同时强调了悲剧的美育作用,认为“虽然,使剧界而果有陶成英雄之力,则必在悲剧”,“而欲保存剧界,必以有益人心为主,而欲有益人心,必以有悲剧为主。”蒋观云这种对悲剧的美育作用的认识对后人影响很大。几乎同时,王国维则引进西方的悲剧理论对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红楼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把握,认为“《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而且认为《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它违背中国人的乐天精神。蔡元培相当重视美育,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说”,“即西人重视悲剧,而我国则竞尚喜剧”,“盖我国人之思想,事事必求其圆满”。在美育中,蔡元培格外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认为悲剧特别感人。1918年9月,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学存在一种“团圆迷信”,“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团圆快乐的文字,读完了,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他认为,西方的悲剧观念是医治中国那种说慌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的绝妙圣药。可见,为中国近现代美学奠定基础的前驱虽然轻视喜剧的美育作用是偏颇的,但他们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这一传统则是弥足珍贵的。
而在一个不断出现悲剧而悲剧创作严重缺席的时代,人们追逐感官的刺激和享乐,在轻松中忘记了生存的痛苦,在陶醉中忘记了人生的追求,甘愿接受各种各样的奴役。因此,我们在抵制各种各样的异化和奴役的过程中不但要发扬光大中国近现代美学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的传统,而且要在美育实践中高度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
一、重视悲剧对人的历史意识的培养。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人们缺乏深厚的历史意识,就很容易为一些短视的“世论”和历史的表象所迷惑。而真正伟大的悲剧作品可以促进人们对整个历史运动的把握,从而超越各种各样短视的“世论”。张承志在他的一系列散文中反复地讲这样一个故事,即一个拒绝妥协的美女的存在与死亡,提出了“世论”和“天理”的尖锐冲突。先是在《清洁的精神》中,接着是在《沙漠中的唯美》中,后是在《美的存在与死亡》中。这个能歌善舞的美女,生逢乱世暴君,她以歌舞升平为耻,于是拒绝出演,闭门不出。可是时间长了,先是众人对她显出淡忘。世间总不能少了丝竹宴乐,在时光的流逝中,不知又起落了多少婉转的艳歌,不知又飘甩过多少舒展的长袖。人们继续被一个接一个的新人迷住,久而久之,没有谁还记得她了。在这个拒绝妥协的美女坚持清洁的精神的年月里,另一个舞女登台并取代了她。没有人批评那个人粉饰升平和不洁,也没有人为她仗义。更重要的事,世间公论那个人美。晚年,这个拒绝妥协的美女哀叹道:“我视洁为美,因洁而用,以洁为美。世论与我不同,天理难道也与我不同么?”张承志认为“天理”与“世论”是根本不同的。“世论”只认强弱,不认是非,绝不相信历史发展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过程,即黑格尔所说的“永恒正义”的胜利。在邪恶势力的强大压力和打击下,我们是妥协退让和屈膝投降,还是坚守理想和奋起抗争?当希望姗姗来迟时,我们如何忍受这漫长黑夜的煎熬和暴虐毒箭的侵扰?的确,对于无数的个体来说,也许抗争是前途渺茫的,甚至是没有希望的。因此,很多人都松懈了斗志,放弃了理想甚至做人的尊严。这就是一些人在日益强大的邪恶势力挤压下不是跻身邪恶势力的行列,就是在轻松逗乐中化解强大压力。他们随波逐流,在迎合中混世,他们麻木不仁,在屈辱中生活。“世论”就是这些人苟活的产物。张承志所说的“我们无权让清洁地死去的灵魂湮灭”,无疑是对这种苟活哲学的坚决抵制。虽然中西悲剧作品都反映矛盾和解决矛盾,但是,它们在反映矛盾和解决矛盾上是各有侧重的。关汉卿的《窦娥冤》和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都有伸冤,即矛盾的解决,前者是父亲为女儿伸冤,后者是儿子为父亲报仇。不同的是,当《窦娥冤》的窦娥的父亲窦天章为女伸冤时,中国悲剧已到尾声。而《汉姆雷特》的汉姆雷特为父伸冤时,西方悲剧才拉开大幕。这两部悲剧都有鬼魂出现。可以说,没有窦娥的冤魂、汉姆雷特的父亲冤魂的出现,他们的冤屈就难以伸张。同样,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都出现了疫情。而这种疫情的产生都是因为悲剧人物引起的。但是,中国悲剧对疫情的追查已是悲剧的结束,西方悲剧对疫情的追查则是悲剧的开始。当然,这种追查的结果不同,中国悲剧追查的结果是真相大白之日,就是悲剧人物平反昭雪之时,西方悲剧追查的结果则是真相查明之时,就是悲剧人物遭到毁灭之日。西方悲剧的悲剧人物俄底浦斯、汉姆雷特都是这种可怕的下场。这就是说,中国悲剧是悲在矛盾解决前,西方悲剧是悲在矛盾解决后。而艺术家选用某一顷刻,“只能是可以让想像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了。我们愈看下去,就一定在它里面愈能想出更多的东西来。我们在它里面愈能想出更多的东西来,也就一定愈相信自己看到了这些东西”。这一顷刻既包含过去,也暗示未来,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最清楚的理解。人们欣赏这些伟大的文艺作品,就要看清它们所反映的这一顷刻的前前后后。而看清文艺作品所反映的这一顷刻的前前后后,如果没有对整个历史运动的准确把握,就不可能达到。孔尚任在《桃花扇》中为什么安排侯朝宗、李香君双双人道?为什么不写晚年侯朝宗的动摇昵?为什么不写晚年侯朝宗的隐逸呢?其实,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所写的侯、李二人,既是对历史上的侯、李二人的反映,也是对清初仍然没有放弃抵抗的明代遗民的集中写照。孔尚任对历史上的侯朝宗晚节不保的改写,就是对这种投降变节行为的抛弃和批判。这既是对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文化生命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孔尚任等的拒绝和坚守。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到侯、李二人双双“人道”可以看出,清初那些没有放弃抵抗的明代遗民的拒绝更加坚忍,更加悲壮。侯、
李二人双双“人道”虽然看破红尘,割断情根,但仍然是对邪恶势力不妥协的抗争。的确,侯、李二人双双“人道”是他们悲观绝望的结果。“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回头皆幻境,对面是何人?”“人道”已是毫无所待,而隐逸则至少有所期待,即“待恢复”和“待后王”。但是,与隐逸相比,“人道”这种抗争在历史上似乎更加彻底。遗民的隐逸终竟存在大限,即徐狷石所谓“遗民不世袭”。钱穆指出:“既已国亡政夺,光复无机,潜移默运,虽以诸老之抵死支撑,而其亲党子姓,终不免折而屈膝奴颜于异族之前。”而“人道”则割断了情根,没有了后代,在一定程度上就彻底断绝了这种遗民后代的背叛,超越了所谓遗民的大限。因此,没有对整个历史运动的准确把握,就不可能领悟这些悲剧作品所蕴涵的深刻内容,甚至还可能陷入历史表象的迷惑中而为各种各样的“世论”所左右,丧失对这些文艺作品的正确的是非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真正伟大的悲剧作品之所以能够摒弃“世论”和伸张“正义”,是因为把握了整个历史运动。尤其当历史发展出现小人得志、正不压邪的现象时,真正伟大的悲剧作品可以帮助人们透过铁屋,看到一丝光亮。可以说,真正伟大的悲剧作品破除了历史表象的迷惑,是人们度过漫漫的长夜不可或缺的。
二、重视悲剧对人的担当意识的培养。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不但反映了个体和群体的矛盾即智叟和愚公的冲突,而且蕴涵了群体的延续和背叛的矛盾。《愚公移山》只是肯定了愚公的斗志,却忽视了愚公子孙的意志。智叟看到愚公的有限力量,而没有看到愚公后代无穷尽的力量。所以,智叟对愚公移山必然是悲观的。而愚公不但看到自己的有限力量,而且看到了后代的无穷力量。因而,愚公对自己移山是乐观的。不过,愚公却没有看到他的后代在移山上可能出现背叛。愚公子孙后代只有不断移山,才能将大山移走。而愚公的子孙如果不认同愚公的移山,而是背叛,那么,移山就会中断,大山就不可能移走。也就是说,前人的斗争精神能否在后人身上延续,不仅要保存后代的生命,而且要教育后代继承和发扬这种斗争精神。否则,等待人们的就只有绝望的死去。后人的历史担当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在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登幽州台歌》中,我们强烈感受到了这种担当意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置身在广阔的天地和悠久的历史中,个体是多么的孤独寂寞。但是,个体可以勇敢主动自觉地承担“古人”和“来者”之间的延续。这就是说,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绝不是陈子昂的胡敲自叹。它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渴望“古人”和“来者”的提挈,而是勇敢主动自觉地承担延续“古人”和“来者”之间的精神文化血脉,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是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品格。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指出:“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而司马迁认为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这似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幻想一种现世报应,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节不到”。这种现世报应的思想在近现代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其实,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绝不迷信这种现世报应。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第六十一》中就深刻地质疑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他不仅是怀疑,“甚或焉”,而且还对“天道”提出了质疑,“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种强有力的质疑在中国历史上绝不是空谷足音。剧作家关汉卿在杂剧《窦娥冤》中借窦娥的口就提出了同样的质疑。在《窦娥冤》中,窦娥说:“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窦娥由怨生怒,“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窦娥不仅对掌著生死权的天地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而且对黑暗社会有了清醒的认识,“呀,这的是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但是,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关汉卿等,都没有绝望,没有放弃。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虽然深知天下无道,但是,他们仍然以弘道为己任,守护和捍卫“道”。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出也。”孔子坚守道和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弘道上真正做到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台生取义。这种精神文化血脉在优秀中国知识分子中代代相传和延续。如果我们的生命和正义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即使生命遭到毁灭,但是仍然可以显世,可以不朽。所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是追求所谓的现世报应,而是自觉地和正义和道紧紧地熔铸在一起,在代代相传和延续的正义事业中获得永生,获得不朽。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承担。司马迁要求正义之士附青云,附骥尾,虽然是“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但是,毕竟这是对人类的正义事业的延续。在中国悲剧中,正义是在一代一代的奋斗中得到延续和发展的。而在西方悲剧中,正义是在悲剧人物不自觉的毁灭中发展的。在中国悲剧中,悲剧人物是自觉地发展和延续了道和正义。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不但是历史正义的化身,而且在道德上还是完善的。中国悲剧的正义力量不是因为自身的局限而遭受毁灭,而是因为邪恶势力的野蛮摧残和毁灭。因此,正义力量的暂时毁灭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罪有应得,而是无辜的,正义力量在道德上是完善的,没有罪过和不义。其实,中国悲剧既有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的先后毁灭,即悲剧冲突的双方的先后毁灭,也有正义即道不但得到延续,而且是在克服重重困难和阻遏后取得胜利。中国悲剧对现存冲突的解决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不是诉诸某种“绝对理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而是诉诸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物质力量即正义力量。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即正义力量是在同邪恶势力的反反复复的斗争中克服重重困难和阻遏后最后消灭邪恶势力并取得胜利的。因此,这种悲剧作品可以培养人们自觉的担当意识。
三、重视悲剧对人的超越意识的培养。在历史上,柏拉图是反对悲剧的。柏拉图认为悲剧“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的那个(在我们自己遭到不幸时被强行压抑的)本性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而“替别人设身处
地的感受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为自己的感受,在那种场合养肥了的怜悯之情,到了我们自己受苦时就不容易被制服了”。本来,柏拉图是不应该反对悲剧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要求人们“应该要自由,应该怕做奴隶,而不应该怕死”。这种自由精神正是悲剧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于柏拉图所说的悲剧“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的那个(在我们自己遭到不幸时被强行压抑的,)本性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虽然是悲剧的重要部分,但不是核心部分。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尽管肯定悲剧“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但仍然没有把握悲剧的核心部分。而在西方悲剧理论发展史上,只有席勒和黑格尔,才逐步揭示出悲剧的这个核心部分。这就是他们不但把握了悲剧冲突,而且正确地揭示了悲剧的美感是这个悲剧冲突的解决的反映。黑格尔指出:“亚里士多德曾认为悲剧的真正作用在于引起哀怜和恐惧而加以净化。他所指的并不是对自我主体性格协调或不协调的那种单纯的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即好感和反感。……我们必不能死守着恐惧和哀怜这两种单纯的情感,而是要站在内容原则的立场上,要注意内容的艺术表现才能净化这些情感。”不过,席勒认为悲剧冲突的解决是人类主观努力的结果,即人在道德上的自觉,而黑格尔的悲剧冲突的解决是客观世界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西方悲剧理论发展史上,席勒首先把悲剧的冲突及其解决看作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认为悲剧的美感就是这个历史过程的反映。席勒不但提出了悲剧冲突,而且提出了三种类型的悲剧冲突,即“某一个自然的目的性,屈从于一个道德的目的性,或者某一个道德目的性,屈从于另一个更高的道德目的性,凡是这种情况,全都包含在悲剧的领域”。其中,席勒所说的某一个道德的目的性屈从于另一个更高的道德目的性这种悲剧冲突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黑格尔的悲剧冲突理论的“先声”。席勒认为,悲剧冲突及其解决就是道德的目的性和更高的道德的目的性的胜利。而黑格尔则认为:“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中。”在悲剧里,永恒的实体性因素以和解的方式达到胜利,它只从进行斗争的个别人物方面剔除了错误的片面性,而对于他们所追求的正面的积极因素则让它们在不再是分裂的而是肯定的和解过程中表现为可以保存的东西。这就是说,在悲剧结局中遭到否定的只是片面的特殊因素。这些片面的特殊因素在它们的活动的悲剧过程中不能抛开自己和自己的意图,结果只有两种,或是完全遭到毁灭,或是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假如它可实现),至少要被迫退让罢休。所以,悲剧的结局是一种灾难和痛苦,却仍是一种“调和”或“永恒正义”的胜利。可以说,黑格尔这是天才地猜测到了历史正是在对立、矛盾和矛盾的解决的过程中前进和发展的。但是,黑格尔把这一历史过程归结为“永恒正义”的发展,他不是寻求解决矛盾的现实的物质力量,而是不分是非,对矛盾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最后是“永恒正义”的胜利。因此,黑格尔尽管认为悲剧的结局不是灾祸和痛苦,而是精神的安慰,但是他反对将这种结局理解为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种单纯的道德结局。也就是说,黑格尔反对的是个别行为的善恶报应,但没有否定人类整体追求的善恶报应,即黑格尔并不否定历史的正义。在这个基础上,黑格尔提出了调解论。黑格尔指出:“在单纯的恐惧和悲剧的同情之上还有调解的感觉。这是悲剧通过揭示永恒正义而引起的,永恒正义凭它的绝对威力,对那些各执一端的目的和情欲的片面理由采取了断然的处置,因为它不容许按照概念原是统一的那些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真正的实在界中得到实现而且能站住脚。”而“悲剧情感主要起于对冲突及其解决的认识”。显然,席勒和黑格尔的悲剧观是建立在对整个历史运动的把握的基础上的。中国悲剧与黑格尔的悲剧观相比,这种宏伟的历史感似乎更加显著。中国悲剧在反映现存冲突和解决这个冲突中,不但敌我界线分明,而且是非分明,爱憎分明。在中国悲剧中,既有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的先后毁灭,即冲突双方的先后毁灭,也有正义即道不但得到延续而且是克服重重困难和阻遏后取得最终胜利。在这一方面,它和西方悲剧没有根本的区别。但是,中国悲剧对现存冲突的解决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不是诉诸某种“绝对理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而是诉诸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物质力量即正义力量。这样,中国悲剧就和西方悲剧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中国悲剧的正义力量在道德上是比较完美的,没有罪过和不义。他们不是因为自我的局限而遭受毁灭,而是因为邪恶势力过于强大。因此,中国悲剧的正义力量的暂时毁灭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罪有应得,而是无辜的。正义力量在大团圆这种现实世界的延续和发展中经过不懈地努力和奋斗,最终战胜和消灭了邪恶势力。这种正义力量终将战胜邪恶势力的历史真相,在现实生活中也许难以看到,但在伟大的悲剧作品中却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人在沉重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和打击,甚至还会出现牺牲,这是悲痛的;但是,人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则是愉快的。而当前中国不少文艺作品不是努力挖掘那些悲剧人物在沉重生活中的抗争,而是着力表现这些人反抗的失败和幻灭。在这些文艺作品所反映的一些人的生活中,斗争和发展停止了。这些人在异化中虽然感到自己的毁灭,从中看到自己的软弱无力和一种非人生存的现实,但是,他们仍然屈服于既成的不合理的秩序,放弃了斗争。与此相反,真正伟大的悲剧作品则培养人的审美超越意识,使人获得改造现实生活的力量。
当前中国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不仅促使人们在以往优秀悲剧作品的熏陶下获得启迪。而且敦促当代杰出的中国文艺家直面现实,创作出更多的优秀悲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