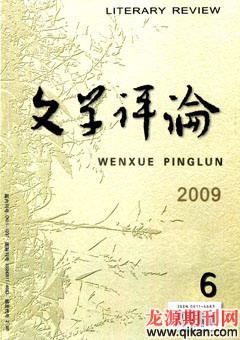神与光
陈 卫 陈 茜
内容提要:艾青是中国现当代诗人中的一个最具典范性的诗人。他见证了旧中国的苦难、新中国的诞生和灾难后的复苏,他的诗歌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见证,再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对于他的评价,人们往往结合意识形态,将其视为一个革命性诗人。然而,他的诗歌内蕴复杂,其中对宗教的表达及意象的借鉴,在文学史上尚未得到充分认识。本文欲从艾青诗文细读中把捉宗教意识的流变痕迹,以期对艾青诗歌进行全面评估,并重新评价诗人在文学吏上的形象建构。
艾青,共和国诗人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他的诗作影响了几代诗人和读者,在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中国自由体诗传统发展到40年代的集大成者”。得到高度评价的是艾青诗歌主题上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忧虑,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艺术上着重太阳与土地的意象特征、色彩运用以及语言上的散文美。
然而当我们从艾青最初的作品开始阅读时,发现艾青是多面目的。正如杜衡对诗集《大堰河》的评价:“这集子,里面所包含的长短篇虽然总共不过九题,但我们的诗人可就取了几种不同的姿态在里面出现。”这与我们现在阅读到的文学史中形象不尽相同。共和国的文学史上,艾青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如果说艾青有不同的姿态,那么不同在何处?姿态间是否有一定的关联?再就是,艾青如何被塑造成一个共和国诗人?就像水果被制成果脯,加工后的滋味与形态会改变它原先的芬芳与色泽。我们现在的文学史上有不少被不同程度加工的作家,在笔者看来,艾青的形象有待进一步还原。
一文学史中的艾青形象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学的中文系使用的大多是唐瞍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介绍艾青的一段话是:“艾青是浙江金华人,生于1910年,自小在山区长大,接近劳苦人民,培养了对农村的深厚感情,这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的生活源泉和思想基础。中学时代经受了大革命的风暴,阅读到唯物史观的书籍,启发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这种向往,经常闪耀在他以后的诗作中,并引导他走革命的路。”这段文字中,我们能看出写作者明显的阶级立场,山区、劳苦人民,农村、革命、唯物史、社会主义等标示意识形态内的词语在为我们塑造一个革命诗人的形象。我们并不否认艾青的革命立场,可是我们从艾青30年代的作品中看到,艾青在接受唯物主义思想的同时,他写过《会合》、《透明的夜》等革命性诗篇。当他因参与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饱受疾病折磨时,他想到过耶稣,想到了耶稣的死,写下过《一个拿撒勒人的死》。
艾青诗作进入牛汉、谢冕《新诗三百首》选本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太阳》、《我爱这土地》、《鱼化石》;进人大学中文系教材的,如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品选(1917-2000)》中有《大堰河——我的保姆》、《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第二册);《礁石》、《古罗马的大斗技场》、《虎斑贝》(第四册)。这些作品是可以证明艾青诗歌的主要风格。人们往往说:《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我们看到的是阶级的同情,《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表达的是对贫穷土地上的老百姓的热爱。这些诗是爱国爱民的诗。90年代的文学史观念有了一定的变化,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上》中认为艾青“是一个能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融汇于自己的创作个}生而讴歌时代的诗人”。评论颇为中肯,但是对艾青诗歌意象分析缺少适当展开,比如指出:“《太阳》里太阳意象的系列表现很奇特,这些象征抒情含意深远,令人遐思无限。”“太阳意象到底奇特在什么地方?
早在1936年,胡风应茅盾之约写了《吹芦笛的诗人》,这是艾青诗歌评论中影响较大的一篇。胡风把艾青比喻成是吹芦笛的诗人,肯定艾青对家庭的叛逆,“诅咒”马赛和巴黎,并且也肯定他喜欢那里的诗人。他还认为艾青的《一个拿撒那人的死》“至情地歌唱了对于人的爱以及对于这爱的确信。”《大堰河——我的保姆》写出了“用劳力用忠诚服侍别人的农妇底形象”,作者对这形象“呈诉了切切的爱心”,作品提出了对于“这不公道的世界的诅咒”,告白了他和被侮辱的兄弟们比以前“更要亲密”。果真是这样吗?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胡风的评论还是新旧文学史,都有一个巨大的裂痕没有弥补,这就是艾青诗歌中的宗教意识的存在及其流变被回避了。艾青的诗歌中,存在两个传统,一是宗教传统,二是五四传统。宗教传统给他的诗歌带来了忍受痛苦、死后复活的主题,五四传统就是传播对旧制度的叛逆,对统治者、侵略者的正义反抗。这两种貌似对立的主题都统一在艾青早期的诗歌中,寻找到了契合点。不知是因为艾青参加革命的身份还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原因,直到新时期思潮自由了,才有个别研究者专文谈及艾青诗歌中的宗教意识,因其多从艾诗作品中找出《圣经》映像,对诗中宗教意识在时代语境中的变化尚未涉及。笔者认为艾青的宗教意识直接影响到他的意象系统形成与演变,从认同到矛盾,乃至否定,大致可以分成三期。希望通过对此剖析,让我们看到文学史上更为真实的艾青形象。
二《圣经》与艾青早期的诗
艾青早期的诗歌,有着明显的宗教意识。具体说来就是《圣经》更像他的一个文学读本。艾青在创作中,从耶稣的形象上汲取写作资源,从《圣经》中的故事,环境描写以及意象中得到诗歌灵感。
1933年,艾青因为革命,被关进了监狱,肺结核病严重,让他想起《圣经》中那个“要救人的如今都不能救自己”的耶稣,于是写下了《一个拿撒勒人的死》。将《圣经》中记载的耶稣被犹大出卖、判刑和走上十字架的故事进行汉语改写,突出耶稣的神性:耶稣被贪财的犹大出卖,自己对十一个门徒交待自己要回到所来的地方。世界都要受到审判,“帝王将受谴责/盲者、病者,贫困的人们/将找到他们自己的天国”。土地与幸福都会归还人们。诗歌完整描述了最后晚餐的谈话,写到法官彼拉多审判耶稣的情形:犹太民众、祭司长与长老们的嘶叫,耶稣在众人的唾骂声中走上了十字架。被钉上钉子时,有的信徒哭泣,有的人嘲笑他,他与盗匪一同被行刑。艾青把耶稣之死写进诗歌,应该有内心深切的感受:群众觉悟不高,面对一个甘愿用自己生命挽救大众的英雄,他们缺少同情和信服,而耶稣尽管经受这样的侮辱与苦难,还在为理想奋斗。此诗的选材角度正是为了凸现耶稣的大爱与高尚。
1936年,艾青再一次从《圣经·新约》中取材。《马槽》写的是耶稣诞生的故事:处女玛利亚在马槽生下无父的耶稣之后,被人嘲笑和辱骂,诗中除了描写环境的恶劣,最重要的是母亲对着未谙世事的孩子说的话:“你记住自己是/马槽里/一个被弃的女子的儿子/痛苦与迫害诞生了你/等你有能力乐/须要用自己的眼泪/洗去众人的罪恶”。诗歌再次描写了苦难的降临以及如何面对苦难,这正是艾青用来激励自己和同仁坚持革命的箴言。
具体说,《圣经》给了艾青两个向度的支持:一是精神信仰,二是形象的借鉴。主要是耶稣的形象,并由耶稣形
象衍生出借代性形象,如忍受苦难者的大堰河、补衣妇等形象。另依据《旧约》中“创世纪”描写,艾青的诗歌中还出现了相应的天/地,明/暗/,昼/夜等暗合的带有比喻性的意象群。
(1)借代性形象与意象的衍生
面对苦难,忍受,并且体现出大爱,1933年艾青完成《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的大堰河就是这样的形象。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并且是一个地主儿子的保姆,加上艾青采用写实的笔法,写她的家庭,她的劳作,她死后的寂寞,读者往往将她当作一个社会底层、贫困勤劳的农妇形象,没有将这一形象与耶稣形象联系起来,在诗歌中看到的就如胡风所言。我们不妨在艾青一系列的排比中,重新审视大堰河的形象:她含者笑,洗着我们的衣服,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她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她含着笑,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大堰河,为了生活,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她就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大堰河,深爱着她的乳儿;——《大堰河——我的保姆》节选。大堰河,一个遭醉酒丈夫打骂的妻子,土匪、小学徒的母亲,受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和“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的农村妇女,在寒冷的冬天,做着那么多活,她为什么还能“含着笑”?她爱什么?只是因为爱这个地主家的孩子吗?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大堰河不是一个具有强烈女性观和阶级观的农村妇女,她不仅没有反抗打骂她的丈夫,也没有把地主的儿子拒之门外,心甘隋愿去劳作,而是含着笑。难道她是一个有智力问题的农村妇女?也不是。艾青的意图不是要强调阶级与性别立场,也不想指责她的愚昧无知,他同情她的早死,被生活压迫而死。从“敬你”“爱你”的结句中,我们能够体会诗人对大堰河深沉的感情。结合同时期写的耶稣之死的作品,大堰河,这个劳作在中国土地上的普通农妇,同样被赋予了宗教徒对于耶稣的那份隋感。
艾青的诗歌中,从耶稣之死引申题材的还有纪念左联五烈士的《春》(1937),诗歌借用了《圣经》中谓耶稣为“人之子”来比喻这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他起来了》(1937)可以看作是耶稣原型与中国语境结合的创作。这也是一个生活在屈辱中的人,“从敌人为他掘好的深坑旁边”,带着血,带着笑,起来了。他起来之后,诗人预言“将比一切兽类更勇猛/又比一切人类更聪明”,这是一个死而复生的圣者形象。
如果说中国的农业文化产生了对自然、土地生产“周而复始”的一种描述,那么艾青诗歌中的土地意象更接近宗教意识,诗歌中充满的是生命“复活”意念。在1937年,他写下了《死地》、《复活的土地》等篇。《死地》是为旱灾而作,诗中土地比拟为“临终时/依然睁着苦干的眼”等着下雨,最终“死在绝望”里的人。诗歌描述死去大地干涸,只有“男人的叹息/女人的咽泣/与孩子的哀号”,可怜的地之子们伸出像“冬天的林木的枯枝般的手/向死亡的大地的心脏/挖掘食粮”,最终都倒毙了。诗人描写了人们生存的痛苦,但没有绝望,在诗篇中写到活着的人“旋舞着愤怒,/旋舞着疯狂”。《复活的土地》可看作是续篇,诗中的土地就是神的人格化身,“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
除了复活意念,另一些土地意象的诗篇描摹出生存的坚忍。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1937)中写的是被寒冷封锁的中国和“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的岁月的艰辛”,《我爱这土地》(1938)描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在苦难当中,两首诗都有“我”在。前诗中的“我”虽然与人们一同“憔悴”,但是希望“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人们“些许”的温暖;后诗中的“我”愿意为这片土地而“死”,而“眼里常含泪水”。显然,“我”对苦难中的人民的同情,也颇有耶稣那种人之子的赤诚。
三象征性意象
文学史一般把艾青诗歌的中心意象概括成土地与太阳。笔者认为这两大意象系统并非沿袭中国诗歌传统,而是暗合《圣经》中的天/地,明/暗/,昼/夜意象,并且意象具有象征性质。
如《会合》,写了一群在“灯光下面”的脸,他们团团的坐着,来自东方,“每个凄怆的、斗争的脸,每个/挺直或弯着的身体的后面,/画出每个深暗的悲哀的黑影”。此场景不免让我们想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在最后晚餐时的悲悯。“窗外是夜的黑暗包围着”,而“房子里,充满着温热”。虽然诗歌语言看上去较为粗糙,然而我们看到了一群类似圣徒的人,在黑夜里寻找光明。
在笔者看来,文学史上提到的艾青诗歌中的太阳意象为光明意象可能更为贴切。在光明意象系统中,包括太阳意象,还有与之相关的光、黎明、煤、火、灯等意象皆可纳入,它们可视作为耶稣形象的象征性转换。
典故来自《圣经》。《旧约》“创世纪”中写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圣经·新约》“约翰福音”中讲到光——“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神派约翰来,就是来为光作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耶稣自己也对世人说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光是大爱,可引申为光明的前景、希望、理想等。它在经书中从耶稣的喻体转化为象征本体。
在艾青30年代初期的创作中,光与暗,灯与黑的意象是结合在一起的。1932年艾青创作的《阳光在远处》中写到的阳光是和暗云形成对比性意象出现:“阳光在沙漠的远处,/船在暗云遮着的河上驰去”,用“暗”来描述旅客的心,而阳光这时是外在的自然现象。《那边》中描写了黑的“河流”。黑的“天”之间,“无千万的灯光”,其中的“警灯”“警告着人世的永劫的灾难”。《当黎明穿上了白衣》(1932)、《黎明》(1937)、《监房的夜》等写的都是:光的到来驱走夜的黑暗。
与光相近的的意象,有灯(《灯》1933-1935?)、煤(《煤的对话》1937)还有太阳(《太阳》1937)、黎明(《黎明》)。太阳意象,与郭沫若诗歌中的不一样,郭沫若的《太阳礼赞》中的太阳代表一种新的生活和理想,“太阳哟!请你永远照在我的面前,不使退转!/太阳哟!我眼光背开了你时,四面都是黑暗!”闻一多早期诗歌中也有Ⅸ太阳吟》,太阳象征着祖国和对祖国的怀念。艾青诗歌中的太阳意象具有更为复杂的含义。
《太阳》(1937)中,“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向我滚来的”的太阳是穿过时空的永恒生命体,它让大地复苏,“使生命呼吸”,“冬蛰的虫蛹转动于地下”,让我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太阳就像是《圣经》中的耶稣一样,有再生不死的力量,有给他人带来万福的力量。如《吹号者》中吹号者死去时,“太阳,太阳/使那号角折射出闪闪的光芒”,太阳增加了希望的能见度。在《向太阳》(1938)
这首长诗分九个篇章,抒情主人公怀着激动的感情描写太阳的到来,“用囚犯第一次看见光明的眼/看见了黎明”,诗歌描写了黎明到来之后的街头生活,回顾了没有太阳的昨天,“我把自己的国土/当做病院”,现在看到太阳,觉得“太阳比一切都美丽”,让人想起“博爱平等自由/想起德谟克拉西/想起《马赛曲》《国际歌》/想起华盛顿列宁孙逸仙和一切把人类从苦难里拯救出来的人物的名字”,相信“太阳是美的/且是永生的”,太阳照在街上每一个人的脸上,少女、老妇,工人和士兵身上,“我”被“这新生的日子所蛊惑”,我向太阳高歌而去,愿意“我的心胸/被火焰之手撕开/陈腐的灵魂/搁弃在河畔……”诗歌中,太阳给人带来新生。这依然可看作是耶稣意象的衍生含义。
四转换当中的宗教意识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艾青成为抗日一分子。他辗转大江南北,在炮火硝烟中穿行,看见现实苦难的蔓延,愈发觉得死亡更加真实……诗歌留下了这些见证。在艾青这时期的诗中,宗教性因素减少,对现状真实描绘增多。
(1)土地意象的转变
1939年在桂林时期,艾青针对侵略者写了《我们的田地》,描写土地与人民生活的关系。1940年创作的《农夫》中,把农民幽作土地:“你们的阴郁入土地/不说话也像土地/你们的愚蠢,固执与不驯服/更像土地呵”。1940年在湘南写的《土地》,将土地比拟成苦难中的中国人,“幸运与悲苦呀,哭泣与欢笑呀,/互相感染着,互相牵引着……/而且以同一的触角,/感触着同一的灾难”。
由土地衍生出旷野意象,在艾青的诗篇中多处出现。《圣经》中,旷野(Desert)具有丰富的比喻,如《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中,摩西领着以色列人走在旷野中,没有水喝,耶和华显灵将水变甜。耶和华为了让老百姓信他,选择在西奈旷野中让老百姓安营,然后在山顶传出他的十诫。旷野是考验不诚信人的地方,耶和华本打算让摩西带领众人经过旷野到迦南美地,可是以色列人的抱怨遭到耶和华的惩罚,他让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尸首在旷野消灭”。旷野意象在《圣经》中,成为一个苦难之地,也是显圣之地。
1940年,艾青先后写了两首具有俄罗斯油画般厚重的抒情诗《旷野》。对旷野意象的热衷,不单单是他有过农村生活体验,《圣经》或他喜爱的凡尔哈伦。都有影响。在年初写就的《旷野》中,描写了田园的荒芜,旷野是“平凡,单调,简陋/与卑微”,“静止,寒冷,而显得寂寞”。在“灰黄而曲折的道路”上走着的人们,“向着不同的方向,/却好像永远被同一影子引导着/结束在同一的命运里”,让读者的眼前不免要出现神的意象,然而诗人要表达的不是神,而是“在无休止的劳困与饥寒的前面/等待着的是灾难、疾病与死亡”。30年代诗歌中所传达出来的忍受与复活的高昂状态被诗人否定了,他不相信有救世主,“彷徨在旷野上的人们/谁曾有过快活呢?”
等到七月份,大地的成熟景象使艾青又产生了描绘《旷野》的冲动,“广大的,蛮野的……/为我所熟识,又为我所害怕的,/奔腾着土地、岩石与树木的/凶恶的海”。就像曹禺的《原野》一样,这里包蕴着卑微、愤恨、沉默、悒郁、贫穷、劳苦,险恶,它潜藏着生命的原动力,让“我的胸中,微微发痛的胸中,永远汹涌着/生命的不羁与狂热的欲望”,每当有苦恼时,“看着旷野的边际——无言地,长久地,/把我的火一样的思想与情感/溶解在它的波动着的/岩石,阳光与雾的远方”。
(2)宗教信仰的怀疑与反叛
如果说面对苦难,艾青还没有完全绝望,那是他还有一个太阳意象在支撑。这是一个希望和绝望共存的悖论式意象。40年代,它也失去了宗教中的神性光辉,更多的是在世的光芒。同是1940年创作的《太阳》,表达了对它的极度渴望和愿意为之付出一切:“只要你会以均等的光给一切的生命/我们相信这话你一定会有一天要证实/因此我们还愿意活着在泥泞里像蚯蚓/因此我们每天起来擦去昨天的眼泪/等待你用温热的手指触到我们的眼皮”。
从诗歌内容看,艾青的宗教信仰的确发生了动摇。1940年在《新的伊甸集》中虽引用了《旧约》中耶和华把亚当赶出去伊甸园的故事,不过是借用。在参观苏联农业展览会照片之后,他欣喜地看到了一个新的伊甸园,“在神与恶魔的妒视之下”,这里“遍地是金果与自由的笑”,这里的人“阅读的不是什么‘圣书,/他们阅读的是‘土地永有法令”,在艾青的心目中,现实远比原典中的伊甸园更美好。他们用“庄严的调子歌颂一个名字一/那名字是万人的喜悦,宣言着正义”,这里人们对这一名字的景仰,仍似《圣经》中描写的教徒之态,但这个名字不是神,暗示了改变国家面貌的领袖。
1942年《给姊妹们》是一首向宗教表示反叛的诗歌,取材于《圣经》中的夏娃、亚当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自从我们的始祖夏娃、亚当/被自私的耶和华驱逐之后,/我们就永离了伊甸乐园,/一起流浪在这广漠的土地”。对耶和华的态度有了转变,如诗歌第二节认为自然给人类的恩惠,不比“狡猾”的耶和华少。第五节充满暗示:“几千年了你们被囚在‘家中,/撒谎者拿着‘美德欺骗你们,/他们说‘顺从是女人的天职,/要你们永远无报偿地劳动”。诗歌具有解放女性的意识,认为女性在宗教的麻痹之下,没有醒悟过来。如果说艾青这时是一个女权运动者的话,他同时还是拆除《圣经》教义的革命者。他对耶和华的态度与对希特勒一样。《希特勒》(1942)“这是一个骗子,/吹牛是他的本领,/自从拿大炮当做牛油/即以谎话喂养人民”“想用白痴和野蛮,/代替人类的文明”。《没有弥撒》(1940年4月4日)中虽然有《圣经》中常用的词汇如弥撒、祈祷等,但是艾青对宗教的态度转变十分明显,“不需要什么祈祷/旷野是和我一样的无神论者”,而且,太阳会“给我说着/Materialism dialectic(注:英文,唯物辩证法)的真理”。七天之后创作的《太阳》就含义较为复杂了。“同我们距离得那么远/那么高高地在天的极顶”,这可以看作是自然中的太阳,也可以看作是不可触及的精神存在。为此,“我们渴求得流下了眼泪”,“我们为朝你匍匐在地上”,“我们为向你飞而折断了翅膀”,“我们甚至愿在你的烧灼中死去”。“太阳”成为崇拜的对象,“只要你能向我们说一句话”,“只要你会说:凡看见你的都将会幸福,/只要勤劳的汗有报偿,盲者有光”。那么,从诗句所表达的内容来看,光就是《圣经》中神的化身。如果我们从《没有弥撒》来推论,那么,这里的“太阳”不是神,而是诗人心中的崇高理想。
艾青的诗歌中有很多人物的素描,可分成圣人、普通人与魔鬼形象,一类是拿撒勒人、《春》中的“人之子”,延安解放区的农民吴满有、毛泽东等圣人或英雄形象。一类忍受苦难的普通百姓形象,如大堰河、补衣妇、乞丐等。还有一类是恶魔,如希特勒。《希特勒》一诗看上去是对战争狂希特勒的咒骂,但也可以看作是艾青对西方文化重新审视之作。他认为打着爱人类信仰的西方人士,为了争夺
利益,对中国进行利益的分割,不过都是像希特勒那样实行法西斯统治。这或许也是他选择舍弃《圣经》的原因之一。
(3)光意象的转变
1940年之后,艾青诗歌中的光的意象发生转变。在《火把》这首叙事诗中,照亮人们,照亮城市的火把与迷途的唐尼的寻找形成复合式的指向,唐尼本来是要寻找恋人克明,但是克明要做革命工作。在第十五节中,艾青引用了《圣经·新约》“约翰福音”中的十二章十二节,省略的内容应该是“只有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在这一节诗中,李茵向唐尼讲述了自己靠着革命书籍从失恋中解脱出来,参加革命团体,在工作中感觉到“无论如何苦都觉得快乐”,唐尼听后感动得表示,自己要从恋爱当中走出来,“李茵/你是我的火把/我的光明一这阴暗的角落/除了你/没有人来照射”。在作品中,李茵被塑造成完美的革命者即“光”的形象。
艾青宗教意识的转变,并不妨碍他继续在诗歌中歌颂太阳。1942年《给太阳》中描写到:太阳光辉能够驱逐噩梦,强烈、庄严,“一切生命将”“在你的光辉里沐浴我的灵魂”。这时候的太阳还是圣人吗?笔者并不这样认为,这首诗中的太阳意蕴相对30年代的要更加丰富。此时的艾青身处延安解放区即革命圣地,那么,太阳我们除了可以看作是艾青常说的真善美的化身,也可以看作是伟大的人物。或许就是毛泽东。因为艾青另有一首诗《毛泽东》(1941),写于前一年。毛泽东在哪儿出现,哪儿就沸腾着鼓掌声一“人民的领袖”不是一句空虚的颂词,他对人民的爱博得人民的信仰;他生根于古老而庞大的中国,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身上,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对于领袖,《给太阳》中的意象也可以看作是时代的景象,或是新的信仰。在1941年12月写的《时代》一诗中,写着当“我”望着山岗和天空时,心里感受到奇迹,看见“一个闪光的东西/它像太阳一样鼓舞我的心”,自感受到这一奇迹,“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表达上仍象是《圣经》中崇拜者对着上帝唱出的诗篇。
《太阳的话》模拟了太阳的口吻。太阳可以理解成是神,结合艾青自己的阐说和时代语境,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美的使者,真的、善的化身。“我带着金黄的花束/我带着林间的香气/我带着亮光和温暖/我带着满身的露水”,“让我把花束、把香气、把亮光,/温暖和露水洒满你们心的空间”。
1943年的《迎》描写的是对太阳的迎接:“它是骑了黄金鬣毛的马驰骋来的/它是从善背后向山颠疾奔来的/它是从松林那边向旷野欢呼来的”,因为它“给我生命的鼓舞、热与光”。可以看作是一种能量,让人的生命重新勃发生机的力量。文字表达与《诗论》中的句子“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那三个轮子,闪射着同等的光芒,以同样庄严的隆隆声震响着的:就是真、善、美”。那么,太阳还可以是诗神,是真、善、美。
五唯物论认识及诗体借鉴
新时期以后,艾青对人和上帝的认识发生转变再一次表现在诗歌中。
《美的展览》中写道:“人主宰着自己,/人创造着一切,/人操纵一切,/人是万物最美的”。这时的艾青,就像又经历了一次文艺复兴,他不认为世界的主宰是上帝,而是人。他甚至质疑上帝的形象,如《人和上帝》仿佛有了彻悟:哪来的上帝人创造了上帝却说:“上帝以自己为模型创造了人。”人在欺骗自己却把责任推给上帝积累的问题太多了人和上帝互相埋怨——上帝说“我后悔创造了你你对我是不虔诚的。”人说:“我比你更要后悔为什么用你来欺骗自己”经历了中国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历新中国以来历次运动的艾青,可以说是像广大中国人一样,承受了巨大的苦痛,他的生存就像他多次描写的土地一样,坚韧、顽强。新时期的艾青,写作热点增加了。就他新时期的作品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咏物诗、哲理诗、体育诗、旅游诗。艾青诗歌中的光的意象仍然被读者关注,不过表现的时间和空间,所阐发的意蕴,更复杂了。
《光的赞歌》(1978)是艾青归来的代表作。这首与当年《向太阳》的篇章同样是九章,但是描述性的画面少了,激情少了,反思增加了,教谕也增多了。这时的艾青是一个智者。诗歌没有早期那种跌宕起伏的流畅情绪,而是在工整的排比中表达对历史、政治、社会、人生的思考。诗歌描写的主题是:每个人“只要他一离开母体/就睁着眼睛追求光明”。看上去仍然和《圣经》中门徒寻找耶稣的光一样。可是中国的现实环境变化了,主要的意识形态也确立了。诗歌第一章写了光的重要性:没有光的世界,“我们对世界还有什么留念”;第二章写了“光”给人类大干世界、艺术和美。第三章讲光的来源,“诞生于撞击和摩擦/来源于燃烧和消亡的过程/来源于火,/来源于点/来源于永远燃烧的太阳”。这几句诗可以看作是艾青对从30年代以来毫不厌倦地歌颂“光”的意象的注释。光是黑暗的对立体,黑暗可以吞蚀光,光可以照亮黑暗。作为能源的光,它会消耗,会消亡,它是火、是太阳的化身。诗歌将光以人格化,“胸怀坦荡、性格开朗/只知放射、不求报偿/大公无私,照耀四方”。就像40年代郭沫若在历史剧《屈原》中的方式一样,屈原眼中的雷和电是铲除奸臣的正义化身,艾青笔下的光也成为高尚者的化身。这里并没有当成上帝形象来塑造,而是当成高尚者的品质。第四章中相应塑造了一些小人的形象,肯定“只有通过漫长的黑夜/才能喷涌出火红的太阳”。诗歌将光与太阳进行了意象的转换。第五章站在科学的角度,进一步对意象进行比喻性转换:“愚昧就是黑暗/智慧就是光明”,歌颂因为光明,我们才有了现代科技,才有了真理。第六章从历史的遭际中谈到光与暗的辩证关系,歌颂“我们的信念/像光一样坚强一/经过了多少浩劫之后/穿过了漫长的黑夜/人类的前途无限光明、永远光明”。第八章写每个人都是一粒微尘,“无数的微尘汇集成一片光明”,“我们的生命就是燃烧”,“即使我们死后尸骨都腐烂了/也要变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烧”。在诗中,我们依然遇见了艾青激情,遇见了《我爱这土地》时对于死亡的寄托。然而,他的诗歌更多地流露出社会,或者说社会运动之后加强的一些主流意识观念:如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如生命与事业、理想的选择。曾经那个忧郁而不妥协,激情而又敏感的诗人,锻造成了一个新时期主旋律的演奏者、民众的发言人。我们不否认诗歌中饱含着诗人的生命意识,也不否认诗人对真理执著的追求,如第八章所写“我是大火中的一点火星/趁生命之火没有熄灭/我投入火的队伍、光的队伍/把‘一和‘无数融合在一起/为真理而斗争”。这一年的春天,中国大地上正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艾青紧跟时代的要求,看到“光在召唤我们前进/光在鼓舞我们,激励我们/光给我们送来了新时代的黎明”,表示愿意“让我们从地球出发/飞向
太阳”。显然,在诗歌中,光不再是上帝的光,而是太阳的光,太阳在艾青的个人语汇中,是真理、希望、理想、真善美等与形而上相联的象征性意象。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发生了观念上的彻底转变,拥有了唯物主义者的坚定信念。但需要补充的是:意识的转变并不成为我们判断诗歌好坏的标准,我们只是试图客观揭示艾青诗歌宗教观念的演变过程。而有的文学史家出于政治或某种需要以此来评定诗歌的价值,在后文中将予以探讨。
艾青诗歌语言的散文美已为研究者多次论证。笔者只想说的是:艾青诗歌以流畅的口语写作,与其说来自五四传统,不如说受到《圣经》诗篇和箴言的更多影响。如《大堰河——我的保姆》、《毛泽东》、《鲁迅》、《播种者》、《光的赞歌》等都是赞美诗,《鱼化石》和《镜子》等咏物诗都采用箴言的形式。《无题》有六十九篇,也都为箴言性质的道德诗篇,
如:“难道把头仰起来/就以为比别人高了吗?”(五),“正直人的咒骂/胜过虚假的恭维”(六十七)。还有不少诗篇引用《圣经》的句子。如《播种者》中引用《旧约·诗篇》中的句子“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作为歌颂鲁迅所用。
1939年艾青写的《诗论》和《诗人论》等,也都是采用箴言的形式,一些词语来源于《圣经》。如《诗人论》第三节中对英雄的描述“他们最坚决地以自己的命运给万人担戴痛苦;他们的灵魂代替万人受着整个世代所给予的绞刑。”第五节中写到的他们“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了解他们灵魂的美,只有他们才能把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第八节模仿了《圣经》中祈祷诗篇的表达形式。只不过聆听着并非上帝,而是诗人,里面仍然有耶稣被审判的片断。诗人啊一但愿那些你们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的众人,不致向你们身上投掷石块,这样就好了,至于彼拉多的愤恨,祭司长和长老们的嫉妒,法利赛人的污蔑,那算得了什么呢?《圣经》给了艾青诗歌灵感和最初写作方式,战争完全改变了艾青对于宗教信仰的态度。30年代受到神的感召,40年代受到革命思想的感召,80年代成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这就是艾青。
六艾青形象重估
自传性质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与《我的父亲》可以说演绎了艾青诗歌中的宗教与“五四”两个传统。《大堰河》中的“我”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一个农村妇女的乳儿。“我”厌恶自己的父母家庭,而敬爱这位不幸的养母。“我”对大堰河就像耶稣传播出来的爱那样,不以贫富,血缘的亲近来决定爱谁。1941年,已经是革命队伍中老战士的艾青,写下了叛逆性诗篇《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母亲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接受梁启超的影响,小村庄里“最初剪掉乌黑的辫子”。喜欢读新刊物,生活现代化,想要建立“新的家庭”,“女儿送进教会学校,/督促儿子要念英文”。可他是家里的暴君,用皮鞋和鞭打管束子女。可是,在“我”的眼中,父亲还是一个剥削者,他经营小店铺,“三十九个店员忙了三百六十天,/到过年主人拿去全部的利润”。还有无数的田地、地产、雇农、佣人。诗歌中对“父亲”表达出一种鄙视。像无数的中国地主一样:/中庸,保守,吝啬,自满”,将五四时期反抗家庭专制的呼声对准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就是这样的两种传统,在与阶级、政治结合的过程中,艾青诗歌中流淌的大爱被部分遮蔽了,革命性随后得以强化。
共和国的诗歌史上,艾青的影响的确不可忽视。从30年代开始创作,与他同时期开始创作的诗人有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臧克家等人,都没有像他那样保持长达五十余年的创作生命力。尽管中断了十多年创作,“文革”结束后,从放逐边疆旷野飘泊回京的艾青,就像复活的耶稣继续传教那样,重新开始了诗歌写作。中华民族来自外与内,存亡危机与精神迫害的种种苦难,艾青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都承受着,反抗着,沉默着,写作着,因此艾青的诗特别容易让从苦难中走来的读者青睐。
艾青的诗还影响了更年轻的绿原、牛汉、穆旦、北岛、叶延滨、海子等著名诗人的早期创作。对人民的同情或赞美,给土地、太阳赋予新的生命,成为新中国诗歌中的经典性意象,艾青也因此成为共和国文学史上的代表性诗人。《大堰河一我的保姆》、《旷野》、《手推车》、《冬天的池沼》、《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献给乡村的诗》、《村庄》、《我的职业》等诗篇由于诗歌的时代性,意象的画面感,来自艺术家艾青对颜色的敏感,还有里面灌注着从心底传出的苦难、悲愤、忧郁、平静、高昂、兴奋、期待,都能感染任何一个时代的读者。但是或许没有过苦难经历的人不容易被打动,也就不容易理解艾青的诗。或许人们对比艾青和他所喜欢的西方诗人之后,会说:艾青的诗中还有凡尔哈伦、有阿波里内尔,有波特莱尔。我们也都不否认,甚至还会补充:艾青诗中还有屈原、李白和杜甫、白居易的影子。生活在太阳下,难免会有影子在地上。
不过,直接影响到对艾青诗歌艺术成就评估的,是他的一部分政治诗歌。比如1943年的《吴满有》,解放后的一些诗《抓得好》、《打得好》,直到80年代,《全世界都看见天安门》。这类诗缺少诗人自身的情感,口号化的痕迹明显。
我们正视艾青的这些平庸之作,但也要注意到文学史家对艾青发生的误读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忽视艾青写作的文化传统。二是名家对艾青的解读导致普遍性的误读。三是因为时代关系,时代精神的原因,政治化的创作倾向掩盖了艾青个人的诗歌特色。这种误读其实直接导致了90年代艾青被重估,不过同样是一次片面的评价。以穆旦的优势和艾青的劣势进行对比,对艾青来说,这是有失公平的行为。
研究艾青诗歌意象的流变,让我们再一次思考文学史写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问题:文学史不应该是写作者的需要史。站在个人角度或时代需要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删节处理,都掩盖了诗人创作的真相。文学史也不应该是某一时代的个人排行史。因为时代美学的变化,会导致形象的放大或缩小。学术标准尽管会有差别,但文本是客观存在的。尽可能置身于创作语境中研究文本,尽可能让研究对象自己的作品来说话,那样就不会重复或袭蹈非历史观念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