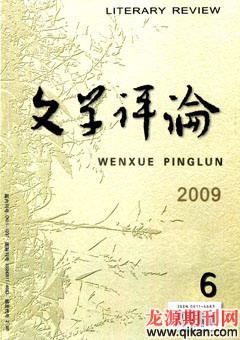中国古代小说写人研究的新变期待与修辞维度
李桂奎
内容提要:近30年来,人们呼唤并期待选择新的维度来实现中国古代小说写入研究全面突围与变新。我们认为,本土化的现代修辞批评能够成为一条新的路径。这主要取决于古代小说的“寓言”性质及“写”与“人”等要素的修辞性。在具体应用中,以狭义的“语言修辞”为基础和纽带,在“戏剧修辞一社会修辞一语言修辞”与“语言修辞一诗性修辞一哲学修辞”两个层面上融通,重构古代小说写入理论体系,对古代小说写入展开“拟剧”批评、“拟画”批评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化修辞批评,以尝试实现这一新变。
一“典型”理论挂帅的
写人研究模式渐行渐远
20世纪初,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经结合《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古典名著,最早论述了中国古代小说写人艺术的发展历程。随后,人们沿着这一研究路数将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典型”理论引入中国小说写人研究,并全面推而广之,使之成为一个歧义迭出、包罗万象的世纪性关键词。其中,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及《致敏·考茨基》中的“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这两封信中的两句话,几乎被当作创作和研究的金科玉律,成为上世纪旧式小说写人研究的核心理论。不仅如此,人们还由“典型”生发出艺术典型、文学典型、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典型形象、典型性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典型化等一系列概念。在“典型”挂帅的批评观念下,人们关于小说人物的研究大多包含政治理念或价值判断,而关于人物的其他精神风貌的探讨远远不够。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典型分析”的热潮渐行渐远,人们才在冲破种种社会化批评的遮蔽后,开始积极地尝试运用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文化学等多种理论方法来对小说人物形象作多维度、多层面的开掘,得以用新的话语表述小说人物形象。于是,各种日趋人文化的“多重论”以及与之相仿佛的“面面观”、“组合论”等观念得以散播和推广。如刘再复在谈到《性格组合论》写作的缘起时说,他除了受到鲁迅评《红楼梦》等作品反对“把好人写得都好,坏人写得都坏”的创作思想启发,“还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这就是:人”。为此,他要把人物分析建立在复杂性格理论基础上。相对于以往好与坏、正面与反面等泾渭分明的简单化评判,“性格分析”的“组合”说无疑显得更为科学,其创新意义自不待言。只可惜这种探讨还只是风光一时,而未得探索前进。近年,在全球多元化文学批评隆盛之时,“典型”理论已彻底衰落。在对这一理论功过得失的清算中,有的论者对“典型”大厦的轰然倒塌而拍手称快,如高波《“典型”——坍塌中的文学迷信》(1995)断言:“随着新兴的文艺观念及艺术趣味不再迷信‘典型塑造,‘典型独占文学殿堂、如日中天般的辉煌将一去不返。‘典型这一文学迷信,正随着本世纪的晚钟而坍塌!”也有的论者对其存在的合法性大胆质疑,如降大任《“典型论”质疑》(1999)指出:“这一理论存在内在矛盾,在实践中作家难以具体把握,不可能对创造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与传统审美观和方法论相悖。”并进而认为,它曾经一度成为“文革”中“三突出”理论的理论支柱,产生过严重的负面影响,理应彻底推倒。关于“典型”理论大势已去的颓景,南帆《典型的谱系》指出:“统计可以显示,典型这个术语出现在文学批评之中的频率愈来愈低。必须意识到,这不仅是某一个理论术语的过时;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支持这个术语的一批命题正在逐渐失效。”一句话,“典型”理论及其主导下的文学研究已经风光不再,再用“典型”理论阐释小说写人问题已显得颇为陈腐落伍。
与此相类的另一端是,上世纪的人物分析研究大多从社会学的角度展开,人们往往采取“人物论”和“人物谱”等方式,对小说人物作道德评价和性格剖析,如太愚(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1948)、孟超的《金瓶梅人物论》(1948)、李希凡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1960)、石昌渝和尹恭弘的《金瓶梅人物谱》(1988)、朱一玄的《红楼梦人物谱》(1997)、陈美林的《儒林外史人物论》(1998)等等。如此下来,古代各大小说名著的人物都被“论”或“谱”过,这些“人物论”和“人物谱”多侧重于阐释人物个性或思想风貌,或通过追踪其原型而纳人某种“众生相”,或勾勒人物生平简历,或理出人物传记,或对其功过得失、善恶美丑作评议,并最终归结出褒贬性的考语。此番研究,如果站在更高的理论层次认识,即可称作“小说人物学”。
除了从社会学视角的“小说人物学”研究,人们还从“人物描写”、“人物塑造”等角度,对以小说为主的各种文本的写人技法进行了例证式的赏评,如吴调公的《谈人物描写》(1979)、王先霈的《小说技巧探赏》(1986)、马振方的《小说艺术论稿》(1991)、张稔穰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1991)、傅腾霄的《小说技巧》(1992)、刘上生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1993)等论著中的相关内容,重在探讨实现某种写人效果的艺术手段和技巧。不过。时至今日,且不说“人物论”、“人物谱”研究因公理缺失而导致公说婆道,失去了叙述研究的底蕴,就是具体笔法研究也面临着人云亦云的危机,许多研究普遍存在大同小异地套用“肖像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等话语问题,难免有兜来兜去之嫌。其间,已经有人开始反思这套话语,如周汝昌在论及《红楼梦》的写人艺术时说:讲说《红楼》艺术,特别是传人造境的高超神妙,就很难只用时下流行的那些“形象塑造”、“心理刻划”、“描写逼真”、“分析细密”等等文艺观念来“说明”他,表彰他,因为雪芹写书,是中国人想中国事,不会像现代人时时夹杂上西方的文化理论。现在一般青年人,心中目中除了“塑造”、“刻划”、“描写”这套词语概念之外,几乎不知还有别的道理,拿它们来“套”一番《红楼梦》,有时真是如入五里雾中,莫名其妙之安在,雪芹之伟大何来,甚至以为中国的曹雪芹并不真懂文学艺术。然而,这些反思常常因未能指出可行的突围出路而影响不大。可喜的是,有些论者注意通过话语还原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如黄霖的《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人物典型论》(1984)总结出中国古代写人论的“坚持绘形传神”、“强调性格对比”、“主张从实到虚”三个重心,杨星映的《中国古典小说批评中的人物塑造理论初探》(1984)集中探讨了古代小说写人论所涉及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从哪里来的”、“人物是不是无中生有、凭空而来的”等理论问题。另外,叶纪彬等人的《明清人物性格理论初探》(1997)主要探讨了明清典型理论重视艺术性格的真实、强调展现独特性和个性化的性格以及突出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人物性格等问题。这一系列的探讨和研究虽则也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都突出了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人物研究、
写人研究的本土性。这些偏重理论问题的研究,期待进一步总结、变新。
总体看来,在百年小说研究中,人们于“人物论”和“人物谱”用力较多。而关于人物描写技法及其富有修辞性的文化底蕴的挖掘不够。尽管上世纪80年代后,人们已开始冲破一元性社会化批评的遮蔽,全方位关注人物塑造的复杂性,推出了“多重论”以及“面面观”、“组合论”等观念,但写人研究至今尚囿于“写什么”的城堡中,急需通过新式理论体系的建构来实现全面突围。
二对小说写人问题进行
修辞批评的可行性分析
当今,随着中国修辞学由“狭义”向“广义”转型,它仿佛逐渐成为一把万能钥匙,正在开启着哲学、文学、史学以及美学等各学科的大门,使之纷纷从“语言学”,途经“解释学”,转向“修辞学”。在小说研究中,现代修辞已较为成功地运用于叙事研究,乃至于“叙事修辞”成为当今文论的一道风景。由于中国传统小说带有“寓言”性质,而其“写人”诸要素本身又常常是修辞性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修辞视角,一窥传统小说中写人妙谛。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现代修辞”或“修辞批评”并非是西学意义上的,而是面向中国古代小说写人文本这一实际,参照西方修辞方法,重新聚合起来的带有本土化色彩的修辞理论。
首先,与中国古诗善用比兴来叙事、写人、抒情的言说风向一致,中国古代小说善用春秋笔法赋予叙事、写人以寓意,自其生成伊始即被视为一道修辞的艺术。唐人李善注《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拟李都尉》引汉代桓谭《新论》有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说明,修辞性的“譬喻”是小说的固有性能,写人作为小说“要妙宜修”事业的重要组成,其使命是通过修辞技术使人物血肉丰满、活灵活现。由于古代小说文本内部安插了比喻、夸张、拟人、双关以及戏仿、隐喻、象征、暗示等各种修辞机关,故而时常被人们称为“寓言”。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二酉缀遗》言:“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然《齐谐》即《庄》,《夷坚》即《列》耳。二书固极诙诡,第寓言为近,纪事为远。”张竹坡《金瓶梅寓意说》明确指出: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撅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的确,《金瓶梅》作者在写人中储人了许多“寓言。陛的密码,期待人们去不断地破译。至于神魔狐怪小说,更是被评点者当作“寓言”看待,如世德堂本《西游记》陈元之序说:“此其书直寓言者哉。”此外,《斩鬼传》、《平鬼传》、《聊斋志异》等小说中的人物无不带有耐人寻味的寓意性。中国古代小说这种固有的“寓言”性质,决定了从修辞维度阐释其写人问题自然奏效。
不仅如此,从文体性质来看,小说属于语言艺术,它不能像绘画艺术那样运用线条、色彩来展现人物的相貌和风采,也不能像戏剧等表演艺术那样通过人的演唱、演奏或形体动作、表情来塑造形象、传达情绪、情感,只能借助于抽象的语言符号来进行。而这些抽象的语言符号却常常修辞化为具体可感的绘画或戏剧。由于古代小说最初被命名为“小家珍说”或“稗官野史”,其“小”字或“野”字的身份和定性使之难以独撑门面,故而面对各种小说文本,人们只能参照“史部”与“子部”等经典来诠释,从而使其理解方式带有修辞性、话语表达具有多元性。相对而言,针对古代小说的叙事文法,人们尽管也曾用“拟画批评”,但运用更多的却是“拟史批评”,即通常把精巧的小说叙事技巧比附于史传叙事技巧;而针对写人效果,人们尽管也曾用“拟史批评”,但运用更多的却是“拟画批评”,即通常把小说栩栩如生的写人比附于绘画写真,或用画论话语评判精彩的小说写人语句和段落。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小说写人评点常常借助“拟画”思维来完成修辞性表达。此外,写人评点中的“拟剧”现象也分外突出,各种写人论话语还从戏剧理论中源源不断地输送而来。
其次,就理论用场而言,以多功能的修辞批评切入小说写人研究势在必行。从发端于1914年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起,在上世纪的西方,形形色色的修辞批评以及带有包含修辞批评的方法论风起云涌。在这种学术风气影响下,运用修辞理论研究小说成为近年中国学术研究的一种新动向。如,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1999)从“中西小说叙事中修辞观的差异”着眼,探讨了中国传统小说叙事中富有特色的。文笔意趣”,并初步涉及到“白描传神”等写人状物手法,重视了叙事修辞研究的本土化探讨。另如,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2003)、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2003)、郭洪雷《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嬗变——从宋元话本到五四小说》(2008)等论著纷纷推出。这表明,修辞批评理论用于小说叙事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其应用于小说写人研究,自然同样值得期待。
就中国修辞本身而言,它亦可分为狭义“修饰文辞”和广义“调整或适用语辞”。后来,狭义的传统修辞从单纯研究辞格的固步自封状态中解放出来,并在文化意义上初步形成广义现代修辞学的气派和品格。林语堂《中国人》曾经指出,汉语人常用意象性言说而不习惯用抽象性言说;常用隐喻、曲折、迂回的言说方式,而不习惯用直白、直言的言说方式。隐喻、曲折、形象的言说方式,意在营造出许多“微言大义”的场域,这种言说本能在古代小说写人文本中同样得到体现。况且,小说文本写人的修辞性以及后来评点言说方式的修辞性无处不在。如题名李卓吾(实为叶昼)评《水浒》所谓的“如画”、“逼真”、“传神”,金圣叹评《水浒》所谓的“极近人之笔”、“声口”、“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张竹坡评《金瓶梅》所谓的“追魂摄影”、“白描之笔”,闲斋老人评《儒林外史》所谓的“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等等,都是对小说写人技艺所作的修辞表述的精妙理论。总之,传统小说写人理论包含着修辞批评的立场、话语,尤其突出地存在着援引和征用画论术语的“拟画”批评现象,这是我们今天选取修辞批评进行写人研究的基本理据,也是我们展开小说修辞性写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再次,从“写人”这一研究对象的语义分析来看,“写”、“人”二字本身的文化修辞性也决定了应用修辞批评切实可行。“写人”之“写”最初使用于书论和画论。如《世说新语·巧艺》载著名画家顾恺之的画论名言说:“四体妍蚩(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在此,“写”兼有“画。的涵义,意为“描摹”。尔后,宋代陈郁《藏一话腴论写心》指出:“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否则君子小人,貌同心异,贵贱忠恶,奚自而别?”将表现“君子小人”、“贵贱忠恶”的精神境界纳入“写心”,作为“传神”的必要条件提出。同时,“写”有时还通假于“泻”,《诗经·邶风·泉水》说:“驾言出游,以写
我忧。”这里的“写”就意为倾吐。清人周星莲《临池管见》曾经对“写”与“画”作过这样的语义分析:前人作字,谓之画字,……后人不曰画字,而曰写字,写有二义:《说文》:“写,置物也。”《韵书》:“写。输也。”置者,置物之形,输者,输我之心。两义并不相悖,所以字为心画。若仅能置物之形,而不能输我之心,则画字、写字之义两失之矣。由此说来,“写”比“画”更富有修辞寓意。在小说评点理论中,人们最初常用。画”字来代替。写”字,并把“小说家”修辞化为“画家”。如容与堂刊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第三回总评说:“描画鲁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第二十一回回末总评有言:“此回文字逼真,化工肖物。摩写宋江、阎婆惜并阎婆处,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顾虎头、吴道子安能到此?”这些评点中,“描画”、“传神写照”、“逼真”、“画心”等绘画术语被自如地援引征用。明末清初,金圣叹所用之“写”字既指通常意义上的“书写”。包含着今天所谓的“刻画”、“塑造”意,其《读第五才子书法》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在“写”字本身从画论向小说论转移的过程中,由它引导的一系列画论术语也乘机向小说论输送,如“勾勒。、“工笔”、“白描”、“皴染”、“衬染”、“虚白”以及“背面敷粉”、“画龙点睛”、“绘形绘声”、“传神写照”等等几乎无一不来自绘画。一句话,“写”不仅与“画”融通,而且还含“泻”意,是一种富有寓意的修辞行为。而根据Ⅸ说文解字》的说法,作为“写”之对象的“人”,乃“天地之性最可贵者也”。这种说法无疑本自儒家经典。宋人李昉所辑《太平御览》第三六。卷《人事部》一《叙人》搜录了历代文献典籍关于“人”的定义和解释,有的强调“人”在宇宙间的崇高地位,有的重在阐释“人”之性情,有的涉及到“人”的分类、等级及性别差异,可见,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是天地之德性的化育、阴阳的化合、鬼神的凝合、五行的菁华,是天地万物的中心,是五行的终点。尤为重要的是,在原始宗教与中古政治宗教基础上形成的“感生异貌”观念、庄子的“物化”观念以及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都丰富了传统关于“人”的学说。生成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小说赋予其中之“人”以丰富的修辞性,理应从修辞维度加以阐释。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寓言”性质以及“写人”二字的语义蕴含都期待修辞研究。在传统“拟画”批评等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我们完全有理由利用修辞所代表着的一种由此及彼的拓展性想象力,去透过“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的小说文本表象,去叩问探究其“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写人文化意蕴。
三古代小说写人文本的
修辞批评及其融通操作
现代修辞学号称“大修辞学”或“广义修辞学”,其“大”而“广”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它具有广大而开阔的应用面。应用于中国古代小说写人研究的修辞学不仅与传统狭义修辞学相关联,而且更借鉴并吸取了戏剧主义批评、社会修辞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现代批评等“外部联系”的文学研究方法,它势必突破以往仅仅借助修辞学点评小说语言美的功能,而通过融通狭义与广义各派修辞批评理论,来建构古代小说写人理论的新体系。
首先,通过修辞批评在“戏剧修辞——社会修辞——语言修辞”三个层次上的互相融通,探讨中国古代小说写人文本的“拟剧”批评及其“角色”修辞蕴涵。
现代修辞批评方法既有利于调和传统社会批评与现代形式主义批评的矛盾,又颇能集结二者之长。在运用这一理论进行写人研究时,我们应摒弃叙事学不同程度地割断文本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关联的局限,而注意综合运用现代社会心理学、伦理学、语言学以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关于社会角色、性别角色研究的成果,来探讨小说人物描写的“角色”意蕴和修辞特征。在众多修辞批评范式中,戏剧主义批评(Dramaturgical Criticism)思潮尽管形成并流行于上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世界,但作为一种思维范式,在中国却是“古已有之”。这一理论源于戏剧分析,其逻辑起点是“人生就是一场戏,而世界就是他的舞台”这一隐喻。该批评范式又进而链接到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的“角色”(role)理论。而最先将本指戏剧舞台上所扮演人物的“角色”一词引入社会心理学的著作乃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后来,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帕克在其《种族与文化》中认为,人(person)是带着一种面具(mask)在社会上生存的。扮演不仅是一种戏剧行为,而且还是一种社会行为。扮演的方式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和人进行自我反省的最佳方式。每一种社会角色都有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或规范。随之,美国符号互动论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研究互动仪式的意蕴时认为,“角色”这个名词代表一种动态的概念,当人们表现出实际地位的权利与责任时,便是在表演某个角色;“角色”实质上是一种暗喻(metaphor),有时候被扩而大之用来说明社会是个舞台。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指出:身份、地位、社会声誉这些东西,并不是可以拥有而后还可以将之展示出来的实体性事物;它是一种恰当的行为模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断地被人加以修饰润色,并且具有很强的连贯性。不管人们的表演是轻松自如还是笨拙不堪、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狡诈的还是真诚的,它都必须展现和描述一些东西,并且让人们感知到这些东西。这就是说,社会角色是人们期望中的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或身份的个人所应有的行为。这些“角色”理论丰富了传统戏剧修辞批评理论,有助于我们阐释小说人物的身份、地位等难题。
在中国,基于某种“拟剧”思维,古代小说批评不仅借用戏剧专业术语,而且还运用了“身份”这一角色化的准“拟剧”术语,形成了一种“拟剧”批评传统。为将这一批评传统发扬光大,我们不妨借鉴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论”,对古代小说所描写的人物之千姿百态作重新审视。我们不仅致力于探讨古代小说中的性别角色扮演问题,而且结合传统文论探讨传统小说人物角色表演的“假象”、“伪态”等问题。如张竹坡提出的“真假”说是从伦常角色扮演切人的,以《金瓶梅》为代表的小说追摄了许多“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辈”图景。“真假”世态中的“伪态”备受后人关注。刘备、宋江、薛宝钗等人之所以常常给人以“虚伪”的印象,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角色扮演中始终戴着虚饰的人格面具,且其表演镜头多集中于“前台”。在“伪态”表演中,“作态”又是一种特别耐人寻味的表演样态。与此相关联,作为社会学修辞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兴起的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以及当下人们广为认同的“性别诗学”(The Poetics ofGender)等理论,对阐释各种男女有别的小说写人现象颇有用场。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已经与叙事学联姻,生成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由于该研究意在将叙事学的结
构分析模式用于女性主义批评,从而拓展、改进和丰富女性主义批评,因而未被人们纳入叙事修辞研究范畴来看待。但女性主义批评不仅完全可以应用于写人研究,而且十分有助于阐释戏曲小说等文本的写人意蕴,故而不妨视为社会性别修辞的有机组成部分。另外,为避免女性主义的锋芒而提出的“性别诗学”理论既包括男女两性之间富有张力的修辞关系,也包括男性霸权话语关于“我性”与“他性”的修辞性符号指述,自然饱含修辞意蕴。这就意味着,要探究中国小说所蕴含的富有修辞性的写人之“道”与“技”,“性别诗学”是一个富有洞察力和发现性的视角。从社会角色扮演来看,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角色的丛集,而在某一特定的时空场域中,每一个人又只能选择一种话语角色进行言语交际。近年,“角色”一词又被引入语言研究,形成了“话语角色”观念。所谓“话语角色”或称“言语行为角色”,实际上是社会角色在言语交际场域中的具体化。语言学中的自我角色认知、他人角色及角色关系认知、交际双方之间的话语角色关系认知、话语角色的社会心理认知等理论,为小说写人研究又开启了一扇难得的视窗。
在这个修辞融通层面上,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小说评点中的“拟剧”思维及其影响下的“角色”理论应用前景。为此,我们完全可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小说评点,来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写人问题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拟剧”批评,重新阐释小说人物的“表演”样态及其修辞意蕴。
其次,通过修辞批评在“语言修辞——诗性修辞——哲学修辞“三个层次上的彼此融通,探讨中国古代小说的写人规律、范式及其背后的文化修辞蕴涵。
毋庸置疑,用于写人研究的修辞批评还是应当以本原的“语言修辞”为基础。在具体运作上,譬喻、类比、象征、对照等传统修辞术和辞格经过放大处理,依然可以当作理论武器,为我所用。当然,修辞研究的革命性变革还是发生于西方,许多西方学人借鉴现代哲学、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从认知角度认识修辞。如意大利著名学者维柯《新科学》将隐喻、转喻、提喻、反讽置于。诗性逻辑”这同一个话语层面来考察,把“隐喻”视为一切原始诗性民族都必有、必用的人对自然的认知方式。从跨文化比较的视野看,这种物我合一、由己度人的认知方式带有普遍性,在中国“古已有之”,其经典表述便是“天人合一”、“观物取象”、“目既往还,心亦吐纳”。不仅如此,以隐喻为主体的修辞还成为嫁接小说写人研究与哲学论人研究的桥梁。
在“语言修辞”基础上,现代修辞延展到关于文本文化意蕴的探讨,我们不妨将这种修辞方式称为“诗性修辞”。这里所谓的“诗性”,主要是指处于技巧层面的文化密码性、文化寓意性。小说中的这种“诗性修辞”符码可以借助西方后现代主义修辞方法来破译。在西方,相对于戏剧修辞批评,后现代主义修辞走得更远,它的研究范围包括一切文化形式和文化现象。对此,常昌富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后现代主义将一切符码化、话语化,实质上是将一切修辞化。这样,修辞批评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狭窄的、传统意义上的言语或演讲,而是一切文化形式,包括批评本身。这样,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精神分析学说、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等,这些在“叙事学”研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修辞学批评方法,皆可应用于写人研究。如依照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的“能指”与“所指”理论以及其影响下的符号学,我们可以发掘中国传统文学在写人时苦心经营的经得起叩问和追问的联想域、信息链,启发人们从文本具体人物本身联想更多、更有意义的文化现象,我们也可以总结中国古代经典著作通过写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建立特定语义场、语流场的经验,从而对小说所描绘的人物之“态”进行创新性的解读。又如,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关于“梦的象征”理论有助于我们谈论人物“梦”描写的心理潜隐功能。相对而言,神话——原型批评学派最具备修辞再生能力,无论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还是弗莱的“置换变形”学说,都十分有助我们解读小说写人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受这种修辞观念的影响,谭学纯、朱玲在《广义修辞学》一书中提出了“修辞原型”这一概念,并以此为基础,生发出“伦理修辞”、“色彩修辞”、“数字修辞”等一系列富有文化底蕴的诗性修辞概念。我们不妨融会贯通地运用这些修辞理论,对中国古代小说写人文本中的。五伦”修辞、“五色”修辞、“七情”修辞等话题进行寻味。
在小说文本中,随着文化含量的不断蓄积,诗性修辞又进而上升为哲学修辞。哲学修辞的基础是“哲学的便是修辞的”观念,一方面是指抽象的哲学道理要靠形象化的修辞来言说,另一方面是指古代哲学理论构架本身即是修辞性的。保罗·德曼《隐喻认识论》一文曾指出:“一切的哲学,以其依赖于比喻作用的程度来说,都被宣告为文学的,而且,就这一问题的内含来说,一切文学又都是哲学的。”当然,“哲学修辞”理论是另一面“西洋镜”,带给我们的同样是启示和参照,而并非直接生搬硬套。小说写人研究之所以要打开哲学修辞这面视窗,不仅是因为作为小说描写对象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而且小说所塑造的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所生存的时空同样带有哲理性。具体到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而言,“天人合一”互喻文化谱系、“阴阳对立”象征文化谱系、“五行生克”联想文化谱系等哲学思想都对小说写人发生过渗透和影响,形成一个个富有修辞意蕴的联想阈。其中,古老的哲学经典《易经》之《系辞上》、《系辞下》分别提出“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观念,即从天地、日月、阴阳、乾坤等天人秩序的哲学高度来论证男女的尊卑、内外、刚柔、贵贱等修辞关系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进而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以及“阴阳五行”原理来论证“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宋代理学家又从“太极”、“天理”来论证“三纲五常”的普遍性和“灭人欲”以“存天理”的必要性。这些根深蒂固的哲学修辞理念自然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古代小说写人文本中。据此,我们可以去追寻“物我互喻”、“人情物态互拟”等小说写人表达体系,探索“性别越界”、“双性同体”以及“严父慈母”二元角色对立等写人结构现象。另外,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发生发展还有一条基本规律,即其概念和范畴往往发端于哲学,经美学(尤其是画论),再演化到小说写人论。也就是说,传统小说写人评点往往一方面参照生活经验发表感受,另一方面直接移植或间接应用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如“形”、“神”、“态”、“气”、“真”、“味”等,即从最初的哲学概念或范畴,后经画论而转入小说戏曲写人论。根据“哲学的便是修辞的”原理,对这些写人论范畴,我们自然都可以展开行之有效的修辞阐释。
综上所言,以狭义的“语言修辞”为基础和纽带,我们可以把在“戏剧修辞一社会修辞——语言修辞”与“语言修辞——诗性修辞——哲学修辞”两个层面上彼此融通的现代修辞理论应用于古代小说写人研究。换句话说,运用多维交汇的修辞维度,以“拟画”批评与“拟剧”批评为基础,我们可以有选择地把中国古代小说写人理论重新聚合为珠联璧合的新式理论体系,并借以不断地挖掘小说写人文本的修辞意蕴,重新建构中国本土的写人理论体系,从而真正实现中国古代小说写人研究的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