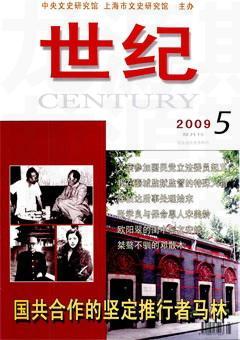并非“白卷”
王尔龄
白振奎、陈婧两先生撰写的《鲁迅为青年开书目缘何交“白卷”》(刊于《世纪》2009年第4期),颇有见道之言,但以鲁迅于1925年2月应《京报》副刊之请填写《青年必读书》而未开列书目,就说他“交了白卷”,愚以为未见允当。无论按照它的本来意义还是依循它的比喻意义看,似乎都不能认定他所交的是“白卷”;因为他已就“必读书”申述了自己的意见,并非不著一字,或者不着边际乱说一通,倘以“白卷”目之,得无冤乎?
鲁迅当年在填写的表格上先写了“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又在附注栏申述了理由(或曰原因)。这在白、陈两位的文章里已经全引,自不必多引。其要点在于主张“少——或者竞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的意见不断地遭到误解,白、陈的文章里也作了许多回答,足以启人之思。而“白卷”说亦未尝不是一种误解。
就鲁迅的这一见解本身而言,我们应当让它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观察。“五四”前后著名文化人,倘是接触新学的新人物,旧学根柢都很好,年长者如严复、俞明震、辜鸿铭,年轻的如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尽皆如此,举不胜举,年岁介于两者之间的鲁迅,对新学与旧学的感受尤甚,他从自身及同时代人的经验中悟及启蒙的重要,“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略近于严复所说的“启民智”,而“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亦非虚话,有他自己在绍兴会馆居住的年月抄古碑、校古书“应对苦闷时的经历可证。作为旧学有根柢、新学得门径的文化名人,他的这一番话并非故作惊人之论,意在表明他从不久前的经验中获致读书主张:读切近于今而不读悠远往古之书。
鲁迅亦非终其一生未开书单,他在1930年为许世瑛开过一份书目,全是中国古籍。许世瑛是许寿裳的长子,鲁迅应知交许寿裳之请而写下来的,每种书都附注阅读注意点,包括取舍的意见;但他是给进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许世瑛开的,虽不庞杂,大学四年仍难读完,但于专治中国古代文学是有实用价值的,自不能认定非此专业的青年同样适用,因而不能看作与《青年必读书》的论述相左。
本栏责任编辑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