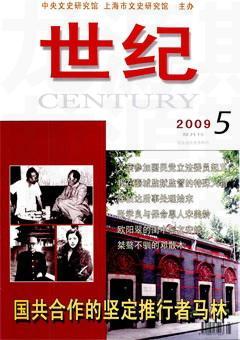我在秦城监狱监管的特殊人物
多年来,一些书刊的文章凡涉及秦城监狱的内容,总给人有谈虎色变、毛骨悚然之感。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十年浩劫一批冤假错案的受难者被关押在那里。我从1952年至1992年在监狱任管教员,1960年后于秦城监狱工作到离休。这期间我在204监区担任科长,1985年2月晋升为副处长,离休前定为正处长,经历了从功德林到秦城,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四人帮”垮台到拨乱反正时期。如今我已年近八旬,趁记忆力尚好之际,就撰写文章,让更多人对秦城监狱有进一步的了解。
秦城监狱名称由来
秦城监狱(以下简称秦城)是1960年3月15日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1号公安部预审局和监狱迁移到秦城后,才有了这一名称。那里原是个小村落,位于北京市北面昌平区地界的燕山山脉南侧,距市中心40公里,离小汤山镇10公里。监狱东、西、北三面依山,南面是一片平原,有一股山泉水从监狱东北流向监狱前面泄入水库。秦城建设初就有办公区、生活区,以及周边的林地、农田。建有四个监房区(均砖木、水泥浇铸结构)。潘汉年、徐雪寒等关在204区。204有较高生活待遇,每人有20平方米的房间。配有地毯、沙发床、桌椅和热水瓶等生活用品。伙食即使1960年前后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午、晚餐是二菜一汤,一年四季供应高档茶叶、水果。这种待遇从功德林起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
我在1952年7月察哈尔省撤省建制时,随原察哈尔省公安厅部分干部调入公安部,分配到一局四处(预审局前身)功德林监狱(以下称功德林)工作的。老北京AS功德林为第二监狱,它是一座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卦形的庞大监狱。据说晚清年代就有,袁世凯当大总统年代修葺过。
1954年3月因工作之需我调到丁字号(大监区)工作,丁字号有120名犯人,他们大多是历史反革命。监管员是吴生福与我,1955年4月领导上调我去执行看管潘汉年的任务,直至1960年3月15日功德林迁移到秦城后,我就在秦城204监区工作。204监区除潘汉年外,还有饶漱石、胡风、范明、王少庸、徐雪寒、薛向程、王超北等高级干部,负责他们的生活、疾病治疗等。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礼堂开大会时讲“砸烂公检法”以后,同年11月7日秦城实行军管,“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令下,在一两天内秦城的全体职工(仅临时留几名炊事员、电话员)调用三十多辆卡车将他们送到复兴门外木樨地政法干校去办学习班。1969年我全家下放黑龙江地处北大荒的“五七干校”。秦城军管几年后,在周恩来总理过问战犯改造工作后,才采取了“原管教干部应调一些回来工作”(见群众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第366页)的措施。于是1972年11月我从“五七干校”调回秦城在201监区工作。不久,毛主席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反映秦城虐待在押人员等问题的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见《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一书,第346页)批示下达后,1973年间先谢富治病亡,后代部长、部长李震自缢。接着华国锋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和赵苍璧任公安部长期间,先后对秦城进行了整顿,1974年间军管人员和一批转业人员陆续调离。经过机构调整,充实干部,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秦城的管理才逐渐走上正轨。
黄维是改造战犯中最顽固的一个
1975年3月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后,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特赦释放大会,释放战犯293名(见《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第368页)。这是在国内外极具影响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绝大多数战犯都是走过从不认罪到认罪的过程。这与我们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教育方法是分不开的。简要地说运用了多种“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如每逢“五一”“十一”两大节日都带他们观看天安门游行和晚上的烟火盛况。这是件很费心思和艰苦的工作,黄维起初从被俘的那一天起压根儿不认罪,属极个别的顽固不化的犯人,总认为在战场的失败,不是他没有能力和解放军较量的结果,而是解放军对他偷袭而被俘的。他心里一直憋着这口气,进监狱后极少与其他战犯接触,别人在一起说说笑笑他就视而不见,我们领导和监管人员对黄维的教育花了不少心思。如动员他妻子、女儿做他的思想工作。他妻子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女儿在清华大学任教。她俩什么时候来探视就什么时候来,不加限制。可是他妻子苦口婆心地劝说,甚至对他说:“有的人已出去了,论关系在共产党内你和周恩来不是也很熟吗?只要你认错,不坚持顽固观点,政府会让你出来的……”等等。黄仍无动于衷,他说:“我出去是因为我曾做出科学贡献……。”经过领导批准,我们把黄维研究策划的所谓儿童“秋千”(即永动机)草图,请中国科学院专家教授测试鉴定,认定所谓“永动机”是没有任何动力的,只不过是个科普幻想而已。但黄仍无转变。直到1974年他到平山县西柏坡参观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是怎样指挥“三大战役”取得最后决战胜利的,此时才有醒悟,也就是说他的顽固立场在特赦前一年才有转变。
接触最多的人是潘汉年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原判,宣告潘汉年无罪。1983年4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潘汉年和夫人董慧的骨灰从湖南长沙移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我知悉后心潮起伏,潘汉年两进秦城,我同他们夫妇接触最多。这对患难夫妻的喜怒哀乐的容貌在我脑海里印象深刻。
第一次见到潘汉年是1955年4月,他49岁,被关进功德林。当时潘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住在北京饭店。4月1日他直率地向陈毅讲了历史上见汪精卫的事及当时的动机和目的。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写的材料交给了毛。4月3日傍晚,在北京饭店由罗瑞卿向他宣布了逮捕令,于是他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当天领导决定我执行看管潘汉年的任务,他一进功德林我就住在他房间里,10多天后我搬到隔壁房间去住。他的一切生活料理都由我做。所以那时可以说我就是最贴近他的人。头几天对潘审讯很紧张,几乎天天审,主审官是李局长,记录是邵处长,潘就是不说话,僵持了好几天,直到徐子荣副部长同他谈话,徐对他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给写个条子……”的话后,他才开始讲话。此后也就在同我接触中讲了一些内心话。潘说他的问题是1943年在上海被胡均鹤(据说胡现在上海,是离休干部)、李士群硬拉着去见汪精卫一次,此事到
延安和解放后一直没有向党中央毛主席讲。那他为何在1955年4月在北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时才讲,他说在前些日子与毛主席同乘一列车,两人闲谈中,他听毛主席讲了“人心隔肚皮……”这样一句俗语后,产生了压力,感到毛主席对他的历史有怀疑。于是想趁在北京开会时找机会向中央领导讲心里话。后来1963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同年2月23日被“假释交公安部管制”。他的夫人董慧来秦城陪同。这时他俩从204监区迁居职工生活区3号楼东门西单元二楼二室(当时饶漱石住在生活区9号四居室平房),他们夫妇的生活、看病等仍由我负责,在行动上也可算是自由人。他俩每天到秦城南边水库钓鱼或到小汤山镇逛逛。我们之间也是谈笑自如的。不久,夫妇俩就被转移到北京团河劳改农场居住,由北京市公安局负责管理。
第二次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为潘夫妇安全起见,他俩从团河搬回秦城,在监狱二门里(监区外面)卫生所二楼居住,生活管理由我负责。不久随着运动不断升级,秦城的部分造反派要造潘汉年的反。当我得到这一消息告知他俩作好思想准备时,潘对我说:“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不会出事的。”并表示让我放心。接着1966年6月8日下午,造反派在没有经过部领导批准的情况下,将潘夫妇关进201监区,我也随着到201监区工作。直到1967年11月7日秦城军管,我离开秦城,只能与他俩告别了。时隔近5年后,1972年11月我从“五七干校”调回秦城,当我再次见到潘汉年时,他苍老许多,头发几乎掉光了。1973年经医生检查潘肝部有疑点,我就带他去日坛医院请专家会诊,后住进复兴医院两个多月,经过造影五次,最后排除肝病的问题,他松了口气。对这次住院检查治疗他是很感激的,向我说“今生有机会来报答党组织的关怀”等等。
1973年9月潘从医院回到秦城201监区,仍由夫人董慧陪同。到1975年5月潘夫妇被遣送到湖南茶陵县涞江茶场安置,作为“特殊犯人”管制,他俩就离开了秦城。后来我知道1976年初潘70岁时,身患多种疾病,住进简陋的茶场医院,1977年3月获准转到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疗,但为时已晚,于1977年4月14日逝世,终年71岁。我这个熟悉他的小人物得知他病故的消息,内心感叹不已。以前我认为潘夫妇送去湖南茶场会加快他往死亡线上走的,因为潘已年临古稀,夫人董慧那时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记得董在秦城时有一晚停电,她上厕所时跌倒在地,造成骨折,去医院做手术不理想,右腿拐了,造成他俩生活许多不便,如果仍在秦城吃住、看病、上医院等等可能情况会好些的。
陆定一讲的一些心里话
陆定一是1967年关押进秦城。之前,1965年底陆的妻子严慰冰在西城区一个秘密据点里被隔离审查一年多,当时安排陆定一离京去安徽农村蹲点搞调研。据我所知在秦城关的有严慰冰和严的妹妹等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许多老干部都知道严慰冰、陆定一被抓起来,主要是反林彪。他们进监狱不久秦城就军管了。到1972年11月我调回秦城,陆那时在201监区,我才开始同他有接触。陆的案子都归中央“一办”的专案组管,秦城只负责监管工作,即管他们的生活、看病等等,头等任务是保证安全,不出意外。几经接触后,陆对我说:“看您是一位老同志,与那些人(指军管来的转业人员)不一样,他们只会给人扣大帽子,而你能听取反映,也不急躁。故我能给你讲讲心里话。”自此,陆亲口向我讲了一些事:陆说1966年初(“文革”前)毛主席去南方视察,中央召开一次临时会议,康生在会上公开指着我说:“我一看你就像一个特务。”此话一出引得哄堂大笑,然而林彪则气急败坏地指着我说“我林彪恨不得一枪打死你陆定一”。会后我妻子被隔离审查,我被通知离京,到安徽农村蹲点。他还说“开始严慰冰在西城一个秘密据点里,后来升级进了秦城的”等等。讲到专案组审查他的三个问题时,他说其实也不是专案组定的,就是林彪、康生定的调。那三个问题指:一是上井冈山之前在南京做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事,陆说当时我公开身份是商人,没有暴露共产党身份,因我父亲在上海商界有点名气,我向特务提出来,可去上海问问我父亲他有没有我这个儿子。在我一口咬定是商人后,不久就被释放了。此事发生后,党组织安排我到井冈山去,上了井冈山我向党中央毛主席如实报告在南京被抓的前后过程,组织上早已清楚。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康生就以此要把我搞成“特务”。二是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这怎么回事呢?陆说上井冈山不久,父亲病故,让我回家分财产,经过中央批准托人回去办理。那时红军非常缺钱,更缺银元,实际取回的银元三分之二上缴组织,留下三分之一,一半给我前妻的岳母供扶养我女儿用,因为孩子的生母在南京被蒋介石杀害了;另一半被我治病买药用了。对这一历史问题不具体分析作结论,硬要定我“阶级异己分子”。他还说我相信这不是专案组的问题,是林彪、康生的意图。第三是说我反对毛主席在农村的卫生医疗方针路线,这就更离奇,根本没有的事。他说严慰冰被隔离审查,我离京一年多是由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陪着去安徽在农村蹲点一年。在农村作社会调查中,发现农村的土医生能治疗一般的疾病,受到农民欢迎,我就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调查报告反映实际情况,于是就有后来推行“赤脚医生”的政策。他说本来是好事,却被颠倒过来说是反对毛主席的医疗卫生路线。陆还几次说:“不管他们怎么批我斗我,我就是死也要与他们对着干,因为我相信党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直到1975年,党中央为陆定一落实政策,当专案组来秦城向他宣布中央让他出去时,他要求恢复党籍,否则不出去。这样他又躯躭了一年多才离开秦城的。
陈伯达大闹“寻死”
1975年4月26日,领导调我去管理陈伯达,当时领导强调要绝对保证安全,在生活上可满足陈的需求,以利于保存“活证据”。由于那时陈伯达常闹监,动不动耍小动作要“寻死”,还在年轻战士面前摆架子,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30多年,最熟悉毛主席著作”、“我出去还要写毛选一、二、三、四卷的注释”等话。时而对特殊待遇的伙食找茬儿,说这不好吃,那没滋味。为了实地观察他的表现,掌握一些实际情况,我搬到离陈的监房仅几米远的监房住下。经过一周多的观察,看出陈要“寻死”是装腔作势。比如他从床上起身时,往前冲一二步,有点站不稳,这本来是年纪大的自然现象,但看管他的年轻战士,由于思想上压力大,一见状赶紧上前把他拉住,久而久之造成了陈伯达要“寻死”的问题。而陈就利用年轻战士的弱点,故意制造紧张气氛。对此,我作好思想准备,并同他作有理有节的斗争。1975年5月29日,那天天气晴朗,陈伯达吃过早饭,在室内走动,见到一只小鸟停在窗框上叽叽喳喳地叫跳,小鸟飞走后,只见陈沉思片刻,突然情绪不正常,对着两名战士叫喊“我活着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一只小鸟,这样下去还不如死了好……”。边说边从床上起来,用
一个突然动作要往东边墙上撞。战士迅速前去把他抱住,实际上当时离墙有五、六米的距离。然后战士拉响警铃,我即速赶去,还没有说话,就见陈硬要挣脱战士的保护去撞墙。我就来个激将法,高喊一声,叫两名战士放开他,接着说:“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撞个头破血流,有人说你非常难管,你今天的表现只能说明你是用死来威胁我们政府工作人员,好让我们听你的指挥,这是痴心梦想。”我又说:“你要撞死只能证明你的立场顽固到底,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接着我口气缓和一些,说“我劝你还是明智点为好,有什么想不通的可以谈谈,我会把你的想法和要求向上级反映的,这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除此以外,没有好的结果可取”等等。我讲这些话时,陈听着,看他不会有闹的样子,最后我说:“你好好想想,我们政府工作人员哪一点对不起你。”说罢就出监房向战士布置注意事项。果然战士反映,陈中午吃饭很少,躺在床上闭眼静思,不时长吁短叹。过了两天战士报告,陈伯达说:“我要见那位首长。”因他不知那天批评自己的是谁。在战士连续报告的第三天,我才去陈的监房先发制人地对他讲:“从今天起,你的一切归我管,你要很好的和我配合,服从管理,不要胡闹,有什么问题可以正面提出来……”我还未讲完,陈伯达就用右手打自己的脸,边打边说:“我该死,我对不起领导,对不起政府,对不起党,我今后决不再这样……”我即说:“打脸有什么用,只能触及皮肉,关键是要端正态度,配合组织上对你的审查,搞清你的问题,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你说对吗?”陈点头表示同意。自此一年多他老实多了。
其实我看陈伯达活像一条“变色龙”。1976年9月,当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见报后,他就以为良机将临,在监房竭力吹捧“四人帮”,说了一大套阿谀奉承的话:“我和江青、春桥同志是一条心的,我愿同他们同心协力的工作。”“我以个人的名义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江青同志致敬。”“我特别怀念毛主席的忠诚战友江青同志,希望她多保重身体。”“在一起工作当中他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陈伯达还说“毛主席的后事办理完毕,江青同志会派人来和我谈话的,我的问题寄托在她身上”等等。当时我和几名战士对陈伯达的这些话均抱着只当没听见的态度。不久,他得知“四人帮”垮台,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又要出要“寻死”的闹剧,还当着我们的面骂:“国民党监狱也没有像你们这样……”等等极为难听的话来。我就同他针锋相对地说理斗争,责问道:“国民党监狱有严刑拷打,这里有没有?在这里整天给你送牛奶、饼干、水果,吃大米饭、包子、饺子,喝鸡汤,有病请专家来给你治病。你房里有沙发床、地毯,国民党监狱有没有?”问得他瞠目结舌,只得承认自己态度不好,表示服从管理。自此两三年后,陈伯达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中的第五位。陈伯达被依法判处徒刑后,于1981年7月保外就医离开了秦城。
王、关、戚各显“神通”
1972年11月,我调回秦城时在201监区工作,当时有89名局、部级干部关在201区。王力、关锋、戚本禹就在这个监区内。
先说关锋其人。他性情暴躁,时常大喊大叫,似乎精神失常,曾将报纸卷成筒,对着门缝喊叫,谩骂周总理。为制止关这种行为,领导上决定我和马存宝、王安林三人组成专门小组管理他。首先落实生活问题,每天由一人专门照顾他衣食和到监房外活动,加上医疗服务,他逐步改变了精神紧张状态,并开始同我们说话,也不骂街了,加之我们安排家属来探视后,他就开始转为正常状态。不料有一天因为少给他打开水的事与转业战士大吵大骂。这件事发生后我向领导建议尽快整顿队伍,到1974年间军管人员和转业战士大多离开后,关的骂人才收敛。
再说戚本禹这个人。我接触他后就感到戚是个善耍坏点子的人,监管人员在斗智上比不上他。我们采取的对策是避免让他钻空子。比如他经常想睡就睡,晚上不睡就不睡。有一天,晚上战士关了里面大灯,他就大闹,闹得周围在押人员也睡不好。其实他这种行为是拒不认罪的表现。起初我们还是同他评理,我明确对他说:“警卫战士监管你,是政府赋予的责任,如果你做这个工作,也得这样做。”我还指出:“你是故意拿战士寻开心,这反映出你在外边平时生活准则和品德如何。你不是在外有一点名气的人吗?今天在这里戏弄战士,你不觉得太低俗了吗?”最后我说:“你如果实在不听劝告,我们为了你的安全,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此时他对着我说出“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今天我要看一看你对我采取什么措施”的话来吓唬我。戚为何说这样的话呢?那是因“文革”初,在他操纵下,把秦城关押的陈里宁作为“反刘少奇英雄”抛了出来。当时我持反对态度,结果被戚指挥的红卫兵揪斗。我想可能是我与其他相关同志作认真研究,把戚从二楼搬到三楼空监房去,当时是7月中旬,把木门打开,只关铁栅门,这一夜蚊子咬得他睡不着了,第二天他就要求谈话。我让战士转告说“何殿奎出差了,等他回来再说”。第四天我才进入戚在三楼的房间,一进去就感到他已没有前几天那般趾高气扬了。他说:“我们谈一谈好吗?”我说:“没什么好谈的,这样,谁也不影响谁,省得你整天同战士闹别扭。”这次较量,我看到他欺软怕硬的本质。我们还是把关他房间的木门关上了。谈话后,他基本上服从管理了。
王力1973年以前在201监区,1973年12月调他到204监区。因王在201时精神不大正常,发生过又哭又笑的事,考虑到不要同关锋、戚本禹在同一监区,领导决定调的。1975年5月底我调到204监区担任领导(科长)时,王力精神状态有了转变,他每天看书、看报,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讲话后,要求从图书馆借来单行本,又提出要看“文革”初期《人民日报》合订本。经专案组批准派人从《人民日报》社借来三年的合订本。他看了这些资料,对邓小平的讲话提出了一些看法。秦城将王力这一情况报告到中央。邓小平看到报告后,让邓力群找王力谈话,于是我和田江辰用汽车带王力从秦城到中南海东门找到邓力群的生活秘书,带他到朝内南小街邓力群家中。我们等到晚上8点邓力群回来,没有休息立刻就和王力谈话。讲了叫他来的目的是中央准备让他出来搞文字工作,要换个名字等。直到晚上11时,我们带王力回秦城的。后来1982年王力被释放,住国务院招待所,这时候有朋友去看他,王竞对别人说在邓力群同他谈话那天,秦城的工作人员用汽车带他到中南海里边转了一圈。王这一说法被中央知道后,两次派调查组找我核实情况。我明确否定了王力的说法。当时情况是邓力群的秘书向我说王力被关押好几年,对北京市容变化不了解。这位秘书建议让汽车开到天安门,再经过南池子、沙滩,再到朝内南小街,我同意了这一路线。但根本没有进中南海里边转一圈。况且中南海只有中央警卫局的车子才进得去,这也是普通的常识。这件事给我一个印象,怎么王力这号人到八十年代还要往脸上贴金。我以为像王、关、戚这些做学问的人,用一句俗语“浪子回头金不换”才好啊。
写于2009年3月1日
责任编辑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