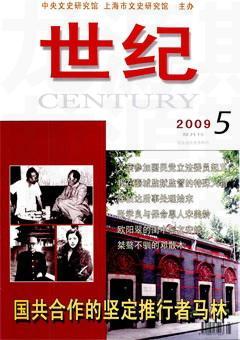异国巧遇陈诚大公子
黎方夏
我的母亲吕迪华与陈诚夫人谭祥孩提时一起玩耍过,非常要好,长大后各自成了家便为莫逆之交。在国共决战前夕谭祥随陈诚准备去台湾时,曾力邀我母亲同行,但她终因子女太多而婉言推辞了。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因这一层关系参加了上海市政协学习小组。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母亲的父亲吕苾筹与谭延闿共事廿年,辗转南北,从未离开须臾。在谭氏为孙中山所召,任广州大本营秘书长之前,无论在青岛、上海、南京我们两家不是一墙之隔相邻而居便是合住一处大宅院。因此两家子女童年时曾生活在一起,长大成人后自然都成了好朋友。母亲和祥姨(即谭祥,谭、吕两家既是世交又是姻亲故以此称谓)志趣相近因此过从甚密。祥姨初抵台湾与母亲尚有书信往来,直至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则音讯全无。
1989年上海市政协将谭祥逝世的消息告知母亲,我们当即拟就唁电准备拍电报给祥姨长子陈履安。跑邮局之事我便揽下来,但无法获得确切的台湾地址,怎么办?陈履安时任“经济部长”,于是只得发至“经济部”。当时大陆与台湾邮电不通,上海思南路邮局虽然受理台湾的电报业务,但实际上是由香港转发。该电报最后是否送到了陈履安手中则不得而知。即使他收到也会因政务在身不便联系的。有去无回不免使老母亲感觉非常失落,总觉得一件心事并未了却。此举虽以个人名义悼念,实质是一件政治任务。
在谭祥逝世一周年之际,母亲为抒发思念之情特与父亲(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前馆员黎叔平)共同完成一篇追思悼念之文。其中除了倾诉离别愁情外还述及谭、吕两家“儿童大军”,年长的大哥谭伯羽(谭延闿长子)组织孩子们读文习字、游戏、甚至体育活动的情景,非常生动又有意义。因不知怎样才能使对方亲自收到信件,无奈只得束之高阁,谁知这一搁竟然就是廿年。父母亲先后去世后,我在整理他们遗物时发现这篇纸张已经泛黄的祭文,总觉得不应让它就这样沉睡于故纸堆中,但一时也没有设想。后来我在整理叔父遗著《文史消闲录》时便把它收集在该书附录中。
2008年暑假我赴美探望住在马里兰州的大儿子一家。闲来无事常去Rockville图书馆消磨时间。一天,在一份华文报纸上见到一则消息:《台湾前监察院长陈履安来罗市(Rockville)举行人生哲学讲座》,会场就设在我常去的图书馆。此则新闻使我眼前顿时一亮。行前我有意无意中将直至赴美前夕才成书的《文史消闲录》带去了几本,于是立即电话预约参加此次讲座的入场券。那天会场布置庄重,由于演讲者是一位大人物,故人气甚旺,座无虚席,气氛相当热烈。与会者大部分为台湾人士。我是有备而来,等演讲一结束,便快步抢先走到陈履安面前作一番毛遂自荐。这样一个来自大陆的人跟他“套近乎”,他可能感到有些唐突,但听我说得很真切,他才慢慢回过神来,并接过收录了《悼念表妹谭祥》一文的册子和我预先写好的一封信。这时求见者已排成长队,我便匆匆结束了这次谈话,合影后互留地址、电话。他说常去上海,以后有机会再详谈。
我将父母所撰写的文字亲手交给祥姨之子陈履安,了却了父母生前的愿望。
陈履安出身于显赫家庭,自己又曾是一位高官,甚至竞选过“总统”。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一派学者风度。儒雅可亲,演讲时自始至终面带微笑,身着一件极其普通的白衬衫,毫无将门之子的傲气。一则因为他研究佛学多年,对世事看得澹泊,另外跟他家教密不可分。我们家里藏有一帧他们小时候的全家照片,父亲陈诚一身戎装,母亲穿着淡雅朴素。男孩子一律白衬衫,女孩子则淡青竹布长衫,不论男孩、女孩脚上穿的都是白底黑布鞋。每次看都觉得很亲切,就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
责任编辑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