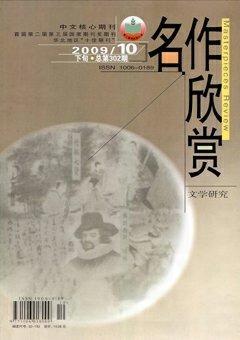历史的细语:澳洲早期殖民冲突中白人受害者的言说
关键词:二元对立 白人受害者 澳大利亚民族属性
摘 要:坊间流行的澳洲早期殖民冲突历史的二元对立叙事,忽略了第三类人——白人受害者。他们是英帝国殖民的牺牲者,是白人中心主义者施暴后果的承受者,是黑人报复的绝望者。在二元对立历史宏大叙事之间,仔细聆听白人受害者言说的历史细语,理解宗主国人民所经受的另一种痛苦,有利于澳大利亚民族的沟通与和解,也有利于塑造新的澳大利亚民族属性。
在审视澳洲早期殖民冲突时,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他们多倾向于将澳洲早期殖民冲突看成是殖民与反殖民的冲突,或者白人与黑人的冲突。
对澳洲早期殖民冲突的二元对立式反观,会影响双方的决策,易形成双方的对立情绪,带来社会生活的不和谐之音。“现实是历史造成的,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对现实状况的说明,这种认识必然要影响到人们的现实活动,并通过现实进而影响未来。”①白人黑人的行为模式选择就体现了二者水火不容的对立态势。
上述二元对立的叙事中,双方都忽略了第三类人——白人受害者的存在。白人受害者是真正的边缘人,他们没有进入白人主流,也没有被土著接纳。他们是参与殖民的白人,却厌恶同类的野蛮与暴行;他们想与土著人睦邻友好,却被迫举起钢枪与屠刀。迄今为止,他们得到的,不是土著的仇恨,就是白人后代无尽的忏悔。
《神秘的河流》一书的主人公威廉·索尼尔是澳洲早期殖民冲突中白人受害者的典型代表。因此本文就从他的故事切入,分析他如何从土著眼中一个十恶不赦的白人施害者变成了一个令人同情的白人受害者。
一、威廉·索尼尔:白人社会的弃儿
威廉·索尼尔出生在伦敦的一个穷人。他的家狭窄、拥挤,煤灰挂满四壁。他家所在的街巷,稠密的房屋低矮、潮湿,垃圾遍地且终日不见阳光,各种污染工业肆意蔓延。他饿得以跳蚤充饥,冻得双脚冰冷如石,穷得与哥哥争夺一条毯子。在最为艰难的日子里,他依靠卖狗粪为生,否则就只有饮浑浊的河水度日。对他而言,偷窃是人生的必修课:大哥偷萝卜时,前额被农民扔的石头所伤;妈妈偷书换钱时所展示的灵机应变能力让人汗颜。
威廉·索尼尔决心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不过,当时英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留给穷人改变自己命运的空间很小。随着父母的去世和两个兄弟的离家出走,养家糊口的重任落到了威廉·索尼尔孱弱的肩头。他什么活都干,可全家人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做了米德尔顿先生(自己没有儿子继承手艺)的学徒,学习做一名水手。正是在此时,他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发誓要成为最优秀的学徒。也正是在此时,他朦胧地意识到阶层的差异和不平等,对绅士阶层产生了莫名的羡慕和鄙夷之情。他心想事成,拥有一份赖以谋生的职业并娶到青梅竹马的萨尔为妻。
对威廉·索尼尔来说,他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幸福的来临和消失都是那么的偶然。就因为河流冰冻月余,没有任何收入,他的整个世界就天崩地裂。岳父母因严寒生病去世,耗尽了家产。当他发现曾经温暖的家也是租来的,他明白自己又成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光蛋。大多数水手都是小偷,因为他们的收入所得不足以养家糊口。明知道赃物所得超过四十先令就会被处以绞刑,威廉·索尼尔却明知故犯,去偷窃巴西木材。看来,酷刑和生存始终是穷人无法逃避的选择。
他请人给沃森上校写了一封请求宽恕的信,沃森上校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链找到了霍克斯布里大人,此人有权决定是否缓期执行。不知道是人际关系起了作用还是正赶上了帝国殖民澳洲的“好时机”。逃过死神魔掌的威廉·索尼尔,被大英帝国视作“人类垃圾”,倾倒在澳洲这片蛮荒之地。他被彻底地抛弃了!
二、威廉·索尼尔:英帝国殖民的牺牲者
英国的殖民政策本来就是为食利阶层服务的。尽管帝国为资本家攫取了大量利润,却对普通百姓毫无益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穷人入不敷出,富人却能积累财富,并将这些财富作为资本投向海外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在母国,威廉·索尼尔是个地地道道的穷人,他走上了偷窃的道路。帝国为了维护资本所有权而制定的严苛刑律,将这个仅仅偷了几块巴西木的威廉·索尼尔打入死牢。又因为帝国官员的腐败、司法程序的人为因素,以及正赶上帝国想在澳大利亚建立“海外监狱”的好时机,他获得了宽恕。
为了维护资本家的既得利益,苛刻的法律使帝国监狱人满为患。随着1776年美国的独立,英国失去了再向那里倾倒“人类垃圾”的可能性。于是,威廉·索尼尔和其他一些罪犯被母国作为祸水东引至澳大利亚。那儿地域辽阔,关山难越,是最佳的流放罪犯之所。
作为君主在澳大利亚的全权代表,总督对土著可以出尔反尔、可以不信守承诺。根据凯特·格伦维尔的调查,1804年12月,约翰·金总督为了解决霍克斯布里河岸边白人与黑人的暴力冲突事件,特意召来三个土著询问理由。土著说河岸上仅存的几块土地,是他们唯一的粮食产地,不想被赶走;说白人占据了河岸丰饶之地,他们只得向下游迁移;说他们穿越白人定居地,白人愤怒地向他们开火;说如果他们能保有下游的一些地方,他们会很开心,不会再滋事。②总督觉得他们说得合情合理,于是宣布“在‘第二支流下游不准再有白人居住”③。总督的承诺不过是空头支票,下游的白人定居还在继续,而政府对此视而不见,致使冲突愈演愈烈。
为了肃清土著人对农民的骚扰,麦克勒姆船长接受总督的旨意,制定了周密的“钳形运动”和“人链”计划,企图在黑鬼溪围歼土著人。英帝国的战争机器装备先进、训练有素,但土著人占有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有利条件。麦克勒姆在黑鬼溪遭到土著的伏击,大败而还。
表面看来,帝国是为了保护白人农民不受土著人骚扰而发兵,但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资本家在澳洲的利益。同时,土著人对任何白人的骚扰就是对英帝国骄傲的侵犯,就是对君主的不敬,这是无法容忍的。威廉·索尼尔说不出这些道理,但他“觉得政府所能做的一切都解决不了当地人的问题”④。他的内心充满怨愤,“觉得君主和国家从来没给过他什么恩惠。”⑤政府的军事行动使冲突不断升温,将他推向了与土著势不两立的境地。在土著反抗殖民侵略的战争中,他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三、威廉·索尼尔:白人中心主义者施暴后果的承受者
在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支撑下,一些白人自我膨胀和傲慢得不将土著当自己的同类看待。早期殖民者视土著为害虫,害虫当然是要被消灭的。直到1967年,澳洲土著才获得选举权并且第一次进入全国人口普查。小说作者不由得质疑:“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从前不是人?你的意思是说不允许他们参加选举?”⑥由此看来,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确实深入人心,要将其根除实属不易,早期澳洲白人的那种无可比拟的种族优越感也就毋庸置疑了。既然土著不是人,在早期殖民地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土著妇女沦为斯迈舍和赛吉提等为代表的白人中心主义者的泄欲工具就不足为奇了。既然土著不是人,随意屠戮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了,因为这种行为是在替上帝“传播文明”。正如罗夫迪在阐释当时政府公报上的一篇布告时说,“这规定已经讲得很清楚,只要有机会,就可以开枪打死那些黑鬼”⑦。斯迈舍可以肆无忌惮地将黑人的耳朵割下来挂在腰间,说“这能保佑我交好运”⑧。赛吉提也可以用绿色的粉末(一种毒药)结果土著的性命。
威廉·索尼尔这个没有从国家和君主那里得到任何恩惠的白人自然也是上帝的弃儿。因为君主是上帝在人间的全权代表,他要普施恩惠给“上帝的选民”。既然都是上帝的子民,为什么自己整日勤苦却不得温饱,不受尊重?而游手好闲之辈却饱食终日,吆五喝六?他对上帝有潜意识的质疑。小时候,妈妈带他去教堂,他感到“上帝就像是一条鱼一般奇特怪异”⑨,离他很远,令他害怕。母亲临终前,基督教堂门柱上的两头狮子困扰着她。在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前,即使在幻象中,她也未能如愿地触碰到它。难道是石狮阻挡了这贫苦的一家与上帝接触的机会?母亲去世后,家里请不起牧师为她祷告。为了表示纪念,他将一团烂泥投进了石狮那自鸣得意的嘴巴里,算是对它的傲慢的一种反抗。
上帝未曾眷顾自己,母国抛弃自己。威廉·索尼尔没有恃宠而骄的傲慢,却有一颗平常人的平常心。时常感觉到土著和自己一样,土著的领袖和他们的总督一样威严而不可侵犯。为了能与土著和平相处,他试着与土著沟通,但因语言障碍而失败;他去找布莱克伍德探讨与土著相处的指导性名言“付出多少,就会得到多少”⑩。以威廉·索尼尔为代表的一类白人对土著的友善淹没在以斯迈舍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者暴行的滚滚洪流中。多数白人征服的暴力、野蛮与血腥冲刷了少数白人的良知和平等意识。
四、威廉·索尼尔:黑人报复的绝望者
在西方殖民强权兴盛时期,他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获取他族土地,即征服、割让和占有“无主土地”。这些权力是由1954年《联合国宪章》宣布使用武力为非法前的“国际法”所确认的。“对于‘无主土地,即万忒尔所谓的‘未垦殖的土地,或虽已‘垦殖,且居民已结成定居社群,但在欧人看来并无成型昭彰的社会组织者,则其与土地二者间不得认作‘国际法上之占有关系。”{11}
尽管有强大的法律武器做后盾,威廉·索尼尔在拔除土著甘薯时还是犹豫不决,在占领100英亩土地时并不理直气壮,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在侵占别人的领地,将此地作为“无主土地”似乎有点勉强,但他不得不占有。威廉·索尼尔的生活经历告诉他只有“占有”才踏实,这点认识已深入骨髓。有了那片土地,他就会有自己的家,即使很简陋。有了自己的家,他就会有温暖、安全和归宿的感觉,就再也不会无根地漂泊。有了那片土地,他就能通过辛勤的劳作换来丰收的硕果,让一家人丰衣足食,不再忍受饥寒。那片土地,是他唯一的希望,拥有它便拥有了一切,失去它也就意味着失去一切。无法指望母国的关怀,威廉·索尼尔必须生存下来,而土地便是生存的唯一依托。没有那片土地,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去向何方。
土著对白人的报复,包括杀人、放火,使得威廉·索尼尔一家寝食难安。唯一深爱自己的萨尔因为无法忍受土著的骚扰执意要回英国,而他本人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到那没有希望的地方。黑人在保卫家园,驱赶入侵者时,他们无从理解威廉·索尼尔这类走投无路的白人;黑人在报复白人,反抗暴行的时候,看不到这类睦邻友好的白人。由于语言障碍,由于白人的整体形象,黑人无法区别对待两类本质完全不同的白人。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所有白人被绑上了一条战船,结成了暂时的利益共同体。甚至是在与土著决战前,威廉·索尼尔就预感到“不管做出哪种选择,他都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活着了”{12}。不与白人为伍,他不仅会被同伴唾弃而且会被土著杀戮。与同伴为伍,他可能会留住心爱的人,可能会保住那片命根子似的土地,但也会终生愧疚。
历史中的人物与人群绝不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如果我们把白人与黑人二元对立叙事称为历史的宏大叙事,那么对威廉·索尼尔经历的言说便是历史的细语。在反思殖民历史之时,我们不要忘记威廉·索尼尔这类人的存在,他们也是历史的经历者和创造者,他们有着自己的痛苦与悲怆。我们不要忘记,当殖民地的人民痛苦万状时,宗主国的人民同时在经受另一种痛苦的煎熬。诚如小说《神秘的河流》的作者凯特·格伦维尔在2009年3月20日与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师生座谈时提到该小说的创作时称“我的祖先被置入一种环境,他不得不进行选择。”与土著决战后,优裕的生活却改变不了威廉·索尼尔忧郁的眼神。“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全然没有胜利的感觉。”{13}他们背着“罪者之痛”的沉重包袱行走于人世间,而这包袱是帝国政府、白人同伴硬塞给他的。在白人与黑人二元对立的历史宏大叙事背后,笔者仿佛能听见威廉·索尼尔的哭泣:我的母国啊,你的殖民是我的痛苦之源,我爱你,可是我更爱真理,不要再傲慢了,让我们与其他种族携手并肩吧!我的白人兄弟啊,所有种族都是上帝亲选的女儿,只有平等地理解与爱才能换来尊重与宽容!我的黑人兄弟啊,我对不起你们,可是我别无选择,只有你的宽恕才能消除我的“罪者之痛”!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助课题“澳大利亚妇女小说研究”(W07211062),以及澳大利亚政府下属澳中理事会支助课题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龚小萍,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研究。
① 刘昶.人心中的历史[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②⑥ Kate Grenville. Searching for the Secret River[M]. Text Publishing Melbourne Australia,2006.
③④⑤⑦⑧⑨⑩{12}{13} 凯特·格伦维尔.神秘的河流[M].郭英剑等译. 译林出版社,2008.
{11} 许章润. 说法 活法 立法[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