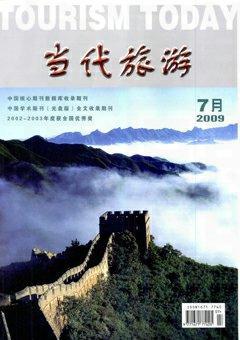传统与现代的亲密接触
陈远洋
摘要:在新文化革命浪潮冲击下,诗歌创作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时代精神要求新诗彻底斩断与传统的联系,而底蕴深厚的古典诗歌传统又深深影响着新诗创作。沈尹默的新诗表现出了新旧融合的倾向,在新的语言形式的外壳下,成功的将时代内容与古典诗歌的美学传统意境融为一体。《月夜》、《公园里的二月蓝》、《三弦》、《生机》等诗作,有力地显示出从旧文化突围出来的沈尹默,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尝试对话而不是对抗,其融古发新的新诗创作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亲密接触。
关键词:传统;现代;新诗;意境;沈尹默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1—7740(2009)07—0081—04
1918年1月《新青年》四卷一期发表了沈尹默、胡适、刘半农三人九首白话新诗,其中沈尹默著有:《鸽子》、《人力车夫》、《月夜》,自此而后到1920年,沈尹默在《新青年》上又陆续发表新诗《落叶》、《除夕》、《月》、《公园里的二月蓝》、《三弦》、《生机》等共18篇。在沈尹默的新诗中,我们发现被新文学革命一开始就否定了的古典诗歌传统,又在新的时代内容中焕发出生机,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努力地对话而不是对抗,融古发新的艺术追求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亲密接触。
一
在沈尹默的十八首新诗里,我们总能感受到强烈的意境感染力,渺小的人事物景背后,散发出的是充沛的真情实感,使得诗歌充满了审美张力。特别是这些诗歌产生在新文学革命的文化背景下,以一种新颖的语言形式,传达着新时代的生活诉求,更加反衬出沈尹默新诗融古发新的美学特点。周作人较早看出了这一点,在为刘半农的《扬鞭集》作序言时,他以直感式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看法:“那时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是刘半农……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能很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用文言……他的诗词还是现代的新诗,它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遍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氛略有差异的缘故。”[1]周作人所谓的“内涵的气氛”只得到底是什么?在这里,我们选取沈尹默两首被称为新诗初创时期的杰作《月夜》和《三弦》来分析之。
月夜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新青年》四卷一期1918年1月15日)
三弦
中午时候,火一样的太阳,没法遮拦,让他直晒在长街上。静悄悄少人行路,只有悠悠风来,吹动路旁杨树。
谁家破门大院里,半院子绿茸茸细草,都浮着闪闪的金光。旁边有一段低低的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
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双手抱着头,他不声不响。
《新青年》五卷二期1918年8月15日)
《月夜》是一首即景小诗,短短四句却在新诗坛上引起莫大的反响。1919年被收入《新诗年选》,编选人康白情评价说《月夜》“在中国新诗史上算是第一首散文诗”,认为“第一首散文诗而具新诗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月夜》”,“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2]。胡适说《月夜》“几百年来哪有这样的好诗![3]而朱自清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却又未收录《月夜》,其在“选诗杂记”里所做解释是认为该诗妙在“我吟味不出,第三行也许说自己的渺小,第四行就不明白。若说是遗世独立之概,未免不充分——况且只有四行诗,要表达两个主要意思也难。因此,这回没有选这首诗。”[4] 是诗陆续有周作人、胡先驌、孙玉石等多人评价。
在上述众多评价中,笔者发现了其中不同而同之处,即无论是康白情的“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还是朱自清的“我吟味不出”,其实都把握到了《月夜》在新形式下难以洗掉的古典诗歌传统的印记。尽管孙玉石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中刻意强调《月夜》“透露了萌芽形态的象征主义新诗诞生的信息”[5],但是他也承认“作者体味传统诗的精髓,以物隐兴,以物寄情。”[5]古诗讲意在言外,讲兴托比喻,讲意境,是数千年来中国古典诗歌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比、兴也好 ,意在言外也好,立意取境也好,都让中国古典诗歌富于象征主义的多义和朦胧。由该《月夜》让人想起了杜甫笔下的《月夜》,苏轼的《前赤壁赋》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月夜,想起李商隐无题诗“来是空言去绝踪”中的月夜。……无疑“月夜”这个意象本身就极富古典诗意,其独有的抒情写意氛围被古典诗词发挥到极致。沈尹默的《月夜》毕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月夜”,有他的新质,那就是月夜中的“我”再也不是一个在旧封建统治意识中丧失自我人格独立价值的人,而是一个与“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的具有个性觉醒意识的新文化“人”。这一点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主题,无疑沈尹默的《月夜》把握到了时代的命脉。但是,从传达这一思想内容新质的艺术手法与表现出的艺术特点来看,该诗具有古典诗歌的传统样貌。“从写作技巧上看,诗人用象征的手法写出了人格独立的要求,避免直白浅露,追求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象征意境,情感和思绪蕴藏的很深。这就是说《月夜》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让读者看到了唐诗的影子。”[6] 其实何止唐诗,“我”和“树”的若即若离所造成的审美意境,让人很容易想到了《诗经·蒹葭》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以及《古诗·迢迢牵牛星》中的“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涵咏不尽的意境。抛开思想内容的区别,仅从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一意境特征而言,三首诗歌是极相类似的。该诗前二句用了肤觉、视觉、听觉,用了动感和静感,诗人自己的情感意识消融在那个霜风吹动着树叶的月夜里,情景相融、借景传情,这些都是对古典诗词优秀的艺术技巧的成功继承。“每句都有韵脚,押‘歌戈O韵(《中原音韵》韵脚),就像古典绝句一样。”[6] 确是对该诗艺术特征的准确体认。
时隔半年后的1918年8月,在《新青年》五卷第二期上,沈尹默又发表了《三弦》。这是一首被时人传诵的名篇新诗,对《月夜》颇有微词的朱自清在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强调,“像《三弦》等诗,是不该遗漏的。”[4] 而胡适则在其《谈新诗》中具体分析了该诗的音节和意境,并称赞“新体诗中也有用旧体诗词的方法来做的,最有功效的例是沈尹默的《三弦》……,这首诗从见解意境上和音节上看来,都可算是新诗中的一首最完美的诗。”[7] 随后胡适对该诗的音韵进行了具体地分析,确实让读者感受到了《三弦》诗声色俱佳,声情并茂的艺术特征。
周作人在《扬鞭集序》中的评价(参见引文1)直观地道出了沈尹默新诗的古典气质,而胡适所着重赞赏的意境和音节,恰恰是新诗所短而旧诗所长。如果将“三弦”与白居易的《琵琶行》略做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在白描,映衬等技巧上的相似性,而于情境上二诗都于结束处用“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手法来创意写境。在音韵方面,胡适指出了《三弦》多用双声,且有十一个字是端透定(D,T,D)的字,模写三弦声响,形容毕肖。实际上这种情形在宋词中就不乏其人,北宋女词人李清照在其《声声慢·寻寻觅觅》中,全词九十余字中,起句连用十四个叠字,五十七个舌齿两声字,故意用啮齿丁宁的声吻来表现自己刻骨铭心的家国之痛(字字如钉子钉在心上),可以推想谙熟古典诗词的沈尹默必定对此也很为了解。而《三弦》在情调上所表现出来的颓唐、破败、无望之情,作者并未直言说出,而是让它们全部压抑下来,潜伏在闷人的炎阳,死一样静寂的长街,寂风中了无生机的杨树和那所破败的房子中,那个可能在军阀混战,饿殍遍野,民生凋敝中失去了一切的抒情主人公——门外坐着、双手抱头,一声不响的破衫老年人,他的痛苦与不幸,愤怒与不平,失望亦或绝望之情,全都静默,一切都让那断续的三弦去诉说。在这里《琵琶行》中那熟悉的手法和情景浮现在我们面前,古诗中诗人白居易的失意和琵琶女的不幸都沉浸在悬泉幽咽的琵琶声中,在《三弦》里则转化为诗人的悲凉、三弦客的激愤和破衫老人的麻木完全消融在鼓荡的三弦声里。在此,古典诗歌的意境传统在沈尹默的新诗中得到了现代回应,周作人所谓的沈尹默的诗略有差异的“内涵的气氛”,正是诗歌的意境所体现的艺术特质。
二
把沈尹默的新诗与同期胡适和刘半农的新诗放在一起,尹默的诗所具有的特点就显得更为特出了。在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1号上,胡沈二人写了同题诗《鸽子》和《人力车夫》。胡适的两首同题诗,语言直白、思想浅切、不留余意。《鸽子》一诗“胡适致力于描写形象,体现他的‘具体的写法”[8],笔触几乎全部停留在对鸽子形象本身的描绘上,而他的《人力车夫》用对话体来写,虽然近于口语,但车夫与乘客心灵隔膜,该诗显得呆板而冷漠,缺乏感人的情怀,诗体实验的意味明显。著名诗人朱湘评价胡适的早期新诗“‘内容粗浅,艺术幼稚这是我加在《尝试集》上的八个大字。”[9]这大体符合新诗初创时期的实际的。而沈尹默的同题诗,情感含蓄,余味悠长。“‘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胡适之的新抒情诗模式,在这里不复存在。”[5] 如沈诗《人力车夫》,先写景“日光淡淡, /白云悠悠,/风吹薄冰,/河水不流。”接着叙事“出门去,/雇人力车”,然后继续写乘车所见“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什么。/人力车上人, /个个穿棉衣, /个个袖手坐, /还觉风吹来, /身上冷不过。”最后才点出诗歌描写的主人公“车夫单衣已破, /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坠。”该诗名叫《人力车夫》,但描写车夫的篇幅仅短短的两句,作者把自己对为富者不仁,出力者受苦的悲凉之情没有透露半个字,诗歌本身不露褒贬,而是在天上和地上、行人和车马、乘客和车夫的对比中,让我们感受到诗人视觉背后那意味深长的悲情。这里诗人和车夫没有言谈,但一路的静默,留给读者无穷的“空白”。旧时代愚弱国民的不幸,作者人道主义同情的无奈,大众在强大压迫下的麻木,都在这空白中回环往复。和胡适的同题诗相比,沈诗除了语言形式的新颖外,更具含蓄蕴藉的诗美,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美。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总结沈尹默新诗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情景相融。无论《月夜》、《三弦》还是《人力车夫》等,作者本人要表达的情感总是含而不露,而那些描写的景物却总是情思充盈,形成的艺术张力让读者涵咏不尽。又如《生机》,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完全消失在各样景物的背后,“生机”在哪里,看一下春风下的残雪、满枝的桃花和那最后全换了颜色的细柳条,处处都是生机,看似写景实则写情。王夫之所言“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在沈尹默的新诗里我们体会到了古诗情景论的现代回应。
二是虚实相生。司空图《诗品》中言“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就是说诗歌不能拘泥于具体描写的“实”象的部分,而是要充分抒发“虚”情,只有虚实相生才有诗境产生。在沈尹默的诗中,看似是写景的实的,在直觉体会的瞬间立即转化为表情的虚的;感觉情感是飘忽不定的虚的可直觉里分明满眼锦绣是实的。以《月夜》为例,呼呼的霜风,明明的月光,树和我只是并排站着,要说是写实全为实,可是突出我和树的距离,就不断诱使读者回味,此时实者已虚,虚者又实。
三是余味不尽。也就是诗看似“行于闲易简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10],从上述所引之诗我们不难看出沈尹默新诗颇具余味。
三
新诗作为“五四”新文学革命的产儿,着力于背叛中国诗歌艺术传统。毋庸置疑,“五四”先驱们为了变革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教传统,便采用了对古诗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处理。胡适的“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单独追求白话形式的新诗模式,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诗艺资源弃之不论。如此猝然实现的新诗,斩断了与中国古诗的脐带联系,仿佛一个断奶的婴儿,要独立成长,其最初的稚嫩是不可避免的。所谓“内容粗浅,艺术幼稚”,所谓“很飘忽的句子一点也不令我觉得飘忽”[11],所谓“专说大白话,诗意匮乏”[12],原因就在于此。问题在于中国诗歌所特有的接受习惯已经形成了接受惯性,可以改变但不可以斩断,胡适等新诗作者生硬的遏制这种惯性,必然造成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对抗而不是对话。
在沈尹默的新诗里,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可能,语言可以新颖,诗味却不会损失;革新可以实现,意境同样能够存在。因为诗语与诗味不矛盾,诗的革新与诗的意境不矛盾。胡适等人为了立新,就完全破旧,而沈尹默则是融古发新,即进行新诗革新的同时又合理的吸收旧诗艺术优点。我们还不能说这在沈尹默是一种艺术自觉,但我们却完全可以理解为这是他的艺术直觉。在新文学理论建设上,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鲁迅等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主张,旗帜鲜明的与旧文学划清界限,可同为新文化最早发起人的沈尹默却没有用理论、口号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在自己为数不多的新诗中显示出传统与革新融合的努力,透露出新诗发展完全可以走一条在革新的同时吸收古诗优秀之处的道路。后来新诗向古典的回归肯定了沈尹默在新诗创作上的这种努力和贡献。
参考文献:
[1]周作人集(上)·扬鞭集序[M].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163.
[2]北社编选.新诗年选(1919)一书后附《一九一九年诗坛略纪[M].上海:上海亚东书局,1922.
[3]胡适研究资料[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374.
[4]朱自清.选诗杂识.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
[5]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4-5.
[6]张德新.沈尹默新诗浅析[J].安康师专学报,2006,(2):3.
[7]胡适.谈新诗[G]//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303.
[8]沈大用.中国新诗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43.
[9]朱湘.中书集[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4:192.
[10][宋]范温.潜溪诗眼[G]//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1362-1363.
[11]冯文炳.谈新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
[12]姜耕玉.二十世纪汉语诗选(1900—1949)《序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