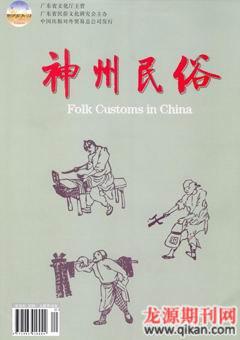苦难的隐喻:玻璃上的“苍蝇”
刘 琪
摘要: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效应渐趋改变着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与此相应的文化意义也发生着急剧变革。“边缘人”也从沉默的少数进入学术的视野,他们被抛出意义之网,身体找不到归依,心智迷失了方向。文章选取经验对象的“生活史” 片段,从社会文化的维度解析其“苦难”。
关键词:生活史;边缘人;苦难
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韦伯也讲人是会编织意义之网的动物,特纳则把人放进象征的森林中来理解。诸种表述说明,人与动物的根本之异在于他们能够创造并播承文化。人只有在文化生产时才显示其真正意义。各人文学科追根究底都是以人类文化意义的解释和理解,即人所创造的且在其潜移默化中行动的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有两种属性:生物性和社会性。“社会性”的精彩之处在于人的文化,其可以把一群人同另一群人区分开来。不同人的文化意义网络之间矛盾重重,彼此都视对方的行动为无意义或作他解。这就是格尔茨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也即“一种赋予特定地方的特定事物以特定意义的方式。”
一、你如何被看
按照结构主义的通常做法,文化可以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一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在1956年发表的《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的。这一概念用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一般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贵族、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或者社会中的上层精英文化;而所谓小传统,常常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大传统”代表官方的、书面的、经教育体制训练的文化意义,“小传统”则指民间的、口头的、靠田间地头传承的符号象征。两个意义网络形成彼此相对稳定的社会规范和共同价值。虽然现代社会日益放开,但依旧可以看到一些“小传统”人无法通过教育途径进入“大传统”的世界。
这使人想到美国学者威廉·托马斯的著作,书中给定了“不适应的少女”的概念,即指通常处于青春期的,由于家庭、社区或特殊事物的不良影响而导致背离社会规范与共同价值的个体。本文要讲的“边缘人”是受过高中教育的,其殷切希望通过读书“跳农门”,从而进入现代都市生活,可是因为诸多困扰,终究折戟沙场,未能进入大学学习,身体旋即又回到生养的乡土,仍旧归于“小传统”空间。这在农村表现尤为突出。十八、九岁,正值学习的黄金阶段,然而他们既缺失父母的乡土生活经验传授,又不能学成荣归。身在乡村,五谷不分,稼穑不事,得不到“小传统”承认;心想山外的生活,却可望而不可及,为“大传统”所摒弃。他们成了两个文化意义之网的边缘人。
在论者多年的乡土经验生活中,见得太多这类人了。他们或疯掉,或生活潦倒,抑或苦难死去。他们需要被引入学者的视野,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
学者把眼睛关注“小传统”,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如近年来,出现的“眼光向下的革命”。赵世瑜身先士卒,率先提出了“大历史”和“小历史”这一对概念。他说,大历史是指那些全局性的历史,比如改朝换代的历史、治乱兴衰的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历史等等;小历史则指那些“局部”的历史:比如个人性的、地方性的历史,也是那些常态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喜怒哀乐的历史,社会惯制的历史。并且进一步强调小历史是大历史的生活基础,一旦将这个生活基础归还给大历史,大小历史的区分就不再需要,历史本来就是一个,就像生活本来就是一个一样。郭于华也做了这样的努力:
近来在从事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口述历史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中,我们常常接触到的是关于苦难的讲述,屡屡体会到的是苦涩的味道浓重的苦难,日复一日让人们在其持续中麻木的苦难,被密不透风的屏障遮掩的苦难。
民众的历史一直都是无足轻重,如同水滴一样随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激不起一点涟漪,留不下些微痕迹。乡土民众的生活世界充满了苦难,这种苦难却是弥散于生命历程之中的,常常无从归因,因而他们对苦难的表叙不免带有先赋论和宿命论。
而上述所说的“边缘人”,身置乡土里,心飘天边外,他们更有着明显的主观自觉意识,因而他们的痛是一种清醒的但又无可奈何的苦。“苦”既是身体的感受,也是心灵的体验,是对客观事物的评判,更是自我认同的表达。“身体之苦”和“心灵之苦”构成他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当然也构成他们历史的重要内容。简而言之,“边缘人”的生活史也理应被研究。
二、你为何发生
(一)玻璃上的“苍蝇”
底层民众的生活苦,值得学者关注。然而,从文化分析的角度,“边缘人”更是没有归属感、没有认同性的苦难的人,同样应被研究。身体的禁锢,心智的摧残,无法适应的苦楚,既无处诉说,也不被人同情,成了彻底的行走在文化边缘的人。
这就必然导致文化问题转变成社会问题。费孝通曾经说过,社会问题起于文化失调。每一文化都有它一定的结构模式,人在新的文化特质中社会化和社会濡化后,就不能配合于原有的模式,如果中断,就会发生边缘化的现象。文化是人类生活实践的物质外壳,故而,文化失调就会引起社会中各个人的生活上出现相似的裂痕,反映于各个人心理上的就是相似的烦闷和苦恼,这种内心的不安使得大家要求解脱,于是社会问题就产生了。
为了针对性的说明他们是怎样成为“边缘人”的,先来看一下,实例主人的生活史。
在江汉平原西北的丘陵地带,桐柏山脉与大洪山的夹角区,我熟识了张宏图。他36岁,已成家室,育有一子。在村里一排的小楼房间,一眼就能看到他的家,一处土坯的三间瓦房。收拾得倒挺干净的,门上贴有一副对联,上联:讀书未尽身先死,下联:耕农不济心已灭,横批:身在心亡。和村里其他人家的“发财”“进宝”等比起来,这显得诉苦、消极、格格不入。他上过高中,曾连续三年参加高考,皆名落孙山。正当他准备第四次时,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遂就此作罢。听村里人讲,他成绩是不错的,还写得一手好字。
不能读书后,他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后来,家里人花了好长时间才在省城一座桥下找到。据说回来时,简直就是一个乞丐。在家调养一些时日,身体稍稍好了些,但不能帮家里干活。一米七的个头,只有九十几斤。常常穿着高中时的校服,东窜西逛,头发蓬乱,举止怪异,他被村里人看成了疯子。
眼见得父母衰老,又无兄弟姐妹,村里人就劝说村干部,是不是想办法给治治。于是大家伙集资凑了点钱,把他带到省城的协和医院看了看。医生开了点药,只说多调养调养,注意休息,便不再言语。还是村里一位曾经念过私塾的老人说,心病终需心药医啊,大家伙才想到去找他以前的高中老师和同学,看能不能凑效。以前的班主任和几个宏图的同学一起来,大家坐到一块,慢慢跟他聊起往昔的岁月。说来也奇,次日,他便早早起来放牛去了。
经过这几番折腾,张宏图也老大不小了,家里费了好大的劲才说上一门亲事。村里人说,新媳妇是看上他喝过墨水才嫁过来的。说这话时,他们露出一点诡异的笑。这媳妇倒也勤快,先后伺候、操办两位老人的事,还给他们张家添了丁。他则较以前更好些了,也能做农活,但总是书生一样的,在农村人看来很搞笑。幸亏媳妇的操持,才没有家徒四壁。小日子过得虽不红火,温饱还算有保障。(被访谈人:Zhang Hongtu,男,1974年生,汉族,高中文化,农民。访谈时间:2008年12月2日。)
这样一个乡村社会少有的文化人(村里近年才走出了一个大学生),其生活经历却是如此不尽如人意,这种强烈的反差激起人探寻其中社会文化内涵的兴趣,并进一步关注他那不平凡的片断生活史。
张宏图的人生故事展示了一种边缘人生的苦难,无论在物质生活、经济活动、家庭生活和社会声望各个方面,他这一生都将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苦难人。处于这样一个共享社区,与村民们不能相互认同,举止言谈也似乎天壤之别,他像一个身在此地而心灵和思想却在另一个世界的人。下学后,他没有参加任何本村社区活动,甚至丧失生存的基本手段和技能。而他的言语和举止又比较多的残存了书本的性格,他喜欢讨论国家大事,一些政治、经济和文化名人经常挂在嘴边,但是这些人物对他而言就像小说里的人一样,一点实际作用都没有。相反,村里人看重的是你能不能吃苦,是否下得了身、挣得了钱,至于用不用官话和科学术语、知道多少天下大事、识得多少大人物,他们并不在意。与此相应,他也不能适应现代都市生活,如前所述,他显然不具备最起码的条件。按他自己的话说,他就像一只趴在玻璃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出路没有。
他被两种文化系统所拒绝。格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一书中,说“不同类别之间的界限是分明无误的。无法归入类别的任何事物都会破坏整个结构,必须加以或者把它消除。而且,基于不同的世界存在方式的意义系统有各自的分野,人们据此去组织行为并维持这些系统的方式。”他们的身体和心智没有停留的空间,是活在意义之外,行走于文化边缘的边缘人。
(二)天地间的“囚鸟”
在《世界的苦难》一书中,皮埃尔·布迪厄等揭示了当代社会普遍人生活中种种苦难。他们记录和研究苦难人的历史为 “边缘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发。比如对“世界的苦难”的研究,他们注重探访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通过观察普通人的生活史,发现了个体遭遇与社会及其变迁的某种复杂关系,并证明了他们重要的方法论主张: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于是,本文也得出这样的社会性解释:“边缘”个体的生活世界遭遇到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却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米尔斯也曾说过,个人日常生活世界中无法理解的烦恼是他们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变迁所造成的。这种分析,可以上溯至法国“社会年鉴派”的代表人物涂尔干。他在《自杀论》研究中,指明自杀虽是个人行为,但该行为受到周围环境的必然影响,因而自杀更是一种社会事实。
在个体生活世界与宏大社会世界之间建立联系,就可能在“边缘人”的“苦难”与社会结构变迁进程之间建立关系,从而获得解释的解释。
三、结语
把人定义为象征的动物,符号的动物或创造意义的动物的确比“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或“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更接近于人的本质。格尔兹说,一种文化是一系列文本的集合,人类学家只能努力地隔着那些创造这些文化的人们的肩头去解读它们。“边缘人”的生活史,记录着个体生命的“苦难”历程,书写了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文化。所以,“边缘人”的研究,势必要从其日常生活世界着手,或者从地方性知识出发,研究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边缘人”。
参考文献
[1]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阿雷恩-鲍尔德温,等,陶东风,等译.文化研究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威廉-托马斯,钱君,等译.不适应的少女[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4]郭于华.在乡野中阅读生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5]克利福德-格尔兹,邓正来译.地方性知识[J].国外社会学,1996,(1-2)
[6]郭于华.倾听无声者的声音[J].读书,2008,(6)
[7]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8]布迪厄、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刘琪(1980- ),男,湖北应城人,供职于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理论民俗学,民俗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