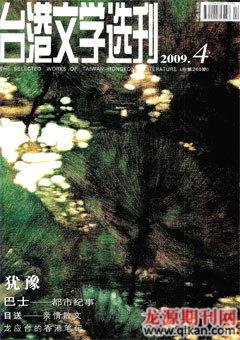席慕蓉的诗画人生
本事
席慕蓉
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我一个人在印尼的峇里岛上,静静守候了一朵荷的成长。
它是一朵极美的荷。刚刚冒出水面的时候,那挺立的小小花苞就触动了我。那样紧密包裹着的愿望啊!就像一支蘸饱了水的毛笔笔尖,服贴圆润,却又蓄势待发。
我每天早上都去端详它,看着它的颜色从敷着一层青绿的暗紫,慢慢转成水红转成柔粉再转成灰白,看着它的花瓣从紧密的蓓蕾到微绽到盛放再到凋落,仿佛是看着一个生命从青涩的少年逐日逐日走到最后。
在池边,我静静地观察和记录,试着画出每一个转折和每一个段落的不同。
当然,在荷池边还有许多朵不断在开开落落的莲荷,荷池旁边还有好几棵巨大的印度素馨,枝干虬蟠,用一种舞蹈的姿态伸到池面上来,甜香沁人的花朵开了一树,也落了一地。早上总有个老妇人拿着袋子来捡拾落花,刚落在地上的花朵依旧洁白光润,拾满了一袋不知道是要拿去敬神呢,还是去装饰那些跳舞的少女们的花冠?
我每天早上都去荷池边坐上两三个钟头。除了画具之外,还带上一大块在当地买的蜡染花布,把整块布铺在池边的草坡上,或坐或卧。有的时候一个早上可以画好几张速写,有的时候就什么事也不做,呆呆地看荷。看累了就躺下来,在树荫底下,把草帽盖在脸上,听那些小鸟从荷叶上飞掠而过,听它们扑动着翅膀不断地换位置,听它们细声鸣叫,听风轻轻在高处的树叶间穿梭。
是观光的季节,在荷池之外,旅馆里和市街上都充满了观光客。好在因为有朋友预先的照拂,我得以住进一间由当地的旧皇宫改成的旅馆。皇宫的庭园很大,房间是一幢幢各自独立的小屋,花径狭窄而幽深,曲曲折折的,隔绝了市街上的噪音,庭园中种了许多花树,还有喷泉,还养了一只寂寞的孔雀。
早上去画了速写以后,下午我就在屋前的平台上,用针笔和毛笔把那些速写重新构图,画成一张单色的素描。我的进度很慢,一个下午只能画一小部分,可是因为心里安静,所以很能自得其乐,常常在桌前一坐就是四五个钟头。
住在我对面,隔着一大丛花树,有时候只听其声不见其人的是一对德国夫妇,大概注意我很久了。终于有一天,在院子里互道了日安和交换了天气出奇地好之类的寒暄之后,金发娇小的妻子忍不住问我,是不是在写小说?
我笑着否认了,并且邀她到我屋前的平台上来,给她看我的速写和素描,告诉她说,我是来这里画荷花的。
她转过身兴奋地向她的丈夫说:
“你听过这样的事吗?一个人跑到这么远的岛上来只为了画一朵荷花?”
她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我好像才忽然间从别人的眼睛里看到我自己,原来是这样的荒谬而又奢侈——
整整一个夏天,只为了画一朵荷。
一年又一年的,荷花原来应该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那些随着莲荷逐年在我心中衍生、互相交错重叠的经验与记忆却将我慢慢地改变了。每次站在荷前,好像总是会发现一些往日所不曾看到的细节,新的困惑和新的难题不断出现,放下画笔的时候,总是觉得还没有说完、还表达得不够。
我想要画的那一朵荷,一直还没有画出来。
前几天去了一次中横公路,在太鲁阁到燕子口的附近,发现山壁间有些岩块崩缺之后只能用水泥来填补,人工修复的痕迹很不好看,我因此怏怏不乐,就向身边的朋友抱怨。想不到他竟然是这样回答我的:
“其实,这个峡谷从开始形成的时候就不断在崩坏,只是我们人的生命太短,看不到这整个的过程罢了。”
初听之下,我不禁一惊。
原来,与我们的一生相比,整个宇宙才是那荒谬与奢侈的极致啊!
然而在最初的那一阵惊悸过去之后,有些什么感觉悄悄地来到我的心中,让我不禁又微笑了起来。
好吧!既然是这样,既然在这件大事上我不能发表意见又无能为力,那么,就让我在此刻,在非常有限的小小范围里坚持一点吧!
是的,既然是这样,既然我只能把握住我手中的几支画笔,那么,就继续画下去吧!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其实可以坚持自己所有的权利——
用我整整一生的时间,来期待美丽的莲荷出现。
时间草原
痖弦
来自察哈尔盟明安旗的穆伦·席连勃是我认识的一个蒙古姑娘,不过我遇见她,不是在通往沙漠市集的路上,而是在“联副”的编辑室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北,中国有报业史以来副刊最兴旺的时期。这种时空的错置,其实不过是一种人生的缘分,就像这位蒙古姑娘,画油画,画线画,写诗,写散文,笔下述说的,无非是许多许多人生的缘分。只是,这缘分里含藏着如此繁复而又如此美丽兼具哀愁的人生情境,让人难以淡然视之。
她第一次来“联副”是准备开个展的时候,带了一个黑夹子,夹了一大叠画稿,我看了印象很深。为了了解她绘画的全貌,我和编辑部同仁专程到石门去参观她的画室,那么远远走近的一段路里,就觉得她的住家与附近的环境真正是艺术家的选择。房产是依着某研究机构的宿舍改建的,外貌并不起眼,但屋里在朴实无华的设计下,处处显示她独特的美感与趣味,比如窗子,用各种色块贴着,仿佛一扇窗也是一幅画,阳光进来,渲染出温暖柔和的色调。画室在对屋,不算大,充满了完成与未完成的作品,有一大幅没画完的杜鹃还在画架上,色彩绚烂淋漓,透着强烈的生命感,她说这是在附近园子观察到的印象,一团团火样的杜鹃,激动着她非画下来才甘休,杜鹃的花季很短,不抓住瞬间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席慕蓉拿出她一张张的作品给我们看;我发现她的油画与线画截然不同,线画纤细秀丽,油画情感奔放,用色大笔挥洒、落拓不羁,有一种原始的j中创力,涌动着女性画家作品中少有的饱满、充沛的气势。我还记得其中一幅画,画中的女子迎风翱翔、长发飘拂,很像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图,有一种健康、雄壮的女性美。如果说她的线画是宋元词曲的小令,油画便是汉朝的乐府长歌。从这两种画风,可以觉察出她有北地雄迈与南国秀丽混合的性格;她的情思细腻,而她不重修饰的样子、不拘小节的生活态度,却流露出一种帅气;帅,原是用来形容男孩子的,但女性有这样的气质,那是另一种的迷人感觉。
为“写生者”画像
亮轩
不久前去看席慕蓉的画展,特意挑选一个人不多的时间,目的就是要好好地看画、好好地想画,也可与身旁的人好好地谈一谈画家的画,几年以来,都是如此,所以画展的开幕酒会就极少参加了。画家可以做纯粹画家,欣赏者也可以做一个纯粹的欣赏者。席慕蓉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面对她的画作,尤其应该做一个纯粹的欣赏者。
席慕蓉从来就不是一个刻意求变的艺术家,无论是她的诗文还是她的画,她求的是真,情感的以及观察的。这也就造成了她的作品长年都能达到雅俗共赏的原因,其实雅俗共赏是美学世界中最难达到的境界,刻意而为毕竟一事无成者大有人在,席慕蓉以她近乎洁癖的真诚执著以赴,又一次证实了她的可观进境。
有人把席慕蓉看作唯美的画家,唯美一词早已被使用得泛滥了,于是难免不予人仅限于皮相之美的印象,如果只是皮相之美,欣赏者深入到某一层次,极可能感受得出内在的虚伪与枯竭,因为皮相之美是没有“心”的。席慕蓉非常之用心,她不
止画画用心,写诗也用心,写散文也用心,席慕蓉是在整个生活中无处不用心的人。她用心地看、用心地想,也很用心地去感动,这就是看她的画总让人不由自主静肃屏息的原因。人一用心便无旁骛,席慕蓉看荷,看得天地间只有荷,连她自己都不见了,所以她的荷也就越来越大了,而三两片的荷叶的影子也就可能充满在她画幅中的三分之二甚或五分之四了。只留下一点点光源的空隙与一两朵甚至含苞未放的荷花,但是在荷叶的这一大片绿里也充满了非比寻常的景致,画家的瞳孔得放得很大很大才见得到在黑夜里的那样的绿、那样的蓝,而非黑。如果有月光,光源或是投射至层层叶影之外的一片叶脉的一角,或是从清浅荷塘微微晃动反射而出,或是荷花荷叶竟然成为零星点缀的配角,画家分明看到了荷塘月下水光的闪动摇曳而转移了主题。
尽管可以如有人所说,席慕蓉的荷花是古典主义、夜色是印象派、花与女人是野兽派,但是以她最近以“一日·一生”为题的展出而言,她的荷画却有着古典派的细腻、印象派的光彩、野兽派的大胆与洒脱,画家显然并不在意自己是什么派别,也无意于表现她师承的源流。早期的师范教育打下了扎实的技术性基础,赴欧习艺开阔了她的心胸与眼界,长年任教则让她在专业世界中从不松懈,而一以贯之的便是净洁无邪的真诚。席慕蓉没有划地自限,这在于她总是保有谦逊的学习精神,虽然她已经从教职岗位退休,但她秉持的学习精神,绝不会比她的学生为少,她甚至会以无限惊羡的态度来赞叹还在学校中杰出的学生,至于她对任何一位她眼中杰出的作家、画家、思想家或是任何行业中的人物之由衷钦佩。也就更不在话下了。谦逊有许多好处,而谦逊最重要的收获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大量地汲取他人的长处,经过了岁月,席慕蓉的融会贯通自属必然。
迈过中年,岁月再也不浪漫了,画家总会担心还有没有足够的时间画下来想画的东西?她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写生者变成更用功的赶路的写生者,然而艺术的世界只有脚程没有路程,怀抱着艺术家本质中的乡愁,她还是会不停地、带着几许焦虑地画下去,终究画出微尘大干尽是故乡的世界。然而她还会持续不断地追寻,正如她在《写生者》一书代序《留言》一诗末尾所说:
波涛不断向我涌来
我是蝼蚁决,心要横过这汪洋的海
最初虽是你诱使我酩酊诱使我疯狂
最后是我微笑着含泪
没顶于
去探访
你的路上
席慕蓉终究要画出所有艺术家的生涯。
红颜情怀永如新
董云霞
画里的红颜不会老去,诗中的情怀,也永远如新。
慕蓉说:“绘画是我在社会中得到认同、与人沟通的主要方式。在技法、知识上都不断拓展、充实,且很在意别人的了解和评价。至于写诗只是我内心喜欢而已,可以说是严肃绘画生活中的休闲。写诗时我的心情很轻松,与作为画家的责任感完全不同。”
到席慕蓉家里,她谈诗的兴致不大,可是讲到画,就迫不及待要拉人到她画室里。她说:“从师范学校到师大艺术系,到海外留学,我学画整整学了十几年,是下过很大一番功夫的!”
学生时代的席慕蓉,对绘画所抱持的狂热和执著,简直到了浑然忘我的地步。
上课以外的时间,她背着画架四处写生,所有的零用钱,几乎全花在买颜料上面。有次班上一位男同学跟她讲:“大家都说你的穿着在女孩子里面,就像我在班上男生里面一样!”席慕蓉望着眼前那个穿着不成样子的男生,心里面想:“我真的这么糟吗?”回家后,她伤心地大哭一场。
师大艺术系毕业后,在德国的大姐席慕德为她申请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入学许可,一九六四年,席慕蓉离乡背井,负笈到比利时深造。
人在海外,一方面环境单纯,实在没有什么娱乐的地方好去;另一方面也是她好强争胜,不愿意落在人后,所以课业方面她拼得很厉害。
两个学年度结束,她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这是该学院在二次大战后多年以来,第一次把第一名的毕业成绩,拱手送给了中国人。
评定毕业成绩那天,七个教授开会讨论了一下午,终于全票通过,把第一名给这个来自中国的女孩。因为她所表现的成绩太优异,远远超过其他毕业同学。不过席慕蓉并没有得到第一名应有的奖学金,因为校方规定,奖学金只提供给本国人。
席慕蓉还记得那天,布鲁塞尔正下着大雨,她印证了得到第一名消息后,兴高采烈回到住处,一个人望着书桌上父母家人的照片,忍不住流了满脸的泪水。
在比利时首都读书的时候,席慕蓉就开过画展,一次画展所得,足供她和妹妹一年生活所需。
“如果年轻的时候知道画画是一生的事,也许当时就不会那么狂热、那么急切了!”做一个艺术家,除了后天不懈的努力,还要许多先天才力的配合。婚后的席慕蓉,化年轻时的狂热为稳健,她心平气和地往前走,一年年下来,她出了画册,开了画展,又有诗集问世,就如同她自己所说:“谁说这不是中年以后另外一种形式的狂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