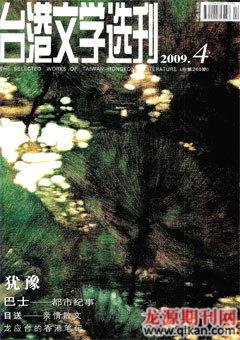新都市咏叹调
马一川 嵩 松
嵩松:读2000年以来的香港杂志,感觉西西发表的小说并不多,不过就视野所及,她的作品总教人目光停留,读后沉吟再三。你知道西西的情况吗?
马一川:西西是1938年生于上海,12岁随父母移居吞港,以后半个多世纪都植根在这个商业化的都市。她当过小学教师,曾任编辑、编剧,也参与拍摄电影和撰写影评,最终专事写作。西西的小说,始终表现一种瑰奇的风格和魅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创作,西西一直在试验、引进不同的现代小说策略。她接受过存在主义,后来受到博尔赫斯、罗兰·巴特、卡尔维诺、福克纳等大师深刻的影响。技巧上融合电影、戏剧、音乐、绘画等各种手法,语言上追求洗练、简洁、诙谐、轻快的特质,题材上关怀文化、信仰、生命和社会心理等,因此西西的小说含义丰富、意象繁美、象征层出不穷,自成一家。香港文学评论家郑树森曾撰文推崇西西:“每个创作过程都是崭新的探索”。
嵩松:西西并不局限于小说创作,她的散文、诗歌都不同凡响,颇受称道。你知道近年世界华文文坛对她有何反映吗?
马一川:2005年年末,有“大马奥斯卡文学奖”美誉的第八届“花踪文学奖”在吉隆坡揭晓,其中分量最重的世界华文文学奖由西西获得。大陆著名作家、评审王安忆在给西西的颁奖词中说:“本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西西,多年来和她所居住的香港保持着静默的距离。她似乎有一种奇异的能力,不让自己蹈入香港的现实,而是让香港谦恭地伫立在她的视野而任她看、想,然后写…她是香港的说梦人。”
嵩松:王安忆的颁奖词真是太好了。从近年西西的小说作品看,我们也能找到“香港说梦人”这个说法的佐证。以“全球”视野观之,如今的香港可说是个高度现代性的社会,西西从香港一地出发,但她所感知的并不囿限于香港一地,她所描述就我们所在的地区而言,也是相当有针对性的。这或许就是好作品的力量所在。不过,我们还得从香港说开来。
马一川:《巴士》及其他四个短篇都发表在2002年后。迈入新纪元,人类行动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生命个体的展现日趋多元。《巴士》通过“我”在行驶的巴土中的平静叙述,以表面看似松散其实肌理啮合绵密的十个片段,形象地反映了都市万花筒的千姿百态。“五百年修得同船渡”,芸芸众生此刻大多相似,乘客泰半都在打盹;两名乘客突然大声说话,也是各自在打各自的手机。相比之下,八十岁的老太太和一对年纪不轻的夫妇的闲话,反而显得有些不同……人与人的关系逐渐冷漠、疏离,而时代在高唱解放个性、尊重自我,真是悲从中来。巴士继续行进。电视里传出动听的歌声,镜头切换成盲歌手和他的家人一起在小城散步。“我”忽然很“意外”。孰料里面在卖唱片广告,又是个美丽的诱饵。有人下车,有人上车。电视播放女子足球赛,“兴奋的球手竟一边跑一边脱掉了球衣。”对比印度妇女所抱小孩性别的误认,可谓男女莫辨、世相纷乱。最后油然而然,“我”想起了法国小说家雷蒙·格诺的《彩虹》:一个年轻人,从衣着、言行甚至到帽子上的细绳,极为夸张,可是因为他失去了人类代代相传的朴素而珍贵的精神、智慧,只能显出滑稽突梯…
嵩松:那巴土上还有关于老太太是否该到站下车,以及巴士楼梯板壁上的新旧图画等等,西西所记让我们感到万象纷呈,你刚才所说“都市万花筒的千姿百态”是贴切的,这在一辆公车上来展现就更加典型化。联系十个小标题来看,这里面有大纲有叙事,有集体无意识有多声道,有确定性有不确定性,有种族有性别,等等。你刚才说到西西接受过存在主义的影响,让我想到“身体”和“自我”这一对概念。巴士作为一个日常生活场域,是一个“自行显现”的“外在实在”,在它上面有许多互不相关的并列的事物,形成一系列感官的碎片,如同生活每天在许许多多场合下所发生的一样。它如何跟同乘于巴土上的观察者发生关系呢?假如观察者不产生对雷蒙·格诺的《文体练习》的联想,那么观察者也只是个纯客体的存在,他(她)也就参与到当下事物的“千姿百态”中去,这种“千姿百态”对于当下社会来说,其实是一种涣散——也就是参与到现代社会生活情境的分散和裂变中去,从而主体成为缺乏感知和反思性的非存在,成为一个涣散的“自我”的缺场。
马一川:“身体”在场而“自我”缺场。
嵩松:是的,尤其在后现代社会,当人的生活缺少某种精神追求时,生活就是随机的,兴趣是随机的,人的视线所投射也是随机的、发散的,没有聚焦,正像在运行的巴士上,此时不做何想,身心都交给一次短暂的停歇,眼见什么头脑就被动地接受什么。这样一种情形类似雷蒙·格诺所描写的公共汽车小故事:“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模糊的并闪烁着珠光,还有各种各样分辨不清的显现物……”然而雷蒙·格诺的公共汽车系列小故事中反复出现这样一个情境“朋友建议他,让人在他的红色大衣上加一个扣子”,我想这应是有所暗示的,一个“建议”是有主体性的;“加”上什么,是因为缺了什么;“扣子”则起连缀、弥合作用,这对于“涣散”的、“碎片”的生活是否有所建议呢……
马一川:你这样说是否有“过度诠释”之嫌?
嵩松:也许吧。不过我还是觉得这篇小说的副题是“向格诺致敬”,而叙述主人公在客观地叙述巴士情景之后产生的联想表明了叙述者主体意识的在场。总是区别于其叙述对象的,这对于感官的碎片不能不是一种穿透,不能不是一种隐藏的主体。西西的小说具有现代寓言性质,她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大师那里吸收了许多表现手法,比如“寓言式、童话式的现实主义”,其中意绪,并不那么一目了然,而是要求读者在辛勤的阅读劳动中产生顿悟,从而获得阅读的快感。卡尔维诺说“阅读就像在丛林中前进。”(《看不见的城市》)就是这个道理。何况《巴士》还是一篇“后设小说”,作者用对雷蒙·格诺的联想应照了前面的叙述。
马一川:由此来看《新春运程记历》这一篇就很典型,初看不懂,不断参悟之下才能明白其中的玄机。这是一篇形式很奇特的小说。看上去很像中国旧年历的一部分。从正月初一至十五,今天适宜干什么,明天可以干什么,标识得清清楚楚。只是旧年历除了一天能干什么,还有不能干什么,而这篇小说背后浓缩的,却是很深层的香港的城市心理。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化的大都市,也是一块传统的迷信的土地。在香港,笃信风水、信奉神灵,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使一些简单的事情,由于与神秘玄虚搅在一起,往往也变得复杂繁琐。传统的新年,这个合家团聚、访亲问友的节日,本来是人生最诗意、最自在、最放松、最尽兴的假期,因为失去了理性,受制于不可知的运程,生活反而变得零散化、支离破碎、无所适从,令人不胜感慨。
嵩松:说得好。一个人的日程如果按照这个“记历”而安排,表明很有计划性,显示了当下社会人的运行轨道:然而从“记历”的内容来看,所谓“宜”这“宜”那,这也好,那也不错,是一厢情愿的,
却又是毫无自我的。假如一个人(依情形看还是个写作人)的生活内容确如“记历”所标示,则是无中心的、充分零散化的,主体在此间不说消弭殆尽,也是“魂离魄散”,这正是后现代人的典型特征。
马一川:依照上述方法来阅读《创业》和《盒子》两篇就容易多了。《创业》中的两个失业青年以经营侵犯人权、有伤风俗的“打傻瓜”而被取缔,却意外赢得显赫的“国际游乐场”的录用,生动刻画了现代都市人的心理阴暗、刻毒的一面,同时也呈现了人间世的无常和荒谬。
嵩松:不错,这个短篇让我想到卡尔维诺的《马科瓦多》,其中有一个故事《弄错了的车站》叙述马科瓦多在一天晚上由于一场大雾使他在回家途中迷失了道路,在一家酒店向人问路却被请喝了不少酒,结果不得要领,自己寻路过程中爬上一处围墙想看清路牌,终于沿着墙头走到了一个“公共汽车”站,上了“一辆车”,十分庆幸,不想那不是车站,他上去的也不是公车,而是飞机,他最终被送往了远方。这个故事的荒谬是事与愿违、南辕北辙,而西西的《创业》,则是无心插柳、柳暗花明,不过人物的命运都阴差阳错、出乎意料;事情都是由小变大,一如“蝴蝶效应”。不同的是,西西所写并非全然讽喻。小说叙述政府鼓励市民创业,那两个开“打傻瓜”店的青年虽然有人身攻击之嫌,但毕竟是响应了政府的号召,也“本来就没有打算永远如此这么打下去”,最终有了正当的去处不是很好吗?
马一川:你是要说这个故事有正面的激励人心或劝诫的作用?
嵩松:我是要说这篇小说其实并不简单。你说的劝诫和激励也是有的,但并非没有笑谑的一面。这里面是有一种荒谬感第一层笑谑是:“打傻瓜”的生意很好,那些被当成傻瓜打的都是些名流,这一方面表明打的人心理刻毒,另方面也表明名流与公众严重脱节。第二层笑谑是:社会认定那两个创业者所创的业不妥,必须由警察来干涉,结果却让那两个家伙就上了更好的业,真是歪打正着,荒谬套着荒谬。但仔细品味,西西的叙述还有另外的一面尽管现实不易,荒谬之事十有八九,但终究是“天无绝人之路”,只要走正道,把聪明才智用在适当的地方,还是有希望。这样看,《创业》就是笑谑中的温馨,温馨中的笑谑,构成小说的张力。或许可看作巴赫金说的“复调”小说。
马一川:这样看,这篇小说是如此丰富,也符合生活的实际。以此来看《盒子》,也是可以深究的。这里讲述了一名“守盒奴”的故事。单身贵族王老五,为追赶潮流率意消费,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消费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如果城民个个做守财奴,商店没生意,厂商少出产,劳动大军个个失业,城市哪来安定繁荣?”这种理论听起来振振有词,颇有说服力。实际上,这是对1933年美国“罗斯福新政”之后影响全球的经济政策“以消费带动发展”的一种曲解。“罗斯福新敢”的初衷是: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盘活呆滞的国家和社会资本,推动社会形成一种处理财富积累和消费的理性的观念,从而帮助美国人更充分地享受物质生活。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王老五东西买回家后,为了完整保留包装盒上的品牌,他把东西一件一件全部井然有序地堆放在房子里,不使用也不拆封。慢慢地,家变成了盒子储藏室。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有则故事:“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椟,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都市贵族王老五,重品牌大于产品,爱形式甚于内容,俨然成了“买椟还珠”的现代翻版。
嵩松:问题的症结呢……?你刚才讲到这个王老五的“理论”……
马一川:——问题更在于王老五为自己的重品牌、爱形式寻找到一种似是而非的价值观,比如“环保先锋”啦、美观、牢靠啦(其实包装物越多越不环保)使得自己的行为具有相当的自觉性,这是非常要命的。
嵩松:是的。卡尔维诺在论说博尔赫斯时说“……解释一位作者在我们大家身上唤起的共鸣,也许我们不应从宏大的归类着手,而应从更准确的与写作艺术相关的诸多动机着手。”(《为什么读经典》)这方面我们还议得很不够。卡尔维诺谈到博尔赫斯的简洁与精练。我想西西的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突出的特征,简洁而含义隽永……
马一川:我想说《巴士》《创业》《盒子》和《新春运程记历》从头到尾,没有许多形容的描绘,没有抒情和主观的议论。四个短篇放在一起,仿佛在做×光照射,先是对当下扫描、透视,然后叩问、思索,最后形成缤纷的现代都市咏叹调。另外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曾评论西西的小说是“寒杯暖酒”。或许这个世界太沉重、太悲观,就像作者在与何福仁对谈的《童话小说》中所说过的那样,“我比较喜欢用喜剧的效果,不大喜欢悲哀抑郁的手法……当悲剧太多,而且都这样写,我就想写得快乐”,她不忍心再刺激、戳伤她的小说人物以及钟情于她和她的小说的读者。
嵩松: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