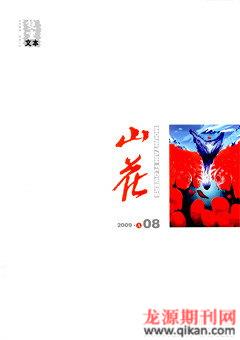正声何微茫
周立民
我是通过《送一个人上路》认识小说家张学东的,至今头脑中还保留着当年读这篇小说的印象,作者不动声色地讲一些似乎杂七杂八的事情,在沉稳的铺垫都完成以后,结尾才水到渠成地杀了个漂亮的回马枪,将底牌亮出,一下子就把岁月、生命、承诺等大问题像堵高大的墙一样横在你面前,你不由赶紧停下脚步,此时回头再看前面的枝枝节节不但不显得冗余,反而更紧密地咬合在一起。现在是作家浮躁,写出的小说显得急躁,像这样沉得住气诱导读者一步步走进它的伏击圈的小说实不多见,因此,一下子你就记住了这个作家和这篇作品。
这几年是张学东创作的井喷期,这也使得我陆陆续续读到他越来越多的作品,不管内容和写法上有多大的差异,它们带给我的总体印象都很鲜明,质朴、刚硬的文字中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正气。何谓正气?是那种文笔所传达出来的直面生活、照拂内心、关怀生命、排解苦难的气象。在近几年西北作家的创作中,这种气如同大漠雄风吹荡文坛令人为之一振。有人说,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中最基本的意蕴吗?我说:是的,但是你看到了吗?这些年当代作家们已经将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丢失殆尽,结果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最有力量、最鲜活和质感的日常生活,看不到人的精神的挫折和昂扬,看不到世界中的光亮和希望,文学如同吸食了鸦片的人,面黄肌瘦,心不在焉,软弱无力;而这时,倘若有一种刚硬有力、正气淋漓的文字出现足以值得珍惜。也有人说,西北一些作家笔法陈旧,脱不出现实主义的路子,言下之意是早已“过时”。对此,我也不能赞同,表达方式的选择受制于作品的题材、内容,甚至是作者的生活经验和自身体验,深入到这些作家们生活的土地和他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会深深地理解,他们自有无法超越现实主义的理由,自有无法轻松游戏的良心,在一个什么都可以被娱乐化的时代中,他们可能无法登上时尚号列车,但却没有背叛脚下的土地和心中的良知,他们有根才不会随意跟风摆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丢了时尚,得了大气、质朴。当一个时代漂浮着靡靡之音和流行着软骨病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对这样的文学精神投入更多的关注目光。
这么说,并非是只承认“大江东去”的文学价值,而否定“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意义,气象可大可小,笔触可粗犷可细腻,这不足以分出高下,我看重的是文字背后凸显出来的精神。这个精神的内容或积极或颓废尚且不论,关键是文字中有没有一个显示出作者强大的精神涌动的气势存在。如果有,那么文字就有了“风骨”。而“风骨”对于文章的意义,古人早有所论,他们把文字的骨力比作人身体中的骨架,情感的教化看作人的气质:“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倘无“风骨”,哪怕辞藻丰赡,也会文采黯淡,所以论者再次强调:“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牵课乏气,则无风之验也。”(刘勰《文心雕龙》第二十八风骨篇)有风骨之作,不论表达生命的昂扬高姿,还是浅唱低吟,都掩不住强大的精神光芒。李泽厚在评价汉魏诗歌的时候,说它们表达的是“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感喟”,显得“沉郁和悲凉”,这样的内容在今天很多作家的笔下最容易变成软绵绵的呻吟,但李泽厚认为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魏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即使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也仍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正由于有这种内容,便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废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美学深度。”(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47—153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那是在那些作家的文字背后有着他们精神上的“信”,而今我们“信”什么?我们关注过这些问题吗?写作在多大程度上不是文字游戏或者显示自己智商的炫耀资本?我并不认为西北作家都是有具体的精神信仰的,但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在精神上都与这片土地、生活和人保持着紧密、畅通呼吸通道,生活本身带给他们的东西要远远比流行时尚、学术概念和都市浮风更有生命的痛感,而这些无疑又是作品中最能打动人和最有力量的部分。
用地域、风格来说明作家的精神养成能够显示出作品的根源,但也容易陷入分类学机械的陷阱中。比如在讨论“南方精神”的时候,有人用“水”的意象来形容,灵动、潮湿、迷幻、充满想象力——都不错,但反过来的北方精神呢?可用“风”做比,但难道它只能粗犷、坦荡、有力,就不能有其他吗?只能有黄沙漫天,就不能有春风化雨吗?反过来再说南方,难道只有小桥流水吗?现在人口流动那么频繁和容易。显然不能这么简单地界定了。比如张学东的小说,在那种质朴、刚硬中却又无比细腻,它们是那么自然地统一在一起让你看不出丝毫的做作。这最为典型地体现在《未来的婆婆》一篇中,小说对于小儿子“定亲”这一天“未来的婆婆”内心的描述可以达到绣花的地步了。孩子们都一个个结婚离开了她,这个家即将只剩下孤单的她,儿女出巢,留给她只有岁月消逝、青春不再的感叹,这种对生命的感悟是在闹哄哄的外在场景下孤独地发出的。张学东的细腻就是捕捉到这种“孤寂”感,那种谁都没有关注她谁也不曾觉察到的生命悲叹。小说中两个细节非常漂亮:如果说这位“未来的婆婆”的孩子与她有代沟的话,那么与她一起经历了岁月风雨的孩子的姑母总算可以理解她了吧?但小说中描述的却是这样的场景:
她躺在床上辗转着,并突然向睡在身旁的姑母问起了老疙瘩出生时的情景,她说好像才一转眼的工夫,他怎么就到了该娶媳妇的年纪?然后她不无叹息地说,真是岁数不饶人呀!我们一晃都老得快不能动弹了。令她没想到的是,姑母的回答竟是含糊不清的,像是纯粹的应付或回避,又仿佛真的忘记了过去的事情。……
有老半天她都奇怪地怔着,好像姑母的话根本不是说给她听的。对于姑母的麻木她多少感到有点生气的。
于是,她不再吭声,在渐渐明亮起来的昏暗中想着姑母刚才说过的话,心里是别番滋味,酸酸的,又涩涩的。想着想着,喉咙有些哽咽,眼角竟无端涌出一珠浊的泪,在即将来临的晨曦中闪着铅灰色的光芒。
她得不到任何回应,姑母的麻木让她生气,但她的泪却不完全是为这而流,那是因为内心的郁积丝毫不为人关注,而她又不能直接去倾诉,这样欲言又止的境地让她“委屈”地流泪了。另外一个细节是当她思前想后,终于按照自己的心愿将那件红色外套穿到宴
会上,儿子丝毫不曾关注她红肿的眼睛,不曾留心她的内心波动,这些只有她自己来反复咀嚼:在人都散了单独一个人在房间时,作者曾描述她如此复杂的情绪:“而此时房间的过于宁静使她有种迷失般的空茫,好像刚才的人头攒动和喧闹只是一场梦,梦醒了,惟独她还留在这间空荡荡的房子里。”她关心着外界的每一个最细微的情绪,但却不希望人家觉察到她的情绪,儿子没有体察到妈妈最重要的内心,却对衣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老疙瘩似乎觉出还有什么不妥,盯着她怪怪地看了两眼,接着他小声说妈你怎么穿成这样,也不看看今天是啥日子。她没好气地把脸撇过一边,她不想让他看见自己的眼睛。喧嚣又重新回到她的耳朵里。”她就这样被忽略了,她甘愿这样,但谁又知道她内心中渴望着歌唱呢?“她也许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事情真的已是时过境迁,青春逝去了便再也无法挽留或弥补。”这里有深入骨髓的生命体验,整个小说在一个“定亲”的故事框架下却细腻地唱出了一曲抒情的歌,对“未来的婆婆”内心的曲曲折折展露无遗。小说中有感叹,却没有堕落到前些年流行现在也不衰的某种怀旧情绪中,那种怀旧更多是对于场景、物品和诸多小细节的留恋,依恋到把这些物质性的东西当作生命本身和世界本身,而《未来的婆婆》在“细”中有“大”,它几乎没有这些物质性细节琐碎的描写却抓住了内心的丝微变化,世界再大也是小的,人心再小也有包容世界的大。在《左手》中,通过对一位少女内心的体察,张学东以另外一种方式捕捉每一个可能被放过的细节,那些不经意的一笔都是作者锐目和匠心精心谋划的结果。《未来的婆婆》是深入内心向外写,而《左手》则是由外而内,从这位少女的一举一动来写她的所思所感。作者从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左撇子写起,写出了少女起起落落的内心变化。左撇子总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感觉,但物理老师的看重,却调高了她的心劲儿;没想到接下来是老师不再教她的班级了,情绪又落下来了,在还不曾落到谷底的时候,同桌男生又出现了,居然有一个为她挺身而出的人,她的心绪又昂扬起来,没有想到嫂子的偶然闯入再次让她的情绪经历了冰霜。直到最后,是情绪陡转直下,当她举起那把刺向嫂子的剪子时,既在情理中。又在理性的控制之外……在这个叙述过程中,作者不放过每一个小细节,比如开头写到嫂子,写到巧手女人剪窗花的那把剪子,看似无意,但当结尾那幕悲剧出现后,都觉得无不体现出作者的精心。
这种精心体现出作家的叙述能力,但我想多问一句:这种叙述能力又从何而来?语言文字的训练、谋篇布局的剪裁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但作者有一颗悲悯、柔软的心恐怕更重要。有这颗心他才能体察到他人内心的瞬间变化,才能捕捉到社会中的点点滴滴,这颗心似乎不在创作的具体过程中,但它却是创作的氧气,弥布在作家的每个举动里。这不是什么玄学,但确是一辈子只会玩弄文字的人所体会不到的博大。在一次对话中,我曾经这样评价张学东的创作:张学东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作家,他能把握住人性中恶的因素,但同时又不让这种人性下降到没有光亮的淤泥中,他总是给他们光,用善良的目光打量他们,用希望的光(指唤醒内心觉醒和人性回归的光)来引导他们。先锋文学当然有很多优点,但作者对笔下的人物都很冷漠,善、恶被取消了,天使和魔鬼平等了,但大家不是都恢复为人,而都成了魔鬼,实际上缺乏一种精神提升的力量。而张学东不排斥现实世界的复杂,又透过文字将你自己内心中美好的追求表达了出来,阳光的力量与正气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三个短篇称不上张学东最优秀的作品,但上述的创作品质也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三篇小说有一个一贯的东西,那就是都体现着作者对于被遗弃者、少数人、弱势者或者说不被人关心的人的心灵关怀。《未来的婆婆》不用多说了,这位“未来的婆婆”被青春时光抛弃了,也逐渐地被子女“抛弃”了,作者的这篇作品是在给这些内心被忽略的一群人送去了温暖。《左手》中作者对于少女内心的这份情感的体察更是让人心颤,在生活中,我们见过多少“左撇子”这样与社会习惯相左的少数人,我们何曾关心过在强大的社会规范压抑下,他们的内心体会?我们又见到过多少对他们粗暴的干涉?所以《左手》的问题完全不是一个左撇子这么简单。其实涉及到很多大的问题:社会与个人,群体规范与个人自由,渺小的个体力量与强大的社会集体力量对抗时的心态、选择和出路等等?“执拗”是这个少女的性格,但小说结束在悲剧发生的那一刻,我不敢想象这位花季的少女下一步路怎么走?这种执拗是否就此被摧残,还是就这样执拗下去?但这样的执拗需要多大的心理承受力啊,她有吗?我想作者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都在小心翼翼地卫护着这个女孩子不被伤害,所以作者给她安排了那位物理老师,作者给她安排了与同桌男生那段朦胧的情感,让这个少女能够看到生活中的阳光。这种阳光甚至都照耀在其他人物的身上,少女的老师、父母、嫂子这些人都在无意地充当凶手的角色,但作者没有把他们写成凶神恶煞的嘴脸,而是照样写出了她们在社会习惯的眼光下对自身行为的浑然不觉。这样的反差,更让人多了几分对少女命运的感叹,再远一点想,我们每个人不都身陷这样的境地吗?执拗,还是放弃、顺从?这真是一个问题。《猫命》是一篇鬼影幢幢的小说,但哪怕在这样非常态的人物身上,也能看出作者的慈悲之心。在这里,小男孩瘦瘦又是一个被父爱遗弃的人,作者虽然没有明确交代,但分明暗示了他的父亲是谁都是一个弄不清的问题,在秋皮的眼睛里,这个儿子还不如猫更令他疼爱。我注意的是当这个缺少父爱照拂的孩子被压在粮堆下死去后,一直对他冷漠的“父亲”秋皮的表现:
现在,我们注意到秋皮从劳模家仓房里将他儿子瘦瘦颤颤微微地抱出来,晨曦沾染着一丝清凉的水星悄悄地落在他们身上,仿佛观音菩萨从玉瓶中弹出的圣水。
事实上,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狗日的秋皮那样抱着他的儿子,我们无从知道瘦瘦是否还能感觉得到这一切。那时,秋皮的眼泪居然也噼里啪啦地往下掉,跟下雹子似的。
秋皮的眼泪,可不可以看作他内心的自我谴责呢?是不是他良知复苏的体现呢?更为值得追问的是,秋皮后来的失魂落魄究竟是为了猫的走失,还是为了不能原谅自己对于瘦瘦的所作所为呢?不论怎样,作者没有在这篇小说中制造一个完全冰冷的世界,而且他的感情投注却是每位读者都能够感觉到,你可以说作者不决绝,但你没有机会去指责作者的冷漠。如果顺着这条线索解读下来,那就是秋皮很清楚瘦瘦不是自己的儿子,但这个难言之隐又不能为外人所道,重压让他内心变形而将很多情感转移到猫的身上,这样,瘦瘦可怜,秋皮不也是吗?那么这对“父子”关系,可以比照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来解读了,余华是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温情,而张学东是曲折的,但不论怎样,两者可能都触及到中国民间社会中最核心的道义感和情感的表达方式。这几年,表现底层、关怀弱势群体的文学作品潮涌而来,在话语上也颇占风头,我常
常在想作家的美好心愿当然值得肯定,但作为文学作品究竟该怎样表现、怎样关怀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心”的问题。作家是为了追逐形势,还是真有一颗悲悯之心?是处处能够体察世界理解他人,还是不过听了感动的故事洒几滴眼泪?这里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汪曾祺先生在讲到小说作法的时候,提到沈从文先生当年给他们上课时说:“要贴到人物来写。”汪先生解释:“笔要紧紧地靠近人物的感情、情绪,不要游离开,不要置身在人物之外。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拿起笔来以后,要随时和人物在一起,除了人物,什么都不想,用志不纷,一心一意。”如何能做到这些?“首先要有一颗仁者之心,爱人物,爱这些女孩子,才能体会到她们的许多飘飘忽忽的,跳动的心事。”汪曾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晚翠文谈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将心比心,用你的心贴上人物的心。从这一点来说,我非常看重张学东骨子里的那一丝温情,是它们造就了当代文学中难得的“大雅”、“正声”。把张学东的作品归到关怀底层的序列中,作者未必愿意,但他的整个写作难道不是时时寄托着这样的关怀吗?
当然,如果非要吹毛求疵找一点我认为的不足,我想选《猫命》这一篇来简单谈一谈。毫无疑问,它是这组小说中个性最为鲜明的一篇,可是作者用劲力气造足了小说的气氛,却似乎忽略了人物之间的关系,这样使得每个人物虽然围绕着猫建立起一个关系,但实际上却没有形成彼此制约或抵抗的小说逻辑关系。比如秋皮和他女人的关系就不明确,看不到两个人内心的交锋;秋皮与其母亲,特别是中间还隔着小说中的重要“人物”——那只猫——究竟是什么关系?母亲是为了找猫死的,秋皮为什么反而那么爱这只猫?难道真的以为母亲的亡魂在猫身上,还是前面说到的仅仅是转移受压抑的内心情感?那么,秋皮爱他母亲吗,还是痛恨?秋皮为什么在母亲死后那么依恋那只猫,在猫跟母亲一起的时候,秋皮跟猫又有什么关系,跟妻儿又怎样?为什么母亲死了就改变了一切人物关系(小说中分明说母亲死了猫才加入到秋皮的生活中)……这一连串的空白也会使小说的内核空洞起来。当然,计白当黑是作家处理小说显隐、虚实的高妙手段,但如果必要的“关系”搭建不起来,小说这栋大房子也没有办法在人们心中挺立起来的。不知道我的感觉是否正确,作者显然是在寻求创作中的某种变化,但我的建议是。变化中不能丢掉西北作家与生活与土地那种不隔的关系,也就是要质朴,而不要花巧。对于张学东的整个创作来说可能也是这样,需要守拙、养气,最初的创作是自然的涌动和生命的喷发,后来的创作是设计和谋划,此时如何能不失本心又能超越一己的局限很重要,拿捏不好,常常顾此失彼,买椟还珠,丢了西瓜捡起芝麻。此时,我认为多想一想少写一点未必是坏事,有时写多了可能不是磨练,而是将许多本真的东西消磨掉了,反倒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