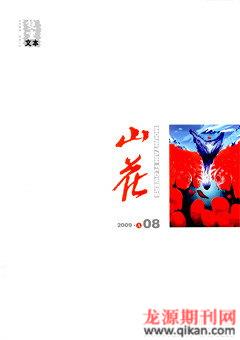“驻校诗人”札记
纽约州暖房的南瓜
9月4日下午,从北京到达芝加哥机场。我们将从这里转机去纽约州的锡拉丘兹。排了大半个小时队,终于通过边境检查后,我们来到大厅外面,小王奂一下子兴奋地叫了起来:原来这个小车迷看到了好几辆徐徐开来接人的加长林肯!
小王奂这次可真够兴奋的,一上飞机就望着窗外,并不时地问“怎么还不到美国呀?”然后头一歪,就睡着了。这次,美国大学提供的条件还不错,我把他和他妈妈都带上了。在那里,他还要上幼儿园,因此临行前有朋友笑着对他说:“等你回来,你就成了‘小海归了”;“我才不是小海龟呢,我是小王奂!”
一切顺利,到达锡拉丘兹机场后,柯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的教授John Crespi——他的中文名字叫江克平,已在那里等了许久了。开车近一小时到达住地,一进屋,拉开灯,见桌上放着彩纸包着的笔记本、笔等礼物,原来这是大学住房部送的。更使我们感动的,是克平的云南妻子刘波涛特意为我们准备好的晚餐:一盆热乎乎的云南米线。打开冰箱,我又惊讶了:原来克平已提前为我们买好了牛奶、橙汁、各种水果、啤酒、肉和蔬菜。再看厨房的桌子上,还有面包、咖啡和大米!我们连声道谢,克平笑着说“不用谢!这在我们这里叫Warming house,暖房!”
最出乎意料的,是桌子上还有一个他从自家花园里摘来的圆圆的红黄色南瓜。在他走后,我把它摆在齐肩高的洁白冰箱上,愿它像个温暖的灯笼一样,照亮我们在异乡的生活!以牙膏大王的名字命名的大学
中午,江克平开车来接我们去学校。先到“人力资源部”报到,然后到东亚系,在系秘书那里领到一大串钥匙,还领到一个崭新的IBM笔记本电脑,更没想到的是,学校还专门为我准备了一间办公室,门口的牌子上写着:Jia Xin Wang,Henry R·Lute Poet-in-Residence(王家新,Henry R·Luce基金会驻校诗人),名字下面,还标注有为我新设的大学的电子邮件信箱。
这使我受到了触动。我所在的北京某大学,因为这些年的发展,从去年起为每个教授开设了单独的办公室,门口也有一块牌子,上书“教授工作室”,不过没有教师的名字,也没有电子邮件信箱。这要靠学生们探头探脑去打听。
办完这一切,出了办公楼,发现小王奂和他妈妈正在校园山坡的沥青路上玩“滚小汽车”。见到我后,他兴奋地说他见到了小松鼠,“像小兔子一样!”我一笑,这里的小松鼠遍地都是,再过几天,他就不感到新鲜啦。
然后,去镇上的超市购物,买牙膏时看着货架上各种样式的“Colgate”牌牙膏(中国译成“高露洁”),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Colgate大学就是以这位牙膏大王的名字命名的呀!
于是回家后就看学校的介绍,它的建校时间是1819年,最初是一个神学院,因为主要受到肥皂大王和慈善家William Colgate的赞助,从1890年起,变为Colgate University。柯盖特大学只有2900名学生,但却是美国文理学院中的名校。中国人往往只知道哈佛、耶鲁这样的综合性名牌大学,但对美国的文理学院知之甚少。所谓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是美国大学的一个重要类别,许多学校都有一、两百年历史,它以本科教育为主,重在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它的录取也很严格,它招收的都是精选出的优秀生,它为学生提供了最优等的学习条件。所以有人说,能上哈佛读本科的,不一定能上顶级的文理学院。相应地,它的学费也很贵。柯大一年的学费为四、五万美元,这大概是一般公立大学的数倍。对于这样的“精英学校”,美国社会上的认可度一直很高。
“柯大”以经济学、社会学、英语文学、古典文献、艺术和一些理科为强项,近些年来,随着所谓“China Rising”(中国崛起),东亚系也有了相当的发展。美国大学的英文系早就有着“驻校诗人”的传统,但由东亚系请一位诗人来做“驻校诗人”,江克平笑着说“这还很少见”!
山坡上的校园
因为时差,这几天天未亮就醒了,于是一家人早早起来跑步。我们跑过周边的学生公寓,跑到橡树大道上时,见小松鼠在草地上抱着橡实啃,小王奂就要去追,但哪里追得上!松鼠跑开后,尾巴抖动起来就像是一大团银亮眩目的蒲公英!
透亮的晨光中,山坡上的校园呈现出来。在我看来,这是世上最美的校园之一。在古老的大树和草坡问,有几十座错落有致的以新古典主义为主调的办公楼和教学楼,Colgate家族所建的白色方形“纪念堂”及其闪耀的金顶则高耸于其上,这使整个校园显得古老而又年轻。山坡下,则是点缀着高大橡树的广阔草地,还有一个小湖,在浸透了晨光的湖水中,两只天鹅徐徐向我们游来。
这是早上。下午五点,参加学校为新学期举办的教师招待会。招待会在教工俱乐部的门廊和花园平台上举行。还没走近,就闻到烧烤的烟味和香味,长桌上则摆有一长排各种吃的和酒水饮料。我们去时,那里已充满了欢声笑语。
许多教师都带着孩子来了。大人们把酒谈天,孩子们则在草地上玩飞碟,或是干脆把自己放倒在草坡上往下滚。小王奂也很想试一试,但中国的孩子就是胆小,好不容易躺下来,小手还紧紧抓住草根不放,我们都笑了。
我们一去,就注意到一个有着黑亮眼睛的三、四岁的中国小女孩,穿着漂亮的裙子,像燕子一样在人群中穿梭。一会儿,她的养父母出现在我们面前,“你就是那位来自中国的诗人?你们的儿子会和我们的女儿在一个幼儿园!”原来,这位生于四川的小女孩在她一岁多时被这对美国教授夫妇所领养,她的中文名字叫“秋雪”,英文名字叫“Dora”(它出自古希腊文,是她教古典学的养父给起的,意思是“礼物”)。就在我们说话的当儿,Dora不时地欢笑着向我们跑来,这是多么让人感叹的“礼物”啊。
说话问,江克平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来了。一个四岁半的儿子,中文名字叫海瑞,“《海瑞罢官》的海瑞”,他笑着对我们说;一个女儿不到两岁,叫爱玛。海瑞生于美国,我们称他为“ABA”(美国生美国人);爱玛生于云南,我们称她为“CBA”(中国生美国人)。这几年克平每年都带学生和家人到中国去,因此海瑞会说不少中文,一见到小王奂,喊了声“小弟弟——”,就一起玩起来了。
小镇生活
今天周六,镇上有周末市场。我们所在的镇子叫哈密尔顿(Hamilton),处在纽约州中上部。除了大学的学生和教工外,当地居民只有数千人。美国很多大学并不像中国那样集中在城市,而是处在乡下小镇。哈密尔顿就是一个以大学为主体的小镇子。
天气如此美好,我们穿过安静的居民区,被一家家美丽的房舍和花园所吸引。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偶尔开过的车、戴耳机跑步的学生和从远处传来的小教堂的悠扬钟声。这种安静,真是让第一次来美国的胡敏深感惊异。
不仅安静,我们在内心里还有一种喜悦。金秋九月,许多家门口的台阶上都摆上了南瓜,就像中国人家门口挂着红辣椒和老玉米一样,有一种喜气。家家户户的儿童自行车也都不上锁,就那样歪倒在草地上。偶尔碰到全家人在外面收拾花园,见我们走过,就直起腰来打着招呼。我想如果梭罗活在今天,他也不一定非要到瓦尔登湖畔隐居,他在这里照样可以过上一种宁静的生活。
就这样走了20多分钟,到了。周末市场设在有着喷泉和小凉亭的镇中心花园草地上,电线杆上则高悬着印有向日葵花卉的风旗,这是哈密尔顿镇的标志。我们去时,四周的农民正陆续开车来,摆上他们自家种的各种蔬菜、水果、烤制的面包、奶制品和手工艺品等等。市场周边烧烤摊上升起的白烟,则为这一切增添了氛围。
说不清从何时有了这个周末市场,人们只知道这是“传统”。在一个工业化时代,这大概是最后残留的“小农经济”了。前来摆摊的农民,有的一家老小还穿着传统的衣服:男的,无论老少都戴着那种宽边牛仔帽;女的,则穿着那种下面撑得鼓鼓的老式农家女裙子。如果不知情,还以为是在拍电影呢!
他们就这样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绝不像中国的小贩那样高声吆喝。这里的东西也不用“大力推销”,它们既好又便宜。苹果,西红柿,还有豆角、甜玉米、茄子以及红壳鸡蛋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买的。买了一小袋黄金果后,我们马上品尝起来,它那么甜、多汁,真不愧为刚从地里采摘来的,一碰就破皮。靠着这个和一个带果仁的新鲜全麦面包,我们闲逛时有了午餐了。
就在逛市场的当儿,我发现镇中心花园的石头上还有一块铜牌,撰刻着“把哈密尔顿的精神传至未来一代代”的字样。这使我不由得肃然起敬。看了这句话,再看这眼前的一切,似乎它已被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
“诗歌和倾听的伦理”
东亚系和其他几个文科系共用一个楼。这里的走廊里挂着各种绘画作品和讲座海报,教室则多种多样,有那种我从未见过的带大椭圆形圆桌的讨论式教室,还有带沙发和小圆桌的学生休息兼自习室。相应地,教师的工作条件也很好,每一层楼甚至有专门的小咖啡屋,放着咖啡和茶,供教师们免费享用。
东亚系这学期的讲座很少,但英文系的朗诵和讲座系列却使我有些吃惊,在其节目单上,我兴奋地看到美国著名诗人查尔斯·西米克将来朗诵,不过是在明年三月(那时我们已回国)。不过,今天下午却有另一个讲座:“诗歌和倾听的伦理”,由耶鲁大学著名教授Geoffrey Hartman主讲。哈特曼有着许多显赫的学术头衔,是诺顿文学选集丛书总编,美国最有影响的老资格的学者和批评家之一。
我和克平都被这个讲座所吸引,那就一起去听听。一进演讲厅,就遇到在英语系执教创造性写作的来自亚美尼亚的诗人彼特,看来他在美国已生活多年了,经克平介绍一认识,就像老相识似的对我说“我们应该在一起干点什么!”“好啊”,我回答。
大概是冲着哈特曼教授的名气,来了很多学生和老师。这次我才注意到,像画展的开幕酒会一样,在演讲厅最后排的桌子上还准备有各种小吃、沙拉、矿泉水和葡萄酒(不过,酒瓶边专门注明了只有过了21岁才能饮酒,这是美国的法律)。克平告诉我柯大的任何演讲都准备有这些东西,这只能让我感叹了。
学生们排队进来,挑选一点吃的,拿一瓶矿泉水,然后走向座位。因为天气有点热,一些女生坐下后脱去外套,有几个甚至只穿着一件小背心。也许,这些露着光洁肩膀的女生,比台上那位白发老教授更具有美学的挑战性?当然,我们的老教授不会去想这些。他在台上动情地谈论着密尔顿、华兹华斯、济慈、斯蒂文斯这些代表着英语诗歌一个个光辉时代的诗人,而“小背心”们也都专注地听着,并不时地记着笔记。从抽烟谈起的演讲
来美半个月,我几乎没发现有什么人抽烟。这真是一个和中国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么,我来这里干什么呢?只是在这美丽的校园里悄悄留下几个烟头?
这就是我在东亚系第一场诗歌讲座的开头。下午四点,我以为只有二、三十个学生来听,没想到来了五、六十人。他们中有学生,也有老师和其他什么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人一多,也就有了气氛。江克平的介绍过后,我从“现代性”在中国五四前后的发生,谈到中国新诗的历史,谈到我自己成为一个诗人的一些经历,谈到目前中国诗歌的状况以及全球语境下的一些文化问题,等等。我就这样讲了一个半小时,然后是回答问题。最后,在听众热情的掌声中。江克平从另一张麦克风桌边挨近我低声说:“讲得很好!”我说“谢谢!是你翻译得好”!
讲座后,东亚系请客。我们分乘两辆车前往离学校几英里外的一家湖滨饭店。一路上,隔着车窗,看着三五鹿群在森林边缘和金色的夕光中出没,真是犹如幻境!我不由得想起了胡敏来这里后的感叹“这才是和谐社会呢”。
饭店的环境安静、优美。讲座之后,大家也都很放松,尤其是点的酒上来以后。系主任卞荣青教授是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50来岁的样子,朴实、和蔼、细心(我们来后,她也专门去我们家送去了一条新毛毯“暖房”,这让我和胡敏都很感动)。教学之外,卞老师还在写一本关于法国象征主义与中国新诗的书,因此席问我们又谈起了波德莱尔、李金发等。后来不知怎么的又谈到了钓鱼(大概吃的是鱼、又处在湖滨吧),我真希望克平如他在中国说的那样带我去钓鱼,“好啊,不过,你需要办一个钓鱼证”,“啊,这么麻烦?”“这是在美国呀”,说着,他从钱夹里摸出了一个像驾照似的钓鱼证,我们都笑了。
秋天的音乐会
昨夜一夜秋雨,但早上起来,天空仍晴朗如初。这真是人们所说的“暖秋”了。一个月来,除了树木开始变成彩色,天上有更多的雁阵飞过外,气温并不见下降。柯大的男孩和女孩们仍是初秋的装束。
下午三时半,去Colgate纪念堂听音乐会。这座有着白色方形金顶的纪念堂,内里是一个中型的音乐厅,可用高贵典雅来形容。这里每个周末都有音乐会,对学生和教职工开放。这是柯大校园人文氛围中浓郁的一笔。
我们已经在这里听了一场音乐会,那是舒伯特的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这种忧郁而热情、富于幻想和安慰的音乐在初秋演奏真合适,它仿佛就是秋天本身发出的声音。
这一次,是柯大管弦乐队演奏圣桑、布鲁赫、莫扎特的作品。管弦乐队由学生和教师混合组成,年龄悬殊很大。女指挥的名字叫MariettaCheng,四十岁左右的样子,一头黑亮的短发,我猜她是出生于美国的中国人(幕间休息时间熟人,她果真是。她已在柯大音乐系执教多年)。她身着黑色露肩礼服,指挥风格刚柔相济,优美的身子经常倾向乐队,真有一种舞蹈之美。
音乐会以莫扎特的第39号交响乐开始,随着女指挥的手势和示意,十多架小提琴的齐奏就像秋天山坡上最先燃烧的红叶一样,一下子就把人们吸引住了。但我更喜欢的还是布鲁赫的大提琴协奏曲,尤其是其中的大提琴独奏,深沉、悲怆、激越,那是艺术家灵魂
深处最感人的道白。
音乐会后,黄昏的回家路上,又一群大雁从头顶的上空飞过。它就像是那袅袅不绝的余音,再次把我的视线引向那金色澄亮的远方……
友人来访
晚上九点,麦芒终于从他执教的康州学院(位于东海岸的新伦敦)赶到,他大概冒雨开了五、六个小时的车。麦芒来美前为谢冕先生的博士,早年在北大读书时即崭露出诗歌才华,和西渡、臧棣为诗友,两年前在北京新出了他的诗集《接近盲目》。这个留着长头发、看似放浪不羁的人,在异乡多年仍不能忘情于诗,并且在骨子里保有他对诗的赤诚和严肃。记得几年前突然收到他发来的英文电子邮件(我们很少通信),说在网上读到我的一首诗《田园诗》,感动得流泪,因此给我写来这封信和一个英文的短评。就凭这,我们可以在一起更深入地交流了!
因为和麦芒也很熟悉,克平也连夜过来了,并带来了本地酿造的带南瓜味的黑啤酒。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吗?在这个安谧的雨夜,在那间透出灯光的屋子里,有两三友人在谈诗……
康乃尔大学
柯大离康乃尔大学不远,同在纽约州中上部,开车一个半小时即到。我前后去了两次,一次是和麦芒一起,一次是去看定居在那里的老友一平。
第一次临近康大所在的伊萨卡时,我们在路边居然看到了一家孤单单的旧书店,这不禁使我欣喜若狂。这正是我来美国后最想发现的地方。我在那里买了一本希尼诗选和一本洛厄尔诗选。洛厄尔诗选里画满了线,还有评注,但为什么又流落到这家旧书店里?
而“伊萨卡”(Ithaca),也正是荷马史诗中尤利西斯家乡的名字。看来移民来的欧洲人,最初是想在这里重建家乡啊。这真应了一句中国古诗:却把他乡当故乡。
康乃尔,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之一!纽约州上部有上十个手指形的湖(Fingerlakes),康大就建在面向其中一个最大湖区的山坡上。大学艺术馆的五楼是看风景的最佳所在,从那里,校园和山坡下的伊萨卡城镇尽收眼底,那悠长的“手指湖”也像河流一样,把我的视线带向远方。怪不得胡适当年在这里留学时会写下“皮克里克到江边”(他把英语的野餐Picnic变成了四个汉字,以符合旧诗的七言形式)这样的“诗”了!如此美的地方,这位从中国安徽乡村来的小子一高兴就到江边(湖边)野餐去了。
和柯大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不同,康乃尔校园的建筑,大都为哥特式风格和现代风格混杂,错落有致,十分耐看。它的图书馆里有中国专馆,里面有数十万藏书,真让我吃惊。它那颇有名气的艺术馆也以亚洲艺术收藏著名,我们去时,那里还有一个新展出的西藏宗教艺术展览。挤满了参观者,由此可见西方人对西藏的关注和兴趣。三楼则是美国当代艺术,一进入展厅,吓了一跳,以为走错了地方,原来一个真人大小的“超级写实主义”女性裸体斜躺在那里。这让我们一时弄不清现实和非现实的区别。啊啊,连小王奂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第一次来时,麦芒特意要去看康大那条著名的桥。它之所以著名,不仅因为它横跨瀑布峡谷,把两片山坡之间的校区连接起来,还因为时有学生在那里跳桥自杀。不过,现在想从那里往下跳就困难了,因为桥两侧已围上了高高的网栏。
那么,问起康大什么传统的学科最有名,答曰:农学系。它的农学专业为什么这样受重视?因为当年它的创始人之一和主要赞助者康乃尔先生就是一个农民(当然是一个很有钱的农民了)。这说明农民办教育,也可以办出一个世界名牌大学来。
康乃尔先生的高大铜像就立在校园广场上,让我们向他致敬。
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另一个人,即曾长年在这里教书、生活的纳博科夫。他就是在这里写下他的惊世名著《洛莉塔》及其他作品的。我本想找找他的旧居什么的,但据一平说,因纳博科夫在伊萨卡时不断搬家换地,已很难找了,那么,且让我们在他工作过的教学办公楼前合个影吧。
与儿子一起喝酒
真要谢谢麦芒!他要开车带我们去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校区,我的大儿子王岸就在那里读研究生。自我们来美国后,就不断通电话要见面,但因为交通困难,直到今天。
孩子早已大了,比我高半头。他一开始见到王奂这个小弟弟时还有些难为情(他们之间差了21岁),但小王奂却对“王岸哥哥”崇拜有加,紧跟在他后面屁颠屁颠的,居然也不要人抱了。路上,王岸看见一只毛毛虫爬过路面,掏出相机要拍,但小王奂早已蹲下,把头探向那地面了——还真默契呀。
傍晚,回到金色夕光下的阿默斯特镇,王岸带我们到一家老饭店吃饭,周末人多,看得出大都是学生,排了半天队,才有了座位。好在这家饭店自酿的黑啤酒很好喝,一大口下去,一天的疲劳一扫而光,大家又兴奋起来。
终于可以和儿子一起喝酒了!而这,似乎是很多当父亲的一个“梦想”,他们盼望能见到儿子,盼望能和已长大的儿子有两个男人之间的交流,盼望那两只杯子能碰在一起!
我发现王岸的酒量不错,一会儿两大杯就下去了。他已不再是几年前那个只喝矿泉水的男孩了。说实话,看着他喝酒,我真的很高兴。
送胡敏和小王奂到预定的饭店后,王岸、麦芒和我意犹未尽,于是又开车到镇子附近的一个老酒吧。一进门口,要查我身份,因为把门的人搞不清我的年龄(按美国法律,不满23岁不能进入酒吧),这时王岸回过头来笑了“他是我父亲啊。”
这里的啤酒真不错,免费的带壳花生也很好吃。怪不得王岸说他和朋友们常到这里。王岸和麦芒再次聊上了。我四下看去,这里气氛热烈,来这里的人大都是当地居民。到外面抽烟时,发现一个穿军装的黑人青年,似乎已在那里徘徊了许久,后来我看到他鼓足勇气走了进来,和我们边上的一个胖女孩搭讪(用麦芒的常德家乡话来说,就是“吊妹妹”),但他运气不佳,那个胖女孩稳如泰山一样坐在那里,对他不感兴趣,于是他只好蔫蔫地离开了。
酒吧,就是这样一个安慰人们孤独、或者说加深人们孤独的地方。
狄金森的花卉
次日上午,麦芒开车先回去,我们在这里再住一天。我们要和王岸多在一起待一待,也想好好逛一逛这个人文荟萃的阿默斯特镇。
白天,看了诗人弗罗斯特曾长年执教的著名的阿默斯特学院,看了王岸在大学里的宿舍,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了镇上的艾米莉·狄金森故居。花园里那棵曾伴随诗人一生的古老橡树仍在茁壮生长,默默地告诉我们什么是永恒。我正在那里沉思,胡敏和小王奂已在草地上捡起了橡子。那些橡子已炸裂,十分光洁,沉甸甸的。由于雨水浸泡,还有一些已发芽了。小王奂说他要用它们喂小松鼠,我说把它们带回北京吧,带回到我们的书架上!
晚上,王岸和我们一起住(饭店里房间很大,可以打地铺)。小王奂睡觉后,王岸打开了他的手提电脑,让我们看他拍的东西。他现在读创造性写作研究生(这可是他自己的选择),但仍保持着对影像艺术的爱好(他的本科是在加州一学院学电影)。他那个20多分钟的小故事片还是几年前他上电影学院时回北京拍
的,朋友帮他找的演员,我则是他的司机(那帮比他还大的演员对他“王导”“王导”叫个不停,都指望他出名呢)。这个作品是他带回到美国编辑的,我们这是第一次看,还真不错!但我和胡敏更喜欢他后来用照片编的一部小电影,那是他和他的日本女朋友在东京的“故事”。作品的形式新颖,情感真切,配乐也很好一也许,年轻时代的爱情本身就是音乐!我也更多地了解了我自己的孩子了。
就在这次,王岸对我讲“爸爸,我已加入美国籍了”。而我该说什么呢。
我想起当年从北京送他到美国俄勒冈尤金的情景(他母亲在那里读博士)。他在那里开始上初一。第一次去学校接他时,当校门打开,当他夹杂在一大群喧闹的美国男孩女孩中间一起涌出校门时,我的泪不禁往外涌……
这些,已是十来年前的事了……
而胡敏用数码相机拍的照片,现在也转到电脑上了。我一看,这些在诗人故居四周和篱笆间拍的鸢尾花、百合花……这些都是狄金森一再在诗中写到的花呀(她死后,她妹妹为她出的第一版诗集的封面上,也正是一丛鸢尾花、百合花)。我和王岸都被这些照片吸引住了。在那里,在一道异样的夕光中,树干后面的丛林为深暗色,树干和花枝却生机勃勃。的确,那是狄金森的花卉,它们忍受着生生死死,忍受着风霜雨雪,仍在我们面前无言地开放着。
我想我还要把这样一张照片,永久地挂在我们在北京的家里!
摘苹果
周六,风起云涌的天空,充满色彩的秋日山川。克平约我们去十多英里外一个著名的家庭农场摘苹果。那里的苹果不仅便宜,而且比超市里卖的要好吃多了。这里的苹果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品种丰富,不同树上的颜色和口感都不一样,有的青红,有的通红,有的脆,有的面——随心所取吧。
许多带孩子来的人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孩子举到那果实累累的枝叶间,让他们的小手去够,或是发出快乐的大叫……
采摘完苹果,克平一家去购物中心了,我们和马克一起则顺访了附近山坡上掩映在树林中的哈密尔顿学院,这也是在美国很有名气的古老的人文学院,诗人庞德当年就曾在那里学习。
在路上,我们还碰巧赶上了一个小镇上的古董拍卖会。原来这个我们多次路过的小镇竟是一个古董集散之地!我们走进拍卖屋时,旧家具、老式灯、古画、瓷器等一件件地从后屋抬到前台来,那拍卖者像唱快板书一样念念有辞,看到台下有人举牌,眼疾手快地一指,然后又紧接着“唱”下一件,一刻也不停。那声音,真是动听极了。我们本来只想进去瞅一眼,但一坐就是半个小时。我和胡敏都很感叹,这本来是一件商业行为,但他们却把它做得这样艺术,重要的是,他们仍保持了那古老的仪式感。
在中国,现在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苹果园、这样的古董拍卖会、这样到处都是的古老的学院?近百年来,那种“进步的风暴”,已把我们文化的根基给摧毁了。美国大学的“创造性写作”
在大学图书馆里浏阅。图书馆宽大明亮的窗户正对着山坡下的“天鹅湖”。两只白天鹅整天在那里游荡,也不读书。据说这两只天鹅一个叫亚当,一个叫夏娃,这都是学生给它们起的名字。
图书馆里有许多中国文学研究和翻译专著,但更多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和翻译集,一本《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我很感兴趣,收有关于王维名诗《鹿门》十九种不同的翻译和评论,其中还有诗人帕斯的翻译呢。
《美国诗歌评论》的版式则和多年前的一个样(90年代初我曾在那里发过一组诗)。它最新一期的卷首诗是一位女诗人的诗《我妹妹的自杀》。其中还有一篇谈米沃什“晚期风格”的长文,我在图书馆里把它复印了。
《美国诗歌评论》和其他杂志上还有多种诗歌出版、诗歌大奖赛消息和大学里的“创造性写作”招生启事。所谓创造性写作(Creative Writing),主要指的就是文学性写作,它往往由著名作家、诗人主持并任教,招收具有写作才能和本科学历的学生,学制为两年,一半时间从事文学课程的学习,另一半时间从事写作实践。第二学年内提交作品初稿并在教授的指导下修改完成,毕业后授予艺术硕士学位(MasterofFineArts)。
这种在美国到处都是的创造性写作项目,已成为美国大学英文系学科机制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美国式”的培养人才的方式。活跃于美国当代文坛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许多都出自各大学的这种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
在中国高校开设创造性写作项目,看来也有着它自身的发展前景。复旦去年正式设立了偏重于小说的创造性写作研究生专业,北大曹文轩教授名下的当代文学研究生,也可以拿创作的小说当论文了。我所在的人大如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专业设立起来,则会侧重于诗歌的创作、翻译和批评。不过,在眼下能否招收到很优秀的学生?或,诗人是能“培养”的吗?
这时再看看那山下的湖,那里已落满了大雁和嘎嘎叫的野鸭,两只白天鹅却不知到哪儿去了。
万圣节
没想到万圣节在这里这么被看重!九月,似乎南瓜一成熟。到处就有一种氛围了,那摆在家家户户门口的南瓜,虽然也可以吃,比如用它做南瓜派什么的,但主要就是为做万圣节的面具灯准备的。
万圣节,在中文中也被译成鬼节。“鬼文化”在这里也很盛行,但被赋予了更多的幽默色彩。节前,这里许多家的门口都挂起了骷髅剪纸,随风飘摇,甚至超市的入口也立着黑色的骷髅,手伸得长长的,邀请人们进入。第一次看到时,真吓了我们一跳。
节前的晚上,克平邀我们去他们家一起做南瓜灯。晚饭后,克平搬来四、五个大南瓜,摆在餐桌上,并开始示范,我一看,很好做嘛。美国的南瓜似乎是专门为南瓜灯而生长的,它的肚子很大,我们先用小尖刀在顶上开个洞,掏空内瓤,然后再用刀来掏出“眼睛”、“嘴巴”……最后,在肚子里放上蜡烛,并点亮,然后关上屋里的灯,啊,效果还真不错!
万圣节那天很热闹,幼儿园老师给小王奂找了一件“小蜜蜂”衣服穿,后背还带着两个翅膀,海瑞则扮演他所崇拜的“蜘蛛侠”。最吸引人的是傍晚,我们和克平一起带着海瑞和小王奂在Dora家集合,然后一起出门,孩子们提着南瓜形的布兜,挨门挨户要糖。海瑞最凶,先是敲门,说几句“狠话”,然后糖就乖乖地递出来了。其实,家家户户早都准备好了各种糖果和巧克力。有的老太太还干脆点上了南瓜灯,坐在家门口等待着孩子们到来。
待我们这支小队伍走到镇中心后面一条街时,远远就听到那里人声鼎沸,原来镇周边的居民也都开车带着孩子们集中到这条街了。黑暗中南瓜灯游弋不绝。孩子们成群结队,装神弄鬼,有的甚至还带着一把大镰刀什么的。看来这条街上每家每户每年至少得准备一大筐糖果才行。安静的美国小镇,一下子显得比中国过春节还要热闹了。
纽约行
柯大艺术系组织学生去纽约大都会艺术馆看展览,大巴上将有多余的座位,问我们想不想一起去,当然,胡敏还没有去过纽约呢,而我,虽然多年前去过,但这次我也很想去看看那里新展出的“林语堂个人收
藏展”。
同中国一样,这里学艺术的大都为女生,一上车,哇,一车的美女!使我感叹的,还有柯大为学生提供的学习条件,这次活动是艺术史课程的一部分,由学校全部负责,不仅参观门票全包,还在车上发给了每个学生中晚餐补贴费!
使我和胡敏感动的是那位带队的女教授,她细挑个儿,近50岁,人很精神,也很有学者气质。但在车上,她像仆人似的为学生服务。因到纽约有四小时路程,车走得很早,人们未吃早餐,她在车上不时地摇摇晃晃地端着面包和饮料,从车前到车后,一个个地递给学生们。而那些年轻的美女们,心安理得地坐在那里享受,一点没有为老师帮忙的意思。这一切,和中国是多么不一样啊。
因此胡敏有想法了,在车上对我说:以后让王奂也来美国上学吧。
我嘴上说好吧好吧,眼睛却被车窗外那些银装素裹的结霜树林所吸引。多么美丽的蒙霜的冬日啊,难怪昨晚那样冷,睡觉时盖很多,仍感到寒气袭人。
马克·斯特兰德
天气真好,带着小王奂骑车到克平家找海瑞玩。
一栋单独的两层带车库的house。我首先去看了它的后花园,在那里顺手摘了一些红红的朝天椒,带回家供我自己享用。这么宽敞、漂亮的房子,当克平告诉我是以十五万美元买下的时,我和胡敏都有点不相信了。这在北京,恐怕得以四、五倍的钱才能买下吧。
趁孩子们在一起玩,我看克平的藏书。他的大部分书和中国有关,也有一些欧美诗人的诗集和诗论集,其中有一本马克-斯特兰德的诗选,上面还有诗人的亲笔题词呢。原来江克平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选过斯特兰德开设的创造性写作课。我随手翻开这本诗选,是这样一首短诗:
尽管为时已晚它发生了:
爱的到来,光的到来。
你醒来而烛火仿佛自己燃亮它自己,
众星聚集,梦涌进你的枕头,
传送空气的暖人的酒香。
尽管为时已晚身体中的骨头闪亮
而明日的灰尘在呼吸中燃烧。
——《光的到来》
这样的诗,我真喜爱。斯特兰德是一位在中国有影响的诗人,多多曾给我他一组诗的复印件,其中一句“你站到那里就被多了出来”,马上就使我联想到斯特兰德的名诗《保持事物完整》,王小妮纪念父亲的那组诗,也使我想到了斯特兰德的《献给我父亲的挽歌》。但斯特兰德还有着这样的诗:
我宁愿整天坐在椅子上
像一只麻袋,
整夜躺在我的床上
像一块石头。
当食物来了
我张开我的嘴。
当睡意来了
我闭上我的眼。
我的身体唱着
唯一的一首歌,
风在我的臂弯里
变成灰色。
花儿开放。
花儿死去。
多就是少。
我想要更多。
——《一首歌》
这样的诗集,晚上可以带上床看了。
布鲁克林那条街
连续性的旅行:从哈密尔顿先到纽约,再坐火车到东海岸新伦敦康州学院做一个朗诵,又从那里到波士顿……现在好了,我们又回到纽约,可以在这里安顿几天了。
没想到12月的纽约及整个东海岸竟是如此寒冷。在波士顿时,一个朋友开车本想带我们到处看一看,但那从大西洋上猛烈刮来的冰风,让人几乎推不开车门。现在,雪暴似乎已经止息了,但在纽约的街道上,在摩天大楼问,寒风仍在吹拂……
但既然来了,总要看一看吧。而这次我们最想看的,是惠特曼歌唱过的布鲁克林大桥,是“911”后世贸大厦的遗址。看完这重创后的仍在清理并施工重建的遗址后,还看什么呢?那就迎风走到曼哈顿的尽头,把自己献给远方那冰柱似的自由女神!
不走,那巨大的寒冷,就会把你焊在那里。
但纽约也有它可爱的地方,这就是这次我们一家人住的布鲁克林区那条街。这次,是《圆周》国际翻译诗刊主办者、女诗人简妮佛请我来做一个朗诵,她没有安排我们住旅馆,而是住在她的一个出差了的朋友的小公寓里。它处在一座老楼的二楼,木头地板一使劲踩就会吱吱嘎嘎响,但年轻的女主人却把这个家布置得很温馨,并充满了艺术情调(她是一个艺术策展人)。楼下那条坑坑凹凹的老街也充满了魅力,沿街尽是一家家咖啡馆、小餐馆、书店、小商店,街上走过的那些年轻人、咖啡馆里谈天或读报的人,看上去一个个也都像是艺术家似的。真没想到这次来体验上了纽约艺术家的生活!
那几天,白天我们在曼哈顿瞎逛,晚上回来后就在这条街一家日本小餐馆里就餐(在那里可以吃到汤面,合乎咱们中国人的味口呀)。早上,下楼到咖啡店里排队买新鲜的小面包、热咖啡和牛奶,在那路上仍有寒风吹拂,但是,已不觉得它怎么冷啦。
胡敏说下一辈子,就在这里租一问小公寓过吧。
大学书店,诗选
大学书店不在校园里,而是在镇上。我常去看那里的文学理论专柜和诗歌专柜。除了一些诗人的专集外,马克·斯特兰德编选的《二十世纪一百首伟大的诗》也吸引了我,因为是按字母顺序,笫一首诗即是阿赫玛托娃的《哀歌》,奥顿选的是《悼念叶芝》,在这个一人一首的诗选里,米沃什破例选了两首。
还有一本剧作家、诗人哈罗德·品特编选的《99首翻译诗》,则过于偏重于政治性,例如他选的曼德尔斯塔姆那首讽刺斯大林的诗,而这首诗无法代表诗人本人的艺术成就。说到这里,坦率地讲,我也不看重在美国流行的那些反战诗,那些被绑在“政治正确”战车上的诗。
而从网上订的书也陆续来了。首先来的是策兰的诗集《雪部》的英译本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费尔斯蒂纳所著的《保罗·策兰:诗人,幸存者,犹太人》。我读着《雪部》中的诗,边读边译。我想,我可以靠这个过冬了。
学期末
柯大的学生们玩归玩,上课都很认真。每次我路过那些教室,都看到他们在那里认真地做笔记。临近学期末,他们更紧张了。
教师们更认真。克平一周有二、三门课,但他几乎每天都在学校里,因为这里重视“一对一”教育,除了上课,他还要把学生们单个叫到办公室里来指导,一个都不能少。上个月里,他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讨论我的诗,为此他提前邮购了伦敦威尔斯威普(Wellsweep)早年出版的我的诗集《楼梯》,并从几个英文版中国现当代诗选中复印下我的诗,提前分发给学生。仅为这一节课,他就花了这么多精力!
学生们在课堂上的讨论也使我受到触动:他们对《田园诗》、《变暗的镜子》几首诗的细读、他们提出的问题都很深入。这使我多少有些吃惊,因为他们还是本科生啊。
学期末了,克平告诉我分别有两位学生的论文写我的诗。他给我看了,一篇是比较于坚和我的诗,近20页,仅其资料的收集就让我惊讶!一篇是对我的诗的专论,后面附有五首诗的译文,且不说论文本身,选译的诗都是别人没译过的。我自己比较满意。这让我惊异于这位学生独到的眼光。
我知道,这都是在克平指导下的产物,但克平把这一切归之于学生的优秀。
周末,我把这些学生请到家里一聚。我在餐桌上准备了啤酒,说“这里不是酒吧,法律管不着,喝吧!”没想到我这样一说他们都笑了,“王老师,我们很早就在家里开始喝酒啦!”“那好,今晚咱们就当一次李白吧!”
安静的圣诞节
从华盛顿坐长途大巴回来,学校已放假,这里已是一个静静的雪国。克平一家和卞荣青教授也都去远方的亲戚家过圣诞节了,他们走之前,特意为我们预定了一辆出租车,在月底的最后那天送我们到机场回国。
吕贝卡约我们去她家过圣诞夜,说烤鹅已准备好了。王菁老师则给我们送来了酒和她自己烤制的面包。她将留在这里过圣诞节。陪伴她自己的,是她那只安静而又神秘的猫。
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动。
黄昏,回家,发现家门口的树丛边,有一只母鹿和两只小鹿。待我们靠近时,母鹿反应最快,小鹿缩起后腿向前一跃,也跟着消失在暮色中……
静静的圣诞节。我多么喜欢这种安静!我想到在华盛顿看到的霍珀(1881—1967)的纪念画展。这位一直生活在寒冷的新英格兰一带的艺术家,无论他画什么,也无论他以怎样明亮的光来画,他画的都是那“不可打破的宁静和孤独”!有人甚至这样来读解他的画:“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穿过铁轨,定居在那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陪伴它那棺材般的终结……”
在这片天空下,人们就这样来面对他们自己的上帝。
昏暗的冬日下午,屋子里轰鸣着洗衣机的搅拌声。它使一切都显得更为寂静了。
那就生起壁炉。除了克平送来的劈柴,胡敏还从周边捡来了一些树枝,够这最后一周烧的了。在熊熊燃起的炉火边,小王奂兴奋地用锡纸包土豆朝壁炉里扔,我则在我和胡敏的躺椅边,各放上了一杯葡萄酒
该怎样感谢呢?短短四个月,我们却在这里经历了夏秋冬三季,经历了万圣节、感恩节和圣诞节。我们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难忘的一段时光。
我也知道,只要生起火,就总有面对余烬的时候。不过,那清凉的燃烧后的炉膛,也正是一种怀念。是到了要告别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