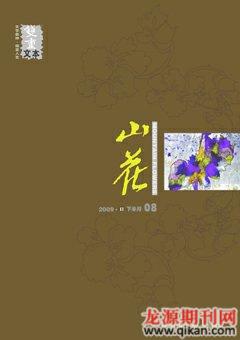1967年的那些破事
那天上午,我同一伙同学在“体育课”里鬼混。我们二十出头,正是精力充沛、好勇斗狠的年纪。
这所谓的“体育课”原是一个可容八辆大型货车的保养场,有顶、有柱,里面陈列着两排体操器械:单杠、双杠、木马、吊环、乒乓球台、排球网等。三年来我们都是在这里面上体育课,没有日晒雨淋,没有碎石水洼,因此外校的学生都对我们刮目相看。有言过其实把它夸大成室内体育场的,也有矫情的说像市体委的体育馆,但要是把它说成个“室”我们就不依,争来吵去干脆就叫它“体育课”,这名字不伦不类,叫顺了也就约定俗成了。
从六六年五月停课搞“文化大革命”运动至今,这里自然就成了我们发泄多余精力的最佳场所。这段时间局势已很紧张,到处都有两派武斗的消息,已经掌握省革委会大权的那一派人,以“红色政权”的名义向反对派展开了“文攻武卫”,他们四处出击、大打出手。但我们这里还没有人敢来挑衅,因为这间“体育课”,我们交通学校早已名声在外,况且我们也是很有战斗力的!
那天上午我们在混什么呢?先是比引体向上,两只手挂在杠上,收腹屈臂,咬牙切齿,脖子上青筋暴突,脸颊上汗珠滚滚。单杠前围着一圈既是拉拉队又是裁判的观众,个个都赤裸上身张着大嘴,配合着杠上人的动作,节奏整齐地报数:“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比胜的人自然神气,围观的人中就会有人站出来挑战,于是两人开始讨论赌注,但立即又被更多的裁判制止,大家说这有失公平,胜方刚才已耗掉了体力,要比必须重新搭配。
接下来裁判又变成了运动员,各选强项找对手,于是双杠、单杠、跳马、摔跤……比赛一轮接一轮,尘土飞扬,喊声震天,倒好像这里是体育学校的竞技场了。
其实“体育课”里的这群学生去年就已完成了毕业实习,三年理论半年实践,技艺已经练到把一根汽车凸轮轴滚在地上,凭眼晴就能推算出哪一个汽缸在进气,哪一个汽缸在压缩、哪一个气缸在做功……要不是因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早已手握方向盘,嘴上叼着烟,兜里揣着票子,眼睛刷着“马子”,当真正的男子汉啦!
两副拳击套很快又搭配成一对新的组合,这次是我同猪头对阵,赌注是我那支小号一周的使用权。我的小号是地道的德国进口货,虽然年代久远,喇叭上已有磕磕碰碰的痕迹,但自有人把它擦拭得闪闪发光。这支小号音质很好,在高音区特别嘹亮辉煌,当年我的压轴戏,就是当今NBA职业联赛主场球迷吹响的那种冲锋号。每天清晨我的号声滴滴答答一响,全校的人就活泛起来了。小号玩得转,当然就提高了我的身价,且不说男生,哪个女同学不对我侧目?
看到众多女生对我的顾盼,自然有很多人想学,我一一推辞,倒不是我这人不“四海”,实在是小号就这一把,人多了,顾得过来吗?
不过后来猪头倒成了例外,我真的将他收为弟子。
那天在食堂门口他缠上我时,我从他身边跳开一步,从头到脚地把他给扫描了一遍。一袭土布对襟衣,一条鼓囊囊的黑灯芯绒裤,一块瓦片的“马锅头”,分明是山沟沟里钻出来的暴发户,土得掉渣,亏他想得出,居然想当“西班牙骑士”?
我说:“猪头,你回到你的山沟里拜一个贫下中农老头为师学个唢呐得了,你在那里吹这种号别人还以为是鬼子进村呢,保不定把新媳妇都吓得尿裤裆了!”
他没把我的话当回事,绕到我身后给我一个熊抱:“当哥子的就是想在你成亲时看见弟媳妇尿裤裆……”
其实猪头有恩于我。实习回来搞运动,有人揭发我,说我有次在工地劳动时,说那天的太阳虚情假意,一点也不暖和。太阳就是毛主席,这还了得?
猪头是班干部,祖宗三代是贫农,他站出来作证说我没有讲过那句话,我逃过一劫。于是我答应教猪头吹号。
正应了那句格言,热爱能产生动力。很快他就入了门,能吹出点调了,每天清晨练得人睡不了觉。
除了食堂还在正常运转,学校早已无人管理,我们这群学生正好自由自在地“放敞猪”。猪头当然肆无忌惮,每天把腮帮子鼓得要爆。
“猪头,你的屁怎么放得震天响?”
“猪头,你还让不让人活?”
“猪头,你以后只能娶个聋子当老婆!”
“猪头,你把我们睡到自然醒的乐趣全毁了!”
我们那栋男生宿舍楼四处响起了抗议声,后来连操场对面的女生宿舍也惊动了。
真得要佩服这家伙的厚脸皮,执著坚守,咬住不放,现在又得寸进尺,死缠烂打,要向师傅挑战。
这当然不行,我还有个姓赵的正宗徒弟,十五岁的初中生,同我家住一个大杂院,那小子天生的薄嘴唇,先天条件好,悟性高,那当口我正在打他姐姐的主意。于是我就对猪头说:“拳击不是摔锭子,要击中有效部位才计点……就算输给你,就凭你那嘴唇和门牙,就是把小号送给你,你也吹不出我的调!”这话反倒激得他更来劲,先就把拳套给套上了。
猪头长得鼻塌嘴大,两颗门牙从厚嘴唇下不知分寸地突出来像要咬人,同学们都说他像《平原游击队》里的日本猪头小队长,这个绰号给他真是恰如其分。
我们读书那阵子哪有现在的年轻人这么光鲜,什么电视、电脑、MP3、MP4,、网聊、网恋……我们就是那几本教科书,还有就是三顿饭,最快乐的去处不过是“体育课”,因此相互取绰号,拿别人的生理或别的什么特征来取乐是最大的乐趣。
比如说有位同学叫“鸭子”,那是因为他走外八字,屁股一扭一扭的形同母鸭;而叫“妖怪”的那小子,是因为他晚上躲在宿舍里,站在一把椅子上,用一条白床单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待到我们下晚自习,进门一开灯,一个高大的白色僵尸杵在面前,尿都吓出来了,于是大家给他取名“妖怪”。我们那个圈子名目繁多,什么骆驼、瘦马、肥鹅、鲨鱼,什么都有,有的取得确切,有点道道,而有的则纯属瞎扯,根本没有依据。绰号形同名号,要求简洁、响亮、上口,喊的人和听的人都觉得有派。比如他们叫我“色狼”,说我一见女生就两眼发光,这纯属诽谤,老实说那会儿在学校里我还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其实我的心早已有属,真正让我两眼发光的人在化工学校。
其实入我们这圈子也并不困难,关键看你是来自哪个部分。我们大都是来自工人、城市贫民家庭,吃和穿都不像个样子,有一双胶底白球鞋就不得了啦,打一次球回来还要用牙膏去擦……穷而豪爽是我们这个圈子的特征。可猪头的那副土老财相,与我们实在是格格不入。但这也不算什么,导致猪头难以与我们合流的根本原因是他是班干。他与我同班,他大哥是一个什么公社的书记,成绩虽差却铁定要当班干。就凭这一点,即令他削尖脑袋也钻不进我们的圈子。班干部在那年月是什么概念?政工处的眼线,打小报告的卧底,搞阶级斗争的打手。
我们这些城市学生,已经经历过这所学校的两次阶级成分清理,因出身不好被强制退学的学生近四分之一,留下来的家庭成分都符合标准,但学校的“思想管理”者不信任这些人。那两年正在搞“四清”运动,从部队转业来的校党委书记,学过不少毛主席著作,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他介绍自己的心得体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活学活用”的收获,就是他学懂了毛主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并将这个战略思想实践于这所学校的管理之中。因此他要用农村学生包围城市学生,各个班级的领导权自然与城市学生无缘。于是班级里的气氛异常紧张,造成城乡学生间的互相警惕,互不买账。但毕竟城市的学生大大多过农村的学生,包围变成了反包围。虽然他们领受了政工处的任务,但打了小报告的后果也很严重,况且政工处对学生的处罚也还有个底线,久而久之,掌权的班干部反而成了弱势。
我们当然认为猪头是政工处的走狗,是来包围我们的。
这所学校的刘书记瘦而高,脸上少肉,表情永远严肃,全校师生从未见他笑过。想必在他那政治挂帅的内心世界里,笑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感情流露,是软弱的、虚伪的,是同无产阶级的思想面貌格格不入的,因此,凡是可能调动出微笑、讪笑、浅笑、大笑的肌肉动作,都在他那张颧骨突出的脸上消失了,甚至连那些给领导者专门设计的笑容都被他坚定地摒弃了,面对来自师生员工的任何思想错误或是“苗头”,他都会旗帜鲜明地批判,义正辞严地谴责。为了逃避他,最好的办法是在课余时间躲进“体育课”,这里没有思想只有动作,虽时有打架斗殴发生,上纲上线也能牵扯到资产阶级思想,但至少反不了——革命。
猪头最终被我们接纳,除了上面提到的作证之事,还有一桩与我们圈子荣辱相关的大事。
一九六五年中越边境上发生了北部湾事件,美军越过17度线轰炸北越,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型群众集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援越抗美的决心,并表示中国人民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独立事业,不惜作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了防止美机对中国内地轰炸,我们这座远离边境的山城也抓紧备战,事涉交通,当然就由交通学校的学生停课去修战备公路。
我们的工作是开山放炮,班上四十个男生被分成四个小组,女生则去干一些相对安全的活。开山的石方量是有定额的,紧邻我班的工作面是社会民工队,这些民工队大都是城市里的失业青年,有很多是被各大中专学校清退的学生,也有多年浪迹社会的散兵游勇,其中当然也有我们过去的同学。除了在政治待遇上不如我们外,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民工队的幸福指数远比我们学校的高。第一,他们没有我们每晚的政治学习,当我们在沉闷的读报声中昏昏欲睡时,他们的工棚里却在莺歌燕舞吹拉弹唱,手风琴奏响的是外囯歌曲,“你呀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小提琴拉出的是《梁祝》、《冰山上的雪莲》……他们自己作词编曲的《筑路工人之歌》就比我们千篇一律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悦耳动听。他们队里的那些资产阶级小姐们更是肆意妄为,居然在工地旁的草地上伴着月亮跳起了《玛伊拉》!红短祅、细腰身,脖子平行移动,媚眼左顾右盼,娉娉婷婷,把她们的青春曲线展示无遗。我们这群被政治挂帅束缚得呆头呆脑的学生哪见过这般阵势,一个个男生眼睛瞪得溜圆。
工程指挥部为了追求进度,对民工队的行为放任不管,因为政工处举办的墙报上,天天显示各队的工程进度,民工队的业绩一点也不差。而我们的刘书记据说曾到指挥部去提过抗议,指挥部的解释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反而要求刘书记取消我们晚上的政治学习,要让学生娃娃们休息。但毕竟涉及政治层面,即令指挥长的级别比刘书记高,指挥部政治处还是对局面作了调整。晚饭后工地上响起的广播喇叭压制住了草地上的轻歌曼舞,激昂的进行曲和队与队之间进度竞赛的挑战书在空旷的山谷里交相呼应。实在没有新花样了就干脆广播越战战报。于是当我们累得瘫倒在工棚里的草席上时,就知道了英勇的越南人民军又击落了多少架美军飞机,知道了越南女民兵用步枪击落了美军的“鬼怪式” ……
这政治思想工作还是有效的,不久我们就很激动,很沸腾,我们就很放眼世界,很愿意为越南人民作出巨大的民族牺牲。落实到眼前,我们当然要彻底战胜被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民工队!
我们在山岩上更加玩命。唯一让我们憋气的是,我校各个队的头都由过去的班干部担当了。面目丑陋的“猪头小队长”,就是我那个队的头,每天清晨列队出发时,我们得听他的吆喝,这让我们在民工队面前很没有面子。
开山放炮的头一周,头当然知道我们瞧不起他,因此他要在劳动技巧上露一手。开初他以为干体力活我们会露怯,谁知我们很快就适应了腰束安全绳在悬崖上打炮眼的工作。于是他又提出一项考核指标,每个挥锤的人必须每锤必中钢钎头,滑闪一次重新计数,计满千锤方算及格。他作示范时居然一气打出了一千五百多锤。头一周我们居然被他镇住了,但到第二周后我们个个都练出来了,虽然每个人手掌上都是血泡。
但他后来还是成功了,连我都信服,因为他上演了一场真格儿的“英雄救美”,使我们这一伙人名声大噪!
工地上的劳动竞赛搞得如火如荼,我们这个组正好同民工队的工作面相邻,于是双方铆上了劲。
那天上午我同猪头配对,我俩站在一块巨石上打眼,这块巨石正位于我们同民工队的分界线上,足足有十吨以上,由于它又高又大完全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到民工队那边的“男女搭配”,于是我提出把这障眼石炸掉。
猪头围着巨石绕了一圈,划了三个炮眼位置后我俩就赤膊上阵了。我俩轮换着掌钎挥锤,这家伙真算是老把势,两个大手掌抓着锤把尾,把那八磅锤抡得飞转,每划过一次圆,钢锤就准确扡击打在钎顶上,声音沉,下力狠,我只管应着锤声旋转钢钎,根本无须担心锤滑手臂。这家伙相貌虽然丑陋,可脱掉了对襟衣,那身古铜色的腱子肌肉却煞是好看,胸腹肌上块片分明,该鼓的鼓,该收的收,没有半点赘肉。更有趣的是他那胸肌上两个暗红色的乳头上,居然还长着几根长长的黑毛,他扭开腰板奋力向下一击的时候,那几根黑毛就随着他的呼吸在胸脯上起起伏伏。
第一个炮眼很快就完成了,我俩交换场地,由我来挥锤他掌钎了。我先玩的是“滑把锤”,这姿势没有他玩的“尾把锤”好看,可锤落钎顶下力更重,钎头咬石狠,进石深,在这些细节上我不能输给他。刚打了一小阵他叫我停下来,原来是民工队的一男一女向我们走来了。
戴眼镜的是他们的头,据说曾是贵阳某中的高才生,进了大学又被清退出来。如今流落到民工队,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革命的。跟在眼镜后面的那位红衣姑娘,我瞟一眼就同草地上的玛伊拉对上了号,我迅速地在石头上把两腿调整成一副可以入画的站姿,两眼放光,等着他们开腔。
其实他们是来同我们商定统一放炮的时间,和炮场区安全警戒区域。
眼镜同猪头的对话很严肃,因为都是事关安全的大事,而我同那位玛依拉就不一样了。别把我想得那么坏,我绝对没有挤眉弄眼,更没有轻佻地吹口哨,我只是关切地问:
“你那纤纤细手也能挥锤打炮?”
玛伊拉那双大眼睛朝我一瞪:“不要用这种腔调同我说话,告诉你,我不但能打锤,我还负责点炮!”
点炮?我吐了一下舌头,这可是个玩命的勾当,我至今还没有开过荤呢!我被这姑娘镇住了。
那天收工前,我一直在同猪头交涉,我对猪头说:
“点炮的活不能由你一人霸着玩!”
我又说:“连民工队的姑娘都能点炮,我一个大小伙子还干不了?”
猪头依了我,可当天就出事了,不过出事的不是我,而是民工队的玛伊拉。
点炮是个精细活,要求胆大、心细、动作敏捷,因为点炮时的场面有点恐怖。比如每人确定点十炮,装填炸药埋导火线就很有讲究,从第一炮算起你要留出足够长的引线,否则后炮未点前炮一响你就被炸飞了。点炮前要由专人布置警戒线,炮区所有人都得清场,只剩下几个点炮工在现场,点炮顺序是千万乱不得的,这关系到你自己和其他人的性命,点完自己的炮位之后立即就顺着你早已看好的线路奔跑,隐蔽点一般就在炮场附近的大石岩下面。为了节约导火线和便于处理哑炮,点炮工是跑不出炮场的,只能在各自的隐蔽点趴在石头下,屏息静气地等待炮响,待到轰轰烈烈地炸开之后,炮场上硝烟弥漫碎石乱飞,那情景就像在战场上一样。
那天傍晚,天气阴沉,山崖上起风了,有点下大雨的前兆。我们这边是我同猪头点炮,民工队那边是上午来交涉的眼镜与玛伊拉,看好各自的奔走线路之后,双方选择的隐蔽点正好在同一岩石下。
那天是我第一次点炮,拿火链的手情不自禁地发抖,听到警戒线外的第一遍锣声响过之后,我感觉炮场上阴风惨惨,令人心惊肉跳。第二遍锣响后,我同猪头同时点燃了火链,第三遍锣声一敲响我同猪头就冲出去了,按着顺序把火链往导火线上凑,看到火药嗞嗞地喷出火花,急忙奔向第二个炮位……我们跑回隐蔽点时,眼镜同玛伊拉也刚到,我们四个人挤成一团,脸上的汗烧辣了眼睛也顾不上擦。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不,是零距离同一个姑娘贴在一起,我嗅到了她发辫上的气味,虽然同我的汗味差不多,但我当时却感觉到那是一种撩拨人的香味,因为空间太小,我的手臂有一会触到了她的胸脯,她不做声,只是悄悄扭转身避让了一下。说实话,人在那样的时刻,是不该、也不会有其他的想法的。我们喘着气,抱着头,等待着外面轰轰烈烈的爆响。
本来一切顺利,硝烟散过之后四个人都很完好,就是数响声上出了问题,我同猪头说还有一炮未响,玛伊拉却说她数的数已经炸完。她的眼神那么自信,把我都有点要搞糊涂了。眼镜比较谨慎,他拦住了玛伊拉。我们又等了几分钟,这时天上下起雨来,玛伊拉挣脱了眼镜的手,率先走出了隐蔽点,我们三人也跟着出来。我刚走出两步,就见到上午我同猪头对付的那块巨石只被削去了一半,肯定还有一炮未响!
玛伊拉走在我的前面,她已暴露在危险区域,我还来不及张口,猪头已从我身后一步蹿上去,一个熊抱把玛伊拉压在身下。就在此时,只听到“轰”的一声,那块石头被炸得粉碎,碎石哗哗地砸落在地面,头上的安全帽“咚咚”作响,我趴在地上,感觉腾起的烟尘已把我淹没。
烟尘散后,站起身来,才发现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受伤,玛伊拉还是受到了惊吓,她被猪头拉起来后又坐回到地上,抱着头半天不说话。看着她散乱的头发,蜷缩成一团的身子,我真想上前去搂着她安慰一下。特别声明,这同性别无关,因为当时我先就把猪头给搂抱了!
猪头的这般作为,难道还加入不了我们的圈子吗?
眼镜后来把这个事件编成了一个短剧,由民工队在工地政工处组织的国庆联欢会上,隆重地演出了,作为救人英雄的猪头,还有我(可能是根据剧情的需要吧)都被介绍给观众,这不光让我们全校长脸,连刘书记的脸上也生辉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体育课”观场。
猪头在我身边跳来跳去,他想靠近我,用他的组合拳向我进攻,我用左直拳阻挡,冷不防用右直拳直击他的胸膛,这家伙很会躲闪,而且抗击打能力超强,围观的人对计点不感兴趣,况且谁会相信这些乱七八糟的歪裁判?真正能引人兴奋的是击倒!大家围着我俩胡喊,我俩绕着圈子胡打,最后是汗流浃背,灰头土脸,谁也不能把对方击倒,我终于熬不住了,举手认输。
我把小号交给猪头时有个附加条件:下午陪我去化工学校。
昨天,我那正宗徒弟给我带来口信,他姐姐约我去商量毕业分配的事。这当然让我两眼放光。我为什么要带上猪头?一般的小青年就不懂了,说白了,这叫“陪衬”。你想,我第一次去化工学校,他姐姐的同学一定会给我打分,同猪头这种长相的站在一起,参照物的起点那么低,我还能不得高分吗!
猪头当然不明白我的鬼板眼,他还以为我是要让他见识未来尿裤裆的弟媳妇。这个心愿可是他求我教小号时就表明过的。
化工学校在城郊,吃过中饭乘郊区车一会儿工夫就到了。
我当然得着意打扮一下,那双白球鞋是一定要穿的,一套运动短打是头天就洗干净的,头发嘛,用梳子沾点水是要打理一番的。我不光要在形象上到化工学校去震一震,从气质、胆识上也要让她那帮评头论足的女参谋们没有话说。
猪头只顾去把玩那把小号,他一边用袖口仔细地擦着喇叭,一边对我的惺惺作态冷笑。出发前他又鼓起腮帮吹响了小号。
“你怎么吹得像放屁一样?”
那天下午我踌躇满志,对猪头讲话毫无分寸。
猪头嘛,对我的话根本不当回事,兄弟已经做到这个分上,谁计较谁呀。
化工学校是反对省革委“红色政权”的一个小堡垒,那里被乡村环抱,周围的公社农民才不管你反对派的什么七七八八的理论,一句话,他们只听上面的,因此这个小堡垒在那个地盘上随时都有被摧毁踏平的可能。我那天去就是想劝我的意中人收兵回城的。
当时她的一群同学都集中住在篮球场旁边的教学楼里,校园很大,空空旷旷的。她的那些男同学可能是精力过剩,也可能是想过点“街垒”瘾,居然用钢筋烧焊把一二楼的门窗都封死了。那几十个男生还个个充英雄好汉,每人拿一根镀锌铁管称为“齐眉棍”,而且自称是“敢死队”。
知道我们是来自交通学校的战友,我同猪头自然受到大家的热情欢迎。
她把我介绍给她的同学之后,根本没有同我单独谈什么毕业分配的事,而是惴惴不安地同她的几个女同学坐在一起左顾右盼,果然不出我所料,她是让我来亮相,让她的女伴评分的。
我同猪头坐在一起,要评就评吧,我怕什么?猪头在家乡早有女友,此时他手里玩着小号,心无旁骛也坦然得很。
既然有人评分,我也就当仁不让地表演。因为敢死队员们给了我这样的机会。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课”,我拿得出手的也就是“体育课”,于是我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地把那里描绘成一个可以叱咤风云的练武场,从那里摔打出来的人个个身手不凡,以一当十……我吹得沫星四溅,间或还站在屋当中摆个身段,拿个架势。
我的话虽然说得满了点,但同这群玩花架子的,还未曾没见过多少世面就敢称“敢死队”的化校生来说,我那天的魅力肯定是把他们全盖了。
她从惴惴不安变成信心满溢,看她那红喷喷的脸,看她那神采飞扬的笑,我知道我一定得了个高分。
大家正吹得热闹,一个男同学急慌慌地冲进门来,他说他们在球场上同村民起了争执,后来动手把两个村民的头打破了,现在他们搬兵去了,一会怕要赶来寻仇。
“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化校的一个白胖子,一直同我交谈的那位,听语气我早已判断他就是这支“敢死队”的头,从从容容地站起来走到我跟前:“来就来吧,我们这支队伍还正想玩点真格的哩!”
白胖子的语气听起来有点滑稽,因为他太漫不经心了。报信人的焦灼与不安他难道看不出来吗?打破了头一定不是小事,头一破,满脸血,以这种形象回村子里作号召,哪还不邀来几十百把号人来!
就在此时从远处传来一阵喧嚣的呐喊,我们急忙跑到窗前,只见一大群人黑压压的一片,从操场上拥过来,他们手里拿着扁担、锄头,有的还拿着镰刀,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看来他们今天是要打个花儿开!
我们这二楼上首先炸开锅的是女同学,她们一个个吓得脸色惨白,抱成一团。
我站在窗前,我在紧张地判断形势。猪头悄悄对我说:“惹翻了农民,不好收场……”
还是白胖子勇敢,在化校当头,不是浪得虚名。他霍地站起来,脸透杀气,脱去运动衫,露出光膀子,大声发令:“敢死队准备武器!今天同他们拼了!”
室内一阵骚动,旁边教室的男生也冲了过来,没有人怯场,一个个都同他们的头一样脱去了上装,脸上是大战前夕的兴奋,手里都拿着早已准备好的“齐眉棍”。
以我的判断,此仗非打不可,我方一旦露怯不敢应战,对方的气焰和士气就会成倍增长,若被对方围起来攻,这楼是守不住的,一旦被攻破,后果不堪设想。
我同猪头都脱去了上衣,也同大家一样露出了赤膊,我抓了一根“齐眉棍”在手,为大家提劲:
“不要怕!他们都是乌合之众,没有咱们齐心!”
白胖子用一条白毛巾束在自己头上,带着众人冲下楼来,楼前几十个光赤膊手提棍棒虎视眈眈地站成一排。
“他们有老婆孩子,老子们光棍一条,冲啊!”白胖子的最后动员非常奏效,我们端着“齐眉棍”勇敢地冲上去了。
对方没有料到学生这边还有如此胆气,黑压压的队伍迟疑了一下,但很快又在领头人的带领下冲上来了。
两边的人都在呐喊,似乎这声嘶力竭的呐喊既能恐吓对方,又能给自己壮胆!
不知什么时候我已同白胖子冲到了我们这支队伍的最前头,我俩目光灼灼,同仇敌忾,呐喊着并肩前进。
正当呐喊的声浪将我震昏了头,两边人就要在球场上遭遇,血肉就要横飞之际,我耳边的呐喊声突然消失了,就像大海退潮一样,四周变得了无声息。
这人数悬殊的两队人是在球场上相遇的,相遇但还没有相接,双方相距约二十米,两边前队的头领都在呐喊声消失的那一瞬间停止了冲击,谁也不知道是哪来的指令叫停了呐喊,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阻止了两支队伍的冲击。
刚才还喊声震天,此时却一片沉寂,死一样的沉寂。
我勾着腰,手里端着“齐眉棍”,两只眼睛火辣辣地盯着对方头的眼睛,那边那一双火辣辣的眼晴也在盯着我,我看到他的额头上有汗珠滴下来,他也一定看到了我的眉头在颤动……
或许是我们双方都意识到这场血战的危险,或许是我们双方都想象到血肉横飞的后果,我们都有点后怕了!
两队人就这样静静地、剑拔弩张地相持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滑过,究竟滑过了多少?
怎么办?怎么办!
冲?不敢!
退?不敢!
两边的头都没有了主意,两边的头,脑子里都已空白!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清脆的声音尖厉地划破了我的耳膜,号声,我熟悉的小号声,是那种金属被空气冲击后爆发出的鸣响!
我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驱动,像被一根滚烫的铁棒触到了神经,我闭上了眼睛本能地喊出:“冲啊!”
同我并肩的胖子,还有我们后边所有的人,都在号声的召唤下,整齐地呐喊:“冲啊!”
我的脚步还没有移动,对面那双眼睛闪烁了一下,立即就暗淡了。
就像是火星倏地一下就熄灭了。
我的脚步还是没有移动,我的眼睛已看不见那双眼,我的视觉里出现了一片赤裸的脊背,他们的头在我们突然爆发的呐喊声中转身逃跑了,对面那黑压压的一片像得到指令,全都扭转身争先恐后地落荒而逃。
真是一鼓作气!兵败如山倒!
我知道是猪头突如其来地吹响了小号,神啦!中午我不是还说他吹得像放屁一样,怎么这一下就吹得如此激昂、如此嘹亮、如此惊心动魄、如此气壮山河、如此雄兵百万?
我们没有趁机撵杀,我们见好就收,我们用勇气阻止了劫难,我们——鸣号收兵。
这就是我,一九六七年经历的那些破事。
后记:
1、那支德国小号我送给了猪头,他不只是拥有一周的使用权,而是永久使用权。
2、我同化校的那个女生没有搞成,她分配的地方离我太远,本来我曾用小号向她吹过一首苏联歌曲,歌词内容大概是:“我们不害怕风涛的路,路途遥远隔不断爱情。”可后来她给我来了一封短信,对歌词改了几个字:“我们虽不怕风涛的路,路途遥远谈不上爱情。”
3、猪头毕业后被分回家乡,他结婚时吹的唢呐还是小号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后来当了他家乡车站的站长,很神气地走在街上,满街的熟人都冲他招手。还听说他退休有两年了,在县里组织了一个退休干部乐队,经常出来吹吹打打。
作者简介:
徐筑敏,生于一九四六年,一九六六年毕业于中游贵州省交通学校,从事公路交通运行管理十七年。一九八二年开始文学创作,后调入贵州省文联《山花》杂志社,担任过编辑、刊物发行人。一九八五年下海经商,创办过国防教育基地、旅游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