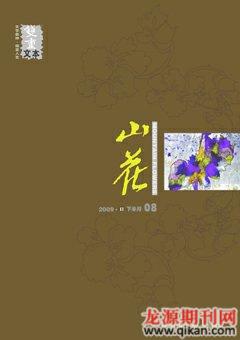余震
陆 军
“啪!”的一声,马营在朦胧的睡眠中听到了这恐怖的声音。这个声音的背后似乎紧跟着一场灾难。这个响声在马营的意识里就是死神给他们家的一个提示,他在睡着的时候无论如何还得睁上一只眼睛,或者说他与妻子两人的四只眼睛至少要有一只是没有闭上的,如果闭上了,也是醒着养神的,不能处于不知不觉中,这关系到三个生命的生死存亡。对这个声音警觉的时间,决定着马营一家与死神分手的时间。警觉得早,死神会和他们说再见;警觉得迟,死神将会死皮赖脸地和他们在一起。马营是懂这个道理的,他像当年上大学军训时半夜紧急集合,一把将惊醒的妻子拉起来,踩上拖鞋,直奔女儿卧室,不料被脚下一个肉乎乎的东西绊了一下,他和妻子一起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们家的猫撕心裂肺地叫着从马营的脚下跑走了,速度之快如离弦之箭。女儿并没有被凌晨三点钟的这些混乱吵醒,她鼻息均匀,睡得异常安静。马营翻开被子的时候,看见女儿将衣服脱得精光。他气急败坏地“哎”了一声,将被子重重地盖了回去。这一个多月来,他每天晚上叮嘱女儿要穿着衣服睡,万一有情况,脱险容易。可女儿经常在半夜里将衣服脱掉,她说光着身子睡觉舒服。特别是昨晚,他和妻子每人说了不下五遍,加起来就是十遍,那只是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里重复的,说要准备在夜里逃避地震,不能脱衣服,说最后一遍的时候女儿几乎睡着了。此刻,马营面对自己快十五岁的女儿二话没说,用被子将女儿裹严了,抱在怀里,和妻子一起冲下楼去。
这是夏天的时候,被子薄薄的,马营抱着女儿走出小区的时候,像是抱着一条棉被。
从家属区出来不远就是新建的广场,他抱着女儿跑过马路的时候,他发现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一片喧嚣。女儿醒了,喊叫着要从被子里钻出来,马营与妻子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情况给女儿解释清楚。女儿赤身裸体,妻子又没来得及拿衣服,他只好让女儿裹着被子蹲在地上。这时,围过来好多人,想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们和马营妻子打着招呼。
有人问:“孩子怎么了?”
“跑得急,没顾上带衣服。你们真快!”妻子不好意思地说,手里提着一双女儿的拖鞋。
“我们吃完饭就来了,你们跑什么,都几点了,有什么急的!”
“刚才有地震,我家桌子上的啤酒瓶倒了!”妻子说。
“我没感觉到,只是头晕。”一个穿着棉衣,打着哈欠的中年妇女摇了摇头。
“我二十个晚上没睡觉了,听说还有余震。”旁边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躺在用三条棉被铺垫的行军床上,有气无力地说。
“我们家亲戚从省城打来电话,说近期内有六级余震,我们一家在广场上已经待了十个晚上了,就是没觉得有什么余震。”这是马营他们一楼的一个女人得意的声音。
妻子听到这些话,觉得离题万里,有点不悦地说,“在外面是感觉不到的,如果你在房子里,那感觉很明显,我家桌子上的啤酒瓶都倒了。”妻子一连问了十多个人都说没感觉到什么。
马营听到了妻子她们的对话。他看着对面的楼里静静的,偶尔也有一两家的电灯突然拉亮或熄灭,而且有规律,像是几个人在同时进行着,从下到上,从左到右。
这是第十一次了,前面有九次是被朋友们打电话叫醒的。他对这种脱离危险的方式已经感到厌烦,但桌上的瓶子确实是倒了的,网上说这是预知地震的有效方法。马营记得这次往楼下跑的时候没碰到别人,不像白天,到一二楼时人都挤到一起。
马营感到身体凉下来的时候,抱起女儿准备回家睡觉,妻子不同意,她说要再等一下,说不定刚上楼余震就跟在你的屁股后面,那时后悔都来不及了,再说了,没几个钟头天就亮了,大家一起回家吧。依妻子的看法,他们一家就不应该在家里睡觉,要和这些成群结队的避险者一样睡在露天或野外。
马营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啤酒瓶倒了,他们都说没感觉到地震。妻子向他靠近了一下,说她的腿像摔断了一样痛,她抱怨说马营这方法纯粹是异想天开,纯粹是自己折腾自己。她还说是不是咱们家的猫被踩伤了。马营突然觉得他妈的是不是猫,是不是猫把酒瓶弄倒了。肯定是猫,这该死的猫!这只猫曾经在一个月夜里,趴在三楼的阳台上拍窗子,想约人家的雌猫出来,结果把独身的老太太吓成了恐慌症患者,见人便都说自家窗子上有鬼,没三月就走了。想到这里,马营抡起拳头,恨恨地砸着腿说,他妈的是猫,部长!不是地震。
妻子没听明白,什么猫、部长、地震的,就问马营是不是被吓傻了,说胡话。马营没理会妻子的话,他想部长今晚没出来,说明自己下午说的话有效果,这样部长会高兴,部长一高兴,他的日子就好过了。
马营是这栋楼里唯一的一名还在上班的政府公务人员。他住的这栋楼属于市上给老干部解决的福利房,是快二十年的老房,没有年轻人住这里。从汶川地震开始他就没清静过,每天都有人向他咨询有关地震的消息。二楼退休了的组织部长,一看见他就叫上了,小马呀,今天政府那边有没有最新消息啊?马营知道他这个最新消息就是今晚有没有地震。他心想,地震这种事连国家都测不中,我怎么知道呀,况且此事属于机密,我马营是一个守“便民服务”电话的普通职员,能知道吗?可他又不好说不知道,说了,那部长肯定会像上次一样批评他:你们不知道,谁知道。他只好原则性地说,我们这里发生的地震都是余震,没有什么危害性,即使有也不要紧。部长问,楼房会倒塌吗?他说不会。部长点了点头,马营把手里的预防地震灾害的有关资料给了他一份。部长如有所获地走了。临走时还问马营今晚有没有地震,他说没有。但这个回答经常让马营忐忑不安,如果有怎么办?
这天晚上十点多钟,妻子的电话响了。妻子说她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是午夜十二点左右有破坏性余震,他们都到外面空地上了,你们怎么还不动,在等死?马营初听这话,有点气愤,这不是造谣生事吗。可妻子不干,她说这种事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死活要马营一起走。妻子说话时神秘兮兮的,那个晚上,在十二点三十分到来的时候,他们一家已在人头攒动的广场上度过两个小时了。马营看着广场上东倒西歪的男女老少和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睡姿,对余震的恐惧有八成消失了。马营说这纯粹是谣言,问妻子是谁打的电话,妻子说是个朋友,既然没有余震发生就好,我们可以回家了。
“老公老公我爱你……”妻子的手机突然响了,马营牵着女儿的手正走在马路中央,他三两步奔到对面小区门口,看着妻子拿着手机左顾右盼地从马路中间摇晃着走了过来。妻子说现在不能回去,朋友说凌晨二点左右还有一次余震。马营问是谁打的电话,妻子说是朋友,她看到马营有点生气了。马营大声地、几乎是吼着说,“是什么朋友打这种不负责的电话?”马营从大街上看过去的时候,人们齐刷刷地手里拿着一点亮光,如遥远的太空闪烁的星星,看样子他们是收到了同样的信息而不是电话,因为他们没有将手机放在耳朵旁边。马营怒气冲冲地拉着女儿回家去了。十分钟后,妻子也回家了。
马营在饭厅的餐桌上倒放了一个啤酒瓶。说是地震发生前,有预兆,就是地壳会先动一下,之后约三十秒或一分钟,才有正式的地震到来。当那个啤酒瓶倒下,从桌子上掉到地板上摔得粉碎,声音足以惊醒沉睡的任何人。这是马营从网上得到的预测地震的办法。马营想从今晚就开始用这办法,不再听各种传言而瞎折腾。
马营那个晚上没有睡觉,他几乎是在看着周围起伏的人头和楼群里的灯光度过的。他看到大块大块的地毯把能容纳几千人的广场贴得面目全非。当黎明来到的时候,广场和所有的事物都被露水淋得像洗过一样。马营呆呆地坐在塑钢椅子上,屁股上的潮气凝成了大水珠,从椅子上一颗一颗滴了下来。他在渐明的亮光里看到偌大的广场上,有很多人在行走和摇晃,像是在巨大的列车里,又像是漂浮在海面上左右移动、上下起伏。有人和衣躺在草坪上,有人紧抱着自己的老婆或丈夫,动作淫秽;有年轻人裸着身体睡在一起;有的人睡在车里面,这是最令人羡慕的有车一族,但大都是一家小三口;有的将旅行帐篷展示了出来,在晨光中晃动着,有几个初中生走过去时,一脸坏笑,说肯定是新婚夫妇,声音太大了,像牛哞;有的还在四处走动,像公安便衣,又像不自信的扒手,当有人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的动作会改变方向;有的在有气无力地叫卖旅行帐篷;有的像死猪,横七竖八,旁若无人地放着响屁;有的在夜色里偷窥别人的隐私,现在开始打着哈欠,双眼还不放过别人的每个动作……
看着这些乌烟瘴气、下流恶心的情景,马营心想,下一个晚上不能再来了。这样下去,何时才是尽头。各种媒体异口同声说余震至少还得持续三个月,这三个月里,每个夜晚总不能在这样乱七八糟的草地上过吧。看着身边熟睡的女儿和妻子,马营不明白,她们怎么能那么安详地在如此喧哗的地方入睡,怎么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了梦乡。紧挨着他的是一对蜷缩在一张行军床上的老人,四只眼睛朝布满霞光的天空注视着。昨晚马营没有注意到这两个老人的存在,他们在相互讲述着一件或几件往事。男的说,那是三十多年前,有过这么一回,他们在农村的晒场上度过了整个夏天和秋天;女的说,算上这个,她已有四回躲避地震的经历了;他们俩同时叹息了一声说,不知还要经历多少回!他们相互笑了笑,接着开始无休止的咳嗽。马营想,都这把岁数了,还怕死!不到家里好好待着,跑出来受这罪,真是不值。
“你就死在这个婊子的身上吧!——”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飞进马营的耳朵,他站起来循着声音的方向看了看。广场西口隐藏在晨光阴影中的一部高级小轿车前挤满了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忘记那个狐狸精……唔唔——唔唔——”一串哭骂声冲了过来。很多躺在草地上看星星的人哗啦一声全体起立,循声跑了过去。马营没有过去,妻子被草地上庞大的哗啦声震醒了,将圆浑浑的屁股在马营眼前晃了几下,问马营是不是地震了,怎么这么大的响动。马营说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不是地震。这时,两个一胖一瘦的中学生从马营旁边甩着胳膊走了过去,嘴角叼着香烟,说得手舞足蹈,神采飞扬,说到高兴处还相互对笑几下,然后猫着腰坐一下,接着再说再走再笑。胖子说,听说那人没当领导的时候感情特专一,现在当局长了,怎么就有那么多情妇,连一个晚上都不空过?瘦子说,现在是人人避灾的时期,他倒好,一出来就找别人老婆去了,结果那东西取不出来,让妻子发现,逮了个正着。胖子压低了声音,怪怪地说,人的那东西怎么能拔不出来呢?狗才那样。瘦子回过头来朝左右看了看说,有可能他长的是狗的吧,不然怎么每个晚上都干那活,要是人还不累死。胖子站住脚,用手抓了一下小瘦子的裤裆说,你能行,听说你把咱们班的毛娟都用了好几回了,弄得毛娟走路都一拐一瘸的!她给女同学说,你不是人,是驴!哈哈哈……胖子像发了疯似地大笑着走不动了,坐在台阶上继续说,猛男啦!瘦子飞起一脚将皮鞋和胖子一起踢跑了,自己用一条腿跳着下了台阶……
马营看着他们俩打闹着狂奔远去的背影,心里一阵发冷,他跺了跺脚,想把内心的寒气跺掉,结果把旁边帐篷里的人吵醒了。那人睡眼矇眬地从里往外探出头来,想看看是什么声音如此沉重。那张脸看起来有五十多岁了,带着浮浅的虚肿。马营好奇地把目光从他掀起的窗口中送了进去,一张和自己女儿一样稚嫩的脸把他的目光死死地抓住了。马营几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目光,他在心里纳着闷: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怎么和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睡在一起呢?不会是父女吧!他屏住气用力将目光移了移,她裸露着一对结实的乳房……马营像是从梦境中走了出来,他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后悔自己不该看到这一幕。突然,“哗”的一声,那男的用力将窗口拉拢了。马营吓了一跳,他感觉到有一阵强劲的风从那声“哗”中刮了过来,把自己差点从台阶上刮了下去。他下意识地猛然抬起头,朝刚才那两个中学生走去的方向看了看。一辆白色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地从两个中学生走去的方向狂奔而来,他看到车子停在了那辆被人围得水泄不通的小轿车旁。
马营觉得这辆白色的救护车印证了刚才中学生的谈话。白天已经和那辆救护车一样明晃晃的。他看了看手表,是早上六点半。马营走过去问女儿是不是要上学了,女儿从被子里跳了起来,说快迟到了。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外面,是脱得精光的。马营一把将女儿按了回去用被子裹了,和来时一样像抱着一条棉被似的抱了去,妻子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挖着眼屎跟在马营身后。
“小马呀,你这同志思想品德有问题!”马营抱着女儿在二楼的过道里与张部长相遇了,部长满脸严肃,透出上级对下级的不屑,“你怎么能骗我呢?你这是什么行为,你是党员吗?”马营心想,这跟党员有什么关系?这话问得气喘吁吁的他一头雾水,他把抱着的女儿给了妻子,自己留下来听老领导指示。“如果昨晚地震了,今天我们可就见不上了!”马营听张部长这么一说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回想着自己这几天是否说错或做错什么了。他两眼直直地盯着部长同志,辩解说,昨晚没有余震呀!部长背着双手从鼻子里出了一股粗气,哼了一下,一只手从背后抽了出来,在空中用力地划了上去。马营觉察到了速度带来的风声,他向后闪了闪,他想躲开那个难以预料的手可能会落到他的脸上。不料部长的手停在了半空中,同时向广场的方向指了指,慢条斯理地说:“既然没有,你们一家怎么在外面?”马营刚要解释,张部长举着一只手转过身去,将防盗门从里面狠狠地关上了。马营听到关门的声音,感觉部长那只空中的手狠狠地抽在了自己的脸上,火辣辣的。
他看到眼前有好几个人上上下下,还向他打了招呼。
马营不清楚自己在部长家的铁门前站了多久。这时,女儿已经背着书包从五楼下来了,走过他身旁时说,发什么呆呀?还将右手的两个指头在他眼前晃了几下,问他:“爸爸,这是几呀?”他摇了摇头。女儿说声拜拜走了。马营的脑袋里突然闪过凌晨的光亮里的两个中学生和那顶帐篷里袒露的双乳,他大声吼着对女儿说,到学校要好好学习!下到一楼的女儿被他的吼声怔住了,定定地站了一会才无声无息地离开。
“再不能到外面去了,哪怕死在家里!”马营愤怒地盯着墙壁说,将捏紧的拳头狠狠地砸在昨晚放啤酒瓶的餐桌上。他想用响声引起妻子的注意。在卫生间洗漱的妻子双手擦着护肤霜快步跑了出来。马营背对着妻子,他知道此时妻子已和晚上判若两人,那张晚上黄里透红的脸,现在像雪花一般白。妻子把头发向后甩了甩说,你想死,我还不想死呢?为什么——不去?马营捏紧了拳头,一转身坐在餐桌边,低着头,看着在晨光里闪闪烁烁的啤酒瓶碎片说,这样下去会影响工作和学习。妻子说,哟!连命都没了,还要学习和工作?有什么意义?此时,马营无法忍受妻子这样理解他的意思,他倏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将两只紧握的手用力摊开说,你知道什么是余震吗?余震就是就在远离震中的地方发生的地震感觉!根本就造不成伤害。你们这些人啊,脑袋进水啦?这话在马营的感觉中是楼下的张部长说的,他还没有从部长莫名其妙的问话里走出来。妻子觉得马营声音有点大,她只好把声音压了下去说,好吧,明晚就不去了。但你得想办法呀,万一出现了什么情况怎么办?比如楼房倒了什么的,要死就死到一块儿吧。
事实上,妻子被这么多半夜三更的起床外出弄得有点神志不清了,她说她晚上睡觉最怕睡着,白天里,有什么动静,她都觉得像是地震,大喊一声撒腿便跑,她这一跑让单位上成百号人也跟着她往楼外跑。有一次,她办公桌前的一盆花被风吹动了一下,她觉得是地震来了,没命了似地惊叫了一声,拔腿就跑,边跑边喊:“地震啦,快跑!”大家听到她的喊叫,一个传一个,以惊人的速度往楼下院子里跑。她往楼下跑的速度很快,到四楼时,楼道里塞满了人。一位四十多岁的档案管理员,摇着肥胖的身体从办公室里出来往楼下跑,不小心,一脚踏空了,从四楼滚到一楼。和她以同样方式下楼的还有三个男的,他们三个都是被她的巨大的滚动力带倒的。
当大家一起站在院子的空地上时,都喘着粗气,没有人说话,甚至连给家里人打电话都忘了。他们紧张地等待着惊天动地的巨响,等待着这栋六层高的楼房在摇晃中突然倒下……他们压着心跳和恐慌,在盼望的事件没有到来时才开始说话,开始打电话,然后开始在院子里走动,打听其他人感觉到了地震没有。大家都说没有,只是听谁喊了一声就开跑了。有的到别的地方看了看,说别人也没有感觉到。后来领导说大家都回去,没什么事,以后大家不要听风就是雨,当然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
虚惊一场过后,三三两两谈论着回办公室了。这时,他们滚下来的四个人发觉自己出了问题。那位女胖子双脚肿得像馒头,裤子从两个屁股蛋中间开裂了,一条粉红短裤在深蓝色裤子里像一只眼睛一眨一眨的。那三个男的中有两个呆呆地站着,像打晕的鸡愣在那里,好像脑袋出了问题,鲜血犹如汗水从苍白的面孔上漫下来。另一个“哎哟、哎哟”叫着说自己的胳膊断了,在院子里走着转圈子。大家被“哎哟、哎哟”的叫声扯了回来,门房的保安拨通了110,不一会他们被送到医院去了。
从五月的地震开始,这个楼里带血的事件每一次都会出现,但没有今天这么严重。马营的妻子后来知道是自己的感觉出了差错,是自己的神经太过紧张了,当听到马营说以后不出去了也就没反对。广播电视里全天候播着防震知识,你不去听也知道该怎么做,再说了,电视里每天惨不忍睹、血肉模糊的画面谁能接受。但那是事实,每天都有新的生还者被发现,有新的肢体残疾者进入意想不到的人生行列。
马营说,先得在卫生间存储足够多的食品和水。妻子说有牛奶就可以了,那样营养和水分都够。马营说还要足够的方便面,就要“康师傅”桶装的那种,万一灾难到来时,他们可以照常吃饭,等待救援。妻子说牛奶要“伊俐”和“蒙牛”的两种牌子,还要把纯牛奶和酸奶对半搭开;妻子说孩子喜欢喝酸奶,正在长身体,要多备些鸡蛋和肉……马营说,行啦行啦!这不是去旅行,这是预防生命不要丢失的,你以为是去享受!妻子说我们家在顶楼,倒塌后是在最上面的,我们会被最先救出来的。马营想了想,觉得妻子这句话说得还有道理。他们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多钟头,是他们俩结婚以来最漫长的一次促膝长谈,谈得温情脉脉,谈得相互舍不得离开了,谈得像刚刚开始谈情说爱的恋人。余震让他们俩重新走到了十多年前恋爱的路上,那时他们形影不离,要不是在一个月内就结了婚,恐怕他俩就被单位开除了,因为他们俩从白天谈到黑夜,从黑夜谈到黎明,都不去上班了。
平时他们总觉得上班是最重要的,今天例外,妻子说要和马营一起去买东西。单位领导也说了,这几天没有特别的事还得正常上班。马营和妻子此时想到一起了,他俩共同认为领导所说的特别的事就是“防震”。
他们来到小区外面最近的一家超市,说要五箱牛奶、三箱方便面、两箱水、一箱火腿肠……服务员话没听完就从中间截住说,你们要的东西早就没了,五天前就被人排队买光了。那几天,这里人山人海,夜以继日。你们怎么现在才来?现在城里都没这些货了,听说有余震,居民都来买,有的来了几次……听说省城也没有了,外面的货因为交通堵塞,没法运进来,更多的是运到灾区了……听说还有地震!你们不知道?服务员神色异常,像看着三十年前的两个陈旧的人突然来到自己面前,交流有点困难。马营不相信她的话,他亲自到货架上看了两遍,妻子也在超市里来来去去走了两遍。马营觉得莫名其妙,向单位的同事打了个电话,问了些有关情况,放下手机对妻子说,要不到别的地方去看看,离市区十公里有个叫宁庄的镇子,那里或许还有存货。
他们从宁庄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了,女儿一个人在家,问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俩弄得满身是灰尘,上气不接下气地抬着一箱子矿泉水。马营在沙发上呆坐着,他不能理解的是,别人把防震用品都买完了自己怎么不知道。妻子说几天前,她就看到听到别人在抢购那些食品,你愣是不信,现在倒好,什么都没有了……说着眼泪刷刷地往地板上掉,说现在没法活了,每天都去广场上睡觉。马营说,别这么没有知识,我们这里顶多是余震,不会造成危害的。他说这话的时候心在跳,地震这东西本来就不好测,谁能说得准不会造成危害,他在安慰妻子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没底了。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翔……”手机响了,是单位同事小吴打来的电话,说是有好多人打“便民热线”,要马营来处理。那些人说他们家昨晚上被盗了,说他们全小区几乎所有的人家被盗了,说在晚上十点钟他们同时收到一条信息:今晚十二点左右有七级余震,请速到开阔地带,保密,你最亲爱的朋友。他们不约而同地到了广场上时,发现很多人已经在那里了,都说是朋友说的。有的说是自己在省地震局工作的亲戚打电话的,并且嘱咐一定要保密;有的说是部队上的朋友说的;有的说是北京的朋友说的……说什么的都有,都异常自信。第二天回家才发现自己家被盗了……马营让小吴先把这几种情况整理清楚,等着他来。
马营问妻子,昨天晚上是谁打的电话,妻子说一个朋友。马营问是不是一条保密信息,妻子只笑不答。
那时候,马营一只脚已经跨出了家门,一只脚还在家里的地板上。他突然停了停,像回忆起了什么事,将抬起的左脚放下来。他回过头大声地朝屋里喊了一句:走的时候别忘了把家门锁好。
那个黑影的出现就在此刻。他刚好将脑袋转了过去,准备把还在屋里的左腿抽走,好关上门。“咔嚓”一声,他听到防盗铁门关闭的响声,马营抬头看时,一个黑影在楼道一闪而下,只听得哒哒的下楼声。
那个黑影在马营的脑海里幻生成楼下的张部长,但他马上就否定了。马营走过张部长门口时心里像有只兔子在跳。几天前,在市政府防震救灾新闻发布会上,张部长和市长显得亲密无间,像兄弟一样有说有笑,会后亲自拿着1000元的特殊党费走向了捐款箱。随后,他支持抗震救灾的事迹被市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二十一日下午的时候,马营知道他还会碰到张部长。这次他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一张“内部明电”的复印件,内容是说二十五日凌晨二时左右可能会发生六级余震,请各地区做好相关预防工作,是省上专家组的研究意见,属于机密。马营得到这份密电后比往常下班早一些,他知道张部长会在他回家的时候与夫人出去散步,据说那是他心情最好也是各种意见能够得到接纳的最佳时期。
马营在楼下晃悠了大约一个钟头,却没见到部长从楼上下来。那时,春天刚刚过去,天色还早,夕阳把整个城市上空都染成红铜色,温暖从那些光线中散发出来,被一阵紧一阵的晚风抢走了,凉意不时向马营袭击而来。当他哆嗦了一下的时候,妻子满面春风地向他走来,夕阳的红色涂在她脸上,使她的脸像一朵盛开的鲜花,艳丽无比。妻子问马营,你在等我?马营点了点头。马营背对着阳光,妻子没有看清他的脸色。
马营走到二楼的时候,对妻子说他要找张部长说个事,让她先走。妻子上楼了,马营站在部长家的门前,侧着耳朵听里面是否有人。马营什么也没听到,他伸出去准备摁门铃的手在空中停了停。以前他从没给部长送过报纸文件之类的东西,早晨又发生过不愉快,现在这样做是不是合适?他决定明天去。马营走到四楼的时候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转过身又走到二楼,勇敢地摁响了门铃。开门的是部长孙子,孙子说他爷爷正在看电视,孙子把那张“内部明电”复印件拿了去,关了门。马营心想这次部长会高兴的吧,这可是省上的涉密文件,是他冒着风险弄来的啊。
马营的后背被人抓住的时候,头脑里出现了早晨那个黑影,但他随后听到了一个声音:小马,你等等。马营站在三楼的第二个楼梯上,他小心地转过身,张部长一手拿着文件一手抓着他的后背说,这是机密,你拿走吧,我知道,谢谢,这样做组织上不允许的!你是干部是党员是人民公仆是有保守秘密责任的,你这是违反纪律的,你知道不,以后不能这样!张部长说得马营的腿颤抖不止,马营的笑容僵在那里,脸像一张折皱的纸。马营知道自己是站在楼梯上挡住了别人的去路时,他的身前身后已经围了五个人。他手里的机密文件有几个人或许已经看了几遍。
“内部明电”里提到的那个晚上终于到来了,张部长一家在晚饭后,被一辆银色小面包车接走了,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马营那天似乎心情不错,唱着歌去了广场。他们是在午夜十二点后,一家三口到广场去的。那个本来不应该平静的夜晚平静地过去了。马营一夜未眠,所有恐惧,以及恐惧中所有的期待,随着黎明的到来都结束了。
作者简介:
陆军,本名丁陆军,1971年生于甘肃省通渭县。经济学硕士。甘肃省作协会员,国家政务信息化培训讲师。大学期间开始创作,作品涉及小说、诗歌、散文等方面,发表于《诗刊》、《飞天》、《光明日报》、《甘肃日报》等报刊,获省级以上文学奖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