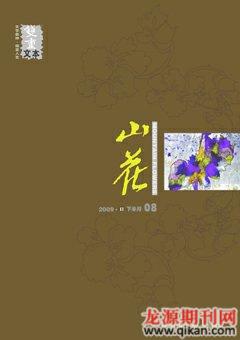蚱蜢
李 颢
叶片在阳光下晃动,一只蚱蜢趴在上面,光线打在它细长的翅膀上,隐约透出股青绿,翅膀上显出隐秘的纹路。它把脖子竖得老高,用伸出嘴角的几根触条啃食着叶片的边角。在它啃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凹凸不平的痕迹。马刚趴在草地里,全身一动不动,鼻翼微微抽动,眼前的野草被呼出的气流所吹动。他右手拿着个透明塑料杯,阳光下显得晶莹剔透。
夏天的蚱蜢是美的,它们出现在春季末期,那时体积尚小,不细看压根儿看不到。而秋季又是它们的末期,能活下来的极少,即便有,恐怕也是油尽灯枯,活不长了。所以此时是它们的黄金时段,体格庞大,繁殖力旺盛,每天这个时候它们就会分散地趴在草丛里,啃食嫩绿的叶片和青草梗。一般都躲在暗处,像这么光明正大地趴在叶片表面吃的,那是蚱蜢中的“勇者”。
马刚的眼中,蚱蜢的细部被无限地放大了。它的后腿,前肢,头上的触角,后身的翅膀,在阳光下无不透出一股奇妙的美丽。光线在它的身上变得细微,青绿的身体把光线聚焦,放出微微的射线,然后变得散乱细碎,模糊不清起来。马刚喜欢这种空幻的美感,好像自己一伸出手,抓住的不是一只蚱蜢,而是一块晃荡的倒影。终于,他放弃了欣赏,慢慢地伸出左手,往蚱蜢掠去。指尖带起的微风“扑”地撞在蚱蜢的两只触角上。蚱蜢一蹬后腿,就从马刚的两指尖飞走了。马刚并不慌张,他放下塑料杯,用手填满蚱蜢将要经过的空间。蚱蜢就这么盲目地撞进了马刚的手掌心。马刚合拢拳头,但不敢太紧,他害怕会把这小家伙捏死。他缓了一下,慢慢地分开合拢的拳头,他的手臂打着哆嗦,感觉自己的手变成了一把老虎夹,分得特别吃力。蚱蜢的触角先从缝隙中伸了出来。在它的半身全部爬出来后,马刚又合拢了拳头,把它丢进了塑料杯。
蚱蜢在塑料杯里上下跃动,身子不断撞击着杯盖,又不断被反弹回杯底。马刚瞪大眼睛凑近杯子,蚱蜢扇开翅膀,隐藏在翅膀下的血红的身体露了出来,细看还有红色的斑点。后腿极为粗壮,伸出细小而尖利的倒刺,显得比普通蚱蜢更为强壮。看着蚱蜢滑稽的挣扎,马刚不禁想:这小家伙不疼吗?不自觉就笑了出来,显得狂妄极了。他转身离开草地,往家中走去。
青山湖小区位于南昌郊外,是游离在都市建筑之外的独特存在。它没有高大的巨型楼房,全院都是清一色的小平房,院中长满了杂草,风一吹就随风摇摆。到夏天,男人们都摇着折扇,打着赤膊,在院中纳凉,口中止不住地抱怨这该死的热天。
马刚就在这长大,他的家住在六单元,窗口正对院中。
阳光透过光线射进楼道,打在铁制的栏杆上。厚厚的灰尘在光线中变成了一匹灰色的布,散射出阴沉的光辉、“501”镀金的门牌号在岁月中失去了遮掩,露出金字下的黑色塑料。门边放着一只黑色垃圾袋,上面围着一群“嗡嗡”乱叫的苍蝇。
马刚站在门前,从口袋里掏出钥匙。还没等钥匙进孔,门就自动开了。马刚用手一推,门在开到五十度左右的时候被卡住了。马刚从门的缝隙中挤进门来,一只红皮鞋使他的脚微微地拐了一下,挡住门的是另一只红皮鞋。
“当,当”,厨房里传来有节奏的切菜声。声音像是水波中慢慢荡起的波纹,在空间中绽开。马刚顺着声音来到厨房门口,母亲正在灶台前砍肉骨头。她左手压着排骨,拇指紧贴掌心。为了避免砍到手,另外四指呈弓状弯曲。右手由上往下不断挥刀,每次刀一接触骨头,就“哐当”一声响。马刚看见母亲的右手爆出了“蚯蚓”般的青筋。
“妈”,马刚叫了一声。这声音刚出口就被“当”地一声拦截了,马刚又叫了两声,母亲的刀切得非常碎,每一下都赶在马刚的声音之前,于是马刚的声音全被刀声掩盖了。这种态度带着一种霸道,把马刚捕获猎物的喜悦摧毁了。他感到憋屈,心中还升起一种隐秘的阴郁。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他哇地大叫一声:妈。这声音拖得特别长,整个嗓子眼儿都因为过分的尖厉而嘶哑起来。刀“呛”的一声砸在砧板上,母亲脸色苍白地盯着自己放在砧板上的手指,继而转过脸来,嗔怪地看着马刚,说:“跟你说几次了,切菜时不要和我说话,不然会切到手。”
“看,我抓到了什么?”马刚炫耀似地挥动塑料杯。他已经成功唤起了母亲的注视,就不在乎母亲的批评。母亲看着杯中的蚱蜢,皱着眉头说:“你少玩这东西,脏。” 这话好像一盆冷水,把马刚好不容易涌上来的热情浇灭了,他不自禁地嘟起小嘴。嘴唇翘得老高,好像一只挂油壶的铁钩。母亲擦擦手,走过来,用左手揪着马刚的一小撮头发,说:“刚,咱们好久没出去玩了,明天妈妈去钓鱼,你跟着一快来吧。”
马刚说:“不去。”
母亲:“为什么?你不去明天也没人给你做饭,你想一个人在家吗?”
马刚:“不去就不去,就是不去。”
母亲:“别这么淘气了,熊大伯想见你。”
马刚:“不去,不见那个矮子。”
母亲:“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
马刚:“不去,不去,我要去游乐场,不去钓鱼。”
母亲还想说什么,喉咙动了动,吐不出话来。她转身回到灶台,拿起刀,继续切菜,对马刚的一举一动不再注意。马刚感觉自己又一次被霸道地忽视了,他原地蹦跳,把地板踩得 “嘎嘎”响,嘴里不断喊着“不去,不去”。可是不管怎么喊,母亲还是自顾自地切菜,不再看他一眼。马刚放弃了,他知道即便自己喊哑了母亲也不会依他。为了显出自己最后的“尊严”,他回到自己的卧室,“砰”地把门重重地关上了。
马刚感到一肚子委屈,可惜这委屈,这痛又不足以让他哭出来。他憋得全身燥热,每个汗毛孔都被上涌的热气弄得全身发痒。他扑到桌前,头重重地砸了几下桌面。还不解气,又把桌上的东西“哗”地推翻在地上。推完他感到好受了点,看着被推得空落落的桌子,发现装蚱蜢的塑料杯不见了。他转头往地上看去,杯子摔在地上,杯盖开了一条口,飞出的蚱蜢落在床沿上。蚱蜢显然不适应环境,以它的角度看来,四周都是硬邦邦的。于是它飞起来,滑过马刚的眼帘,落在纱窗上。马刚顺手一掌往纱窗拍去,蚱蜢巧妙地飞开,落在了马刚的床上,纱窗上的灰尘沾了马刚一手。马刚来火了,他往后方猛扑,蚱蜢没能逃开,毕竟这不是它的地盘,以往那些潜踪逆行的把戏在空荡的床上失去了作用,它在起飞的那刻被马刚抓在了手里。马刚用手分开了蚱蜢的后腿,把它拉成了一个十字。蚱蜢用力挣扎着,未受控制的前肢不断地摆动,后腿根上的倒刺把马刚的手指扎得一阵痒痛。马刚两手微微地用力,蚱蜢的两腿如弓一般张开,椭圆的后身拉成了扁平。马刚脑中轰地一响,身子里响起“咔嚓”一声。蚱蜢落在了地上,两条腿连根而断,伤口处鼓起一个血泡。马刚空洞地看着夹在指间的腿,身上的烦热瞬间泄了出来。
天色暗下来,马刚还把自己关着。起初他睡着了,没感到什么异样。醒来后肚子开始打鼓,他发现饿了,眼前飘着浮在肉汤上的香菇,干贝,鼻中也闻到了鱼的鲜味,舌尖流出了口水。他生出屈服母亲的念头,想到将被老熊捏鼻子,掐耳朵,还要看母亲谄媚的笑脸,他就想哭。可饿得实在狠了,他准备出去吃饭,在起身前他才发现蚱蜢还躺在地上。
失去双腿的蚱蜢没有任何活力,马刚发现它的后身排泄出一粒粒的屎块,黑红黑红的。它的身体开始缩水,屁股干瘪下来,双目镶嵌着的眼仁正在变白,几乎就要消失了。马刚奇怪地看着蚱蜢的变化,伸手轻轻地拨动蚱蜢。蚱蜢恢复了一点活力,身子动了动,转而又停下来,后身又排泄出一粒屎块。马刚又碰了碰它,它不动了,只是不断缩着后身,一会又要排泄。这举动在蚱蜢的身上变成了一种永恒的精神,马刚在瞬间感到了一种尊严,他的心突然一紧,一股凉气从下身涌了上来。他发现弱小的不是蚱蜢,而是自己,他是多么的无力啊。
他开始想拯救蚱蜢。窗外的吊兰吸引了他,他拉开窗子,用手掰下了吊兰的一片叶子,塞进杯中。蚱蜢起初没有反应,后来马刚把叶子塞到它的身下,它才开始有动作。顺着叶片,蚱蜢开始往上爬,到中间时停了下来,横过身子,嘴角伸出久违的触条,开始啃食叶片。望着叶片开始从中间凹下去,马刚笑了。可惜好景不长,蚱蜢一会儿就不动了,只是趴在叶片上。马刚用指头弹了弹叶片,蚱蜢虚弱地落下来。马刚吓了一跳,赶忙用手接着。手中的蚱蜢轻飘飘的,好像再也不能动了。
晚上八点左右,马刚打开了房门。饭桌上摆着冷了的米饭和骨头汤。汤上没有干贝,香菇,只有几块碎肉,大块的肉骨头都被母亲啃尽了。马刚扑到桌前,拼命地扒了两口饭,也不管吃相了,端着碗把骨头汤狠倒进喉咙里,冰冷的汤汁撞在马刚肚皮的底部,他“呃”地打了一个饱嗝。母亲站在客厅,用电熨斗烫着明天要穿的粉红连衣裙。马刚咂咂嘴,舌头卷去了挂在嘴角的肉渣,对母亲说:“妈,我出去会。”母亲不说话,低着头做事。
“就去楼下,几分钟就上来。”
母亲的手带着电熨斗滑过连衣裙的边角。
“我明天跟你去钓鱼,见老熊。”
“你不用去了,在家待着。”
“我去,我真去,我听话,就让我去一会儿。”
“怎么突然这么积极?”
“妈,就一会儿。”
“……”
马刚见母亲不说话,也就不问了,转身扒完几口饭,回房间把蚱蜢装进塑料杯,就下楼往后院去了。夜晚的后院一片阴森,低飞的蝙蝠带着鬼泣般的破空声。对面楼的阳台上射出细微的光线,把草丛染上一层淡黄。马刚扭开杯盖,把蚱蜢倒在掌心,慢慢地放在一片宽叶草的叶片上。回家的蚱蜢获得了短暂的活力,它再次伸长脖子,开始啃食叶片。啃了几下后,它慢慢地往下爬着,马刚知道它即将隐没在草丛里。可惜失去后腿的蚱蜢一点使不上劲,它爬了一半,就晃荡着身体从叶片上落了下来。几只游荡在草丛边缘的蚂蚁发现了这只苟延残喘的蚱蜢,它们分成两批,一批爬上了蚱蜢的身体,用强有力的嘴咬住了蚱蜢的翅膀和后身。另一批则去蚂蚁堆中寻求帮手,不用一会儿,成百上千的蚂蚁就会来到。蚱蜢拼命挣扎着,不断往草丛深处冲击。可惜一块石头躺在它的面前,不管如何努力,失去后腿的蚱蜢也没有能力跃过这座“高山”了。蚂蚁咬得死紧,不管蚱蜢如何扭动身体,就是无法摆脱它们的纠缠。而不远的地方,一条蚂蚁组成的长龙正在飞速赶来。
马刚看不下去了,他用指头捏起蚱蜢,轻轻地把黏在翅膀上的蚂蚁弹掉。被攻击过的蚱蜢伤痕累累,翅膀上裂开了一道道的口子,仅剩的六条腿也只有三条了。马刚怜惜地看着它,知道它再也没有生存的权利了,放它回去只会让它更快地死亡。他哭了,蚱蜢残缺的身体像是一句永久的诅咒,会一辈子伴随着马刚,永远无法摆脱。他的嘴角抽动着,不断地喊:该死,该死。脚就狠狠地往蚂蚁堆踩去。
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经早早地睡下了。马刚用力摇了摇母亲的脸,她没有动弹,往她的耳朵里吹了口气,她转了个方向,嘴角呼了口气,接着睡。马刚在地板上坐了一会,用手轻轻地抚摸蚱蜢的全身,死去的蚱蜢更美了,全身的纹路一闪一闪,用永恒的死之光嘲笑着昏暗的台灯。马刚不忍把它丢弃,那样它会被蚂蚁吞噬。他来到窗台上,手扶住吊兰的花盆,用铲子刨开盆里的土,把蚱蜢轻轻地放了进去,然后又盖上。
当晚马刚做了个梦,梦里阴沉沉的看不见光。只见一堆巨大的杂草和看不见尽头的甬道,一只失去了双腿的蚱蜢被流水慢慢地越冲越远。马刚站在甬道边上,想伸手抓住蚱蜢,可是一股吸力把他拉了下来。他发现四周湿漉漉的,全身赤裸,原来他变成了蚱蜢。而在他站的地方,一只穿着衬衣的蚱蜢正在往自己的腿上装东西,细看,马刚发现是自己的大腿。马刚惊叫了出来,但什么也听不见,只有无边的黑暗。
第二天,马刚坐上了老熊的“大雷”。车很宽敞,座椅柔软,车厢还弥漫着一种兰花草的香气。一上车老熊就打开了车后座的小型电视,有好看的唐老鸭和超级玛丽,还可以玩游戏。马刚突然觉得和老熊在一起也并不难受。今天的老熊很光鲜,头发梳得油光闪亮,穿了一套清爽的T恤衫,显得青春焕发。他没有捏马刚的耳朵,还递给他好多巧克力和健力宝,马刚看见母亲歉意的笑,于是他也笑。
乡下风光明媚,百鸟争鸣。蝴蝶在花丛中追赶,不时还有钻过树丛的松鼠。早起的农民用铲子把打好的稻谷铲得老高,和春雪一般美丽。老熊从后车箱掏出渔具,递给母亲一把。看着母亲笑着接过后,他拉住马刚,把他带到草丛边上。他用脚踢了踢草丛边上的一块木板,然后冲马刚神秘地一笑。马刚“啊”地惊叫出来,出现在眼中的一大片蚱蜢,足有一张绿毛毯那么厚。这些蚱蜢比马刚抓的那只要大得多。它们有的黄中带黑,有的白中带绿,全身还散布着密密麻麻的斑点。老熊说:“马刚,这些蚱蜢被夜晚的露水淋湿了,飞不起来,太阳出来后它们就不会这么安静了。来,帮我把它们装进杯中。” 马刚帮着老熊装了满满一杯蚱蜢,来到河边。老熊从杯中取出一只,穿在鱼钩上,搅了搅鱼线,一用力,就把钩子投进水中。水流甚急,钓钩被水冲往一边。马刚能看见钩上的蚱蜢在水中尽力挣扎着。他心中隐隐有一种希冀,觉得蚱蜢会冲破吊钩的束缚,重获自由。
老熊“呵”地叫了一声,顺着老熊的目光看去,一条鲈鱼从河中露了个头,显然它想往蚱蜢扑去,可是湍急的水流阻止了它的第一波攻势,不过它没有放弃,在流动的河水中出现了一道不协调的曲线,马刚知道它又来了。老熊满脸兴奋,双手紧握钓竿,唯恐一个握不住就脱手了。母亲也被这边的景象吸引,丢下钓竿跑了过来。
三个人怀着不同的心思期待着结果,那条逆水而上的曲线离吊钩越来越近了,钩上的蚱蜢在水中奋力蹬着双腿。钓钩的周围荡起一个细小的旋涡,连着钓钩的蚱蜢被旋涡卷向深处。鲈鱼带起的弧线冲进了旋涡中,它的尾巴打起了一阵水花。马刚感觉自己的汗毛竖了起来,他觉得蚱蜢即将葬身鱼腹。
鲈鱼带起的曲线在旋涡中来回穿梭,在几次扑击不中后,鲈鱼猛地跃了起来,在空中一摆尾,狠扎进水里。“扑通”,河面溅起一圈水花,整个旋涡被震散了。老熊起先感到钓钩一紧,还没等欢喜,整个鱼竿就松弛下来。马刚发现鱼线断了,钓钩,蚱蜢,鲈鱼全都没了踪影。只有一截细细的鱼线飘过河岸。老熊一脸失望,母亲也叹了口气。马刚看着恢复平静的河水,心中一阵欢喜。他觉得蚱蜢没死,脱离钓钩的它一定会悄悄游回岸边,重新开始生活的。
他回到母亲身边,拿出没吃完的巧克力,使劲地嚼了起来。
看这个短篇,要看作者写了什么,更要看作者省略了什么。
因为,它原本可能是一个更复杂更纷繁的故事,母亲、熊叔叔、没出场的爸爸,预示着故事的“远大前景”,初学者往往是受不了诱惑的。
这种“省略”如果不是碰巧,则一定表明作者对短篇小说的奥秘是熟悉的,作者有着不俗的值得期待的文学品位,字里行间也能看出这一点。
当然,全文还稍欠火候,某些文字还不够准确,同时也还有未能触及的“末梢神经”,但是,对一篇处女作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陈继明)
作者简介:
李颢,男,1988年生于江西南昌。 2008年考入北师大珠海分校艺术与传播学院影视系。本篇是他的处女作。